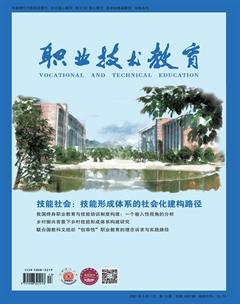技能治理的应然之思与实然之举
李阳 潘海生
摘 要 加强技能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普遍选择。但从现实看,当前技能治理还面临诸多挑战。梳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技能治理的主要文献发现,在“应然”层面,技能治理包括何为技能治理、谁来技能治理、如何技能治理三个层面。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技能治理“实然”之举表明,在政治体制影响下,面对传统科层制的挑战,两国形成了不同的技能治理的实践逻辑,德国强调“权力下放”,澳大利亚采取“统一化”协调。有效的技能治理需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技能治理行动框架,以推行强有力的技能治理制度:一是促进全政府协调与合作,二是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三是构建综合信息系统,四是统一协调融资安排。
关键词 技能治理;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德国;澳大利亚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3-0019-08
作者简介
李阳(1993- ),女,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天津,300350);潘海生(1975- ),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产教融合组织形态及其治理结构优化研究”(BJA190098),主持人:尹绪忠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都将技能治理作为调节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其发展不仅有利于各国制定高技能人才政策,还能推动各国有效监管技能发展,实时调整国家技能战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我国大力推行“双高计划”,力图通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技能治理能力。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实施技能提升行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技能系统的顶层设计,技能治理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其发展目标在于优化技能系统,而破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治理技能系统。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应然层面回应“何为技能治理、谁来技能治理、如何技能治理”,并依此逻辑分析德国、澳大利亚技能治理的实然之举,以期把握国际层面的技能治理走向,为我国技能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技能治理何以存在
技能作为知识经济的统一“货币”,多主体治理是防止其“贬值”的最佳方式。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关于21世纪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建议》中强调了技能政策、规划和管理领域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呼吁建立一个技能系统立法框架,以实现国家技能战略。至此,技能治理被正式提上国际议程。
(一)技能治理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全球化阶段,数字化、贸易自由化和较低的运输成本等因素将全球生产过程分割成全球价值链,就此增强了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各国技能治理水平将影响其在全球價值链中的专业化水平和从事复杂行业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技能治理的重要性,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决策者都积极呼吁加强技能治理和重视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力[1]。国际组织层面,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与欧洲培训基金会(ETF)等其他伙伴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人力资源模式,旨在加强技能系统治理。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学习论坛上呼吁“在混乱时期管理技能”,以驱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革,提高各国识别与治理未来技能的能力。2019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2019年经合组织技能战略”,明确承认技能治理的重要性,将“加强技能系统治理”作为经修订的经合组织技能战略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同年,欧洲启动的Cedefop数据库“匹配技能:旨在预测和匹配技能需求的鼓舞性政策”提供了欧盟成员国的技能治理工具[2]。国家层面,在欧盟成员国中,各国政府加强与行业合作,以监控国家对熟练劳动力的技能治理。一些欧洲经济体不仅注重技能政策协商,还与利益相关者就国家技能战略开展可持续对话。如奥地利、德国、荷兰等国有着长期的社团主义和维持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他们通过建立技能机构和议事委员会,定期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技能决策。而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具有自由化、多元化利益调解体制框架的国家,则以更开放的方式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以期共同参与技能治理[3]。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者正寻求适应本国的技能治理要素[4]。可见,技能治理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重视,在国际社会中日渐凸显其重要地位。
(二)技能治理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国逐渐认识到技能治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技能治理逐渐从欧洲兴起并传播到全球,且深深嵌入到多层次国家系统中[5]。虽然技能治理得到了全球的广泛重视,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学术界看来,技能治理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个人和雇主在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需未达到平衡[6]。二是技能治理主体间缺乏信任和自由裁量权,各主体仅着眼于“机构内嵌的信任关系”,未将技能治理作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富的一种战略[7]。三是当前技能治理配置不存在任何全面系统框架规定融资和监督机构的角色、责任和问责制[8]。换言之,当前技能治理面临主体权责不明晰、治理范围界限不清、技能供需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均扼制了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扰乱了技能供需的平衡,在无法弥合差距的情况下,低技能均衡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主义仍长期存在。且上海经合组织技能战略诊断报告表明,技能治理挑战根源在于政策领域、各级政府及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安排不善、技能和学习成果信息不足以及融资机制效率低下等。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全球技能治理不具备长期性和系统性,这就提出了技能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即在技术变革瞬息万变的未来,技能治理到底是什么,谁来主导技能治理,以及如何进行技能治理,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二、技能治理的应然之思
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领域,技能治理是各部门的交叉点,涉及教育领域、劳动力市场领域、工业领域和其他政策领域等各利益相关者。因此,明晰各利益相关者(治理主体)如何治理技能系统(治理机制)是研究的问题视域。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技能治理的主要文献,从应然层面探究技能治理。
(一)何为技能治理
从政策视角来看,技能治理可看作技能治理主体在特定时期用于达到技能发展目标的政策工具。从学理上看,技能治理概念中包含了“谁干什么”,即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强调技能治理是“部际协调”的治理活动,其主体涵盖了国家各部委与政府机构间的互动、国家和地方机构间的互动以及雇主、工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9]。经合组织强调,技能治理可被广义地定义为涵盖所有机构和个人,以及与技能发展有关的政策、法律和条例的治理活动[10]。欧盟认为,技能治理是跨教育和就业领域的多维概念,其是受国家背景影响的多因素混合的系统,这些因素包括参与主体(私人和公共),机制和实践(正式和非正式),政策、战略和法规(为技能治理行动提供背景),这些因素都与国家教育系统、劳动世界、政治环境有关[11]。霍利·伍德霍尔等人(Hawley Woodhal)将技能治理定义为寻求多元主体共同建立和优化未来劳动力的治理能力,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技能系统的治理,包括在不同程度上规划和控制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培训内容,以及确保教育和培训质量的机制。在他们看来,技能治理是一个旨在平衡技能供需的系统,其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其短期目标追求雇主、雇员的需求和教育系统的稳定发展,中长期目标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以及毕业生和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归属地等[12]。
结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技能治理是基于平衡技能供需的目的实施集体领导、对话、合作和决策的过程,技能治理中集体领导、对话、合作和决策的范围将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以及技能发展过程中所涉问题的性质。其概念前提即是参与对话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技能决策,包含了各级政府、专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与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就技能政策、战略、法规进行有组织地对话与磋商,由此建立由多方参与的国家、部门或地区联合监管机构,并作出利益相关者同意的决策。技能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优化技能系统、平衡技能供需,以此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良序格局。
(二)谁来技能治理
技能治理的实现既要重点审视技能治理内涵,又要全面考察技能治理主体。从国家到地方的不同层次技能治理的权威和责任有所重叠,而非仅将技能治理作为“传统”公共治理主体专有的责任,这不仅意味着“命令和控制”式治理的局限,还需明确更广泛的技能治理主体参与技能治理的必要性。
从技能治理主体来看,技能治理主体是处理治理行动的媒介和产生作用的社会单位,包括个人、组织、领导人、企业、部门、国际机构等。换言之,技能治理主体不是由国家獨自承担,而是由国家、私营市场和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分担的责任,技能治理强调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因此,技能治理主体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技能治理主体间的持续互动,由交换资源和协商共同目标的需要决定。然而,因技能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技能治理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氛围中[13],当其涉及不同层次的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等众多主体,并跨越多个政策部门时,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就会增加。
从技能治理主体的复杂性协调来看,主体协调是教育与培训场所、工作世界与个体终身学习间的桥梁,涉及经济系统的各主体,并依赖教育和培训主体,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工人代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对话和互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技能治理主体复杂性关系的协调包括由教育部或劳动部领导、专门的职业教育部门领导、高级协调委员会设立的独立职业教育机构领导以及各部委之间的互动[14]。由此可见,技能治理最重要的是发展部际间的协调,确定统一的领导主体,使各部委和机构共同参与技能治理。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应然层面确定技能治理的复杂主体,以此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第一,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主要涉及技能开发和就业立法的国家政策和战略,促进出口的技能发展计划等,本质上关乎国家资格体系。国家治理是有关部委和专门机构、国家雇主组织和国家工会之间对话与协调的领域。第二,部门治理。部门治理涉及技能部门培训和就业问题。主要与单个部门及企业和员工有关,部门雇主和工会积极参与国家框架内的讨论和协调技能开发,这是部门治理的推动力。第三,区域治理。区域治理旨在制定区域和地方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确定当前地方劳动力市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并监测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匹配的风险。区域治理是地方政府、雇主的关注点以及工人团体、当地专业协会、社区及其教育和培训提供者的职责所在。区域治理在促进就业和技能发展中的普及程度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程度[15]。
(三)如何技能治理
技能治理作为国际社会的政策工具,其机制随着社会对技能的需求、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以及复杂政治和社会环境等现实需求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革中。在传统社会,社团制、市场制和等级制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权力社会学”中确立的三种治理社会和经济的经典模式。就治理机制而言,可将其识别为基于传统的社团组织、市场驱动或等级制的技能治理[16]。但是,传统治理主要集中在国家决策过程中,通常包括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科层制决策方向。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当前的技能治理更着眼于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依赖及技能系统的运行过程,其运行机制随着国家发展阶段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不断变革。
在治理逻辑下,技能治理机制是技能治理主体运行的行动框架。该行动框架是指在技能治理过程中影响其实施的治理目标、组织方式、政策法规等因素的有形建制,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和运行轨迹等,技能治理机制限制或扩展技能治理主体的行为方式。
在目标层面,技能治理旨在发展高质量技能,确保以工作为基础的技能战略在青年中实施,并为他们提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在技能治理过程中既要有响应能力和灵活性,以期提供充足的工作场所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并增强技能系统快速适应不断变革的经济社会的能力;又要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确保技能战略与其他系统的发展战略相互补充,并有效利用现有资源[17]。
在组织形式上,技能治理包含各级政府、专业协会、培训组织等多利益相关者对话与互动的形式,不仅涉及政府机构、雇主主导的机构、工会、专业协会、职业教育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机构之间定期建立技能发展协议的对话和磋商,还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各部委、各省与各地区之间开展的技能开发咨询和决策,也涉及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私人三方和多方专门机构(理事会、委员会等)培训提供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就技能治理机制展开对话和决策,以及集体劳资协议、国家和部门应对就业与培训资金和其他联合倡议的基础上进行的治理形式,利益相关者就技能发展和就业参与对话并制定政策和战略决策。在政策法规层面,国家技能政策希望得到法律法规的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采用,通过组织结构、战略规划等机制发挥作用。这些政策法规包括增加个体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监督机会平等并成功完成技能培训,监测毕业生的就业能力,监测受训者所学技能与经济需求的相关性,确保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促进技能和就业能力发展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确保个体获得终身学习机会[18]。
三、技能治理的实然之举
基于技能治理的应然之思,本文明晰了何为技能治理、谁来技能治理以及如何技能治理,从而揭示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由此,为进一步验证技能治理的应然状态,选择德国(双元制体系)和澳大利亚(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两个联邦制国家探究技能治理的实践逻辑。
(一)德国:“权力下放”的技能治理
德国作为联邦制共和国,其技能治理主要体现在双元制体系上,该体系根植于行会传统及二战后德国为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社会冲突而設计的发展战略。德国在行会学徒制向工厂学徒制的工业化转型中,催生了工会组织与行会组织以及手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利益政治行为,这推动了学徒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逐渐走向现代化,且为后来闻名于世的双元制奠定了基础[19]。经过几十年的制度改进,德国的技能治理体系受到严格监管,具有“权力下放”的特征。
在治理主体上,因其长期的社团决策传统,德国16个州在许多政策领域都有决策权。德国技能治理是联邦和州之间的权限划分,且取决于各级政府、学校、企业和雇主协会以及工会之间的多个利益相关者[20],最重要的是雇主一方的商会和雇员一方的工会,他们在德国技能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1]。
国家治理层面,国家一级的教育部门等政府机构具有确保教育达到统一质量标准的职责。例如,《职业教育法》赋予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以领导作用,使其负责所有涉及职业教育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另一个机构是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BIBB),其隶属于教育部,且负责若干行政职务,如组织起草职业教育条例和更新培训职业名录等。作为双元制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及培训标准,职业培训条例(Ausbildungsordnung)以培训职业为单位,每个培训条例都会注明该条例所适用的培训职业及其培训目标和要求[22]。此外,联邦政府负责企业的双元学徒制,各州协调全日制学校教育或学校双元学徒制等与职业学校有关的问题[23]。
部门治理层面,部门和区域商业协会的政府代表有责任确定其经济部门职业所需的资格,而商会则负责监督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评估,以确保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既定标准,工会和企业的劳动委员会代表技能培训人员和员工的利益。德国每个州自行管理学校技能培训,为确保技能系统的一致性,各州教育部长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并确定课程框架,之后在州一级单独实施。区域治理层面,“主管机构”包括工业部门的工商会、手工业商会以及针对自由职业的适当专业委员会,他们负责确保技能培训中心的适用性并监督技能治理的执行情况。
在治理机制上,德国的双元制体系强调四方面治理目标:一是减少青年失业,改善青年在就业市场上的过渡能力;二是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吸引力和质量;三是使教育和培训系统现代化,重点实行双元制改革或基于工作的教育和培训;四是将利益相关者纳入技能治理系统[24]。
在组织形式上,德国技能治理体系具有利益相关者高度参与和“权力下放”的特点,工会在德国技能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德国成立“初始和继续教育联盟”,让工会作为合作伙伴参与技能治理,实则采取了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方式,旨在使技能系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协调[25]。因此,德国工会和商会都能参与三个层次的技能治理决策。层次一是各级政府的政治领导人每年在联盟内举行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技能治理问题开展培训,进一步讨论并通过技能治理的长期战略目标。层次二是联邦政府和各州代表通常作为审查专家出席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委员会,该委员会针对国家一级的技能治理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此外,该委员会支持联邦教育部监督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的任务。层次三是工会和商会负责企业和学校的培训内容,利益相关者中的专家与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共同制定新的职业教育条例,并修订现行的职业教育条例[26]。
在政策法规层面,德国技能治理的法律框架由《职业教育法》和《手工业法》确定,其价值在于维持技能治理和国家治理间的结构性平衡。《职业教育法》要求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通过研究职业教育,为技能治理作出贡献。《手工业法》关乎德国学徒制发展,为技能治理提供可靠支撑。另外,两个法规还涉及民法规定的技能治理,并通过确定劳动和就业法规定的课程标准,规定了适当的指导原则、治理标准和监测程序,保护了利益相关者和治理专家的行动范围。
(二)澳大利亚:“统一化”的技能治理
在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中,澳大利亚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技能治理历经三个重要节点:一是发展国家培训市场;二是实施培训机构的国家标准和培训包框架;三是建立“统一化”的国家资格框架,就此赋予技能治理“统一化色彩”。澳大利亚具有成熟的国家资格框架,该国有适用于公共和私人培训机构(RTO)的国家资格框架(AQF)、国家认可和质量保证安排(AQTF),以及国家和州政府之间的职业教育正式资助协议。其还具备支持技能治理的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和其他机构的统计和研究信息中心[27]。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是其实现“统一化”技能治理的必备条件,其利益相关者间能够有效合作,源于技能培训宪法权力名义上属于各州,但在很大程度上,各州政府的实权已被中央政府掌控,以作为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的条件[28]。因此,在没有正式宪法授权技能治理(包括职业教育)的地区,澳大利亚中央政府愈加倾向于对州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控制。
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层面,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负责联邦、州和领地的统治,负责制定和监督具有全国意义的技能治理改革[29]。技能治理政策制定的主要部门是教育、技能和就业委员会(SCOTESE)。工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DIISRTE)和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DEEWR)主要负责技能政策执行监管。
部门治理层面,首先是行业技能理事会(ISC)承担技能发展和国家培训,监管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重大技能治理政策改革。其次,行业培训咨询机构(ITAB)是基于州的组织,代表技能培训行业并反映特定的行业结构,其实施活动涉及技能培训发展计划,以反映行业的实际变化。最后,工业和技能理事会(CISC)掌管行业竞争力、生产力、劳动力市场、技能开发和培训安排,其致力于需全国合作的重大技能政策改革,可直接与国家选定的行业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有关技能发展的国家合作协议[30]。
区域治理层面,技能治理由地方部长负责,并通过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和支持网络实现,但地方政府的治理实权大部分受中央政府财权控制,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在技能治理的公共資金总额中贡献了大约1/3。
在治理机制上,澳大利亚技能治理具有“统一化”步伐。就治理目标而言,澳大利亚与多利益相关者明晰了技能治理目标,主要涉及制订有针对性的技能发展计划,并将国家发展定位为知识经济;增强技能开发能力,提高工作场所的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度以满足行业和个人的需求,并促进社会包容;为公民提供所需的语言、读写和算术技能;明确行业需求及个人充分参与社区、教育和工作的需求;确保第三级系统具有响应能力,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行业和个人需求;支持个人终身学习等[31]。就组织形式而言,澳大利亚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技能治理并为雇主和行业提供了参与国家、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技能政策的机会。
澳大利亚拥有行业或企业主导的培训体系,其治理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州和地区部长组成的负责立法、政策和法规问题的工业和技能理事会(CISC),该机构还协调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发展方面的利益;二是行业培训咨询机构(ITAB)与其他相关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合作,共享有关行业培训和技能需求的信息;三是联邦政府要求行业技能理事会(ISC)在行业内或跨行业间就培训包和资格框架等事项与多个司法管辖区的雇主、雇员代表之间达成协议。行业技能理事会(ISC)是确保行业、教育者和政府之间互动的重要桥梁,以促进行业主导的国家技能发展议程[32]。政策法规层面,《澳大利亚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管辖权,明确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运行技能系统,参与制定国家技能政策、规划和目标,并商议执行技能政策和优先事项。自1990年以来,在国家培训改革议程的幌子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资金安排、监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实施技能治理计划,以期在技能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33]。
(三)比较分析
以双元制体系为代表的德国和以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在技能治理上均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主张“权力下放”,澳大利亚强调“统一化”,实则大部分实权掌控在联邦政府层面,各级政府间多是横向协调,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
在治理主体上,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利益相关者都处于国家治理、部门治理和区域治理的框架内。德国技能治理责任由联邦政府、州政府、雇主、工会、商会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并达成共识,联邦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各利益相关者,使其具有决策权,技能治理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严格监管。其中,工会和商会是德国技能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部门治理和区域治理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澳大利亚技能治理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行业部门、工业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行业部门在澳大利亚技能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利益相关者在联邦政府统治下共同参与技能治理的重要决策改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技能治理实权受联邦政府财权控制。
在治理机制上,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治理目标都聚焦在技能开发、培训系统、社会伙伴、工作场所等方面,与应然层面强调的高质量、灵活性、一致性、协调性等治理目标具有同质性。就区别而言,德国技能治理目标指向满足青年技能提升及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吸引力和现代化水平,而澳大利亚更强调劳动力的供需匹配与个人技能的需求,重视第三系统的响应能力。在组织形式上,德国和澳大利亚技能治理都是在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进行的社会活动,两国均涉及技能开发和就业参与的咨询与决策。德国具有利益相关者高度参与和“权力下放”的特点,工会和商会都参与了几个层次的治理决策。而澳大利亚技能治理由行业主导,行业组织是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对话合作的重要中介。在政策法规上,澳大利亚和德国都拥有本国法律框架规定的技能治理主体及行动准则,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不同之处在于德国技能治理的政策法规趋向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其政策内容重视治理标准和监测程序,而澳大利亚是在联邦政府的财权控制下颁布相关技能政策法规,政策内容关注资格框架和供需系统。因此,面临传统科层制治理的挑战,德国“权力下放”的技能治理和澳大利亚“统一化”技能治理均能作出集体和协调一致的决策反应。
综合来看,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技能治理实践均是各国政治框架内的产物,即不同国情下的差异化选择,尚无国际统一的技能治理模式。各国在技能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可变因素包括:国家运行集中式或分散式的公共管理系统的程度;法律框架是否确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是国家或州的责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社会地位和技能发展情况;劳动力市场中经济部门的负责主体;正规经济或非正规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人口趋势;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对话的程度;跨政府行为是否支持技能治理等[34]。各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技能治理行动框架实现不同的对话方式,这与技能治理的“应然”逻辑相一致。
四、结语与反思
知识经济背景下,德国和澳大利亚均构建了技能治理的行动框架,在其政治体制影响下,表现为不同的实然状态。面对技能治理的现实挑战,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治理权力日益从中央政府转向各利益相关者,并通过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技能治理行动框架、明晰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和行动范围等合理举措,解决了技能治理的内在矛盾。这表明有效的技能治理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技能治理行动框架,以推行强有力的技能治理制度。
(一)促进全政府协调与合作
技能治理强调协同和赋能,而非科层和控制。全政府治理与传统科层制下国家构成的中心权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治理形态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互动,提高技能治理决策的质量和效益。全政府治理适用于中央和国家以下各级政策领域,其还包括政府与外部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使不同治理主体在各治理级别上达到平衡,允许政府协调负责不同部委(横向协调)和各级政府(纵向协调)对技能治理的设计与执行,以确保一致性。其一,技能治理应以共同愿景为指导,并在设计和执行上相辅相成[35]。其二,推行长期技能政策议程,建立强有力的机构,监测和评估政策改革的执行情况和结果,让利益相关者分担政策改革的所有权,在这一框架内,公共部门需对技能治理的质量和可获得性负责,让全政府内部灵活协调,以考虑特定地区或部门的需求。
(二)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提高技能决策的相关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并有助于技能治理的有效执行。首先,中央政府应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技能治理,确定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和权限,以激励他们在决策过程中考虑集体关切,确保他们切实参与技能治理设计、执行和评估。其次,中央政府要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持续资金、专门资源、场所等,努力平衡利益调解制度中固有的权力不对称,让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以建立相互信任。最后,在利益相关者互动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有不同的合作和互动方式,各国在与私人行为者接触的形式和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最重要的是防止私人行为者为特殊需要滥用其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技能治理制度和互动形式需要以确保行为者参与集体问题解决,而不是以特殊谈判和游说的方式来设计。
(三)构建综合信息系统
随着技能系统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管理数据和信息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提高数据整合能力和在各级传播技能信息有助于更好地设计技能政策,实现供需匹配,减少技能失衡,最终改善技能的使用效力、就业能力、生产力和竞争力。首先,构建综合信息系统,收集和生成所有与技能、劳动力市场和学习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以此制定基于证据的技能治理政策。其次,提高质量不佳的某些区域或地方的信息化水平,将行政数据整合到纵向系统中,确保该系统能将行政数据转化为可获取和量身定制的信息,从而帮助合作伙伴做出恰当的技能选择。最后,信息系统应以用户为中心,并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在建立收集和管理数据基础设施的同时,利用定性数据的来源区分治理类型和问责制度,例如雇主协会的技能需求评估或其他质量评估等。
(四)统一协调融资安排
技能系统的治理、融资和管理是确保满足个人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核心[36]。技能治理资源分配应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和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基于全政府治理,克服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第一,技能治理融资应采取长期的战略性办法,并提供一个明确的融资框架,具体说明哪些利益相关者利用资金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作出贡献。第二,财务安排应依靠更灵活的成本分摊机制,以促进多种资金来源一体化,谨慎分配公共资金,以促进更好的政策成果,并确保人人都能公平地获得技能发展机会。第三,为了在技能形成方面推行長期技能战略,国家需建立体制框架,以保护技能投资不受其他部门短期资金需求的影响。第四,在努力提高技能支出水平和效率的同时,还需要治理主体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分配资源的方式需使主体责任和问责制与融资相匹配,实现技能治理的标准化运作。
参 考 文 献
[1]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Learning for Jobs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R]. OECD, Paris, France, 2010:21.
[2]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Cedefop launches‘matching skillsonline information tool[EB/OL]. (2019-01-09)[2019-03-02].https://www.cedefop.europa.eu/en/news-and-press/news/cedefop-launches-matching-skills-online-information-tool.
[3][25]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Skills Strategy 2019: Skills to Shape a Better Future[M]. OECD, Paris, France, 2019:5-48.
[4]REMINGTON T 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TVET: adapting the du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2018,70(4):497-523.
[5]POWELL J J W, TRAMPUSCH C.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varying responses in collective skill systems[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skill systems, 2012:284-313.
[6]LAUDER H, BROWN P, DILLABOUGH J A, et al. Introduction: The prospects for education: Individu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M].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1-70.
[7]BROWN P.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 skills[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999,12(3): 233-251.
[8]Great Britain National Audit Office. Further Education and Skills Sector: Implementing the Simplification Plan[J]. London, England: National Audit Office, 2014:1-40.
[9]TODD, ROBIN; DUNBAR, MURIEL. Taking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to skills development[M]. Paris, France: UNESCO Publishing, 2018:14.
[10]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f Skills Systems Lessons from Six OECD Countries[M]. OECD, Paris, France, 2020:15.
[11]European Commission. Skills Governance in Europe: Final Report[EB/OL].(2014-08)[2019-03-02].http://www.eiead.gr/publications/docs/European%20Commission%202014%20Skill%20governance%20in%20Europe.pdf.
[12]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The involvement of employer organisations in the governance of skills systems: a literature review[J].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8:1-33.
[13]HODGSON, A., SPOURS, K. & STEER, R. All change for the learning and skills sector?[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2008,21(2):115-131.
[14]ILO, UNESCO. Strengthening inter-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on TVET and skills[R]. Cambridge Education, 2017:15.
[15]V. GASSKOV. Governance of skills development[J].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8:1-48.
[16]GONON P. What makes the Dual System to a Dual System? A new attempt to define VET through a governance approach[J]. bwp@Berufs-und Wirtschaftsp?dagogik, 2014(25):1-13.
[17]AU W D G . Governance and Architecture of Australias VET sector: Country Comparisons[J]. Skills Australia, 2009:1-173.
[18]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 (No.195)[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4:24.
[19]王星.技能形成的社會建构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2015(1):184-205.
[20]HOFFMAN N. Schooling in the workplace: How six of the worlds best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prepare young people for jobs and life[M].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1:29.
[21]EMMENEGGER P, GRAF L, TRAMPUSCH C. The governance of decentralised cooperation in collective training systems: a review and conceptualisation[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2019,71(1):21-45.
[22]李俊.德國职业教育的想象、现实与启示——再论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原因[J].外国教育研究,2016(8):14-27.
[23]ROTHE G. Die Systeme beruflicher Qualifizierung Deutschlands[J]. ?sterreichs und der Schweiz im Vergleich-Kompendium zur Aus-und Weiterbildung unter Einschlu? der Problematik 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Villingen-Schwenningen, Wien, Luzern, 2001:1-36.
[24]CLAUDIA SCHREIER. Succes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trial of du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ms in Europe[EB/OL].(2015-06)[2019-03-06].https://www.bibb.de/en/37031.php.
[26]EMMENEGGER P, SEITZL L. Social partner involvement in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governance. A comparison of Austria, Denmark,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Switzerland[J].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20,26(1):27-42.
[27]KNIGHT B, CULLY M. A patchwork quil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ining statistics[J]. Informing policy and practice in Australia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 Reflections and futures, Adelaide: NCVER, 2007:1-58.
[28]CULLY M, KNIGHT B, LOVEDER P, et al. Governance and architecture of Australias VET sector: Country comparisons report prepared for Skills Australia[J].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NCVER), 2009:1-171.
[29]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System.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EB/OL]. (2011-08-19)[2019-03-06].http://www.ivet.com.au/a/183.html.
[30]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COAG Industry and Skills Council Communiqué[EB/OL]. (2017-11-24)[2019-03-06].https://docs.employment.gov.au/documents/coag--and-skills-council-meeting-skills-ministers-24-november-2017.
[31]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Future-proofing Local Government: National Workforce Strategy 2013-2020[R].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n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 2013:23.
[32]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System. Industry Skills Councils (ISCs)[EB/OL]. (2011-06-01)[2019-03-06].http://www.ivet.com.au/a/35.html.
[33]NCV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kills policy in Australia[EB/OL].(2011-12-06)[2019-03-09].https://www.ncver.edu.au/news-and-events/opinion-pieces/vocational-education-and-skills-policy-in-australia.
[34]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The involvement of employer organisations in the governance of skills systems: a literature review[J].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2018:1-33.
[35]TRAPASSO, R. AND B. STAATS. Towards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to skills policies[M]. OECD Publishing, Paris, France, 2018:36.
[36]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Financing and Regulation of Skills Systems[EB/OL].(2017-03-16)[2019-03-09].https://www.ilo.org/skills/areas/skills-policies-and-systems/WCMS_547502/langen/index.htm.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Skills Governance
——The Cases of Germany and Australia
Li Yang, Pan Haisheng
Abstract Strengthening skills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universal choice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eal with the knowledge economy. However, in reality, the current skills governance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By sorting out the main literature of skills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ideal level, skills governance includes three levels: what is skills governanc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skills governance and how to improve skills governance. The reality of skills governance in Germany and Australia show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system,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the two countries have formed different practical logic of skills governance. Germany emphasizes “decentralization”, and Australia adopts “unification” coordination. Effective skills governance requires stakeholders to jointly build a skills governance action framework to implement a strong skills governance system: the first is to promot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government; the second is to encourage stakehold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the third i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ystem; the fourth is to coordinate financing arrangement.
Key words skills governance; governing body; governance mechanism; Germany; Australia
Author Li Yang, PhD candidate of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Pan Haishe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ducation of Tianji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