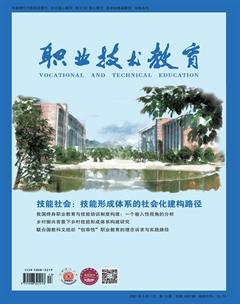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与优化


摘 要 “赋能”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使命。职业教育的全民性、时代性和跨界性是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基于当前职业教育在乡村的实践,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有三类实践路径:“输入技能”“引入产能”和“循环智能”。通过对三类路径的实践主体、服务对象、运作方式及成效表现等方面的比较和分析,可知当前实践中的不足:实践主体协同性差、实践内容渗透力弱、运作方式难再循环。因此,可以从构建协同框架、开辟融合路径及融入数字乡村等方面,实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实践策略的优化。
关键词 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实践路径;赋能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3-0059-06
作者简介
瞿晓理(1981- ),女,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苏州,21500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人工智能+X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研究”(ECA190482),主持人:王佳;2021年度江苏省“青蓝工程”青年骨干培养资助对象中期考核成果之一,资助对象:瞿晓理
在脱贫攻坚期,职业教育开展多种实践,“赋能”三农,助力决胜小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教育部随即颁布“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相关政策,积极部署“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计划;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提出职业教育应“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等要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更是强调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乡村振兴“赋能”依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探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应然是各界关注的内容。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绝不仅是我国政策的要求,在国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均体现出服务“三农”的功能。在美国,以“扶持农民、协助农场主致富”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技能教育项目已有多年历史,也为美国的乡村发展培养了大批职业农民群体[1][2]。在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用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治理发展,一方面,针对乡村人口,构建了提升农业经营能力的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入驻乡村,通过聘请乡村本土的传统技艺掌握者,推进文化传承和保护,因地制宜治理乡村[3]。印度的“喀科运”实践经验,是职业技术教育服务“三农”的代表,通过成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推广农业技术及职业技术、教育立法等手段,推进了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取了显著成效[4]。由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可见,职业教育具备面向“三农”的特有优势,而这种优势源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也构成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一)职业教育的“全民性”,是实践的前提条件
职业教育是一类“全民性”的教育,其可以是学历性的教育,也可以是非学历性的培训。学历性职业教育对象的来源途径有两种,一部分来自选拔性的招考途径,另一部分来自非选拔的注册途径[5]。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且建成一定数量的职业教育机构,培育了一定规模的职教资源。低门槛的入学条件和规模性的教育资源,成就了职业教育的“全民”属性。同时,我国农村人口占极大比重,并且这一群体的各类资本均呈现偏于弱势的状态,使得他们通过选拔招考途径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偏小。事实上,走精英路线的普通教育,受其教育定位和资源的限制,也无法支撑和承担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教育问题。而职业教育的“全面性”恰恰能够应对这一问题,这也成为职业教育能直接面向“三农”的前提条件。
(二)职业教育的“时代性”,保证了实践的方向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从事职业的种类、内容及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作为指向“职业”的职业教育,也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发展,“时代性”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特征之一。
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对外封闭。因此,农村要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获取外界信息,打破封闭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咨询等多种手段,向农村引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拓展了农产品对外的消费市场,传播和保护了乡村的风俗文化,增强了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能力,开阔了农村人口的眼界,促进了乡村社会的与时俱进[6]。而“時代性”特征,也让职业教育在乡村教育实践中,始终能引导乡村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回顾过去的实践成效,职业教育能推进农村人口的职业身份转变,实现由传统农民到职业农民再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型;能促进农村人口职业技能的更新,实现由手工农具到机械农具再到数字农具的升级。
(三)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为实践提供了资源
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职业界”“教育界”“技术界”及“产业界”等多领域的复杂系统[7][8]。横跨多界的特性,使得职业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多种发展资源。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其在赋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的同时也稳定了乡村社会。农村职业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人口对教育的诉求,提升乡村社会人口的整体素质。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乡村社会的现代农业技术水平获得提升,传统农民转型为职业农民。职业教育还能通过产教融合的途径,推进乡村社会的产业兴旺发展。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能促进乡村社会的教育、人口、经济及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黄炎培先生曾指出,职业教育具备“社会性”特征,认为职业教育活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9]。而本文在这里作出补充,社会活动是涉及多领域的活动,职业教育是横跨多领域的教育,两者在“多领域”上的重合,使得职业教育契合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因此,“跨界性”使职业教育具备“赋能”乡村社会的多样实践资源。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基于国内实践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
1.路径一:输入技能
“输入技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最基本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农村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以“输入”为主。此后,通过开办县级职教中心、设立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点、送“技能下乡”和送“技能上门”等实践举措,职业教育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技能培训。时至今日,“输入技能”依然是我国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从全国范围来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农村地区的技能培训达到395.2万人次;而據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职业院校面向农村地区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累计近万场次,培训人次约达99.3万。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依据自身资源条件,将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输送入乡”,形成了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以苏州地区为例,一方面,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本地各农村合作社,形成网格化技能培训点,聘请苏州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农业专家、涉农企业家等为讲师团,定期向各乡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传统手工艺、现代农业管理”等内容的培训;另一方面,在苏州地区的职业院校,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每年定期开展“技能下乡”活动,面向苏州农村地区提供现代农业技术、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物联网等内容的培训和咨询服务。通过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的合力“送技能”,苏州打造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符合地方产业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赋予了“鱼米之乡”的时代活力,也为苏州后续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路径二:引入产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内容是产业振兴,职业教育要“赋能”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乡村“引入产能”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引入产业技术,如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打造“航空生态牧场”,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创新建立了生产性实训基地,将先进产业技术引入四川阿坝洲的乡村地区,扶持当地农牧产业的发展。二是引入产业项目,如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通过“科技特派员+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模式,助力江苏涟水县陈师镇红旗村成为雷允上药业公司的定点供应商,打造了红旗村“中药原材”的产业名片。三是引入企业,如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聘请农业领域经营管理专家,在湖南官溪村成立官溪洣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鼓励村民入股,改革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动力。四是引入产业资金,如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与宜昌市国土资源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分行等单位合作,利用当地政策,入股苏家河村农产业种植基地,推进当地猕猴桃、羊肚菌等产业的规模发展。除此之外,职业院校还通过引入产业专家和产业市场等做法,“赋能”乡村振兴。
3.路径三:循环智能
“循环智能”的路径,是职业教育打破农村封闭状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手段,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返回来”,整个过程中让他们获得外界的“能量”,高质量地参与乡村建设。2015年国家号召广大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职业教育通过“循环智能”路径“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不断涌现。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项目,定向培养农村高职大学生,学生们学成后返乡创业,成为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带动更多村民走致富之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利用“东西协作”模式,每年定期选派大三学生进入东部协作院校的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学习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经验,之后学校引导和激励西藏学子返藏建设,助力西部乡村振兴。除此之外,过去我国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山西等,如今都已成为享受返乡创业红利的大户。据国家人社部门估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约达1300万人,成为乡村建设中的“精英”和“能人”。而无论是劳务输出还是返乡创业,职业教育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培训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二)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分析
上述三类“赋能”路径是对当前职业教育在乡村实践的归纳,本研究从实践主体、服务对象、运作方式及成效表现等四个方面,分别总结它们的实践特征,见表1。
第一,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主体构成均呈现多元的特征。职业教育横跨产业界、技术界、教育界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主体构成了各类路径的实践主体;也就是说,主体的多元特征,本质是职业教育跨界性逻辑的实践表征。此外,由于不同路径涉及的领域不同,导致构成它们的实践主体也不同,其中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主要载体,参与了每一类“赋能”路径,成为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
第二,综合三类“赋能”路径的服务对象,有职业农民、农村子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多类人群,而这几类人群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人口的类别,也说明职业教育在农村是面向全员的教育。这正呼应了职业教育“全民性”的实践逻辑,也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三农人口”的意义所在。
第三,比较三类“赋能”路径的运作方式发现,如果说“输入技能”和“引入产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单向”运作,那么“循环智能”则是双向通道,并且是一种“双循环”的运作,见图1。三类“赋能”路径的运作方式,均是来自时代的需求。其中,“输入技能”是最早实施的,是基于20世纪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背景所采纳的。而如今,这种运作方式可以高效率地完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任务,依然是时代的选择。“引入产能”是基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时代发展要求,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必然呈现的一种运作方式。而“循环智能”的双向运作,更是基于时代发展的现实背景:职业院校向农村兜底招生,是脱贫攻坚期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要求;地方政府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是现代都市发展的需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号召大学生返乡建设,号召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是乡村振兴的要求。因此,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职业教育时代性的实践逻辑催生了不同的运作方式。
第四,从整体来看现有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已经实现了对乡村“五大振兴”内容的全覆盖;同时,每一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表现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其中,“输入技能”路径的目标是为乡村地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践成效主要表现在人才振兴;进一步来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参与当地乡村的产业建设,传承传统手工艺文化,因此辅助成效表现为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引入产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一条关键路径,将技术、项目、企业及资金等一系列生产要素引入乡村社会,助推乡村的产业发展,即主要实践成效是产业振兴。在职业院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引入的新技术、新制度等又推动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智能循环”是职业教育“賦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其让农村人口的脑子“活络”起来,通过“双循环”的运作为乡村振兴提供“智能”,因此主要的实践成效是人才振兴;而返乡大学生成为乡村组织的后备力量,返乡创业农民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间接体现了组织振兴和产业振兴的实践成效。
三、思考与优化
(一)现有三类“赋能”路径不足的思考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表明,职业教育面向“三农”是具备基础和优势的,但是现有的三类“赋能”路径依然存在不足。
1.实践主体虽然多元,但协同性不高
如上文所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是多元的,从三类路径的实践主体构成来看,有职业院校、职教培训机构、各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力量;但回归具体实践,多元的实践主体在整个运行中的定位和分工并不清晰。如“输入技能”路径采用了政府和学校联合的方式,政府组织,院校开展培训,分工非常明确。但是,依然以苏州地区为例,却出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院校”两套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政府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造成职教资源的浪费。在“引入产能”路径中,虽然是以“产教融合”为抓手,但事实上都是以“职业院校”为主在积极推进,而社会产业力量作为实践主体之一,实践自觉性偏低[10]。还有在“智能循环”路径中,出现“输出—流入”两地政府的责任不清晰、相互推诿,而职业院校单方面又不能完全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循环”中风险和保障的问题[11]。由此可见,当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协同性不高。
2.实践覆盖虽然全面,但渗透力偏弱
综合职业教育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呈现出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五大振兴”的全覆盖,并且在“五大振兴”的独立维度上,职业教育的实践成效显然是各有侧重的。人才振兴的成效显示最高,产业振兴其次,而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兴等维度的成效并不显著。实践成效的各有侧重是常态现象,但进一步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振兴”维度是存在逻辑关系的,即产业振兴是根本,人才振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动力,生态振兴是发展,组织振兴是保障[12]。“五大振兴”是相互支撑、有机渗透的。
本研究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每一类路径所指向的实践成效内容,均都不能完整地支撑乡村“五大振兴”体系。而且,在“引入产能”路径中,其实践成效只是指向了“产业振兴”,而依托“产教融合”的乡村人才培养,在众多实践中居然没有获得显现。此外,对教育而言,人才和文化是其系统内两个重要的组成[13];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有密切的联系,并呈现在实践成效中。但本研究中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未能显现此类联系。上述各类问题充分说明当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渗透力偏弱。
3.“赋能”通道虽然双向,但再循环较难
“循环智能”路径构建了双向通道,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返回来”,成为外界“能量”的载体,助力乡村发展。但是这种双通道的“赋能”路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实施的。对于“输出通道”的形成,一方面,是来自20纪90年代以来沿海发达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化发展,创造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机会[14]。而对于“返乡通道”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工业智能化的发展,“机器换人”降低了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另一方面,三、四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使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创业”的政策。在双向通道的两个循环中,“农村子女→返乡大学生”的循环规模,要远小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循环规模;但“农村子女→返乡大学生”循环的可持续性相对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循环,是依靠时代背景驱动的,但时代背景是不可复制的,也意味着这种路径的再循环较难实现。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优化
1.构建主体协同框架:明确目标、厘清责任、共享信息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确立了职业教育多元主体的实践表征;同时要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的产教融合,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提质升档,离不开多元实践主体的协同。学界对该类问题的探讨颇多,并提出推进主体协同的各种策略,主要有:提升职业院校水平,增强其协同能力[15];出台相关政策,激发企业自觉性[16][17];强化行业组织建设,发挥其桥梁作用[18]等。
除上述推进主体协同的优化策略外,需构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实践的“多元”主体协同框架,而协同框架的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由上到下”明确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目标体系,即将“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逐级分解、不断细化,由此可以确立多元主体的实践目标清单,以确保子目标和整体目标的一致性,作为协同框架的基础。第二层,“由小到大”厘清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责任体系。一是要明确各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如政府是引导者和保障方,院校是教育者和执行方,企业是生产者和执行方,行业是协调者和技术方等,并进一步分析各主体的功能。二是对应各主体的功能,分配实践目标清单中的子目标,明确每一个小目标的责任方,由小职责汇集成大任务,由此厘清各主体在实践中的责任。第三层,“由点到面”共享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信息体系。要实现协同,实践信息必然要共享。打破原有实践主体间“点对点”的单一信息传递方式,创立共享信息面板,将有利于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各主体方,能及时依据外界环境调整自身决策,保持与其他主体的一致性。
2.开辟“赋能”融合路径:集聚资源、集成举措、集约治理
如前文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五大振兴”内容是一个有机逻辑系统,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因此,开辟一条既指向人才振兴又服务产业振兴,同时推动文化、生态及组织振兴的“融合路径”是可行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第一,在探索融合路径中,首要解决资源融合问题。跨界性使得职业教育在乡村实践中拥有诸多资源禀赋,这些资源横跨教育、职业、技术、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只有理顺这些资源的关系,将教育链延伸至产业链、职业链、技术链及文化链,巩固各条“资源链”的节点,才能集聚各类资源的最大“能量”。第二,开辟“融合的路径”需要“融合的举措”作支撑。在本文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中,职业教育采用了技能培训、创业教育、新建基地、服务项目、技术咨询、研发工艺等多类举措;事实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文教融通”的理念,表明实践举措的叠加将获得“1+1>2”的结果。因此,在乡村地区构建集成“教育、培训、研发、创业、服务”等多举措为一体的平台,将为融合路径的探索提供重要载体。第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活动,更是一种治理行为。有学者曾提出乡村治理的基石是教育[19]。因此,在集聚资源、集成举措的基础上,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融合路径离不开集约治理。只有立足“集约”理念,职业教育才能充分利用各类跨界资源,才能合理实施多样举措,达成多资源、多举措的融合,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最大成效。
3. 融入“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循环、科技赋能、持续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要“赋能”乡村振兴,一定要用好“数字技术”。首先,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创新循环”的通道。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将乡村的发展需求、农民的发展诉求推送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畅通“信息输出”通道;另一方面,将外界优质的职教资源建成网络数字资源,对接乡村、服务农民,打造“资源输入”通道。提升职业教育在乡村的信息化水平,让“数字技术”融入到职业教育的“循环智能”路径中,让“传统农民→智慧农民”的创新循环,代替“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旧循环。其次,实现“职业教育+数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数字化职业教育资源,建立面向“三农”的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库,为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提供在线教育、培训及咨询等服务,大力提升农村人口的数字素养,推动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此基础上,融入“互联网+小农户”计划,利用职业教育激发乡村社会的各类要素资源,提升“小农户”们的职业发展能力,助力数字时代的乡村就业和创业。最后,构建乡村职业教育的“数字生态圈”,增强乡村持续发展力。依托“数字技术”,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乡村职业教育的“数字生态圈”建设,数字化融合各方资源,扩大和增强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成效;同时,联结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各方主体,形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各负其职、各具特色、协同共进的多元主体的数字融合发展新格局。
参 考 文 献
[1]徐和平.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下的美国乡村发展与振兴[J].中国名城,2019(10):13-19.
[2]夏金梅.“三农”强富美:美国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其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9(5):10-14.
[3]韩玉,崔天岚.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特色课程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24):91-96.
[4]张东娇.从“喀科运”到“定县实验”——中印两个另类教育个案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阐释[J].比较教育研究,2006(1):55-59.
[5]吴一鸣.扩招推动下高职教育类型发展的动力与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20(Z1):83-89.
[6]朱德全,黎兴成.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研究嬗变与范式反思[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5-19+201.
[7]崔永华,张旭翔.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J].教育发展研究,2010(17):43-46.
[8]朱成晨,闫广芬.跨界与共生: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分析框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1):20-28.
[9]费重阳.试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及现实意义[J].教育与职业,2000(8):4-7.
[10]王慧.产教融合: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J].教育研究,2018(7):82-84.
[11]瞿晓理,刘轩.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优化的现实需求[J].地方财政研究,2016(7):38-45.
[12]胡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第四届“三农论坛”征文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20(12):130-138.
[13]曹莉.关于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辩证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24-33.
[14]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6):30-43.
[15]贺书霞,冀涛.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构[J].职业技术教育,2021(4):35-41.
[16]江颖,夏海鹰.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表征和价值路向[J].教育与职业,2020(23):5-13.
[17]王羽菲,祁占勇.国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基本特点与启示[J].教育與职业,2020(23):21-28.
[18]刘旭,徐佳琦.地方高校产教融合与校企一体化平台构建探析——评《行业学院模式下地方高校产教融合专业群建设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21(1):141.
[19]袁利平,姜嘉偉.关于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59-169.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Zhai Xiaoli
Abstract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history peri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lude facing to all, epochal and transboundary, which are the practical logicality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are three paths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put of skills, the introduction of capac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ntellect.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subjects of practice, the object of practice, the mode of operation and the validity of practice, the research had gained the deficiency of practice: the poor synergy of subjects, the poor correlation to practices contents, the unrecycled mode of operation. So, the optimized suggestions on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lude building coordination framework, opening up integration paths, etc.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 approach; empowerment
Author Zhai Xiaol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uzho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rade & Commerce (Suzhou 21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