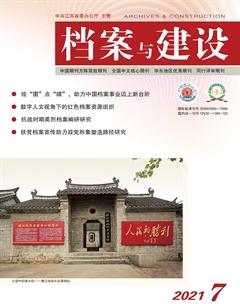治理主体视角下的档案治理:本质思维、内在逻辑与效能增量
路璐
摘 要:档案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档案治理区别于传统档案管理的重要特征。政事型、服务型、知识型、参与型主体对应的依法治理、元治理、协同治理等治理方式蕴含着档案治理的本质思维,主体间的确权、放权、分权与赋权揭示了档案治理的内在逻辑,完善档案权利制度、培育档案治理伦理、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是实现档案治理效能增量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档案治理;多元治理主体;治理效能
分类号:G270
Archives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Subject: Essential Thinking, Internal Logic and Efficiency Increment
Lu Lu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ubject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that archives governance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archives management. Government-oriented, service-oriented, knowledge-based and participatory subjects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modes, such as law-based governance, meta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tain the essential thinking of archives governance. The affirm, d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empowerment among subjects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archives governance. The practical path to realize the incremental goal of archives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to perfect the archives rights system, cultivate the archives governance ethics, and enhance the archives governance abilities.
Keywords: Archives Management;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在国家治理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目标与档案事业后现代转型的内生需求,共同推动档案事业由管理范式向治理范式转变。在治理环境中,作为档案治理事务承担者的档案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以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公共服务机构为代表的政事型主体、以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为代表的服务型主体、以档案学会和档案智库为代表的知识型主体和以社会公众为代表的参与型主体在档案治理实践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档案治理主体也以其能动性、可塑性和发展性特征影响着档案治理的效能。当前,学界对档案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治理的涵义、内容、特征、功能、理论框架等认识性问题[1-3],参与全球档案治理路径探索、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档案治理现代化转型等实践性问题上[4-7]。相较之下,基于主体视角的档案治理研究相对有限且大多围绕主体角色定位展开。邢慧[8]将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作为档案治理的多元主体,李孟秋[9]将多元主体中的档案部门细化为档案主管部门和国家档案馆,周耀林[10]进一步划分了多元治理主体,将社会组织扩展为文化事业单位、政府信息管理机构、档案研究机构以及档案服务企业等。可见,当前研究成果已经基本明确了档案治理多元主体的构成与定位,但除个别研究中指出了“构建主体能力持续优化体系”[11]和“建立多元协同共治的责任伦理”[12]等主体视角下档案治理实现路径外,多元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方式、主體权责配置、基于主体逻辑的档案治理效能优化等问题尚未形成系统的观点。因此,本文立足于多元治理主体视角,重新审视档案治理的本质思维与内在逻辑,并从主体权利、主体伦理与主体能力三个层面提出实现档案治理效能增量的实践路径。
1 档案治理的本质思维——以人为本
多元主体是相对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中的一元主体而提出的概念,是档案治理区别于档案管理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标志。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强调在维持和把控档案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基础上,不断开拓社会力量,以自下而上的主体扩展形式弥补管理范式下档案事业的不足之处。究其原因,多元主体的档案治理行为在承袭传统管理行为秉持的法理性规范与行政性规范的基础上增添了公共性规范,进一步强调依法治理的治理方式,衍生出了元治理、协同治理等治理方式。不同档案治理方式分别在保障主体权利、调和治理矛盾和实现公平正义中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治理思维。
1.1 以保障主体权利为要义的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指多元主体以档案法规条令为依据,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遵照法定程序有序参与档案事务,并依法承担自身不当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的治理形式。依法治理是档案治理的基础,其基础性表现为依法治理的适用性包容了参与档案治理的多元主体。《档案法》作为档案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践的法理依据,保障了各类主体生成档案、管理档案和利用档案的权利。《档案法》第十三条规定,“反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活动的材料应当纳入归档范围”。[13]这一规定确定了社会公众形成档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多元主体的档案形成权。《档案法》第七条指出,“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第二十四条明确提出,“档案馆和其他机关、组织可以委托档案服务企业进行档案整理、寄存和数字化等服务”[14]。其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多元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正当性,保障了主体的档案管理权。《档案法》第五条还直接规定了“公民享有依法利用档案的权利”[15],这是对治理主体档案利用权的直接法律认定。此外,档案封闭期的缩短、档案开发利用的救济条款等都有效保障了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防止了公民利用权利的空置和缩水。
1.2 以调和治理矛盾为核心的元治理
元治理是指通过调适档案主管部门的权力,实现“自治”与“控制”平衡的治理形式。[16]元治理是档案治理的统领,能够有效地调节治理规则的模式化与治理实践的动态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治理层级程序的承继性与治理监督的扩展性三方面的矛盾。档案主管部门作为元治者能够总揽治理全局,兼顾多元主体特别是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做好宏观调控资源的分配和治理成果的共享,并根据治理实践对治理层级与监管范围进行调适,实现监管对象及其作用场域的延伸,可以说在档案治理实践中享有不同于其他治理主体的行政权力和主导地位。这并不悖于多元共治的档案治理特征,反而对于调和治理矛盾、化解治理失效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档案主管部门在常态化治理中遵循着固有的治理规则,在规则失灵或固有规则脱轨时能够及时将治理实践切换回传统的层级治理模式,维持治理的稳定运行。[17]
1.3 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在共同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明晰各自的档案职权,调和矛盾、化解冲突,从而和谐、高效地参与档案事务的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是档案治理的核心方式,不同于依法治理以法规条文保障治理主体的档案权利,也区别于元治理对档案主管部门角色的再界定,协同治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引导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档案治理实践,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档案诉求,实现治理的公平正义目标。[18]具体来说,协同治理要求政事型、服务型、知识型和参与型治理主体共建治理框架、共治档案事务、共享治理成果。第一,共建治理框架是前提。治理主体以其角色定位与职权划分为基础共建治理框架,使得多元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共同服务于治理实践。第二,共治档案事务是关键。治理主体以治理对象范畴为内容共治档案事务,完成了治理档案资源、治理档案事务等不同深度的治理要求。第三,共享治理成果是本质。治理主体以治理综合贡献力与需求结构为导向共享治理成果,实现了治理激励与需求满足的统一,强化了治理的可持续性。
2 档案治理的内在逻辑——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
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需要解决主体间的权责调整、配置等问题,政事型、服务型、知识型和参与型治理主体间的确权、放权、分权与赋权是治理主体间权责配置的直接表现,揭示了档案治理的内在逻辑。
2.1 “确权”于政事型治理主体
以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公共服务机构为代表的政事型治理主体是档案治理的中坚力量。传统“局馆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深刻影响了档案局、馆的职权划分和问责追责[19],是管理部门“行政性”与服务机构“公共性”的相对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增强档案治理效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制度性障碍之一。2018年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旨在实现机构独立性的基础上理顺政事关系,解决因局、馆合署办公导致的权责不清、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等问题,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与公共服务职责的对应主体,完成政事型治理主体的“确权”。机构改革后,档案主管部门的核心职能聚焦于“治”,从宏观上把控治理进程中的总体布局和前进方向,同时独立行使档案执法、监督、检查等行政权力。档案公共服务机构的核心职能集中于“收”“管”“用”等业务,分别对应着丰富馆藏资源、创新业务流程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三方面内容。政事型治理主体的“确权”是提升档案治理效能的政治性保证。
2.2 “放权”于服务型治理主体
以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为代表的服务型治理主体是重要的市场治理力量。档案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存量数字化的信息化战略要求、档案主管部门宏观调控职能的强化、档案公共服务机构主体业务职能的精准化服务趋向以及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宏观背景,共同促进了档案中介服务机构的产生。这里的“服务”区别于公共服务的无偿性,服务本身作为一种“竞品”存在,在市场环境中表现出鲜明的商品化特征。档案中介服务机构的机构性质及市场化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参与档案治理的实践方式,即承接档案主管部门与公共服务机构委托的部分档案事务,具体表现为档案的咨询整理、档案数字化加工、档案业务培训、管理软件开发和技术转让、数据库建设等业务。[20]“放权”于服务型治理主体是提升档案治理效能的效益性保证。
2.3 “分权”于知识型治理主体
以档案学会和档案智库为代表的知识型治理主体是档案治理的学术力量。档案学会与档案智库都是研究性机构,前者定位于独立的学术性组织,后者则充当决策咨询的“智囊团”。在原有的机构隶属关系中,档案学会挂靠于同级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会的独立性。2018年档案机构改革在实现政社分开的基础上推动了档案学会定位与职能的转变。在组织定位上,档案学会由具有半行政性和机关性的依附机构转变为独立的学术性社会组织。在组织职能上,参照《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档案学会承接了档案主管部门让渡的部分行政职能,其业务范围也相应拓展为档案理论研究、档案科技评估与应用、创新学术交流与科技奖励推荐、普及科技知识与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社会服务。[21]档案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成员,其核心职能在于为政府决策提供知识咨询与智力支持,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档案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分权”于知识型治理主体是提升档案治理效能的科学性保证。
2.4 “赋权”于参与型治理主体
以社会公众为代表的参与型治理主体是档案治理的社会力量。与政事型、服务型、知识型治理主体相比,社会公众具有显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源于其在檔案治理实践中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在于对其“参与”权利特征的理性认识。在管理范式下,社会公众的“利用者”角色根深蒂固,随着以多元叙事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公众积极寻求其在档案治理中的合理地位,成为了具有“治理者”与“利用者”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社会公众的“治理者”角色赋予了其参与档案治理的权利。这种“参与”权利与档案行政执法权、档案公布权等职能性权利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是一种准入性权利而非功能性权利、一种抽象性权利而非具体性权利。同时,公众参与权利的行使层次在不同层级的档案治理实践中存在差异。在宏观档案治理实践中,公众更多地参与到档案常规业务,如档案资源建设之中。[22]在微观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公众参与权利的行使深入到了社区档案资源的利用、管理与服务全程。[23] “赋权”于参与型治理主体是提升档案治理效能的民主性保证。
3 档案治理的效能增量——主体权利、主体伦理与主体能力
档案治理是由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方式参与到各项档案事务之中进而促进档案事业有序发展的系统工程。治理主体维度下,维持治理工程的有序运转,实现档案治理的效能增量归根结底是要完善档案权利制度、培育档案治理伦理、提升档案治理能力。
3.1 完善档案权利制度
档案权利是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档案治理的基石。完善以档案权利确认、档案权利实现、档案权利保障为基本内容的档案权利制度是实现档案治理效能增量目标的制度路径。档案权利并非源于法律的直接赋予,而是依据社会对治理规则约定俗成的共识性认知和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事实推定所形成。因此,就权利的性质而言,档案权利并非法定权利,而是应有权利、事实权利。档案权利的确认要求将多元治理主体的应有权利和事实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从而在制度规范上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合法利益。而档案权利的实现则以明晰档案权利行使的边界和程度为前提。明确档案权利行使的边界应当准确把握以治理需求为导向的治理主体角色的转换,实现治理角色与档案权利内在逻辑的统一。明确档案权利行使的程度要合理分析档案治理实践中准入性权利与功能性权利的行使惯性,建立档案权利行使程度的调节机制,确保多元治理主體档案权利的合理行使。此外,档案权利的保障要求丰富档案权利救济渠道,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方式纳入多元主体档案权利的救济途径,化解治理中的矛盾冲突,防止档案权利的空置或缩水。
3.2 培育档案治理伦理
主体治理伦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档案治理的保障。培育以身份信任、情感认同、责任担当为核心的主体治理伦理是实现档案治理效能增量目标的内在驱动力。主体治理伦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在档案治理实践中共同遵循和维护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的总和。[24]相较于制度、法规等刚性控制手段,主体治理伦理以治理成员的思想、情感、心理等隐性力量作用于档案治理实践。引导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身份信任是培育治理主体伦理的基础和前提。建立身份信任的主要困境在于边缘化治理主体的身份认知障碍。因此,要切实提高与边缘化治理主体相关的档案及档案事务的治理比例,始终将合作协商作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第一准则,使其在心理上接受并信任治理者的身份。随着身份信任的建立,培育治理主体伦理的关键便转向了构筑多元治理主体的情感认同。要充分利用“记忆”的情感属性形成多元主体的情感联结,推进以延续和填补记忆为目标的档案治理工程,使其产生共情效应。多元治理主体责任共担是身份信任与情感认同作用于实践层面的结果。责任共担不仅要求多元治理主体互相关护、尊重彼此的责任,同时要求在治理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下承担治理责任。
3.3 提升档案治理能力
档案治理能力是多元治理主体高效参与档案治理的关键。提升以知识能力、行为能力和调适能力为重点的档案治理能力是实现档案治理效能增量目标的现实要求。主体知识能力、行为能力和调适能力共同存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我构建中,并通过化解主体之间、主体行为之间、主体环境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发挥作用。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知识能力,要求统筹基于主体职能需求的知识学习和知识组织。一方面,依托档案治理目标建立多元主体的知识学习目标,以治理目标需求的变化为依据设置知识更新的周期,扩充主体的知识容量,完善主体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立足于档案治理的专项知识需求,运用语义分析与逻辑分析方式建立高匹配度的主体知识组织模型,实现知识组织的精准化。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能力,重点在于提高多元主体监督行为、管理行为、服务行为以及参与行为的有效性。建立档案治理的监督问责机制保障监督有力,运用数字技术简化档案业务流程实现管理科学,坚持用户至上的行为导向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成立第三方行业协会保证社会化服务质量,搭建档案学术与实务的交流平台增强学术服务质量,建设人才引进机制完善的档案高端智库提高资政服务质量,推广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的建档指导实现规范参与。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调适能力,要求多元主体具有对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敏感性,并据此选择调适情形、制定调适标准,充分发挥调适能力在档案治理中的功用。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浪潮下,档案事业的治理转型逐渐加速,档案治理构成要素不断丰富和延伸。档案治理主体作为档案治理的核心要素随着档案治理实践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主体视角重新审视档案治理的本质思维与内在逻辑,对于创新档案治理研究视角、丰富档案治理理论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从主体权利、伦理和能力层面提出的实践路径也为优化档案治理实践提供了新思路。然而,治理主体的不断拓展固然有利于发挥合力提高治理效能,但其所带来的治理主体权责配置的调整、治理工作重点的转移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尚不明确,同时权力让渡的程度和界限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标准,仍需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持续探索和研究。
*本文系2021年度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面向数字创意产业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21-050HLJU)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晏秦.论档案治理的内涵、特征和功能[J].档案管理,2017(4):4-7.
[2]李孟秋.档案治理的涵义、内容与内在逻辑——基于中外治理观的审视[J].档案与建设,2020(8):40-44.
[3]常大伟.档案治理的内涵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8(5):14-18.
[4]沈洋,赵烨橦,张卫东.现代化档案治理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档案,2021(2):73.
[5]常大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我国档案治理能力建设研究[J].档案学通讯,2020(1):109-112.
[6]杨智勇,贺奕静.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档案治理的路径探析[J].档案学研究,2020(2):37-42.
[7]金波,晏秦.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的实现路径[J].中国档案,2020(1):74.
[8]邢慧.档案治理多元主体角色分析及其协同创新探究[J].档案管理,2020(6):25-27.
[9][11]李孟秋.整合视角下多元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机制与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1(2):12-19.
[10]周耀林,邵金凌,姚楚輝,张兆阳.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档案治理研究[J].浙江档案,2021(4):22-25.
[12][24]张帆.基于主体视角的档案治理伦理研究:基础、目标与内容框架[J].档案与建设,2020(8):9-13.
[13][14][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EB/OL].[2020-06-20]. https:// www.saac.gov.cn/daj/falv/202006/79ca4f1 51fde470c996bec0d50601505.shtml.
[16]卢芷晴.元治理视阈下档案行政部门治理能力现代化策略探析[J].档案与建设,2020(6):25-28+33.
[17]晏秦,刘海兰.元治理理论视角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探析[J].山西档案,2021(4)72-77+87.
[18]陈忠海,宋晶晶.论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档案治理[J].档案管理,2017(6):21-24.
[19]徐拥军,张臻,任琼辉.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特点与方向[J].档案学通讯,2019(1):15-22.
[20]华林,杨娜,吴雨遥.基于档案中介机构管理办法的档案中介机构安全治理问题研究[J].北京档案,2017(9): 24-26.
[21]李颖.新时代背景下提升档案学会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与实践——以辽宁省档案学会工作为例[J].兰台世界,2020(S1):5-6.
[22]徐拥军,李孟秋.再论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走向“社会模式”[J].档案管理,2020(3):5-9.
[23]陈桂生,林路遥.社区档案服务的行动逻辑:一个过程、主体和价值的三维框架[J].档案管理,2020(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