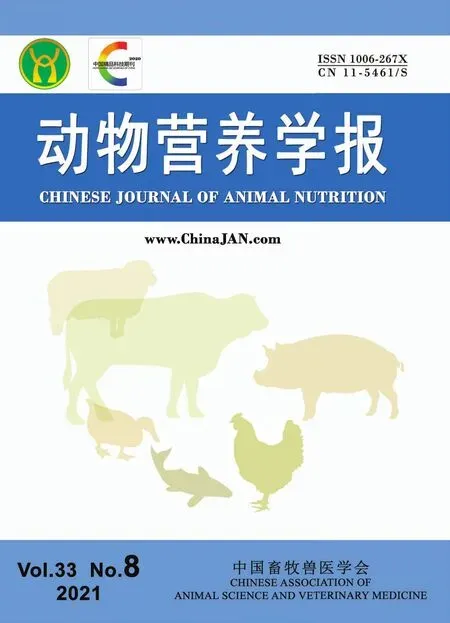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研究进展
李陇平
(榆林学院陕西省陕北绒山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榆林 719000)
反刍动物瘤胃内栖息的多种微生物组成一个复杂的微生态平衡系统,这些微生物群落之间协同作用,通过厌氧发酵将动物采食的饲料降解转化为一系列动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影响着反刍动物的免疫、营养、健康、生长、饲料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1-4]。发挥这些功能的瘤胃微生物包括细菌、原生动物、真菌、古生菌和病毒等[5]。其中,瘤胃病毒主要由噬菌体构成。瘤胃菌群对反刍动物健康和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但是,关于瘤胃病毒,特别是瘤胃噬菌体如何影响反刍动物微生物群落及其在整个瘤胃微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具体机制也不清晰。
噬菌体是感染细菌、真菌、放线菌或螺旋体等微生物的一种病毒,普遍存在于大自然中,通常在泥土、动物内脏、江河湖水、污水、粪便、空气中都有噬菌体的踪影[8]。据报道,地球上一共大约有1×1031个噬菌体,其数量十几倍于细菌,不仅影响着细菌的存活及其致病性,而且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研究比较深入的海洋病毒群落表明,随着水体的深度、纬度、温度、氧含量、微生物多寡以及季节的变化,病毒多样性会发生变化[9-11]。Twort[12]在1915年首次报道在细菌培养物滤液中发现了可以裂解细菌的物质和清晰的噬菌斑,D’Herellets于1917年正式提出了“噬菌体”概念,噬菌体发现之初被应用于治疗人体痢疾、霍乱等细菌感染[13]和治疗犊牛、仔猪和羔羊大肠杆菌疾病[14]。直至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逐渐出现对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的一些报道,从Adams等[15]1966年首次报道从瘤胃液中分离得到裂解性噬菌体以来,到现今为止,人们对瘤胃噬菌体病毒的研究经历了从认识和识别瘤胃噬菌体到瘤胃噬菌体分子生物学探究及组学分析(表1)。本文从瘤胃微生物群落结构出发,主要对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的形态学研究、分子生物学研究及组学研究进行综述,重点阐述了瘤胃噬菌体的作用及功能,旨在为研究瘤胃噬菌体在瘤胃微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供基础。

表1 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研究概况
1 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群落构成
反刍动物瘤胃(温度38.5~42.0 ℃,pH 5.0~7.5,氧化还原电位-250~-450 mV)栖息的各种微生物(细菌、原生动物、真菌、古生菌和病毒)之间形成竞争、共生、拮抗、协作的平衡关系,通过降解饲料纤维、半纤维和木质素等宿主自身难以消化的纤维,为宿主提供能量,并维持着瘤胃微生态(微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微生物与宿主之间)平衡。瘤胃细菌占瘤胃生物量的50%~80%,种类和数量最多,数量达到1010~1011个细菌/mL瘤胃液,超过450种。除细菌之外,每毫升反刍动物瘤胃液还含有104~106个原虫、103~105个真菌、1011个古菌、109~1010个噬菌体(细菌病毒)。研究关注较多的瘤胃细菌主要有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丰度分别为瘤胃细菌的12%和21%[36]。多数拟杆菌[包括栖瘤胃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ruminicola)和布氏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bryantii)等]具有降解淀粉、木聚多糖并参与蛋白质和肽代谢,厚壁菌[包括丁酸弧菌属(Butyrivibrio)和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等]则参与纤维素代谢过程[36-37]。属水平研究较多的细菌有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Butyrivibrio、Ruminococcus和琥珀酸丝状杆菌属(Succinoclasticum)等[38]。瘤胃原虫个体较大,数量较少,可以与古细菌共生,吞噬细菌[38],有利于纤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产生氢气(H2)[40],多数属于纤毛虫纲毛口目和内毛目。瘤胃厌氧真菌中,研究较多的为新美鞭菌属(Neocallimastix)和瘤胃壶菌属(Piromyces),均具有降解纤维素的功能[38]。瘤胃古菌主要为广古菌门(Euryarchaeota),大多数为产甲烷属的甲烷短杆菌属(Methanobrevibacter)[38]。除此之外,瘤胃内还栖息着大量病毒,其中数量最庞大和研究最多的为噬菌体,这些噬菌体具有不同的形态,大多数属于有尾噬菌体目(Caudovirales),包括肌尾噬菌体科(Myoviridae)、长尾噬菌体科(Siphoviridae)和短尾噬菌体科(Podoviridae),绝大多数功能未知,数量达3.0×109~1.6×1010个/mL瘤胃液[41]。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反刍动物甲烷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对瘤胃中产甲烷的古生菌噬菌体(Archaeaphage)的研究或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多样性研究表明,这些噬菌体可能通过裂解瘤胃细菌进而影响瘤胃细菌种群动态变化和宿主营养物质代谢[17,34,42-43]。
2 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形态学研究
1966年Adams等[15]发现瘤胃中存在噬菌体之后[17,34,42-43],1967年Hoogenraad等[18]对过滤后的绵羊瘤胃液负染后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技术对瘤胃中噬菌体形态进行研究,发现瘤胃中主要存在的是有尾噬菌体颗粒。Hoogenraad等[18]的研究不仅是最早采用TEM技术研究瘤胃噬菌体超微形态结构的报道,而且证实了噬菌体是瘤胃微生物的固有组分。随后,利用TEM技术对绵羊[17]、牛[19]等动物瘤胃中噬菌体进行分析,发现瘤胃中大部分噬菌体均属于Caudovirales的Myoviridae、Siphoviridae和Podoviridae[19]。且瘤胃液中噬菌体的数量超过细菌数量,两者比例在(2~10)∶1[44]。早期通过利用TEM技术对瘤胃液中病毒颗粒的研究表明,反刍动物瘤胃中噬菌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形态各异[44],瘤胃噬菌体影响着瘤胃细菌种群的动态平衡变化[45],对瘤胃细菌的裂解及生态平衡有重要贡献,提示我们可以从生物技术角度利用噬菌体调控瘤胃菌群变化从而提高动物生产效率,加强人们对复杂瘤胃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调控。
TEM技术对瘤胃噬菌体形态及其多样性研究分析还发现,显微镜下观察得到的噬菌体数量远高于从瘤胃细菌中分离得到的噬菌体数量,提示瘤胃中大多数噬菌体可能与宿主处于溶原状态,或者是由于噬菌体的宿主谱范围窄,已经分离鉴定的瘤胃细菌有限,尚未得到更多的易感宿主[17]。另外,除了大量存在的有尾噬菌体颗粒外,还有一些属于无尾噬菌体颗粒[复层噬菌体科(Tectiviridae)、覆盖噬菌体科(Corticoviridae)和微小噬菌体科(Microviridae)][46]。在制样过程中,有些有尾噬菌体颗粒尾巴容易断裂或丢失,这种情况下将会造成TEM错误判断[47-48]。尽管如此,TEM技术仍然被广泛应用于噬菌体研究,特别是对新的噬菌体进行分离和鉴定,TEM技术是噬菌体超微形态结构研究的主流技术[49],甚至在通过宏基因组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噬菌体-细菌互作以及噬菌体颗粒组装和释放过程的研究也需要借助TEM技术[50-52]。另外,TEM下形态和结构相似的噬菌体基因组中,某些重要的功能基因具有保守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TEM技术结合病毒(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将在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的鉴定和功能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分子生物学研究
随着分子克隆、RNA/DNA分析技术、分子指纹、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和微生物分离鉴定新技术、新手段的出现和发展,反刍动物瘤胃液被证实是裂解性噬菌体的重要来源[15],众多瘤胃主要细菌特定菌种的特异性噬菌体被相继分离鉴定,包括坏死梭杆菌(Fusobacteriumnecrophorum)[53]、反刍兽新月单胞菌(Selenomonasruminantium)[28]、植物乳杆菌(Lactobacillusplantarum)[26]、白色瘤胃球菌(Ruminococcusalbus)[29]、牛链球菌(Streptococcusbovis)[20, 24-54]和拟杆菌属(Bacteroides)[55]等。目前,只有5种瘤胃裂解性噬菌体病毒被全基因组测序,其中,2株是以Prevotellaruminicola、1株是以Streptococcusbovis为宿主菌的长尾噬菌体,其余2株是以Ruminococcusalbus为宿主菌的短尾噬菌体[30],也是首次对瘤胃特定菌株特异性噬菌体的基因组研究。作为瘤胃中的主要细菌,溶纤维丁酸弧菌(Butyrivibriofibrisolvens)具有纤维降解、木聚糖发酵、蛋白质水解、生物氢化以及在淀粉降解产生丁酸的作用,最近的研究首次从绵羊和牛的瘤胃液及粪便或混合样品中分离鉴定并全基因组测序了ButyrivibriofibrisolvensDSM 3071菌株5株新的特异性裂解性Siphoviridae噬菌体[32],研究表明这5株瘤胃噬菌体属于3种不同的Butyrivibrio噬菌体,分别为Arian和Bo-Finn属、Idris和Arawn属、Ceridwen属,基因组大小30 000~40 000 bp,GC含量39.7%~46.9%,进化分析表明与Butyrivibrio噬菌体Ceridwen属亲缘关系最近的是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噬菌体,而Butyrivibrio噬菌体Arian和Bo-Finn属、Arawn和Idris属之间的亲缘关系比其他任何噬菌体都近。另外,噬菌体Arawn和Idris属基因组中带有许多与溶原相关基因。从瘤胃样品中成功分离鉴定出共同以单株瘤胃细菌Butyrivibriofibrisolvens为宿主菌的3个不同属的5株Butyrivibrio噬菌体表明,反刍动物瘤胃中还有更多功能性噬菌体有待发现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4 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组学研究
随着营养基因组学技术和系统生物学理念在动物营养和饲料学科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通过(宏)基因组学、(宏)转录组学、(宏)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对于解析饲粮、环境和管理等对瘤胃微生物和饲料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整个营养饲料学科的快速发展[56]。其中,宏基因组学是一种不依赖于纯培养的微生物基因组分析手段,通过高通量的测序方法,能够全面分析生境中获得的总微生物结构和丰度,研究宿主与微生物、微生物与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功能关系[57-58]。相比于对瘤胃单个噬菌体的研究,宏基因组学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整个瘤胃噬菌体微生态的有效方法,宏基因组技术也为我们研究饲粮如何影响瘤胃病毒的变化提供了可能[59]。目前为止,通过宏基因组技术对绵羊[60]、山羊[33]、水牛[31]、鹿[35]、肉牛[34,61-62]、奶牛[63]等瘤胃噬菌体的研究都已经报道。然而,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饲喂相同饲粮的动物之间瘤胃噬菌体组成(丰富性)和变异(多样性),而很少针对瘤胃噬菌体群落的动态变化及整个生态系统[43,63]。一项针对饲喂不同饲粮的牛瘤胃病毒种群的宏基因组学研究表明,饲粮总可消化养分、锌含量以及瘤胃微生物功能的多样性影响着病毒群落的变化[34],这是首次报道饲粮变化对反刍动物瘤胃病毒组影响的研究;尽管随着饲粮的变化,瘤胃病毒群落发生变化,但是在动态的瘤胃病毒中鉴定出了14个核心瘤胃病毒群,推测反刍动物瘤胃核心病毒群似乎早于瘤胃Prevotella、Butyrivibrio、Ruminococcus等这些瘤胃细菌核心群[34];此外,该研究对病毒编码的辅助代谢基因(auxiliary metabolic genes,AMGs)分析表明,瘤胃病毒具有糖苷水解酶等一些辅助代谢基因,有利于碳水化合物的分解以增加能量生产,进而影响微生物代谢[34]。对3头牛的瘤胃病毒宏基因组学分析表明,瘤胃中噬菌体主要以Firmicutes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为宿主菌,且溶原性噬菌体的数量是裂解性噬菌体数量的2倍[63]。由于噬菌体种群变化往往与其宿主菌的变化相关联,瘤胃病毒组通过激活溶原性噬菌体致使基因转移从而操控瘤胃基因池变化以及烈性噬菌体的细胞裂解作用控制细菌群落变化,从而发挥着调控这整个瘤胃微生物组的重要功能[63]。除此之外,对水牛[31]、绵羊及山羊[33]的瘤胃病毒宏基因组分析表明,反刍动物瘤胃中主要噬菌体群落为Caudovirales,包括Siphoviridae(32%~36%)、Myoviridae(24%~32%)和Podoviridae(12%~16%)[64-65],这与之前应用TEM技术的研究结果[64-65]吻合。宏蛋白质组学是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对微生物群落进行研究的一项新技术,其定义为在特定的时间对微生物群落的所有蛋白质组成进行大规模鉴定。宏蛋白质组学通过研究不同时间、空间内的基因表达情况,能够把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其功能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了解微生物群落[66]。由于其研究的复杂性,对于瘤胃病毒宏蛋白质组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蛋白质水平的研究可以对整个微生物群落的一致性、活性和功能进行分析,能够提供宏基因组无法获取的信息。
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除了大部分为DNA病毒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是RNA病毒[67]。以DNA分析技术为基础的鉴定手段往往很难对RNA病毒做出准确判断。所以,利用多组学手段,特别是宏基因组结合宏转录组、代谢组学技术手段和生物信息分析技术,可以对瘤胃病毒进行精准分析,最终有望揭示瘤胃噬菌体通过某些特定途径调控瘤胃微生物变化最终影响饲料利用效率和动物健康的机制。
5 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的作用及功能
噬菌体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微生物种群群落,包括裂解微生物[68]、宿主代谢的重新编程[69]、溶原噬菌体的激活[70]等。除了裂解宿主之外,噬菌体还经常获得宿主衍生的一些辅助代谢基因(host-derived auxiliary metabolic genes,hd-AMGs),增强和重塑细胞代谢以支持病毒自身复制[42]。然而,大多数的报道都主要是针对瘤胃菌群开展大量研究[6],针对反刍动物瘤胃噬菌体的形成、分布、以及噬菌体如何调节瘤胃中微生物变化过程的研究鲜有报道。
近年来,随着耐药细菌特别是超级耐药细菌的快速传播以及饲料禁抗、养殖限抗和畜产品无抗的形势发展和行业背景,寻找替抗新产品成为当前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噬菌体及其制剂的功效和产品研制[6]。借此机会,瘤胃噬菌体研究也将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Caudovirales占反刍动物瘤胃病毒的绝大部分,数量最多,研究的也最深入,对于理解瘤胃病毒和宿主之间的瘤胃微生态系统平衡、瘤胃病毒的作用和功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瘤胃噬菌体通过裂解宿主合成子代病毒颗粒的过程中[25,72],产生的细胞碎片、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等也会被瘤胃其他微生物利用,形成瘤胃内循环[73-74]。起初,研究认为噬菌体介导的瘤胃内微生物之间这种营养物质循环对于动物是不利的,因为其限制了微生物蛋白等营养物质在动物后肠道的吸收和利用,从而降低了饲料利用效率[75-76]。然而,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噬菌体介导的瘤胃细胞裂解过程伴随着大量微生物酶的释放,这些生物酶参与碳水化合物的降解过程,从而促进瘤胃内饲料降解,提高饲料利用效率[34-35]。所以,瘤胃噬菌体影响着瘤胃微生物裂解过程和瘤胃营养物质循环,有利于反刍动物瘤胃更好地发挥功能[77]。Swain等[25]通过使用脉冲场凝胶电泳对绵羊瘤胃噬菌体的研究表明,饲粮和饲喂方式对瘤胃噬菌体种群的规律性变化产生影响。瘤胃噬菌体种群变化不仅在动物个体(单独饲养)和群体(混合饲养)的动物小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每天饲喂1次的动物体内也存在明显的日变化:即饲喂后不久(2 h左右)噬菌体数量下降,随后在饲喂后8~10 h噬菌体数量持续上升至峰值,之后4 h内噬菌体数量下降到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并在整个周期内保持不变。这些试验结果表明,瘤胃噬菌体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瘤胃噬菌体与瘤胃微生物种群之间存在着一些动态变化规律。但是,具体的调控途径仍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噬菌体种群的这些变化与饲粮及饲喂方式有关,噬菌体数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饲粮成分诱导温和噬菌体进入裂解阶段,或是宿主数量增加从而可用于裂解感染,或两者兼而有之[25,78]。饲喂后2 h噬菌体数量的减少似乎更难以解释,一种可能性是噬菌体与细菌的结合增加,可能是由于细菌表面受体位点增加所致。一些噬菌体,如大肠杆菌λ噬菌体利用糖转运受体(麦芽糖)感染细菌,只有当这种底物充足时,细菌才会产生受体。当底物浓度低或不存在时,较少的噬菌体能够吸附到细胞并引发感染[25,78]。如果反刍动物瘤胃中也存在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通过饲喂将触发代谢活性的增加,许多瘤胃细菌将产生底物受体。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噬菌体的吸附速度,从而降低它们在瘤胃液相中的数量,这意味着瘤胃中裂解性噬菌体繁殖的主要限制因素可能是受体位点的可用性。这种机制可以部分解释瘤胃中细菌和噬菌体之间的溶原状态[25, 78]。另外,众所周知,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影响着超过1/3基因流动[79],其中,病毒对水平基因转移途径发挥了重要作用[80],和其他环境中存在的噬菌体功能一样[81],瘤胃噬菌体也可以作为移动基因原件,在瘤胃微生物之间遗传物质的不断循环中发挥作用,改变着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基因流和代谢重编程[34],特别是溶原噬菌体通过感染瘤胃细菌和古生菌的重要作用[81-82]。研究表明,瘤胃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换(包括基因水平转移)促进了耐药基因的传播[83-84],然而,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瘤胃噬菌体参与耐药基因的转移过程。此外,Klieve等[85]对瘤胃Streptococcusbovis噬菌体phi Sb01的研究发现,与原始菌株相比,对Streptococcusbovis噬菌体phi Sb01产生耐受的菌株2BAr具有更强的黏附力和生长性能,暗示瘤胃噬菌体改变了瘤胃细菌的生长、生理及代谢途径。总而言之,瘤胃噬菌体通过裂解瘤胃细菌(裂解性噬菌体)或溶原(温和噬菌体)途径,调控着瘤胃细菌种群的多样性和平衡,从而影响着整个瘤胃微生态系统[17,41],使其能够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诸如饲粮或饲喂方式等外界环境。然而,瘤胃细菌和噬菌体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相互之间的平衡状态目前仍不清楚。
6 小 结
瘤胃微生态系统内由一个动态的噬菌体种群,通过持续的瘤胃细菌裂解维持在较高的数量,并影响瘤胃细菌种群变化和基因变化,对瘤胃细菌的种群动态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瘤胃噬菌体是瘤胃微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固有组成部分,具有通过促进瘤胃营养物质循环和遗传物质交换,进而维持瘤胃功能和保障瘤胃健康的重要功能。然而,瘤胃噬菌体与瘤胃其他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尚不完全清楚,如瘤胃噬菌体的丰度变化与瘤胃菌群丰度变化之间的关联,以及瘤胃噬菌体如何与瘤胃菌群相互作用,瘤胃噬菌体如何影响整个瘤胃微生物群落功能并维持瘤胃健康,以及瘤胃噬菌体对动物个体的影响。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反刍动物瘤胃功能,促进动物高效生产,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瘤胃噬菌体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