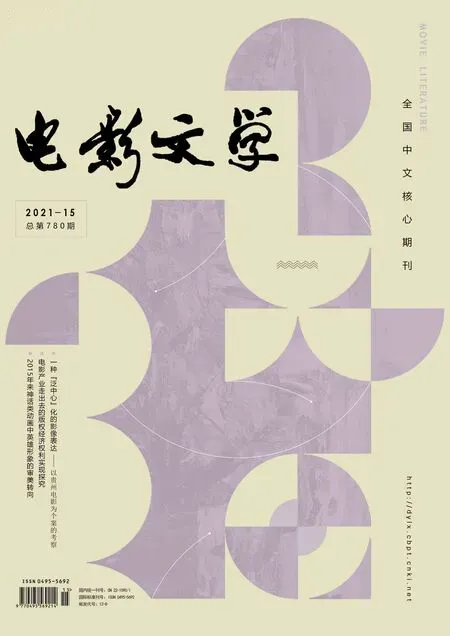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静穆”与“奇观”: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范式
张乃午
(1.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2.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探索极为典型,具体表现出对于电影形式层面的极致追寻。纵观中国武侠电影史,从胡金铨的《侠女》到徐克的《黄飞鸿》系列、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陈可辛的《武侠》、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路阳的《绣春刀》系列、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徐浩峰的《师父》,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视觉形式极为丰富和复杂。在“武侠”的电影世界中,如何呈现“江湖”影像空间的意味,成为一个不断被探寻的问题。本文将聚焦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形式动因,探讨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中的影像造型特质及其意义。
一、静穆: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格式塔”影像特质
“静穆”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温克尔曼、莱辛、歌德、黑格尔、尼采等人都曾专门探讨此问题。“静穆”最初源于古希腊雕塑的评价,后来被温克尔曼总结为希腊艺术的整体特色。温克尔曼称其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宣扬的是希腊雕塑中“节制”“高贵”“单纯”的艺术理想。“静穆”是古典主义的体现,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朱光潜和宗白华都对其进行过探讨。朱光潜说:“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宗白华说:“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在朱光潜和宗白华这里,“静穆”与“艺境”“留白”“虚实”“静观”等中国美学范畴联系在一起。
“静穆”是一种极具古典意味的美学范式。“静穆”是“单纯”和“深厚”的结合,要求形式上和谐均衡、情感上的超然物外,达到一种虚静的状态。在中国关于“静穆”的梳理中,“静穆”和儒释道的文化紧密相连,具体而言,“静穆”和儒家的“和文化”、道家的“坐忘心斋”、佛家的“妙悟”结合在一起,追求意象上的凝定、心性上的虚静、生命的灵韵。“静穆”还与中国天人合一文化命题息息相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一种“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的思维方式”。“静穆”基于中国天人合一自然观和美学观,强调心物相通,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状态。
东西方关于“静穆”的论述,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范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打开了新的思路。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不断追寻传统古典美学理想,注重电影的内蕴和意味,通过化“情”为景和化“美”为媚的视觉呈现方式,营造静穆之美,表现虚静哲思。
化“情”为景的方式,讲究的是情和景的结合,从而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的超脱状态。从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史来看,胡金铨导演的《侠女》就极具此类影像特质。《侠女》的经典在于结合了“静穆”古典气质的美。该片的画面充满古典的意境与禅意,展现出独特的古典意味。具体来看,《侠女》中的竹林大战,就极具“静穆”的古典气氛,已成为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场景。在这场打斗厮杀中,整个竹林场景空幽寂寥,从竹林外射入的光线,碎而笔直地透下来,让打斗厮杀的场面,具有了独特的古典意境。由此可见,《侠女》中竹林大战试图置于“静穆”的情境中完成,营造出最富孕育性的顷刻。自胡金铨导演之后,武侠世界中“静穆”的古典气氛不断弥漫开来。当代中国武侠影片不断在尝试建构此类场景,艺术上运用“电影赋比兴”的表现方式,呈现“静穆”的视觉追求。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就尝试“静穆”古典精神的现代影像转化。该片重复了《侠女》中竹林空间的打斗氛围,试图把侠文化和儒释道思想相互交融,生成武侠电影中化“情”为景的影像范本。之后,路阳导演的《绣春刀》系列也在追随胡金铨、李安的步伐,尝试不一样的竹林大战场景。《绣春刀2·修罗战场》中呈现出夜戏的竹林大战,这种整体上的阴暗色调并没有褪去影像中的古典意境。片中锦衣卫沈炼和敌手遭遇在竹林之中,这一场景同样讲究一种古典氛围的营造。路阳导演曾说过:“希望我的电影是东方的”,这种东方古典影像风格“带着一种刚下完雨的湿漉漉的透彻感”,更是以一种情景交融式的极致影像造型。
化“美”为媚的方式,是用静止的状态呈现流动的美。这种的“凝定”的状态是影像时间“空间化”的一种尝试。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颇具这一类影像特质。影片偏于静态的视觉语言,内敛的表达方式,使得“缓慢”中的《刺客聂隐娘》尽显静穆之美与虚静哲思。在镜头运用方面,《刺客聂隐娘》大都采用远景镜头,这种山水画式的取景方式使得画面产生“时间空间化”的“凝定”效果,观众由此产生远望静观的视觉期待。可以看出,影片以绵延不断的静穆与凝固的抒情意象,为观众提供了近距离观照古人生活的角度。侯孝贤导演回归中国传统语境,诠释了“静穆”在影像表达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刺客聂隐娘》静穆形式层面的体现,更是蔓延在影片中的一种情绪和氛围。这种氛围极大地依赖电影空间的影像造型。例如,《刺客聂隐娘》影片的开头,师徒二人站立于树下,神情肃穆,凝望远方。远处村庄传来狗吠的声音,以及树叶风中作响;影片的中段,聂隐娘登上山峰跟师父请罪,雾气萦绕山峰,宁静且豁达;影片结尾,聂隐娘离去之时,人与自然景再次融合,使用了走向远山的“暮归”长镜头。诚如侯孝贤所说:我是不按照规则拍的,我拍的时候凭一种感觉”。《刺客聂隐娘》的影像致力于寻求寂静之“影”,肃穆之致,其艺术追求上“单纯”和“深厚”的结合,凸显出天地人合的古典智慧和理想。
东西方美学的“静穆”美学观在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中得以呈现,形成新的“格式塔”影像特质,“格式塔”一词的词义,是“整体”的意思。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的整体感知。一部电影就好像一个格式塔,一部电影的影像是由不同的蒙太奇组接方式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表现出了丰富的意蕴,从而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格式塔审美结构,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独特性质。总的来说,电影中的“格式塔”影像特质,是一种整体大于部分的影像意蕴形式。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格式塔”影像特质集中体现在形式上感染力上,即影像的整体性和表现性,特别表现在古典“静穆”意味的呈现。“格式塔”影像中灵动与盎然的整体结构,将影片若干“部件”整合并会通起来,体现影片的韵外之致。一般而言,“格式塔”影像中存在着两个审美空间:一是显在的影像空间,是具实的、可感的、形而下的空间;二是隐在的意蕴空间,是审美的、空灵的、形而上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像胡金铨的《侠女》、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等影片通过化“情”为景和化“美”为媚的方式,试图在故事叙述、人物表演、空间构建、动作呈现等方面营造两个审美空间:显在的影像空间和隐在的意蕴空间。影片寻求各种影像元素的叠加效果,诸如小桥流水人家、风雨云等自然景观,组合成空间意象,诠释人文武侠的虚静意味和庄重气氛。
由上所述,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不断追寻“静穆”式的古典美学理想。这种影像范式是一种精雕细琢的古典意境,一种情绪和氛围,一种灵光一现的感触,一种真实而又缥缈的感觉,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如迷雾一般笼罩在人心里,慢慢发酵,构成了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传统呈现方式。
二、奇观: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后现代”影像特质
电影中的奇观概念源自法国哲学家居依·德波关于“景象社会”的分析。居依·德波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居依·德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景观”的概念,并指出影像生产的方式是景观生产的主导方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图像的中介建立的。依照居依·德波的思路,整个电影工业已然成为景观社会的必然产物。英国电影理论家穆尔维率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电影中的“奇观”,她认为电影是围绕着女性形象的“奇观”来进行叙事的。穆尔维的分析实际上强调了电影影像的突出位置,电影就是一台“影像的机器”。
有学者分析指出:“奇观作为一种新的电影形态已经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电影样式或类型,成为当代电影的‘主因’。”奇观电影是奇特影像的“狂欢”,蒙太奇的结构手段和表意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奇观电影极大的强调“图像性”,将奇观置于叙事之上,运用强烈吸引力的影像造型制造震惊化的视觉效果。归根结底,奇观电影跳脱出了叙事电影“韵味型”影像呈现方式,弱化了情节、人物和主题的意味,转化为“震惊型”,强调视觉冲击力和快感效果。这种视觉范式的典型特点是:精致的画面、强烈的色彩、震耳欲聋的音效。
关于“奇观”的论述,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范式提供另一种视角,即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不断追寻奇观影像,注重电影的影像造型,以反常化的方式来营造运动造型,以奇崛炫目的色彩来构成画面造型,以奇特大胆的场景来构筑空间造型。由此,奇观电影还衍生出动作奇观、身体奇观、速度奇观、场面奇观等诸多类型。
其一,以反常化的方式来营造运动造型。电影影像造型转换为迅捷闪现又变幻着的精心拼凑起来的视觉碎片,景观频频转换,让人目不暇接。贾磊磊曾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奇观场景进行了归类,具体分为:盘肠大战、竹林大战、飞檐走壁、凌波微步、剑光斗法、客栈大战、舞狮大战、擂台比武、英雄取义、双雄对决。这些打斗方式表现出了多样的“舞武”奇观样式。贾磊磊还对中国武侠电影的“暴雨剪辑”剪辑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暴雨剪辑”剪辑方式是一种暴雨如注的心理效果,中国的武侠电影中,勇猛激烈的对打动作与快速密集的剪辑会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视觉影像的激流,会给观众造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从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历程来看,徐克武侠电影中的影像造型极具“暴雨剪辑”的特点。他善于运用快节奏的剪辑方式,把动作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得更加凌厉。这种快如闪电的剪接法极大地依赖剪辑技术,有学者分析指出:“以徐克为代表的技术美学路线,他接连创作了《七剑》《龙门飞甲》和《狄仁杰》系列,将器械设计、动作展现和视觉奇观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另外,张艺谋导演从《英雄》到《影》,就一直在探索动作奇观的模式,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奇观运动造型。《英雄》当中动作奇观尤为典型,影片设置了七场武打场面,频繁而密集地呈现了不同的动作奇观。《英雄》全片长度为1小时32分钟,按以上时间的粗略统计,重要完整的武打场面长达30分钟,占据了全片时间的三分之一,极大地强化了动作造型的比重。由此可见,《英雄》的武打场景精心拼凑起来的视觉碎片,让人目不暇接。之后,张艺谋的《影》又尝试用水墨画、琴音、八卦、阴阳、雨伞、大刀玩起了新型美学试验,片中武打设计颇为独特,以女人的身形入伞,从而达到以柔克刚的视觉效果。《影》的动作设计和“乐舞”动作表现一脉相承。“乐舞”影像是动作奇观的重要方式,营造出了一种“武之舞”的奇观形态。“中国的武舞,在总体理念上要求武(舞)者阴阳俱含,形神兼备,内外合一,刚柔相济。”《影》的动作设计具有浓厚的舞蹈意味,演绎出一幅动人心魄的奇观动作场面。从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奇观视觉效果追求来看,将暴力舞蹈化,始终是中国特色的武侠电影消解暴力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有学者指出:“中国武侠电影的叙述策略,并不在于渲染暴力,而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消解暴力的残酷性。”由此,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将武打转化为一种艺术化和舞蹈化的动作奇观。
其二,以奇崛炫目的色彩来构成画面造型。色彩是电影造型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当代中国武侠电影都极为重视此类视觉造型的营造方式。徐克的武侠电影中的色彩运用就极为奇崛。徐克的武侠电影的色彩较多以黄、红等色调为主,如《黄飞鸿》系列昏黄色调为主来营造片中的武侠氛围,《新龙门客栈》以黄色沙漠场景、大红的灯笼来凸显片中的气氛。《新龙门客栈》和《黄飞鸿》同样以中国传统的黄、红色调为空间场景的主色调,黄色的荒漠、客栈,大红的灯笼,极富奇崛炫目的视觉冲击。张艺谋的《英雄》当中也有鲜明色彩造型:内部空间秦王宫的场景主要以暗黑色调为主,显现皇族宫殿的压抑氛围;外部空间的九寨沟和桂林山水的自然场景则以绿色为主,显示浪漫的人文意象。这些影像造型都带有不同的主题性质,意在凸现场景的奇观性和视觉效果。张艺谋说过:“过两年以后,说你想起哪一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永远记住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那个画面……但是我在想,过几年以后,跟你说《英雄》,你会记住哪些颜色,比如说你会记住,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再如,张艺谋《影》的色彩造型则以黑白灰为主要色调,这种极简主义的尝试,是一种水墨韵味的另类追寻。
其三,以奇特大胆的场景来构筑空间造型。美国理论家利昂·塞米利安指出:“场景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过程,每一个场景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环境的特写镜头。”武侠电影的奇特空间想象极为典型。首先,武侠空间在组接过程中可以实现现实空间和幻想空间的交错组接。例如张艺谋《英雄》开端棋馆打斗场景,出现了现实空间的打斗和意念空间的对决。其次,武侠电影空间组接还可以通过叠加和并置的方式,呈现纷繁复杂的江湖场景,例如徐克导演的武侠电影中经常使用奇特大胆的空间组接方式,如《新龙门客栈》中的戈壁荒漠、《黄飞鸿》系列中市井巷弄,组合成为奇特典型的空间意象。再次,武侠电影空间组接甚至出现了现代写意的方式,利用“晃镜头”画面营造扭曲变形的空间氛围,例如王家卫《一代宗师》以现代写意方式来构筑空间造型,通过极为炫目的“晃镜头”影像造型,来呈现整个武打场面的晃动感。可以看出,王家卫《一代宗师》从开头的叶问雨中打斗场面,到马三和宫二在火车站台决斗,显现出一种后现代影像语言体系之下的空间造型。最后,武侠电影空间还出现了对于传统武侠空间的脱离和变轨,例如陈可辛的《武侠》在影像空间上探索了一条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影片试图采用微观镜头来呈现打斗的肌理,让武侠电影空间的动作元素跳脱出传统的动作造型。另外,徐浩峰的《师父》走出了一条“硬派”武打奇观造型之路,整个武侠空间氛围极具凌厉之感。
“奇观”影像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存在形态,随着消费主义和视觉文化崛起,并日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米歇尔指出:“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控制的文化当中。”贡布里希则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基于读图时代下的武侠电影创作,极大程度地凸显了“图像主因”。进一步来看,奇观化的艺术规则在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美学传统中嬗变成新的影像语言,通过强烈视觉吸引力的蒙太奇组接方式,形成一种新的东方异质文化的奇观,电影本身从“韵味型”转向“震惊型”。
三、类型互渗:“静穆”与“奇观”的影像意义
“静穆”与“奇观”是电影影像造型的两副雅努斯面孔。当代中国武侠电影视觉范式建构的过程,“静穆”与“奇观”两种视觉形式动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衍生出对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影像意义的追问。
一方面,“静穆”影像策略承载叙事电影话语主因。当代中国武侠电影越来越重视空灵、典雅的古典情致,寻求审美上的中国视觉范式。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对意境的强调,对韵味性、时空感的着意,都显现了鲜明的偏好。由此可见,传统古典审美理想并未渐渐远去,而是不断在寻求现代影像的转换。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并没有丢弃传统古典美学的核心理念。《侠女》《武侠》《刺客聂隐娘》等影片成为“静穆”古典美学理想在电影中现代转换的经典代表作品。通过偏于传统美学视野的视觉造型语言,展现了当代中国武侠电影回归古典理想的探索之路。
另一方面,“奇观”的影像策略向图像话语中心范式转变。这种影像语言从叙事电影的“韵味型”特点中脱离出来,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消解倾向。“奇观”影像是对影像造型碎片化、平面化的尝试。“奇观”影像重视“看”的过程,强调影像元素的反常化叠加。我们可以从德勒兹对于“时间—影像”的分析中,看到这种电影影像的“纯视听情境”取向,这种取向强调了影像造型的主体地位,叙事塑造让位于一种分散的、即兴的电影“视觉—声音情境”。奇观电影对于影像语言本身的依赖,造成了视觉元素的无限放大。在这方面,张艺谋的《英雄》到《影》的奇观化尝试,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美学选择及其逻辑演进路径,有学者就这一路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武侠电影之所以为武侠电影,最主要的是审美表现上的奇观化。”奇观化的艺术法则让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范式尝试“类型置换”,并演化成一场东方化的影像狂欢。
综上所述,当代武侠电影的影像造型,不断追寻“静穆”与“奇观”的视觉范式转换,一方面,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不断追寻传统古典美学理想,注重电影的内蕴和意味,通过化“情”为景和化“美”为媚的视觉呈现方式,营造静穆之美,表现虚静哲思;另一方面,奇观化的艺术规则在当代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范式中嬗变成新的影像语言,以反常化的方式来营造运动造型,以奇崛炫目的色彩来构成画面造型,以奇特大胆的场景来构筑空间造型,形成一种新的东方异质文化的奇观,电影本身从“韵味型”转向“震惊型”。总体而言,静穆与奇观影像的类型互渗,扭转的是定型过久的当代中国“武侠影像套路”。有评价指出:“李安、陈可辛、徐浩峰、路阳……或许有更多关于华语古装传统和动作元素的理解正在汇入这条新的影像道路。”在当代中国“武侠”的影像世界中,呈现“江湖”影像空间的意味,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界定与建构,提供了最好的文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