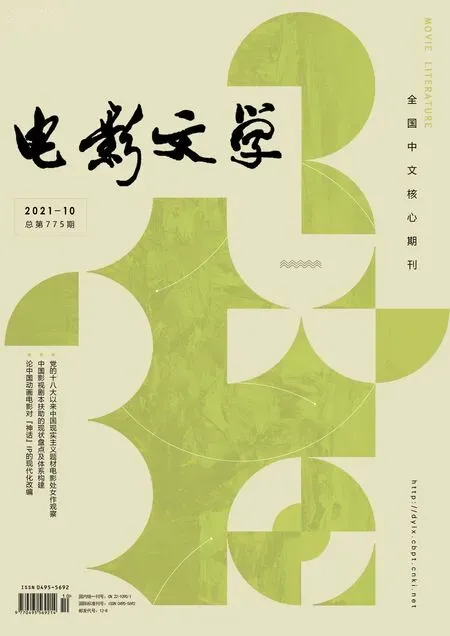主旋律电影的范式转变及其话语表达
——《十八洞村》的创作启示
孙韵岚
(1.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2.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主旋律电影的发展与嬗变总能反映出某段历史所独有的情怀。富有叙事张力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为一种可用以明鉴和自省的镜像被引入这一电影类型之中;同时,亲切质朴又饱含灼灼精神意志的当代英雄模范事迹,又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范例,起到集体情怀的形塑和引领作用,继而也逐步发展为主旋律电影的另一重要分支。上述两种方向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主流话语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强势影响及其某种长期性支配地位”,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尝试以隐喻的方式来建构某类角色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形成了模式化的英雄类型。如《张思德》中塑造的人民解放军,又如《生命的托举》《一个人的课堂》描绘出的教师形象,都可视为国家主流话语的转述者。继而,主旋律电影中不同角色群体之间有关肉体与精神的拯救与被拯救、施教与被施教的既定关系也逐渐明晰。然而,电影《十八洞村》则试图从叙事策略、电影媒介、主题寓意等多个方面打破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范式,一改以往引吭高歌式的表现风格,在人物困境与现实矛盾前巧妙地用影像构架出一个“凸透镜”,以低唱浅吟的方式守候观众去发现社会现实中“缺口”的存在,以此来达成主旋律电影较为完整的话语表意。
一、被“隐匿”的主流话语
由苗月执导的十九大献礼影片《十八洞村》,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坚持贯彻“精准扶贫”的政策方针,从深度贫困村逐步实现脱贫致富的真实故事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以杨英俊为代表的苗族农民在政府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实现了自立与自强,镌刻出我国农民群体的时代风貌。一别以往富有强烈爱国主义号召力与民族情怀感染力的献礼影片,“《十八洞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教片,而是一部用艺术的方式去描写人、感动人的真正的艺术品”。主流话语的宣教功能被弱化,首先体现在创作者对少数民族元素的理解与应用上。“少数民族”作为元素或作为题材经常被视为一种可以表征神秘性、异域性的奇观化手法,为电影作品披以锦衣。除此之外,“少数民族”还可以作为一种从“他者”视角对“本我”的反观态度,也就是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参照,能够让观众直接地感受到因地域差异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文化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绝非对少数民族文化夹杂着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二元对立式的边缘化想象,而是旨在阐明主流话语的引导功能。影片《十八洞村》中多次表现了苗族人生存的地理样貌与生活场景,很多学者以此分析中国电影美学的诗意与特质。其实在展现苗族原生态自然景观的过程中早已埋下了矛盾爆发的伏笔——层层的梯田暴露了农耕用地的短缺,以非戏剧性的手法强化了自然环境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现实矛盾。当影片讲到政府修建公路需要向百姓征地,杨英栏宁愿与族人为敌也不愿交出自家的耕地时,观众也能对角色予以理解,因为这是苗族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理应得到尊重。因此,影片中的“少数民族”亦可作为观众理解角色动机的关键词。
其次,代表主流话语转述者的政府驻村工作人员成为影片中的配角,主旋律电影本应围绕英雄人物或先进楷模展开的角色塑造,被诸多迥异个体组建成的农民群像所取代。在群像之中,有女儿外出务工并嫁给了和村里人喝过断交酒的施家,因此不得不独自生活的残疾老人杨英连;有为了偿还幼女治病的欠款,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脑瘫孙女的抚养重任导致其返贫的杨英俊;有挖了多年矿却没攒下半点家业,一心等着国家帮扶的单身懒汉杨英栏;有妻子在外务工贴补家用,自己却每日坐在门口“守家”,已经因为超生致贫,但还惦念着再添个男丁的杨三金;还有家里耕地少、性情憨直的守林员杨英华。依据国家贫困标准精准识别出的“杨家军”,以各不相似的窘境引人发笑,却又因道明了致贫的真相使人感到了些许的讽刺与酸楚。就像影片中塑造的退伍军人杨英俊,在面对家庭的变故时他承担起了养育残疾孙女的重任;看到妻子面临外出务工时表现出的迟疑与胆怯,他践行着丈夫对妻子的守护;家族亲友们的各类琐事,他也尽其所能悉心照料……即便是这样一位有骨气的汉子,在面对贫困时也不免感叹“我杨英俊几十年一心一意种田,种成个贫困户”。时代侧切下的剖面呈现出了太多我们余光所不能及的真实,这也是创作者试图用镜头聚焦的角色质感。
最后,主旋律电影中拯救与被拯救、施教与被施教的角色既定关系被打破。一方面体现在角色的脱贫观念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本应“被拯救”的农民群体通过主动寻求改变而实现了自我的救赎:不愿做贫困户的杨英俊,非要自己再精准识别一下;看过尾矿库后,杨英栏终于明白自己曾经在山里开的矿洞对自然带来的破坏,主动提出参加填土造田的“战斗”。另一方面,这种既定的角色关系还一度被反转,代表“拯救者”的政府工作人员王申在与杨英俊畅聊时内心得到了释怀。
纵观全片,主流话语的转述人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原本的宣教功能似乎被消减。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对每一位“杨家军”的刻画相当于间接阐明了脱贫的难度与扶贫工作者的不易,也进一步说明了精准扶贫模式正是政府对现实贫困这一缺口的“靶向定位”。此外,国家主流价值观已经植入了杨英俊作为退伍军人的角色身份中。上述无一不在印证着主流话语自始至终并未有所消减,而是借叙事策略转为多种形态“隐匿”于电影之中。
二、“影像间隙”中放大的真实
事实上主旋律电影在最初被提出时是“为了扼制80年代末以武打片、侦探片为主的商业潮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建立电影叙事上的权威性,维持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严肃性,从而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确定不移的正确性”。因此,主旋律电影在向“软性”过渡的过程中,虽然具备影像多样化表达的潜在可能,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仍然遵循着较为审慎的接纳态度,以此来恪守主流话语宣传内容的真实性。这种对真实的恪守与巴赞电影理论对真实的推崇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巴赞认为“我们不得不相信被摹写的原物是确实存在的”,这一“原物体与它的再现形式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即“作为摄影机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使“外部世界的影像……无须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把客体如实转现到它的摹本上”。所以,人们在瞻仰“都灵圣尸布”时所感到的震撼不仅是出自圣物这一媒介,还源于犹如与真“神”的正面对视。胡克先生指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眼见为实,有一种朴素的对‘看’的崇拜”,这和巴赞理论存在交集,说明二者都是以承认物的客观存在为前提而探讨的可信的真实。胡克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需求与巴赞的理论体系存在差别”。首先,被摄物体与影像再现不应停留于表象层面的同一,更应从本质方面“准确全面深入地表现社会现实”。其次,“有些无法直接通过单镜头影像再现的事物”,要以“复现”的方式为观众提供视觉经验,满足观众的观感需求。同时要利用观众的自身经验,突出群体的感觉,使创作主体的个人感受上升为“一种全社会的群体性的联合肯定,要求社会共同对电影中再现的生活给予集体认定、达成共识”。以上两点表明胡克先生对“真实”的理解与巴赞理论存在差异,其认为既要有可信的真实,又要包含可感的真实。
为了达成可信、可感的真实统一,主旋律电影经常采用带有写实风格的影像表达。然而,电影《十八洞村》则多次使用了一种更为夸张的影像修辞手法,通过间隔地删除或保留影像片段中的部分帧,使影像的放映频率低于人眼在常规状态下以每秒24帧捕捉动态画面的接收频率,让画面产生明显的卡顿感。因帧频降低产生的“影像间隙”,让原本在数字技术发展中已被弱化的电影媒介作为一种虚拟化的“物”被观者重新感知。伴随电影画面带有卡顿式的动静交替,“影像间隙”瞬间“抓住某一时刻将其从时间中分离出来”,这让动态影像产生了如同照片的静态假象。麦克卢汉认为,虽然电影作为一种非言语的经验形式和一种没有句法的表述形式,但观众也能把照相机镜头追踪或抛开景物的运动当作文字那样去接受。这是因为电影的序列结构和观众逐行追随印刷形象的观看方式相似,他们能够理解线性排列所蕴含的逻辑。所以,电影观众和书籍读者一样,把纯粹的序列当作自然的东西来接受。观众按创作者提供的线性序列捕获零散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会受到限制,“摄影机对准什么,观众就接受什么,我们被电影送进了另一个世界”。而“抽帧降频”技术是在尝试打破线性序列结构的观看习惯,在可被容许的范围之内,把已被作者赋予完整语法的影片段落分切成最初并不具有任何连贯语义的单个画面,阻断观者以“看”的动作实现简单的逻辑填补,使热媒介的电影在“影像间隙”的产生时带有了冷媒介的特征。观看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不同的观看效果,观众的参与热情得到了释放,以主动思考的状态介入观察画面内部所包含的信息之中,开始尝试谛视影片角色。
《十八洞村》影像处理中使用的“抽帧”技术总会让人联想到王家卫导演的作品,但两者要表达的侧重点却各有不同。王家卫导演的影像经常会给人一种不稳定感,这种感受不是单纯依赖制作技巧而实现的,更多的是由于导演在转述信息的过程中,以梦呓般的口吻让观众产生了不解和迷惑的感受。在空间的展示方面,导演以一种异常的组织形式来加工客观现实存在的景物,使镜头内的空间如同莫霍里·纳吉口中称赞的“外部宇宙的奇景”,以此来表明外部空间是角色内心的等同物。晃动的摄影镜头与虚化的背景为观众提供了匮乏的信息,观众只能试图在角色身上寻找答案。而角色在运动状态中产生的影像“拖尾”,总是将观众滞留于动作的“前一秒”;当角色静止时,又表现出迷离的放空状态或展现出同观众相似的迷惑感。观众始终无法构建出完整的逻辑,只能在体会角色情绪状态的过程中完成带有非理性的感知,如同梦后似是而非的模糊记忆。
与之相比,《十八洞村》则为观众提供了更为完整的信息。“抽帧降频”技术在全片中只有两次被应用于回忆段落,其余都被用以刻画角色的运动状态,分别为:杨英俊陪大哥杨英连去集市寻回女儿小薇薇,杨英连追打女婿施又成;麻妹在得知小龙离职的消息后,急忙跑去通知杨英俊;杨英俊从村寨一路追到城里,劝小龙不要离开;填土造田的群体劳作场面。以“集市寻女”的段落为例,“抽帧降频”技术消减了上一帧动作开始的原因与下一帧动作结束的效果,使角色前后动作之间的关联性减弱,却又突出了画面定格所在帧的角色情绪。并且,整部影片用相对清晰的画质代替物体运动产生的“拖尾”与模糊,观众被置身影片角色所处的时空中,得到了正面凝视角色的机会。我们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杨英连渴望一家人早日团圆,但又忌惮女婿的先祖曾与村寨人喝过断交酒的过往,继而产生的纠结心理。另一方面,角色所处的空间又延展出很多画外信息。同样是“市集”段落,我们不仅能够看见杨英连的动作,体会他的情绪,还能觉察出画面内的围观群众同样也在驻足观看。他们外貌朴实,其中一些人还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以生疏的动作操作着现代移动通信工具,捕捉生活中偶遇的这场突发事件。这些围观群众无疑与久居村寨的杨英俊、杨英连不同,是镜头刻意记录下的正向“城市化”过渡的群体。我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相异元素碰撞而产生的不和谐——现代与传统栖身于同一“宿主”时的尴尬对望。围观群众为我们理解杨英连、杨英俊等角色的处境提供了时代背景,形成了农村、城镇、城市之间的彼此对视,相互熟悉但又互相远离。
如果说“抽帧降频”技术在王家卫导演的影片中刻画出了时代中的个体并细切出个体的情绪,那么电影《十八洞村》则是让我们透过个体及其感知,去反观角色所处的时代环境。这种兼顾角色情绪与所处状态的整体描摹,是真实可信与真实可感的统一,是由“影像间隙”中放大的、比目之所见更真切的真实。
三、带有人文意蕴的本土回溯
和当年麻妹为了把有限的口粮留给家人而不得不离乡务工的初衷有所不同,村委会堆放的铺盖卷仿若一个个外出打工的村民,他们离开的理由和路生大抵一致:能走多远走多远,能飞多高飞多高。这群曾经“以‘诗意的栖居’方式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原乡人”一定不曾预料,即将在城市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完成自我他者化的转换过程中,会以丧失主流意识与身份认同为代价。作为“异乡人”的“他们找不到一个得以结合的可靠文化,甚至连大众文化暂且也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如果参照“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再对这一转变进行解读,似乎在这条不可回溯的道路上,乡民曾经背离乡土,最终也会被乡土放逐。
影片始终围绕人与土地的关系展开叙事、设置矛盾,又在政府工作人员王申的帮助下解决了农耕土地太少的问题,把飞地尾矿库承包下来进行填土造田的改造,最终实现了“杨家将”的脱贫翻身。但对于“杨家将”以及十八洞村的村民来说,又不可以简单地把土地当作服务于社会物质生产所必备的劳动资料来看待。作为纯苗族聚居区的十八洞村,苗族先民基于对自然的崇敬而建立的宗教和信仰,对其后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土地是苗族人感知自然的直接途径,也是延续本民族原始宗教和信仰的重要实践渠道。杨英俊退伍转业时选择回乡,多年来一心一意地耕田,表现出苗族人对原始宗教信仰固有的虔诚与敬畏,他悉心照料的土地也自然会得到神灵的庇佑。“万物有灵观念影响着苗族人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也从精神空间延展了苗族人眼中的现实世界。”所以,杨英俊在田里仰望到空中盘旋的那只凤凰,虽是现实虚无之物,但又是苗族人心中萦绕着的无比真实的神灵,抬头便能看见。当他被告知再次返贫时,生活的困顿让他重新思考土地对自己的意义,这种质疑无疑打破了苗族人对原始神的遐想。传统与现实、留守与逃离等一系列衍生出的矛盾,在其问题的本源——人与土地的关系上通过“杨家将”的亲身躬行得到了回应与解答。杨英俊以自问、自践、自证、自得的方式完成了原始宗教信仰的回归,心灵得到了洗涤。
因此,主旋律电影《十八洞村》是在解析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得以成功的原因,观众在影片中逐步梳理出苗族人与土地的关联,重新思考少数民族群众的归属问题。创作者的叙事方式看似浅谈辄止,却在角色塑造、影像表达与主题寓意等多个方面综合发力,如同在社会现实的“缺口”处放置了一个“凸透镜”,清晰明了地聚焦问题的实质。以人文意蕴的谛视方式从人的归属与民生关切角度打破不可逆的“城市化”进程,实现了乡民向乡土的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