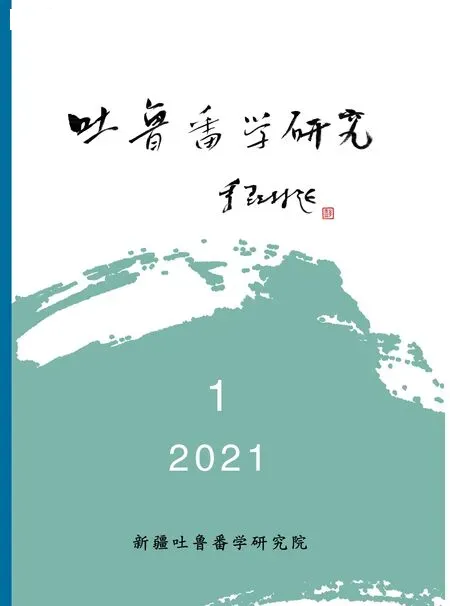汉晋蜀锦研究综述*
杨浏依 赵 斌
关键字 蜀锦 丝绸之路 西域
蜀锦,同南京云锦、苏州宋锦以及广西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原产于巴蜀,兴于春秋而盛于汉唐,因其独特工艺与特殊价值倍受重视,有所谓“独称妙”①(南朝宋)山谦之于《丹阳记》有言:“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之誉。自古以来,便有诸多著述对蜀锦予以研究,且成果丰硕。
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丝绸之路研究成为显学,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地区发现并出土了较多织锦,而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蜀锦,蜀锦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大体而言,蜀锦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蜀锦的历代沿革、织造与纹样、发展与传播以及贸易等方面。而近年来,蜀锦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焦点之一。
一、蜀锦史研究
汉晋时期蜀锦研究大多依托于丝绸史研究当中。例如,赵丰《中国丝绸通史》②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中国丝绸的历史、发展、生产技术、丝绸品种及其艺术风格分别作了简要概述与研究,其中第二章“秦汉丝绸”与第三章“魏晋南北朝的丝绸”涉及蜀锦历史研究,此研究著作展现了蜀锦发展与变化,为蜀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全面性的知识理论框架。黄忠修在《中华锦绣丛书·蜀锦》③黄修忠:《中华锦绣丛书·蜀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就从古至今蜀锦发展简史、蜀锦“整经”与“挑花结本”等织造技艺、蜀锦纹样色彩以及组织结构等风格特征皆有详细探讨,同时注重蜀锦的传承保护和后代发展方向的探索。此著作尤其对秦汉至魏晋时期蜀锦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与其传播范围、蜀锦制造工艺以及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分析研究“韩仁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重要织物,无论是对古代蜀锦研究还是对现代蜀锦的保护皆有重大意义。与之类似的有黄能馥所著《中国成都蜀锦》①黄能馥:《中国成都蜀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深入探究了巴蜀地区织锦的诞生,按时间顺序整理蜀锦在国内外各地区的传播,并且针对成都蜀锦独特织造技术与其相应的特殊织机,在“探讨蜀锦织机”部分有详尽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文质并中的中国织锦传统”篇相比较于其他著作,更加注重探究蜀锦文化内涵。当然,罗瑞林,刘柏茂所编《中国丝绸史话》②罗瑞林、刘柏茂:《中国丝绸史话》,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6年。也有与丝绸文化相关,但其大体还是以呈现中国历代丝绸发展演变为主,其中包括蜀锦产地、生产组织以及墓葬出土蜀锦等方面。《四川省志·丝绸》③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丝绸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亦对蜀锦工艺发展及其对外贸易皆有概括性研究。
关于蜀锦研究著作较多,但大多只简单介绍,占比小。虽也有对蜀锦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但篇幅较少,论述不详尽。而关于汉晋时期蜀锦的研究,并未有专门著作予以讨论。
二、蜀锦织造与纹样艺术
部分学者就蜀锦织造技术、纹样图案以及蜀锦所呈现文化内涵做了专门研究。首先,以黄修忠为代表,对蜀锦织造技术做了全面研究,在其与钟秉章、卢伟平合著《蜀锦织造技艺》④钟秉章、卢卫平、黄修忠:《蜀锦织造技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参考《华阳国志》《史记》《汉书》《益州志》《西京杂记》《丝绣笔记》《三国志》以及《蜀都赋》等文献著作,深入讨论了蜀锦织造技术发展沿革、分布状况、传统工艺以及部分代表性图案,工艺上列举了“挑花结本”“植物染色”等重点技术,图案上按照时间顺序归纳总结各个朝代纹样特点与风格,特别就新疆地区出土汉晋蜀锦纹样与三国魏晋时期蜀锦“加金”技术做详细描述分析,较为完整的展现了蜀锦织造方法、织造过程与其工艺特点。在黄修忠另一著作《蜀锦织造技艺·从手工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术》⑤黄修忠:《蜀锦织造技艺·从手工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年。中,以织机的发展变化为线索,讨论蜀锦传统生产工艺、生产工艺流程、纹制和染色工艺等,内容涉及蜀锦的方方面面,著作篇章虽不多,但覆盖面宽,对织机演变过程,从帘式提花机到多综多蹑束综织机,描述详细,为学界研究织机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参考。路甬祥与钱小萍合著《丝绸织染》⑥路甬祥、钱小萍:《丝绸织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乃是研究丝绸织染技术的专著,不仅在第十四章节“蜀锦组织及制作工艺”专门论述蜀锦,而且书中所见大部分织物组织图尤其是上机工艺图,皆由作者亲自首次绘制,填补了以往文献在此方面的空缺,十分具有可复原性与操作性,在研究方式上也具有创新性。
其次,凹凸撰文《纹道:蜀锦蜀绣漆艺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⑦凸凹:《纹道:蜀锦蜀绣漆艺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专门讨论了成都蜀锦的纹样特征与纹样织法。部分学者重点关注蜀锦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余涛与邓廷良分别在其著作《濯锦集-丝绸文化与织染技艺》①余涛编:《濯锦集——丝绸文化与织染技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一篇“文化的几点”、《丝路文化 西南卷》②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三章第三节“蜀锦蜀布”中,探讨了蜀锦纹样、图案所展现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研究视角不乏新意,涉及诸多领域,既有知识性,又带趣味性。
除却论著中的蜀锦研究,部分学者从蜀锦的工艺、技术方面着手专门研究。王君平自2000年起,在《蜀锦传统工艺研究》③王君平、王斌:《蜀锦传统工艺研究》,《四川纺织科技》2000年第4期。、《蜀锦传统工艺研究(续二)》④王君平、王斌:《蜀锦传统工艺研究(续二)》,《四川纺织科技》2000年第5期。、《蜀锦传统工艺研究(续三)》⑤王君平、王斌:《蜀锦传统工艺研究(续三)》,《四川纺织科技》2000年第6期。、《蜀锦图案风格及其发展沿革》⑥王君平、王斌:《蜀锦图案风格及其发展沿革》,《四川纺织科技》2002年第4期。、《蜀锦的牵经工艺》⑦王君平:《蜀锦的牵经工艺》,《四川丝绸》1999年第2期。、《蜀锦的寓合纹样》⑧王君平、王维:《蜀锦的寓合纹样》,《四川纺织科技》2002年第3期。、《蜀、蜀锦、蜀江的含义及其源流考析》⑨王君平:《蜀、蜀锦、蜀江的含义及其源流考析》,《纺织科技进展》2015年第5期。一系列论文中,专门就蜀锦本身传统工艺过程、纹样变化与特征进行了以番梳理,对研究蜀锦有一定推动作用,是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典范。罗群则在《从经锦到像锦——中国织锦技术变化概》⑩罗群:《从经锦到像锦——中国织锦技术变化概述》,《丝绸》2014年第8期。文中整理自战国以来织锦变化,包括汉代经锦、唐纬锦、辽纬锦和元特结锦,并就汉代经锦、斜纹经锦,在参考新疆出土部分蜀锦基础上进行研究,权威性概括了织锦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变化,认为织锦组织变化取决于织造技术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渐进的,直至清末在西方技术的影响下才出现了较大变化。还有崔岩、刘元风、郑嵘《蜀锦红花染色工艺研究》⑪崔岩、刘元风、郑嵘:《蜀锦的红花染色工艺研究》,《丝绸》2016年第10期。,在借鉴文献材料与染色实践基础上,对红花染色工艺步骤进行研究,还原了古代染色生产程序,并证实蜀锦的生产者或称之为蜀锦艺人,在唐代时期便已经熟练掌握了对红花色素的运用,是学界对蜀锦在染色工艺和染料研究上取得一大进步的重要表现。曾凤杰则于《蜀锦织造中落花流水锦的纹样设计研究》⑫曾凤杰:《蜀锦织造中落花流水锦的纹样设计研究》,《美与时代》(上)2017年第7期。文中,以三国至明清时期的蜀锦作为研究对象,参照各时期所共有的“落花流水锦”,对蜀锦图案中具体纹样予以研究,总结以落花流水为考察的蜀锦流变创作,此次探索对研究甚至提倡蜀锦织造技术的发展有积极意义。马磊《浅析龙凤纹的发展——以蜀锦中的龙凤纹为例》⑬马磊:《浅析龙凤纹的发展——以蜀锦中的龙凤纹为例》,《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4期。一文讨论蜀锦中的典型纹样:龙凤纹,简述了其纹样从新石器时代的兴起,经唐宋的繁荣,直到明清的发展演变,概括了蜀锦龙凤纹在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并认为蜀锦是象征中国民族文化龙凤纹样的实物载体,它记录了中国历史的变迁,是丝绸中的耀眼一点。同时也有周赳、吴文正《中国古代织锦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⑭周赳、吴文正:《中国古代织锦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纺织学报》2008年第3期。、胡光俊、谭丹《浅谈蜀锦及其传统织造技艺》⑮胡光俊、谭丹:《浅谈蜀锦及其传统织造技艺》,《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2013年第2期。、张冯倩、赵敏《蜀锦织物纹样结构形式的演变》⑯张冯倩、赵敏:《蜀锦织物纹样结构形式的演变》,《纺织科技进展》2011年第6期。、刘金霞、任梓熙《锦绣四川:传承千年的丝线交织艺术》⑰刘金霞、任梓熙:《锦绣四川:传承千年的丝线交织艺术》,《四川档案》2018年第1期。以及张晓霞所写《谈汉代丝织品上的卷云纹》①张晓霞:《谈汉代丝织品上的卷云纹》,《丝绸》2013年第4期。等文章,皆从技艺、组织结构方面对蜀锦进行探讨,其中不少就汉晋蜀锦的纹样特点和细微处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三、蜀锦发展与传播
蜀锦产自于巴蜀,又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其他地区。而蜀锦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由自然与历史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吴方浪《汉代“蜀锦”兴起的若干原因考察》②吴方浪:《汉代“蜀锦”兴起的若干原因考察》,《丝绸》2015年第9期。一文就汉代蜀锦在巴蜀地区兴起与发展的原因与背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自然地理、国家政策、发达的交通、社会消费、蜀锦贸易发展等方面提出分析要点,对汉代蜀锦兴起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按照转播路线划分,蜀锦对外传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沿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播,二则是蜀锦在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南方丝绸之路始于春秋,兴盛于唐代,而衰于清代,它是一条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商品,推动中国西部、西南部与中亚、西亚、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而蜀锦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学者专门讨论了蜀锦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例如,陈爱蓉、陈雅劼《如何丝路成坦途——南丝路上蜀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③陈爱蓉、陈雅劼:《如何丝路成坦途——南丝路上蜀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四川戏剧》2016年第4期。认为,巴蜀所产蜀锦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贸易产品之一,由蜀锦衍生出的丝绸文化,不仅是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体现,更是南方丝绸之路沿途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情感与历史的融合,文章第一节“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第二节“蜀锦的发展与南方丝绸之路的繁荣”重点分析了蜀锦在丝路上的地位作用。段渝在《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④段渝:《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与《成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历史地位》⑤段渝:《成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历史地位》,《成都日报》,2015年。中,通过对《史记》《汉书》中有关南方丝路文献的研究,论述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并在第二节“古蜀丝绸与汉通西域前的南方丝绸之路”中重点描述蜀锦在中西方交流中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
蜀锦在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主要涉及蜀锦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笔者将在本文后半部分予以详细论述,故在此不予提及。
四、蜀锦贸易
“四川丝绸贸易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我国丝绸贸易史上举足轻重在古代。”丝绸贸易引起不少学者关注,季羡林先生在其所撰《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古代,西南一带丝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成都的锦更闻名全国,同缅甸的交通又那样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美丽的丝织品,一定会通过(蜀·身毒道)这样方便的交通道路传到缅甸,再由缅甸传到印度去。”①季羨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1~94页。之后有学者专门就蜀锦在丝绸贸易中的地位做了研究,袁杰铭在《四川丝绸贸易历程与特点(上)》②袁杰铭:《四川丝绸贸易历程与特点(上)》,《四川丝绸》1999年第4期。、《四川丝绸贸易历程与特点(下)》③袁杰铭:《四川丝绸贸易历程与特点(下)》,《四川丝绸》2000年第1期。两篇文章皆探讨,以蜀锦为主要商品自秦汉到现代的四川丝绸贸易状况,通过表格形式列举了历代蜀锦的代表品种,例如汉代的“长乐光明锦”、“万年益寿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降地蛟龙锦”、“绀地勾纹锦”,隋唐时期的“赤狮凤纹蜀江锦”、“海蓝地宝相花纹锦”等,为后面学者研究蜀锦贸易提供了方便。同样,在其《四川丝绸贸易史话》④袁杰铭:《四川丝绸贸易史话》,《四川丝绸》1997年第2期。中,分四川丝绸国内贸易、四川与“丝绸之路”两部分讨论蜀锦于南北方丝路的媒介作用。除此之外,蓝勇的《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研究》⑤蓝勇:《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一文,提出学界对蜀锦贸易的研究属于初步阶段,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在中国对外丝绸贸易史上究竟有多高地位?丝绸贸易在这条丝路贸易中占多大比重?是不是象现在有人认为的那样中国丝绸西传最早得助于南方丝绸之路,以后中国丝绸通过此丝路源源不断地转输到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研究中仍未详细解答的问题予以一辩,解答了学界在此研究方向上的不少疑惑。当然,孙先知所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技艺交流和丝绸盐茶贸易(上)》⑥孙先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技艺交流和丝绸盐茶贸易(上)》,《四川蚕业》2016年第3期。也包含对蜀锦在丝路贸易中的分析。
五、汉晋蜀锦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
“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丝绸作为特殊的贸易品,是其最重要的载体。而蜀锦,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撑”。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丝路贸易随之发展壮大,丝绸逐渐成为丝路上的主要商品,其中便有蜀锦。尤其近年来,在新疆以及部分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考古中发现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汉晋时期织锦,此些织锦备受学界关注,不少学者对其所处年代、纹样与组织结构等方面皆有专门研究。
(一)丝路蜀锦考古
自近代,新疆楼兰、营盘等其他地区考古工作陆续开始,大量丝织品随之出土,其中包含部分织锦,织锦中又以蜀锦数量居多。
汉晋蜀锦考古发掘,按照地区主要分为楼兰、吐鲁番营盘以及山普拉四个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其所编《新疆出土文物》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中,分别列举自尼雅民丰遗址出土的“万世如意”锦袍,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的禽兽纹锦、对羊纹锦覆面、联珠对孔雀纹锦覆面、对鸟对羊树纹锦、骑士对兽毬纹锦、“吉”字纹锦(局部)以及牵驼纹“胡王”字锦共七件织锦。同时亦在《丝绸之路——汉唐织物》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中介绍敦煌地区出土“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民丰出土的六菱纹“阳”字锦袜,以及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织成履等重要织物。
除总的考古报告外,汉晋蜀锦的发掘按其地区主要分为吐鲁番、楼兰、营盘以及山普拉四个主要地区。
首先,吐鲁番地区出土织锦。李征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①李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中记录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情况,其中包括少量汉晋时期的织锦。由于吐鲁番地区墓葬时间大多属隋唐高昌王国时期,汉晋时代蜀锦出土较少,故本文对此地区出土报告采用较少。
其次,新疆楼兰地区出土织锦。楼兰地区出土织物墓葬时间主要为汉晋,故在此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织锦。于志勇分别在《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②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1995年尼雅考古的新发现》③于志勇:《1995年尼雅考古的新发现》,《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④岳峰、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考古》1999年第4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⑤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新疆尼雅遗址95MNIM8概况及初步研究》⑥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IM8概况及初步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以及《尼雅遗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⑦于志勇:《尼雅遗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人民日报》,2014年。考古调查报告中,记录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的,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长寿光明”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万事如意”锦为代表的大量织锦,并对其中较为独特织锦予以详细研究。李遇春在其发表的《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⑧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以及《尼雅遗址的重要发现》⑨李遇春:《尼雅遗址的重要发现》,《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中,分别对民丰尼雅遗址两次重要发现做详细叙述,其中包括东汉合葬墓中男尸衣物所穿黄蓝色锦袍,所戴“延年益寿宜子孙”锦制成的袜子与手套,以及女尸所戴“阳”字锦制成的袜子等织物。不止在楼兰民丰尼雅遗址有发现,侯灿在楼兰古城遗址周围皆发现汉代织锦。《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⑩侯灿:《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中记录,在楼兰古城遗址中发现八件丝织品,其中锦有三种,且主要为波纹锦。在《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⑪侯灿:《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中,对城郊发现的五十三件汉锦中有铭文的织锦进行列举,其中包括“延年益寿”锦、“长寿光明”锦以及部分三色显花锦。以上考古以调查报告皆为后人研究蜀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其三,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出土织锦。营盘墓地考古发掘包括主要由周金玲、李文瑛、吴勇等人整理并发表,其发掘时间分别是1995年、1999年。在1995年发掘过程中,经《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⑫周金玲、李文瑛:《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记录,墓地共出土四件织锦残片,并对其中之一的方格动物纹“王”字锦的尺寸大小、纹样以及经纬线规律做详细描述。同时在《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⑬周金玲、李文瑛、尼加提、哈斯也提:《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中,对该墓葬中出土“寿”字锦等进行了梳理。1999年,虽对诸多墓葬有所发掘,但其中却难见到织锦。
最后,洛浦县山普拉地区出土织锦。肖小勇、郑渤秋在《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的新发掘》⑭肖小勇、郑渤秋:《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地的新发掘》,《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中记录了例如绛地兽面壁玉纹锦袋等较为独特的织锦的出土情况。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楼兰尼雅遗址也有类似织锦出土。
(二)丝路蜀锦研究成果
针对新疆楼兰、吐鲁番以及营盘地区出土的大量汉晋时期织锦,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与整理,其中以武敏、赵丰、王晨以及于志勇为代表。笔者在参考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对楼兰地区汉晋织锦研究情况的分类,按学者主要研究视角大致分为:织锦工艺组织结构与图案风格分析、织锦纹样艺术研共两类。
1、织锦工艺组织结构与图案风格分析
武敏先后就吐鲁番出土部分东汉以及魏晋时期的织锦进行研究,在其《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①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6年第Z2期。文章第一部分“织锦”中,从花纹图案、织纹、显花三方面分析出土的东汉与北朝至唐代初期织锦。归纳其特点,东汉至织锦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几何图案等,且图案书有吉祥字样,织纹为经丝夹纬,显花为经丝彩色显花。北朝之后纹样有了重大变革与发展,由于本文时间采汉晋时期,故不对其后时代进行讨论。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文章为之后的织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随后,1984年发表《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②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针对当时新获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蜀锦,按其年代,在参考《蜀锦谱》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的命名,并从织锦产地、蜀锦纹样特点以及蜀地与高昌地区的商业交流等方面考证,出土的“藏青地禽兽纹”锦、“树纹”锦、“盘球狮象”锦、盘球“胡王”锦、“球路孔雀”锦、“夔纹”锦、“对鸡对羊灯树”锦以及“方胜兽纹”锦皆为蜀锦。此篇文章可以说意义极大,不仅规范了织锦的命名,而且为后来学者就如何判断出土织锦为蜀锦提供了依据。
王晨、于志勇主要针对尼雅遗址出土织锦予以分析研究。例如,王晨《从尼雅遗址出土汉锦特点谈蜀锦技艺》③王晨:《从尼雅遗址出土汉锦特点谈蜀锦技艺》,《纺织科技进展》2016年第1期。,以尼雅出土织锦为对象,例举“安乐绣”“文大”“宜子孙”等部分蜀锦,分别介绍了织锦品种、结构和图案风格,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如何加强对蜀锦技术的传承与保护。于志勇则在《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一文中,对楼兰地区出土所有带有文字的织锦以及学术界对汉晋文字织锦予以总结归纳,重点讨论了织锦中的文字类型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需要提及的是,楼兰尼雅遗址出土了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制品,引起中外诸多学者关注。部分学者对织锦组织结构与文字做了深入研究与详细报道,其中包括:王晨《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④王晨:《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王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解说》⑤王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解说》,《光明日报》,2012年。、刘春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之谜》⑥刘春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之谜》,《光明日报》,2015年。、向仲怀,陶红《汗血马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新疆蚕业及丝绸之路考察报道》⑦向仲怀、陶红:《汗血马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新疆蚕业及丝绸之路考察报道(二)》,《蚕学通讯》2016年第1期。、阿迪力·阿布力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⑧阿迪力·阿布力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中国民族报》,2018年。。亦有学者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中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索,例如,于志勇在《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五星”二字所表现的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以及其中的祥瑞含义受到作者关注。除此之外,另有吴钢《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神秘的巧合》①吴钢:《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神秘的巧合》,《四川蚕业》2016年第1期。,通过考察蜀锦历史与出土的“五星”锦历史、汉代四川蚕桑丝绸织造业、汉代织机实物以及新疆出土丝织品实物,以证实作为拉弓射箭时使用的“五星”织锦护臂确为蜀锦。
2、纹样艺术研究
纹样是指,一个单位循环的织物图案的小样,其大小与图案单位的大小一致,与一般的绘画构图不太一样的是,不能任意选择绘画,且配色也受到各个时期的工艺限制。织锦纹样因其独特的精美的特点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赵丰在《连烟和云—众兽群聚:汉代的云气动物纹锦》②赵丰:《连烟和云·众兽群聚:汉代的云气动物纹锦》,《浙江工艺美术》1999年第2期。中认为,汉代织锦在艺术风格上十分有个性,其纹样图案多与道家、巫术等相关,并重点研究云气动物纹锦,总结出动物织花图案主要两个系统,其一是动物站立方向与经线方向一致,看起来动物是正立的,其二是动物站立方向与纬线一致,沿经向对称。对纹样的精确总结,为学者分辨其纹样特征提供依了重要依据。此外,段光利于《汉代织锦图案中禽鸟纹研究》③段光利:《汉代织锦图案中禽鸟纹研究》,《丝绸》2014年第8期。和《汉代织锦图案的排列方式研究》④段光利:《汉代织锦图案的排列方式研究》,《丝绸》2015年第8期。中,就新疆出土汉代织锦,例如:对其图案题材和具体的云气动物纹样进行深入探究,归纳分析发现动物纹样主要包括三足乌、雁纹、凤凰、朱雀纹、鹤纹、孔雀纹、鸿鹤、鸳鸯,以及一些不知其名目的禽鸟纹,同时总结了其主要分为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纹样两种的排列方式。
(三)蜀锦与丝路关系研究
基于大量蜀锦在西域地区的出土以及蜀锦在丝路上的货币职能与商品职能,蜀锦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愈见突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亦逐渐清晰,部分作者亦注意到此点。
王君平在其两篇文章《嫘祖开创的蚕丝文明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⑤王君平:《嫘祖开创的蚕丝文明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纺织科技进展》2015年第6期。、《丝路寻踪——蜀锦在丝路上的传播》⑥王君平:《丝路寻踪——蜀锦在丝路上的传播》,《经营管理者》2018年第6期。,对蜀锦出土文物、文书和文献记载给予总结,以此证明川蜀丝绸和蜀锦制品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传播、应用等诸多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同时注意到蜀锦与丝路关系的还有何一民,在其《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⑦何一民:《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与古代成都的三次崛起——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⑧何一民:《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与古代成都的三次崛起——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以及《天府之国与古丝路》⑨何一民.:《天府之国与古丝路》,《中国城市报》,2017年。三篇文章中,重点就新疆出土蜀锦以及丝路贸易中的蜀锦进行研究,并认为汉唐之际,巴蜀作为蜀锦的原产地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起支撑性作用,并且此观点尤其体现在第二篇文章的第二节“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以上两位学者对蜀锦与丝路的关系,就研究现状来看,是较为详细的。
当然,唐林所写《蜀锦与丝绸之路》①唐林:《蜀锦与丝绸之路》,《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与许新国所论《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②许新国:《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藏学学刊》第3辑,2007年。,虽都在论述蜀锦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但是其年代主要是汉晋以后,对汉晋时期涉及甚少,故在此不做详列。
小 结
综上浅述,学界关于汉晋时期蜀锦的研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学者数量较多,且有大量著述与论文予以专门讨论。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对蜀锦纹样、图案、组织及其与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方面有了更多认识,对蜀锦的认知日渐丰富与立体。但是仍然需要提及的是,就学术发展角度而言,其研究仍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前人研究蜀汉晋时期蜀锦,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蜀锦自身特点的研究,着重讨论了织造工艺、纹样变化、贸易往来以及其发展与传播等。二是针对新疆地区出土的汉晋织锦,研究蜀锦之于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及其文化内涵等。但不足之处在于,历史沿革研究虽时间跨度长,但汉晋时期涉及较少,大多涉及隋唐及其以后。部分论文就新疆出土汉晋蜀锦进行探索,但无系统性著作或论文对出土蜀锦特征予以总结。且受文献资料限制,蜀锦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大多关系隋唐及其后期,少有人论及汉晋时期蜀锦与丝路两者之间的关系。
蜀锦对于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蜀锦与丝绸之路关系角度,探讨汉晋时期蜀锦在西域的发展及其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与地位,将丰富学界以丝绸为焦点的丝绸之路研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