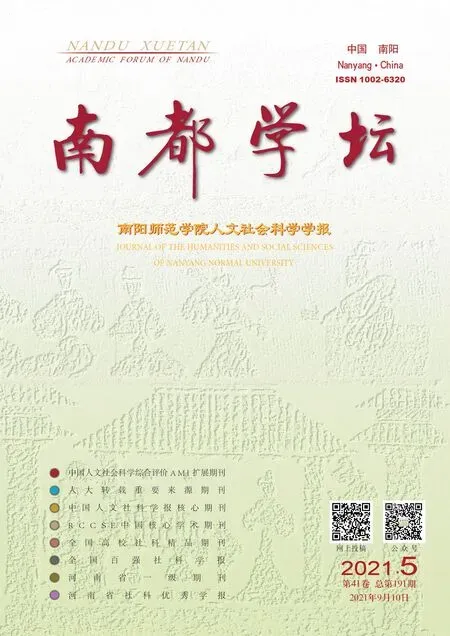阮章竞叙事诗论略
——兼及一种经验的留存
张立群, 夏玉芳
(1.山东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237;2.山东大学 实验小学,山东 青岛 266237)
阮章竞(1914—2000)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其诗歌创作数量大,涉及多个门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很难放在一起进行总体描述。在此前提下,本文主要围绕其叙事诗创作展开论述。
叙事诗是阮章竞诗歌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一种形式。闻名于世、奠定阮章竞文学史地位的《漳河水》便是一首叙事诗。结合已有的研究特别是诗集中的类型划分,阮章竞的叙事诗主要包括《圈套》《漳河水》《金色的海螺》《白云鄂博交响诗》四部代表作(1)关于这种提法,本文主要参考了刘守华的《艰难的探索——论阮章竞的叙事诗》,《长江学术》,2007年第2期。,此外还包括《柳叶儿青青》《草原风雪》《漫漫幽林路》《边关明月胡杨泪》等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2)余下的作品划分,主要结合《阮章竞诗选》中的归类,具体见诗选“目录”,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再者就是《漫漫幽林路》诗集勒口之“内容提要”。。阅读这些作品,可以了解阮章竞的文学之路,总结其叙事诗创作成就,为现代叙事诗创作获取宝贵的经验。
一、从“歌”与“曲”入诗开始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阮章竞的叙事诗可从写于1943年3月的《柳叶儿青青》谈起,而后是《圈套》(1947)和名篇《漳河水》(1949),再之后则是他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金色的海螺》(1955)、《白云鄂博交响诗》(1960)以及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漫漫幽林路》(1988)、《边关明月胡杨泪》(1988),如此长的创作跨度必然会涉及一种“历史的叙述”和相应的逻辑起点。为此,从“歌”与“曲”改编的角度介入阮章竞的叙事诗,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讲述方式。
回顾阮章竞的创作历史,尽管在1935年春夏漂泊上海时就开始了创作,但有意从事职业创作显然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后。1938年4月,“会搞文艺”的阮章竞被调至刚在晋城组建的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简称太行山剧团),任指导员,其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3)刘增杰:《漫长的诗歌之旅——阮章竞访谈录》,见刘增杰、王文金:《迟到的探询》,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值得指出的是,从1938年入太行山剧团、开始剧创作至1947年2月完成叙事诗《圈套》止,阮章竞创作基本使用笔名“洪荒”。。是年夏,因为工作需要,阮章竞开始学写剧本。抗日战争时期是阮章竞“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1]3。怀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创作热情,阮章竞不仅编写了大量的剧作,还尝试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比如,在1938年10月创作的三幕话剧《保卫抗日根据地》中,阮章竞就第一次采用了当地民歌《卖扁食》的曲调,填了一首《秋风曲》,获得成功,这是诗人保存下来的一首诗。“这次尝试的初步成功,使阮章竞开始对民歌发生了兴趣。”[2]205又如,在1940年9月于清漳河畔创作的短诗《牧羊儿》,则是话剧《和尚岭》的一个插曲,至于《柳叶儿青青》本就是一首适合演唱的长诗,它在后来被相继改编为歌剧和街头秧歌剧《比赛》,更证明了阮章竞的叙事诗与“曲”“歌”甚至是“剧”之间的“同源关系”。
叙事诗与“曲”“歌”之间的自由融合与转换,就结果来看是共同丰富了两种文体创作。当然,作为一个发展过程,从编剧逐渐走上诗歌道路也自有其相应的历史:在太行山剧团演出过程中,阮章竞同意演出的《上前线》和编导的《和尚岭》(两部剧演出的时间分别为1938年1月和1940年春,后均已遗失)等剧因“政治性不强”被下令停演[3],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写作者的积极性,阮章竞的创作由此从戏剧转向了诗歌[4]64。但作为一种传承,“曲”“歌”甚至是“剧”的经验被保留了下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阮章竞的诗歌创作。
正如一些研究者在文章中指出的:“在阮章竞从编剧走向诗人的创作道路上,《柳叶儿青青》这首叙事诗的创作过程尤其值得关注。”[5]《柳叶儿青青》作为阮章竞现存下来最早的叙事诗,从其整理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一些特别之处。1963年阮章竞曾两次回太行山,“好不容易才从一些同时代的老同志那里,找到几个残缺不全的油印本子和哼哼回忆起来的小演唱”。根据这些资料,阮章竞不仅整理出《秋风曲》《民兵之歌》《姜四娘》,还整理出了《柳叶儿青青》。“《柳叶儿青青》是一九四三年春以诗剧形式试写的一首演唱长诗,随后改编成小歌剧,更名《比赛》演出。这次我找到了一九四四年太行韬奋书店出版的这个小剧本。现在的《柳叶儿青青》就是根据一些上述的资料和参考《比赛》小剧本复原的。”[1]4叙事诗《柳叶儿青青》和歌剧、秧歌剧《比赛》是一个“底本”、多次创作,并可以在多年之后从“由诗到剧”还原为“由剧到诗”,恰恰说明二者之间可以融会贯通、具有不可分离的共性。
与《柳叶儿青青》相比,叙事诗《圈套》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圈套》是阮章竞使用民歌体创作的“第一首长诗”。对于《圈套》的体裁,诗人曾自注为“俚歌故事”。“俚歌”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本指福建莆田、仙游一带的以竹筒鼓和竹片伴奏的叙事体民间曲艺,其源头是宋代南戏。阮章竞“俚歌故事”中的“俚歌”泛指通俗歌谣,而“俚歌故事”也就是民间叙事歌谣。《圈套》最初发表在《文艺杂志》(太行)1947年第3卷第1期,由于其“通俗易懂,故事情节完整,发表后很受群众欢迎,特别是劳动妇女,很爱听这首诗”[2]22。其次,从《圈套》开始,诗人开始使用“阮章競”(诗人喜欢用“竞”的繁体字),这种被后来研究者称之为“似乎要告别‘洪荒时代’”[2]207的做法,与阮章竞真正步入诗歌创作历程是一致的,及至《漳河水》,阮章竞在民歌体诗歌创作上更加纯熟。《漳河水》是阮章竞行走太行之力作。这部作品是诗人听到当地妇女生产互助组歌唱自己翻身的歌谣有感而发,找人口述,记录下片段歌儿,自己又模仿着编了些,共同组合而成。“这些片片断断的歌儿,原无题名,也无章段和小题。因故事发生在漳河两岸,民间歌谣中常用头一句做题名,故名‘漳河水’。”同时,由于这首诗是由当地许多民间歌谣凑成的,如“开花调”“刮野鬼”“梧桐树”“绣荷包”“打寒蛩”“大将”“一铺滩滩杨树根”,还有好多失名的,故在当地牧童启发下,把这许多曲调总名叫“漳河小曲”(4)关于《漳河水》创作经历,本文依据《漳河水》“小序”(写于1949年除夕),阮章競:《漳河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4-45页。。
从“歌”“曲”到叙事诗,阮章竞经历了几乎所有现代诗人都未曾有过的创作转换。如果说剧作受挫预示着阮章竞诗歌道路的开始,那么,如何获取更好的宣传效果、写出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同时又乐于接受的作品,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是阮章竞自觉追求的创作方向。这一创作精神,在他于1943年春从报纸上学习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真正认识到了民歌的价值,自觉地向民歌形式‘靠拢’”[2]208,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经历连年的战乱,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可以拥有的文化物质条件都是有限的。“能直接看书的读者面是很小的。朗诵,群众不习惯,能唱的诗,倒是影响较快较广。”[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阮章竞汲取民歌资源,相继写出了《柳叶儿青青》《圈套》《漳河水》等作品,他的诗歌之路有着十分清晰的发展轨迹,同时也符合其自身的成长过程。所以,脱离具体的时代语境,是无法解释清楚阮章竞从“歌”“曲”到“诗”的不凡之旅的。
二、与时代“对话”:从“地域性”到“故事性”
既然民歌与谣曲成就了阮章竞的叙事诗,那么由此而得的自然是叙事诗本身具有的地域性与民间性的特质,这种通过语言、形式和叙述而呈现的诗歌特点,同样也会波及诗歌所要表达的故事本身。
从地域的角度总括阮章竞的叙事诗,其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北方故事。自1937年北上、奔赴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阮章竞一直辗转于北方并在此扎下生活之根。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在太行山生活了12个年头。在这12年里,他经历过战火和生死的考验,逐渐成长为革命文艺战士,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将太行山比成自己的“第二故乡”[6],所写作品《柳叶儿青青》《圈套》《漳河水》具有浓郁的太行地方色彩。1956年冬至1959年末,阮章竞一直在包钢工作,感受塞外风情、熟悉钢铁工业生活,在此基础上,他能够历经两年时间,“断断续续”创作完成《白云鄂博交响诗》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如果仅从诗人在不同环境生活过就得出其诗歌具有地域性的特征未免过于表面化。结合阮章竞的创作道路,观其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创作十分强调生活的真实和由此获得的真实感受。正如诗人晚年总结自己创作思想时所讲到的,“为了写好去新疆的诗”,70岁的阮章竞不顾朋友们的劝告,坚持攀登昆仑山,“没有实地考察,没有真实感受,怎么会写出来好的作品呢?”[2]22-23可以说,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文艺战士,始终将源于现实、取材于生活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他从不向壁虚构,始终强调真实的生活体验,人物和故事均有自己了解到的“底本”和“原型”,进而使其作品和现实生活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与生活真实相一致的是诗人在面向读者时始终追求一种艺术的真实。为了能够让广大群众接受和喜爱,阮章竞在获取创作题材时坚持深入群众、熟悉生活,在源于生活的过程中高于生活。他终生履行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强调歌颂人民群众是诗人的职责,这必然又强化了其作品的现实性和接受层面上的喜闻乐见,“诗不能离开时代,不能离开人民。写诗的时候,不是自己在伸手问天,而应看见人民,看他们在如何生活,想什么问题,想说什么话。我不管写什么诗,不管写得怎么样,总是多往这方面想”[7]39。在此前提下,阮章竞叙事诗呈现出的鲜明的地域风格,正是其思想观念、创作方式与当时所处时代生活环境反复“对话”的结果。
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贴近当地百姓的阅读习惯,阮章竞在太行山工作期间曾用笔记录下大量方言、歇后语等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并由此养成了一辈子学习积累的习惯,成就了他文学语言的风格。他曾在后来一篇回忆性文字中指出:“我是南方人,初到北方时,普通话说得很糟。听懂偏远山区的语言,并且使之用于写作,是花了很大的气力去学习和积累的。《漳河水》诗中的语言,除少量直接从民歌中抄录外,绝大多数是从群众的语言中取得原料加工提炼的。我只是利用了当地民歌的情调色彩,来反映太行山妇女群众的悲愁欢乐。”[7]37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写作,适应当地群众的阅读习惯,阮章竞以不断学习的方式改变了自己固有的语言习惯(阮章竞自幼讲的隆都话,是一种从闽南语演化而来的方言)[8],在交流和创作上融入太行地区的方言并达到娴熟的地步,这种为克服语言障碍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自然也强化了其作品的地域性。不仅如此,这种以“外来者”的身份学习本地方言的特殊经历,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其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可以破除习惯的限制,更加自由开放、灵活多变地表达。
无论怎样强调阮章竞叙事诗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特质,其核心都最终要落实到故事及其讲述之上。“一定要有故事性,没有就不成为文艺作品。同时故事要安排得合理得当。大概这就叫‘结构’。”(5)阮章竞文章《我怎样学习写作》,见《文汇报》1951年11月26、27、28日连载。阮章竞《我怎样学习写作》中的这段话,尤其适用于他的叙事诗创作。“故事性”不仅要求作品要有故事,还在客观上决定了作品必须有一套讲述故事的方法;而从更深的层次挖掘作品“故事性”的生成机制,那么,这个“故事”显然应当是符合特定时代精神、符合相应的政治文化标准,经过检验之后才能最终和读者见面。“中国的文学艺术革命、诗歌革命,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有重大的变动,那就是叙事的成分加多,加强……诗一般来说不擅长叙事,但是革命成果要求叙事,要求讲故事。因为革命要求我们把革命的故事讲透,把革命故事里的人物树起来,革命文艺的要求是这样的。”[9]不了解阮章竞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一批有代表性的叙事诗出现的文化背景,人们是很难真正理解阮章竞叙事诗的讲述方式以及故事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同时也很难深度把握其叙事诗相应于“时代”的艺术性和典型性。如果说《柳叶儿青青》通过懒汉大东子从一开始好吃懒做、不愿参加大生产运动,到经过思想的转变,下决心改掉以往的坏毛病,和老婆、孩子比赛,好好干活、争做劳动英雄,是为了鼓励大生产而写,承载的是解放区“旧人变新人”的故事,那么,在《圈套》中,诗人要表现的旨在揭露地主阶级反扑的“故事”则更加曲折复杂:黄河边上槐树台村财主“阎王”杨道怀以及狗腿子“催命小鬼”王玉枝、“马面判官”杨金带,为了实现“变天”的美梦,不断给农会主席李万开制造陷阱、设置圈套,最后,通过英娥娘报信、区长及时来村,才识破其阴谋、揪出幕后黑手,呈现了阮章竞对于现实生活中新“故事”、新主题的捕捉。与以上两个“故事”相比,倍受赞誉的《漳河水》通过多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书写了一首妇女解放的颂歌;写于当代的《金色的海螺》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其独特的现实性会在另一篇文章中单独介绍);《白云鄂博交响诗》将古老的神话传说和蒙古族几代人保卫建设草原的斗争结合起来,展现了我国钢铁基地建设过程中人民团结一心、波澜壮阔的画卷;《漫漫幽林路》《边关明月胡杨泪》则是通过坎坷的经历和反思历史再度揭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
纵观阮章竞叙事诗的写作道路,从早年配合革命斗争及时地书写现实生活,到后来越来越意识到人物是故事的灵魂,不断拓展叙事的厚度与广度,诗人已在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叙事原则;而逐步摆脱叙事诗中的非叙事成分,让其真正具有“故事性”,则充分表达了阮章竞在叙事诗上的艺术自觉。在此前提下,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故事本身,还有其具体讲述时运用的艺术手段。
三、多样化的艺术手法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具体地呈现阮章竞叙事诗的艺术手法,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介入,并在具体展开时以多层次、多维度的方式进行论说。
其一,是对民歌、戏曲及传统文学资源的借鉴、融合并化为我用。这一点在阮章竞的叙事诗特别是前三部即《柳叶儿青青》《圈套》《漳河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阮章竞在创作中融入民歌手法虽早已成为文学史的定论,但民歌所包含的内容何其多样。为此,如何恰当地使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我很早就试用小曲填词。但我有意识地自觉地大胆使用民歌形式,是始于头一首叙事诗《圈套》。《漳河水》的民歌曲调,在创作《赤叶河》时,已大量使用了……我写《漳河水》时,选择的几种最适合表达主题思想、人物感情的民歌结构,基本上是三七言、七七言式、七七五言式和七言四句式。这些结构形式,多是两句一韵和四句一韵,韵母要求比较自由宽广,近似则可,很便利于变化。七七言两句式的曲牌非常之多,如《平调》《太平调》《开花》《对花》《摇三摆》《刮野鬼》等等,是最常见的。[7]38
阮章竞《漫忆咿呀学语时》中的这段话表明诗人不仅熟悉大量流传于太行山的民歌曲牌、词曲结构,而且还能围绕主题恰当选用。显然,为了能够实现完整和谐地书写,诗人需要通过变化、改编以保持一种统一的格调。这其实对诗人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准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此时既要借助民歌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同时又不能给人以拼凑之感。
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诗歌的内容,阮章竞的叙事诗在汲取民歌营养的同时,也不忘借鉴传统文化资源如古典诗词、传统戏曲、民间说唱文学的养分。在《漳河水》中,“往日”“解放”“长青树”三部分每部开头都有首“部首诗”(可以理解为音乐的序曲),在全诗结束时,也同样有首“终曲”,“这是从《乐府》、古典诗中,从声乐曲和器乐曲中取得的启示”[7]36。这便是诗人借鉴传统文化资源的明证。同样,也正因为如此,茅盾在读过《漳河水》之后才会得出“《漳河水》有曲牌,能唱”[10]的结论;艾青在读后认为“有词的味道”[2]20。在运用民歌体写作过程中,阮章竞叙事诗最突出之处是使用了比兴手法。这种从《诗经》中诞生的传统表现手法既能够增强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性,同时也符合中国老百姓的阅读习惯,同样可作为阮章竞汲取民歌、古典诗词等资源并因地制宜、有效使用的一个方面。
其二,追求语言丰富的表现力、反复锤炼。阮章竞的叙事诗在汲取民歌和古典诗词养分的同时,既吸收了民歌的清新自然,同时又十分注意古典诗词的“简练典雅的句法”,语言含蓄精练。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童年喜欢绘画、青年时期投身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优势,在诗中常常融进音乐和绘画的元素,丰富诗歌的表现力。《漳河水》开篇处的《漳河小曲》便充分展示诗人在这方面的特点——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清晨天,云霞红艳艳,
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
漳水染成桃花片,
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在追求语言表现力的同时,阮章竞对于诗歌的字、句反复锤炼,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苛责的地步。他的诗是真正意义上的“锤诗”:“我的经验,写诗要把墨池当炉火,在这炉火里,首先要炼意,再要炼字,再要炼句。”[7]40从字到句,他讲求炼、磨、锤,一丝不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才能突破诗歌不擅长叙事的壁垒,在集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的同时,生动活泼、富于艺术的感染力,在阅读时很少给人留下枯燥、拖沓之感。
其三,讲求结构的完整多变,精心刻画人物形象。阮章竞的叙事诗符合中国故事的讲述模式,在时间上线性发展、有头有尾,在具体叙述形式上,为了避免多次重复,力求情节安排巧妙灵活、疏密相间。以《漳河水》为例:在整体上,三部分“往日”“解放”“长青树”,每部分前面都有“部首诗”,即第一部分的《漳河小曲》、第二部分的《自由歌》、第三部分的《漳河谣》,结尾有《牧羊小曲》,使整首诗结构完整、首尾照应。具体至每一部分,诗人的设计也极具匠心。代表解放区的第一部分“往日”,三个姑娘荷荷、苓苓、紫金英围聚在漳河沿边,互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并以哭诉相互补充,既集中揭示了诗歌主题,又避免分而叙述造成的冗长与分散。第二部分“解放”分述三个姑娘的故事,三线发展。对于荷荷,正面落笔,写其如何在斗争中获得幸福并成为生产小组的领导人;对于苓苓,先侧面着笔,带出她的丈夫二老怪和一场风波,进而写出“夜里训练班”;对于紫金英,则凸显其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在新社会到来时缺乏挣脱枷锁的勇气的情感变化,在姐妹们的鼓励下,她逐步走向新生。第三部分“长青树”,集中写在大家的教育下,满脑子旧思想的二老怪的转变,预示着妇女解放的日子真正来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妇女悲惨故事何止千万,其思想转变、翻身做主恐也非一帆风顺,但诗人却以这样总分式的结构集中讲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故事,整首诗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洋溢着时代精神,这不能不归功于结构形式的精心设计。
与结构相比,诗人在刻画人物时注意对性格的凸显、精神的开掘。首先,诗人总是通过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表现人物。在《漳河水》第二部分“解放”中,阮章竞在描写苓苓和传统封建、有大男子主义作风的二老怪的对话时,相继用了“抿嘴微微笑”“回答慢吞吞”“嗤嗤两声钻进被窝,露出半个头来轻轻说”等动作描写,这些动作及相应的语言内容揭示了苓苓聪明机智、善于处理矛盾的性格特点。其他如荷荷的泼辣、勇敢、干练,紫金英的软弱、自卑,都是通过诗人多角度描写展现的。其次,是成功融入了心理描写。在第二部分“解放”中,描写“苓苓”这段,初写二老怪时,诗人就运用了心理描写,反复强调苓苓的进步行为在二老怪看来是坏了规矩,二老怪的封建大男子主义思想也由此表现出来;再如嫁给个痨病鬼的紫金英,男人死后带着娃,之后她曾与一个二流子厮混,但在姐妹们的帮助下,她最终走向了新生。为了细腻刻画她的形象,阮章竞就多次使用心理描写,而这种手法也确实适用于表现紫金英复杂多变的内心。
其四,调动恰当的艺术手段,丰富故事的表现力。除上述提到的手法外,阮章竞还多在叙事诗中使用对比手法,进而与故事的多线条讲述和时代、人物的新旧转变相呼应。还有使用比兴手法,利用环境描写,衬托人物形象和故事氛围。谈及环境描写、渲染气氛,不能不讲到《白云鄂博交响诗》。这个以塞外为地域背景的故事,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因此开篇的环境描写粗犷雄浑,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风格。这种描写既适合表现人物形象,也极易和作品的主旋律结合在一起,使诗歌充满了力量美。
以上四方面特点虽在归纳总结时分出若干层次,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它们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采用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法,阮章竞的叙事诗自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在多年之后仍会获得“将人物多重对照以及总分结合的戏剧模式融合进去,则显然是阮章竞本人的贡献”[4]89的评价。客观地看,在多种手法的共同作用下,阮章竞的创作确实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叙事诗的超越。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经验与资源,这些取得突出成绩的实践还会以历史化的方式闪现于之后的创作中,阮章竞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漫漫幽林路》正是在继承上述经验后完成的又一部力作,而其注入某些新的艺术元素则可作为诗人叙事诗创作道路上的扬弃与拓展!
四、叙事之再思
尽管阮章竞的叙事诗在总体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就其发展道路而言,却并非一帆风顺。从已有的评价阮章竞叙事诗创作的文章特别是诗人自述性文字中可以看到:围绕某些具体的作品曾产生不同程度的争议,而回顾这些争议,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阮章竞叙事诗的认识,而且也会为现代叙事诗的创作提供某些有益的经验。
在《漳河水》正文前的“小序”中,阮章竞曾写道:“写‘圈套’用了‘俚歌故事’四个字,曾引起个别同志的不同意,这回如果名不正,就更言不顺了。”这个“不同意”涉及的是对诗与歌以及剧的不同理解。在后来发表的、写于1963年1月给刘守华的信中,我们则能读出当时诗人许多不为人知的看法——
《圈套》是“俚歌故事”不是诗。当时在农村,特别是妇女喜听,就算愿望与效果统一了。近年来,有些论者对它感到缺抒情,我从不计较。……
《漳河水》,说得过多了。同样它不算诗,小序中已早公开宣告是小曲。[11]163
阮章竞所言的“有些论者”,当指丁力发表于《诗刊》1959年第2期的《谈阮章竞的叙事诗》,在这篇文章中,丁力写有“这首长诗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它的缺点是:一、单纯叙说故事,没有什么抒情。叙事诗虽然也允许单纯叙事,也有单纯叙事而叙得很好的;但我总觉得叙事的长诗,最好能带有抒情成分,能催动读者的感情,激起共鸣。如果单纯叙说故事,不带一点抒情味道,就会干巴巴的,难于见佳。二、在语言运用上,还嫌有些粗糙,没有经过很好的提炼和加工,好像顺口溜出来的,有的是诗,有的就不一定是诗了,因此,有些地方显得不够精美,诗意不浓。这两个缺点,在诗人以后的叙事长诗中,得到克服”[12]。此外,在给刘守华的信中,阮章竞还提到《白云鄂博交响诗》“惹下麻烦”[11]163;而在刘守华的评论文章中,则指出:“这部长诗曾引起广泛的争议,也是阮章竞在叙事诗创作上最为艰苦的一次探索”,至于为何“争议”、如何“艰苦”,从刘守华的文章中大略可以看到一些原因,诗篇“在豪壮表层之下显得内容贫弱无力”,有些人物“站立不起来”,“诗句也有缺乏锤炼的地方”,明显受“大跃进”时期诗风的影响[13]……这些看法与观点从侧面揭示了围绕阮章竞叙事诗创作与评价,还有很多曲折的“故事”。
对照1985年出版的《阮章竞诗选》,将《圈套》《漳河水》列为叙事诗,我们不难读出诗人在信中的话有些意气成分,同时,从评论者的角度,坦言自己的观点,见仁见智,也属于批评的正常现象。所以,围绕阮章竞叙事诗而产生的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双方对于叙事诗本身、具体写作以及写作时代性理解存在某些差异。当然,从阮章竞叙事诗发展轨迹来看,围绕《圈套》是诗还是“俚歌故事”的不同看法还是促进了他的写作。《漳河水》声情并茂,集叙事、抒情、描写为一体,曾被舒乙评价为“现在纵观这个时期的作品,可以说阮章竞的 《漳河水》是最好的一部”[14]14。显然阮章竞是对以往写作经验进行了总结才实现了艺术上的超越的。
结合一些研究者的看法,叙事诗的特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它要表现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变化,交代人物的行为和动作;二、它对“行为”的描述,总是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三、它对“行为”的描述,总要受到诗歌节奏、韵律和意向性句法结构、修辞规则的制约。[15]
叙事诗作为诗歌的一种,可以抒情也应当抒情,但这一判断显然要建立在具体文本上并和对“抒情”理解的历史化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仅从抒情的角度去评价叙事诗这一种长于叙事的诗歌形式,肯定会使后者“暴露”出很多问题。而当我们判定《漳河水》是一部优秀之作的时候,它肯定也在整体上解决了叙事和抒情之间的“固有张力”,并给读者带去了全方位的艺术美感。因此,叙事诗如何抒情、怎样抒情就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还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评价的问题。
与叙事诗的抒情问题相比,围绕阮章竞《圈套》《漳河水》及至《白云鄂博交响诗》的评价,还涉及诗与民歌的问题。从中国诗歌发展历程来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的诗歌概念正不断遭至解构。“诗”与“歌”分离并日益成为两个文类,其实是削弱了诗的音乐性并对现代诗创作提出了一道难题。在此前提下,诗与民歌之间虽从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且一直有许多有识之士期待从民歌中为现代诗找到更多的出路,并涌现了刘半农《扬鞭集》《瓦釜集》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耳熟能详的作品,但诗与民歌在进一步划分后毕竟已属于两个范畴:民歌可以当作诗,但毕竟不是诗;广义的诗可以包括民歌,但还有其他具体的形式。在现代出版和文字阅读成为现代阶段以来文学最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接受途径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更加复杂了,因此,民歌如何入诗同样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一方面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文化语境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歌体叙事诗的诞生,造就了《漳河水》诗与民歌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在文学创作风格渐渐趋同之余,涌现了这样优美的、温暖的作品,它“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与民生相关的温暖、对小人物命运的关照,恰巧应是关于那个伟大时代的喜悦、激情、赞美与拥护中最具说服力的表达方式”[16]。脱离具体语境去评价《漳河水》一类作品的合理性和艺术性,无助于客观评价民歌入诗的问题,同时也不能更好地审视新诗的资源和形式问题。何况,从阮章竞后来的叙事诗以及系列诗作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到,民歌的元素虽不时闪烁其间,但已不再是主要表现方式,“民歌体也不是写什么都是合适的。从我的实践看,写现代工业,写政治诗,我不得不另辟蹊径,探索古典诗与民歌结合的道路,往新诗民族化的方向做番尝试。适应反映现代生活,新诗仍然是主要的,但它应该民族化”[7]39。这说明相对于个体而言民歌入诗也是一个辩证的问题,需要客观、公正地看待。
总之,叙事诗在阮章竞整体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它,阮章竞既为现代叙事诗创作奉献了经典之作、拓展了叙事诗的表现空间,又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而重审其叙事诗创作,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知阮章竞的文学道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获得启示的同时,推进现代叙事诗的研究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