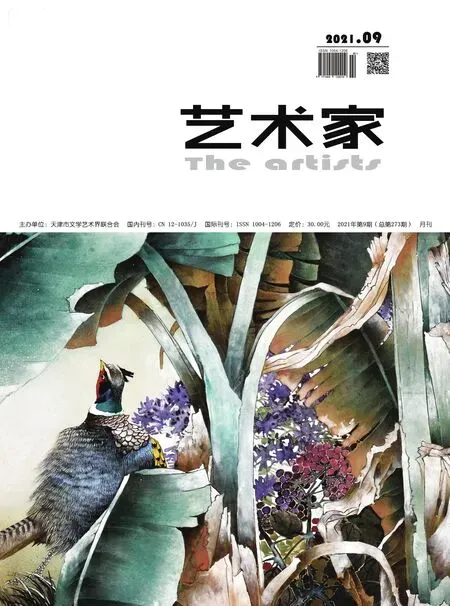别样乡愁
——白先勇小说离散书写研究
□沈 燕 吴 娟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离散与乡愁
“离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分散不能团聚(多指亲属)”,也可指人的地域性迁徙,在英文中写作diaspora,可译为散居。童明认为“这个词长期与犹太民族散布世界各地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增添了在家园以外生活而又不割断与家园文化种种联系的含义”[1]。在文学作品中,离散书写一般指的是因主动或被动原因离开地域或文化母体,在异地和异质文化中保留对精神故土和母体文化的无尽怀念之情。文学作品中的离散群体多存在身份认同的困境,游走在异地和原乡的精神夹缝之中。
“乡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指的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们一直固守着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行、叶落归根等思想,“家园”除了现实的生活效用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意义。当人们背井离乡,对故土眷恋的情感便油然而生。“乡愁是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冲突的结果,是人生旅途中的心灵诉求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情感与感想”。而在离散文学中,乡愁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它并不特指地域范畴离散下对故土的情感眷恋,而是扩展到在地域情境下的族群、文化、精神等各个层面。简单而言,这种乡愁指的是精神原乡的失落。
白先勇个人的地域性离散经验奠定了其离散文学写作的情感基础,桂林、上海、重庆、南京、香港、台北、纽约等地的生活辗转,让他遍尝人生流转的百般滋味。个人情感经验的独特性再加上其生活的多地流转,也为其提供了离散书写的情感基础。本文借助白先勇的几篇小说,通过其对人性的观照来分析作品主人公精神层面的离散状态,他们一般都是被家庭、社会彻底抛弃,但也不乏主动离开主流社会,生活于城市的边缘人,可以称之为自我放逐。在这种主动和被动的放逐背后,恰恰包蕴着他们找寻精神原乡的痛苦和努力,其中包含着人物本身的身份认同问题和传统的父权社会下是否允许异质存在的问题。相应的,对白先勇作品离散现象的关注,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传统文化的契机。
二、情感离散下的别样乡愁
白先勇出生于大家庭,父亲是军中高级将领,母亲也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家庭生活优渥,童年因其身体原因,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隔离独居生活,每日只能与花草和小动物为伍,这让他的性格由热烈外向转为敏感内向,第一次在心底产生被人遗弃的感觉。后来因为时局变化、家庭变故,他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目睹人事变幻得那般迅速,令我产生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2]。而这种对人生无法言说的寂寞和孤独感直接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他小说写作的基调。
(一)对家园的找寻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很多主人公都是被家庭放逐的边缘人,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他们命运的同情,同时也向读者传达了他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寂寞的十七岁》是他早期的作品,发表于1961 年,讲述了十七岁的杨云峰放逐自我的故事。在家庭生活中,杨云峰无疑处于边缘状态,上面有两个成绩优异的哥哥,下面有一个每年都考第一的小弟,而他自己则“念个私立学校还差点毕不得业”,让他的父亲觉得“我连脸都没地方放”。在学校生活中,他总是独来独往,找不到玩伴。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他缺失了来自同伴和家人的情感关怀,处于一种情感被动离散的状态。但在杨云峰内心,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可能比任何人都来得热切,他渴望一个可以真正走进他内心的人,所以他才会在魏伯飏送他回家之后整天跟他磨缠在一起,尽己所能地报答魏伯飏,所有在现实生活中的帮助其实都是他内心精神回报魏伯飏的外化表现。他没有选择对他主动示好的唐爱丽,而是将自己的满腔热忱都献给了魏伯飏,这何尝不是他在被家人放逐后想要努力寻找精神家园的表现呢?白先勇说过他很同情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杨云峰无疑是一个情感离散的悲剧,在感受到被家人和朋友抛弃之后,他跑去了新公园,再一次踏上寻找精神家园之路。在这篇小说里,虽然没有地域性的离散,但精神的原乡对杨云峰而言早已散失,他一次次的努力都表现了他对精神原乡的执着和怀念。
(二)对父亲的找寻
在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慈爱、厚道的人,律己甚严,在教育子女方面同样很严格,他对待下属则体恤宽容,不允许对下人有不公平的对待。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既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人物,又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长辈。白先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就是对传统文化中父子关系的展现,并由此引申到“中国的父权中心社会以及父子——不只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父亲已经不单纯指家庭血缘关系上的父亲,而更多的是父权社会的代言。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人际的伦常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为不可改变的常道,并且通过社会统治强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白先勇称《孽子》为孩子们的寻父记,“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伊甸园,在乐园之外流浪,沦落为娼。但他们并不放弃,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找父亲,找自己……”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台北的新公园,主人公李青被学校开除之后遭到父亲暴风骤雨式的痛骂,最终以被赶出家门宣告父子关系的终结。“老鼠”则因为幼年丧父,长期寄住在哥哥家,受到传统观念“长兄如父”的影响,宁愿忍受屈辱和虐待也不离开,但最终仍避免不了被赶出家门的命运。小玉生来不知道父亲是谁,他的一生就是寻父的一生,但他寻的是血缘关系上的父亲,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父亲的存在,不得而知。在新公园的乐园里,他们隐去了彼此的伤心过往,任自己的灵魂被放逐。这是一群在情感上经历着离散的“青春鸟”,他们渴望来自父亲的关爱和接纳,但作为传统父权社会的代言,他们情感上对父亲的渴望是被压抑的,所以他们只能在乐园里寻求一个新的“精神之父”,以此寄托内心对父亲的情感。在这里,父亲就是原乡,原乡就是父亲,“青春鸟”的乡愁就是对父亲的渴望,这一渴望驱使着他们一次次走上寻父之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孽子》中的父子冲突也反映了被社会放逐的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危机,表达了对社会伦理、父权社会等方面的关注。在这些人物身上,他们的人性被压抑,而只有在新公园他们才能短暂展露最真实的情感渴求,白先勇通过对他们离散经验的书写,表达了对人性最基础的情感状态的关注。
(三)对自我的找寻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思考,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中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道出了人类永远无法认知自己的真谛。白先勇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让他在写作中常常关注人的困境和苦处,“我写的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地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分尊严?在我的小说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
《青春》中的老画家竭尽全力想要抓住的看似是他已逝去的青春年华,实则是曾经的自我。他怀念年轻的岁月,渴慕少年匀称的肌肉和结实的身材,他无法接受布满皱纹和白发丛生的自己,但这一切只是他艺术生命消逝的证明,他所有的努力只是想要挽回那个曾经富有艺术生命力的自己。他只是错误地将生命的青春和艺术的青春混为一谈,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徒劳的追寻恰恰印证了他自我认知的困境。《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是白先勇小说中寻找真实自我的代表作,作品发表于1969 年。小说主人公教主朱焰曾经是30 年代上海明星公司的明星,红遍了半边天,但随着默片时代的结束,朱焰的艺术生命宣告结束。但他并没有在内心宣布“照片小生朱焰”的死亡,而是一次次执着地找寻着他艺术生命的替代者,从“骑着白马,穿着水绿的丝绸袍子”的白马公子姜青,到长得标致的男学生,再到最后面庞异样姣好的小玉,这些年轻人何尝不是朱焰心里另一个自我呢?朱焰的精神原乡应是舞台上那个光彩熠熠的唐伯虎,虽然现实一次次告诉他今时不同往日,但他依旧执着。作品看似讲述了一个过气男明星的故事,不如说是在表达作者对人性的关注,“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人生困境围绕着白先勇的一生,在无常的人生变动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身份认同危机下如何找寻到精神的家园,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结语
1952 年,白先勇从香港来到台北与家人团聚,对他而言,台北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在此之前,他的生活一直在经历着“背井离乡”,虽然出生于桂林,但在上海、重庆、南京、香港等地的辗转生活早已让他不知故乡所在。与其说他的乡愁是对某一地的思念,不如说是一种对精神原乡的渴望,在一次次离开后,家园早已成了幻影。不难发现,白先勇的小说中很多提到了台北的新公园,新公园里有撩人的景色,睡莲、棕榈、大王椰,处处散发着热烈的气息,当夜色来临时,新公园就成了很多人的庇护所。相较于台北而言,新公园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它接纳了一群丧失精神家园的游子的孤独、漂泊、放逐,提供了游子情感的栖居地。同为社会上的人,很多人背负着艰难的命运,承受着生命不该承受之重,白先勇自身的生存境遇给他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对他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身份的失落恐怕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困境,但纵使一次次遭到放逐,他们依然在寻找精神原乡的路上孜孜以求。因为体验过这份漂泊孤苦,白先勇才能构建出新公园,并将此作为游子们别样乡愁的寄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