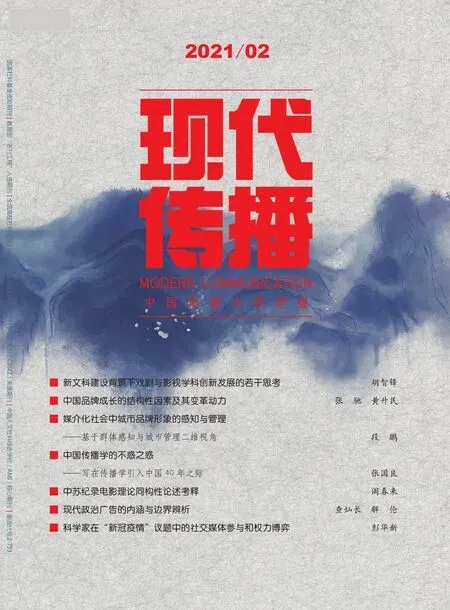科学家在“新冠疫情”议题中的社交媒体参与和权力博弈*
■ 彭华新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背景
(一)科学与权力的关系研究
历史上的科学权力几经浮沉。文艺复兴后,科学成为一股思潮,击败了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知识就是力量”正是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强调系统的归纳逻辑和实验对认识的作用。随后的17—18世纪,启蒙运动给西方社会打上了“理性崇拜”的烙印,开展了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科学观发生了两次转向,即从追求实证的逻辑主义转向追求价值取向的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转向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在此过程中,对科学权力的批判从未停止,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认为“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①,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变成了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②。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每一种自然观都部分地来自于科学观察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③,他们将科学看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工程,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嵌入符合统治利益而精心设计的社会机体内部。在所有的后现代科学观持有者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cault)的研究独树一帜,通过对监狱、疯人院等空间的分析,展开对微观权力的思考,总结起来,即:“人类科学生产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个层次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与它们被用以约束和规范个人的方式息息相关”④。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承继并发展了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的谱系,关注更为微观的实验室的科学生产,并将建制化的实验室与权力进行了关联,进而研究其对社会的规训作用,“为了理解科学知识,我们需要对技能和实践性的能知(know-how)作出正面的描述,它们建构了现象并使之稳定化,从而使科学家能够以见多识广的方式来介入并操作它们。只有在这样的技能和实践中,知识和权力才相遇。”⑤这些研究为笔者观察科学家的知识与权力关系提供了理论背景。
(二)科学家的媒介传播和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传播
20世纪末开始至今,随着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医学技术的井喷式发展,科学越来越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导致了科学理性价值重新回归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西湖大学讲席教授许田甚至将生物科技遇上人工智能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科技革命”⑥。出于对自身环境的担忧和对新型设施的使用,人们的日常对话也开始触及科学概念和科学原理。归纳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可发现,其对所谓“科学沙文主义”的批判依据之一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合谋”,形成一套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独特话语,成为一种上层建筑式的自我封闭模式。因此,科学概念、科学原理是否能进入非专业人士的日常对话,是“科学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2000年以后,《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与社会》两部报告先后引入中国,对国内的科学传播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有学者在这两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传媒与科学界的关系不容乐观”⑦,二者对对方的运作逻辑和话语方式互不了解。刘华杰曾提出科学传播的三阶段,即“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有反思的(reflective)科学传播”⑧。根据这一分类,传统科普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心模式,居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一种知识不对等的缺失模式,居于科学共同体立场,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是一种对话模式,具有公民立场。这种分层方法为社交媒体中不同话语主体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定位。
作为科学家的对应关系,公众的科学素养早在1983年被提出来,即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hn D.Miller提出的评估公众科学素养的“Miller体系”,可总结为三点,即“1.具有科学术语和概念的语汇;2.对科学过程的理解;3.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意识”⑨。刘兵认为科学传播是“动态反馈系统”的研究,其主体结构包括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之间的动态反馈,因此,科学传播“必须与传播机制及传播活动结合在一起”。⑩基于这一点理解,科学传播的偏差将对整个社会系统造成灾难,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培罗(Charles Perrow)认为,“科学技术曾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但现在却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这一理论契合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多方互动的“动态反馈系统”是本文原始材料搜集和遴选的依据。
(三)疫情的传播学研究
本文试图从2020年“新冠疫情”网络传播中观察科学家的话语动态,因此,传播学领域疫情研究的前期成果对本文有借鉴意义,其中,在时间跨度上最近的案例即为2003年的SARS事件。一部分学者结合疫情传播与社会危机开展研究,如夏倩芳观察了2003年“SARS危机”的媒介传播,认为这次危机“引发了对于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公众知晓权问题的关注。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环境下,给予媒体独立运作空间,将媒体运作纳入政府科学的公共管理大系统中,以减少公共管理成本支出,提高管理效益是问题的关键”;一部分学者结合疫情传播与媒介功能来开展研究,如孙旭培通过研究SARS报道和禽流感报道,分析比较了媒体负面信息的封锁理念和疏导理念,认为“实践证明,传媒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能够避免社会恐慌、化害为利”;一部分学者则从科学传播角度分析了疫情的社会影响,如尹韵公反思了SARS时期“医学界内部对SARS病原的不同认识和争论,以及这场争论对新闻传播产生的影响”。综观关于SARS的传播学研究发现,该事件中科学家在媒介中的存在感很低,科学家更没有主动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二、“科学家”在“新冠疫情”中的概念范畴与问题提出
笔者在前期观察中发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2—3月)的网络传播中,科学家的参与度和显示度均高于往年疫情事件,包括科学家亮相政府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科学家群体作为“共同体”形成自媒体平台,以及公众对科学家的评论,从这种网络互动中,建构不同的话语主体关系。
(一)“科学家”在“新冠疫情”中的概念范畴
“科学家”概念出现于技术迅猛发展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1834年,英国哲学家威廉·惠威尔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首创了‘scientist’这一名词,”此后“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也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特别是政府或社会机构建立各类实验室之后,科学家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也成为现实。1949年以后,“科学家”在中国承载振兴民族的使命,因而被赋予了无私奉献等价值理性,但随着大型高科技公司纷纷组建实验室,非建制层面的科学家逐渐增多,工具理性抬头,他们的研发产品也由宏大叙事的国家事业入侵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来。本文所研究的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大学理工科教授、医院具有科研能力和科研背景的高级专家、医药公司等企业具有科研能力和科研背景的高级专家等。本文择取的文本参与者包括:科学共同体(上述的科学家、在读理工科博士生、科研机构的官方自媒体)、媒体(媒体机构的官方社交账号、知名媒体人和科技专业记者的个人社交账号)、公众(作家、大学文科教授、公务员、普通公民、社会评论家的个人社交账号)。对2020年2—3月社交媒体(以微博为主,同时包括微信、知乎、凯迪社区)中关于“新冠疫情”海量文本的分析发现,以上类型的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中的显示度较高,以上类型的文本参与者的影响力也较高,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的对话形成权力博弈关系,形成对峙格局的话语主体。
(二)问题的提出
对前期文本的初步观察发现,“新冠疫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家的价值理性(道德人格)和工具理性(专业能力)造成了一定的挑战,公众对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中的呈现有褒有贬,而非一致的专业崇拜和迷信,甚至导致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科学权力体系受到质疑。依据对原始材料的梳理和概念提升,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研究:第一,“新冠疫情”中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中身份关系如何?与其他主体间的话语内容是什么?即科学家的媒介呈现问题,以及如何将这一问题进行框架化。第二,科学家在上述媒介中有怎样的互动行为和权力关系?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分析,更系统化、理论化地验证初步观察。第三,如何使科学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获专业权威性,并更好地服务于信息沟通、谣言控制、民意疏导?依据媒介呈现和权力关系的现状描写,在结论部分进行延伸性思考,并从应然层面发现权力秩序的重建。
三、“新冠疫情”中科学家的媒介呈现:身份与内容
在2020年2—3月期间发表于微博、微信朋友圈、知乎等社交媒体的疫情话题中,很多账号以科学家(专家、医生、技术官员等)的身份参与了讨论。围绕这些账号形成了讨论疫情科学议题的话语主体关系网,即相关的文本参与者,结合前期的理论设定与经验材料梳理,本研究为文本参与者建构起“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的身份框架,试图从这一框架中观察科学知识向公众渗透和反馈的身份介质,或由科学共同体直接在社交媒体中完成,或通过传统媒体间接完成,公众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反馈。
(一)科学家在媒介呈现中的身份框架
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无法孤立地履行自己的天职。在制度的框架当中,他必得占有一个确定的地位。化学家会成为化学专家中的一员;动物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每个人,都属于专业化了的科学家之特定的集团。这些科学家的不同集团,就形成了科学团体(scientific community)。”在“新冠疫情”初期的经验材料搜集中,社交媒体中的科学共同体可以归纳为三类:(1)著名科学家,如微博中的@饶毅(生物学家)、@鲁白(神经学家),两位科学家共同创办@知识分子,并在该平台呈常态性地发表科普文章。(2)在读理工科博士生,如微博、抖音、B站等众多社交媒体中的@毕导THU,实名毕啸天,清华大学博士生,在自媒体中给自己的定义为“一个爱开脑洞的科学段子手”。(3)科研机构,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网易号等社交媒体中的@中科院之声——中科院的官方自媒体,在各类平台中的简介为“我们邀您一起,以科学的眼光看世界,以全球的思维论科学”。以上三类属于主动利用社交媒体参与科学传播的参与者,自主注册自媒体账号发表意见和互动交流,这是此次疫情的重要特点。但是也有一类被动参与者,即科学家无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但被动接受媒体参访之后,由媒体或公众将采访观点转发至社交媒体。
媒体在科学话题中有特殊的地位,在本文的经验材料中,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1)科学专业类媒体,如在此次事件中较为活跃的《生命时报》(包括微博@生命时报)的记者邸利会,具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教育背景,专门从事科技报道。(2)非科学专业类媒体,如@评论员曹林(《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曹林)、@侠客岛(《人民日报》海外版账号)、@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账号)、@瞭望智库(新华社批准成立、立足于国情国策研究机构的微信公众号)等在此次事件中,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进行了观察和评论。
公众是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传播对象,也是构建科学家形象的话语主体,在此次疫情中,几乎所有的社会身份均参与进来,相较于科学共同体,他们不具备理工科的知识背景,相较于媒体,他们缺乏对新闻规律与传播伦理的基本把握,因而形成了不同于前二者的鲜明特征。一些公众参与的原始材料显现,公众的话语权分层很明显,例如,作家、公务员、律师、文科教授等粉丝量大、原创作品发布量大、被转发和被评论数量大的参与者与科学家具备较为平等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赋予了他们“对话权”,他们在评论科学家议题时更具有可信度,从而能起到定义社会事件性质和牵引舆论导向的作用。在此次疫情前期影响力较大的有@段郎说事(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十年砍柴(历史作家、头条文章作者)、@五岳散人(自由撰稿人)等,其发布的微博文本的评论量均达到10000条以上,并在当时形成了与科学家相关的议程。相反,粉丝量小、原创作品发布量小的普通参与者不具备相应的话语权,其影响力在于以“量大”为优势在评论区造势。
(二)科学家在媒体呈现中的内容框架
1.“确定”与“不确定”
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认知过程,科学家传递的信息永远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补充和纠正的,有可能被后续的研究所推翻。但是,在科学传播中,“不确定性”却为科学家的权威性打了折扣,“在科学家看来,公众不了解科学,不确定性是科学的一个正常也是必需的特征,也是科学的魅力所在,是可控制的。公众则认为,不确定性削弱了科学的权威性,科学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不应由公众承担。”在“新冠疫情”中,不确定性成为公众挑衅科学家的依据,“确定”与“不确定”也在“谣言”与“辟谣”之间摇摆,比如事发初期科学家发布病毒“人不传人”和“可防可控”、“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等言论,最后遭遇公众质疑。在病源方面,“新冠肺炎”的传播过程一直充满“不确定”,由最开始的“蝙蝠病源论”,到后来的“穿山甲病源论”,不同的研究结论致使科学传播的话语呈现无序状态,但始终无法得到广泛认同,导致公众无法在信息获取中消除恐慌感。例如,@知乎(知乎官方微博)对几种动物病原论进行了推测:
@知乎:华南农业大学发现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相对来说,动物越接近,病毒越共享,哺乳动物穿山甲要比之前猜测的蛇靠谱。当然,真正确认还需要更加真实的证据,比如那些染病者到底有没有接触穿山甲。
在不确定性造成的恐惧感中,公众开展了针对专业性的质疑。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也着手反击,比如徐旭东(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在微信公众号“中科院之声”上发表的文章《大疫当前,岂能围殴科学家》,正面质疑了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科学素养:
自媒体成分复杂,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但是某些官媒也参与嘲讽科学家。只想弱弱地问一句:是不是忘了自己正是需要补足科学素养的关键人群……多家媒体深夜以“有药了!”开头的标题发布这一新闻,导致民众误解,造成双黄连口服液迅即被哄抢。次日,媒体采访的药物专家和临床医生可不认这个账:这个哪能叫药?按照药物研发的程序这个只是第一步,临床肯定拒绝使用。……甚至有媒体对中科院药物所开展训诫,好像他们比院士更懂药物研发程序。以我个人经验,这个“有药了”的标题应该是媒体添加的,而不是科学家的手笔,但是围殴之时,矛头对准的是科学家。
在这一案例中,科学共同体与传统媒体(代表官方)和自媒体(代表公众)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科学共同体并不认为药物专家的言论代表了双黄连研发的“不确定”,仅仅是表达了研发程序的开端,并非结论,也非药物成品。但是,公众在质疑真相时则跳过了媒体环节,直接将“有药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归结为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指出了不同科研机构或不同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自相矛盾,有的甚至违背常理。
2.“科普”与“反科普”
科学共同体在批评公众的科学素养时,也在建设性地开展科普工作,除了普及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性科学知识,还主动传播人类灾难中的科学史、科学实验史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在公众对新冠肺炎的传播感到焦虑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几位科学家(牟庆璇、仲萌萌、陈柯宇)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中科院之声”发表了《应对新冠肺炎,我们可以从鼠疫浩劫中学到什么?》一文,介绍了人类历史上鼠疫的三次浩劫和治鼠疫的科学方法,其内容并非学术探讨或理论研究,而是以平易近人和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科学历史,向公众普及了防范知识,控制了恐慌扩散。
科普不仅与内容有关,而且与修辞有关。@新京报“我们视频”发表文字《专家称粪口传播就是“吃别人屎”》:“当事医生刘玉萍告诉记者,‘粪口传播就是你吃了别人屎’只是一个比喻,意在告诉人们勤洗手对防控肺炎疫情传播的重要性,科普就是要通俗易懂,没想到视频会被人断章取义传播。”但是,对这种“通俗易懂”的科普方式,公众的观点存在分歧,比如一些网民在评论区写道:
@晨风拂林:那叫“通俗易懂”吗?那叫粗俗,俗鄙。
@纯属虚构alex:说的正式官方点,又批人家打官腔,说的接地气点又嫌人家没文化。
@幻觉欢笑声:话糙理不糙,专业用语你们又听不懂。
四、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中的互动行为与权力博弈
作为知识权力的拥有者,科学家与媒体、公众之间的隔阂一直存在,他们掌握的知识领域和阐释技术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训练方能获取,因而并不在普通媒体和公众的认知范畴内。这带来了两个相反的后果,其一,造成了科学家自说自话与不被理解的被动境地,其二,这种“不可沟通性”又塑造了科学家的技术霸权与话语垄断。如前文所言,科学家在此次疫情中,主动或被动地利用社交媒体参与科学传播,这种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家的知识话语权在公众中的实现。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帮助中国科学家绕过传统媒体,吸引更多的观众,更容易实现各种回报,并有助于他们摆脱所在机构不合时宜的宣传模式。”这种情况突破了科学家指向媒体和公众单向传播模式,即公众缺乏科学素养而导致不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甚至,从此次疫情的社交媒体传播来看,科学家与媒体、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些研究者所说的“共生模型”(co-production),协商完成了知识生产过程,共同强化了科学家的专业权威和职业话语垄断。结合经验材料与上文的参与者身份框架,可以观察到“共生模型”中的权力实现:
(一)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互动行为与权力博弈
1.协商式互动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在对话中达成知识共识和情感共鸣,在本文的经验材料搜集中可以发现,一些科学家(专家、医生、研究人员、理工科博士生)在社交媒体中是有一定粉丝量的,科学家通过社交媒体来说服公众,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公民通过社交媒体来表达对科学家的认同。如疫情爆发初期,@毕导THU(理工科博士生)在微博上发布视频进行科普:
最近宅在家里看了关于新冠病毒的几乎所有学术论文,有个一百来篇。这期就给大家讲个文献综述吧,看看科学家对新冠病毒都研究出来了些啥。看完后也许我们会更能理解,实验室,同样是科学家拯救生命的战场。
该条微博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维护了科学家防治“新冠肺炎”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大部分的网民评论也支持这一观点,如有网友评论“这种对科研的认识和态度真是令我热泪盈眶呀!”。
2.对抗式互动
在这种互动行为中,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在观点和立场上均处于对立状态,在疫情爆发初期,一些科学家意识到公众(表现为自媒体和网民)的对抗情绪给科研和救治工作带来的干扰,并提出了反抗,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上文所提及的徐旭东(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的一篇文章——《大疫当前,岂能围殴科学家》,该文显性化地质疑媒体和自媒体的信任,维护科学家的权威,比如文章提到以下几点:
围殴科学家的有自媒体,也有一批官媒。自媒体成分复杂,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但是某些官媒也参与嘲讽科学家。只想弱弱地问一句:是不是忘了自己正是需要补足科学素养的关键人群,忘了自己在这场大战布局中的位置和任务?大疫当前就是大战当前,不要做瓦解政府、民众与科学界相互信任的事。
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对抗式互动表现为一种不对等的博弈关系,在不同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中均呈现出强弱悬殊的态势,公众不仅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修辞能力上也胜于科学共同体。在公众看来,科学家的语言有严谨、枯燥、讲究证据的特征,不适应于评论区的日常辩论,甚至有学者发现“科学家只在论文发表之后才与公众讨论相关观点”。因此,对抗式互动演变为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单向权力制衡,导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权力失势,从而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或者称科学家在公众中系统信任的失守。从疫情初期的社交媒体互动来看,这种信任主要包含技术信任(官本位、外行管内行等质疑)和道德信任(骗取科研经费、有意引导市场、拒绝公开信息而提前发表论文等质疑)。
(二)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互动行为与权力实现
一些研究表明,限于科学议题的专业性等因素,科学家个体或机构自媒体的传播力较弱,善于使用自媒体开展科学传播的一般为较为年轻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如理工科博士生或青年科研人员,而年龄较大的则通过传统媒体来参与互动,如“医学界李佳琦”张文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则依靠接受媒体采访来传播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一些媒体(官方)与科学家关系和谐,媒体从各种角度塑造与疫情有关的科学家正面形象,科学家也依赖媒体来获得传播通道和建立话语权力。在科学家遭遇到公众“围攻”的情形下,媒体往往站出来为其“解围”,其中与科学家立场较为接近的是机关报、时政电视栏目的官方机构及其采编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开设的账号,在这一互动关系中,媒体的官方话语也是科学家知识权力实现的重要因素。例如,自疫情初期“抢双黄连”事件爆发后,科学家遭遇了公众的质疑,公众认为科学家专业不精误导了消费者,甚至有人怀疑某些科学家有双黄连生产商的商业背景。在此之时,《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曹林适时地在微博中发表评论《别骂抢双黄连的人了,他们是疫情迷信链的受害者》,其中说道,“如果专家被当成神了,专家作用被透支,媒体热衷去做符合公众情绪期待的新闻,迷信链的潘多拉盒子就打开了。”通过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该文实际是在这次冲突中给科学家“正名”,科学家也在与权威媒体的互动中重拾专业权威与话语权力。
五、结语与反思: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中的话语秩序重建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之间的博弈关系有极其复杂的原动力。从以上分析可见,社交媒体打破了科学家对话语权的垄断,网络评论释放了话语权,从而在公众中形成反智主义,冲击科学家的职业权力,这涉及到公众对科学家的技术信任与道德信任问题。虽然,在这种博弈关系中,公众在人数与修辞上占优势,科学家在专业与知识上占优势,彼此挟持优势互相制衡,也即前文所言的“强弱悬殊”态势。但是,这种“强弱悬殊”是在某一方面呈现出来的,并非说明二者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而是在不同轨道上的两种文化的对话。英国小说家查尔斯·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悲观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敌意”“代表着我所命名的‘两种文化’的形成这一突出事例,来说明人们之间怎样缺乏交流。其中一个集团有科学家,他们的分量、成就和影响毋庸再加强调。另一个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代表、说出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和预言了非科学文化的情绪:他们不作任何决策,但他们的话却渗透到那些决策者的头脑之中”。这一说法类似疫情期间我国社交媒体中的“文科生”与“理科生”之争,后者则成为科学共同体在网络上的代言人。平行轨道的思维模式、知识背景、叙述立场,看似井然有序地编制了当代科学传播在网络上的话语秩序,但却制造了二者之间的“不可沟通性”。
协商式沟通模式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并非单方面的鼓励科学家纷纷加入社交媒体阵容中开展科普工作。由于科研工作的复杂性、精确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受到诸多限制。话语秩序的重建,需要着眼于科学家、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沟通模式,尝试从制度性方面进行反思,重建科学家的系统信任关系:第一,技术与行政对等,即从建制架构上维护行政权力与技术权力的对等关系,避免遭到“外行指导内行”的质疑;第二,技术与道德平行,在传统媒体与科学共同体社交媒体平台(官方或个人)中显现科学技术的严谨(技术信任)、科学家在灾难事件中秉持的奉献精神和在日常生活中保有的“正常人”心态(道德信任),避免将科学家神化,而需要将其“人化”;第三,个体与群体的权衡,建设性的科学传播不可能依赖于某一个明星科学家的全维度沟通,这仅能建立公众对某一位科学家的人际信任,而对科学家系统信任的养成,需要着重于对群体形象和结构性特征的建构;第四,功利与兴趣的互补,公众对科学家的兴趣不应停留于“有用”,而应聚焦于“有趣”,例如@幻想狂刘先生(作家)在2020年4月22日的微博中写道:“现在很多人把专家的话奉为圭臬,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半个字。这不是相信科学,这是相信科学能解决问题,问题顺利解决后,就把科学家丢在一边,忘在脑后。”帮助公众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建立起兴趣,同时帮助媒体建立起分析科学的能力,这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科学家知识权力的重要方法。
注释:
① [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② 黄瑞雄:《科学的本质是否就是权力》,《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6期,第46页。
③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 [澳]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⑤ [美]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⑥ 《史上最猛烈的科技革命,将如何改变未来?》,博科园,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6900906628868255&wfr=spider&for=pc,2018年4月5日。
⑦ 庞万红、赵勋:《从两部科学传播经典文献看争议性科学议题的报道》,《文化与传播》,2017年第6期,第 58页。
⑧ 刘华杰编:《科学传播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5页。
⑨ 罗红:《科学传播的叙述转向及其哲学思考》,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页。
⑩ 刘兵、侯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5期,第 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