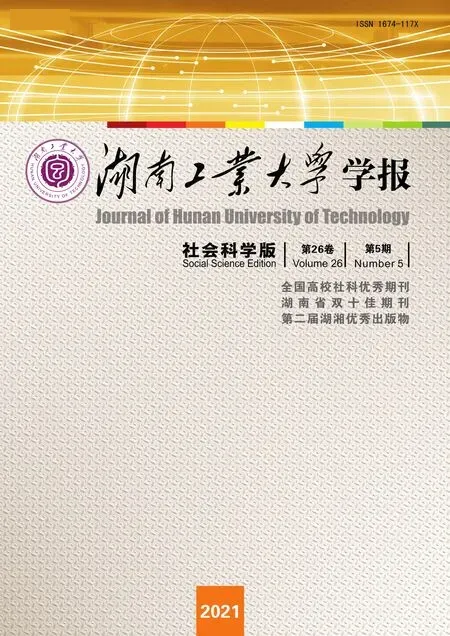《韩非子》争议词句考辨二则
高 扬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中文系,浙江 海宁 314408)
法家典籍《韩非子》中有些词句的含义的解读,自古以来见仁见智,直接影响着对韩非子法家思想的精确理解。传统训诂学者基于相关书证,充分利用音训、义训、形训等方法解决了不少争议,但是古人局限于语料的匮乏,未能对词语在整个语言中的总体分布进行考察,自是遗憾,如今古汉语语料遗传缺失,脱离了时代也不再能产。于是部分当今学者选择把语言外的证据如“义理”等作为主要证据,以此来提出诸多“新解”,这些“新解”大多属于“古人应该说了什么意思”,而非“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以此出发,不仅违背了语言系统性原则,其所宣扬的“新解”往往也是违背语言社会性和历史性原则的。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这些方法或者是先有结论后论证,或者是运用弱归纳和不充分演绎,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逻辑,必须加以警惕。
杨逢彬先生在其著作《论语新注新译》和《孟子新注新译》的导言部分批判了这些相对错误的考据方法,肯定了清代以来高邮二王、杨树达先生等大家在传统考据之上运用文法观念进行考察的做法。他更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遵循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系统性,从语言内部证据入手,广采书证,系统考察词语、义位分布特征,从而以分布为主轴整理古籍的方法。杨逢彬对分布理论的阐释是“每一词义,每一词,每一句法结构,它的出现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上下文条件(或可称之为语境,或可用专业术语称之为分布)。既然如此,考察其上下文条件为何,也就锁定了究为哪一个词义、哪一词,或哪一句法结构。”[1]这种古籍整理的方法有着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开展研究时要坚持采用的核心方法。
我们利用这种研究方法,针对《韩非子》中一直存在的一些争议词句进行讨论,下面列举两例,分别是词义解释方面存疑和字词置换方面存疑问题的代表,希望可以通过考察分布和语法分析,平定争讼。
一 “明主厉廉耻”解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韩非子•用人》)
本段中“明主厉廉耻,招仁义”一句,历来颇有异议,争议焦点主要是“厉”字义,现摘录学界诸说如下:
其一,“厉”同“励”,鼓励,劝勉。如陈奇猷:“厉、励同。明主以廉耻励人,以仁义招人。”[2]546《韩非子》校注组:“厉,通‘励’,勉励。”[3]
其二,“厉”作“举”解,与“招”同义。日本学者松皋圆认为:“招,犹揭也。《庄子》:‘自虞氏招仁义以乱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4]344太田方在前一句“君人者不轻爵禄”下注云:“重爵禄而不能赏人,非,所以厉廉耻也。傲富贵而不能下人,非。所以招仁义也。夫若此,何以救危国乎?《难一》篇云:‘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也。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4]344简言之,两位日籍学者认为“厉”与“招”同义。张觉也持此种观点:“尹桐阳解为‘勉’,陈奇猷、《校注》等解为‘励’,恐不当。因为古代‘厉’虽然有时表勉励义,但这‘厉’字与下句‘招’相对,当与‘招’同义,应解为‘举’。《吕氏春秋•恃君》‘而厉人主之节也’高注:‘厉,高也。’《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杨注:‘厉,谓抗举。’《广雅•释诂一》:‘高、厉,上也。’王念孙《疏证》举《淮南子•修务训》‘故君子厉节亢高以绝俗’为例,皆可证此文‘厉’字之义。”[5]500
以上诸说,陈奇猷及《韩非子》校注组的观点是将本句视为“明主厉(之以)廉耻,招(之以)仁义”的缩减形式;后面三位学者则认为句子就是简单的主谓结构陈述句。但是双方都没有就“厉”在先秦典籍的分布情况进行考察,所用书证也都与本句语法结构不同,以至于所举例证都是对自己主观判断的附议,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分析。
我们的观点是:“厉”的分布规律决定了其后宾语不可能成为“厉”凭借的手段,在本句语法结构下的“厉”在句中没有“对象”语义角色共现时,“厉”应取“举”义。
(一)“厉+NP”时NP从不承担“工具手段”语义
首先分析“明主厉廉耻”的语法结构,从语法形式上看,不论“厉”作何解,该句都可以描写为“S+厉+O,O=NP”,也即谓语动词“厉”前有主语,其后接一个名词性成分宾语。同时,“廉耻”一词在名词中属于抽象名词小类,表示动作、状态、品质或其他抽象概念,因而上述描写公式可以完善为:“S+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
据此,我们以“厉”加抽象名词性成分宾语作为对象,考察其在《韩非子》本书及时代相差不远的其他典籍《吕氏春秋》《孟子》《国语》《荀子》《战国策》《商君书》《新书》《淮南子》《史记》等十部典籍中的出现情况,分析它的分布特征。经统计,在这十部典籍中,形式为“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结构的书证有12例,如下:
(1)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战国策•齐策》)
(2)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吕氏春秋•遇合》)
(3)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埶,而羞居浊世。(《吕氏春秋•离俗》)
(4)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吕氏春秋•恃君》)
(5)此则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新书•阶级》)
(6)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新书•阶级》)
(7)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淮南子•氾论训》)
(8)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
(9)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新书•阶级》)
(10)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鬼不厉祟,民不谤怨,故曰宥谧。(《新书•礼容语下》)
(11)故鼓鸣旗麾,当者莫不废滞崩阤,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其前者。(《淮南子•兵略训》)
(12)咸为师傅,崇仁厉义。(《史记•自序》)
这12个例子中,例(8)较为特殊,虽然“厉”后是代词宾语“之”,但因为“之”指代上句中的抽象名词成分“僄悍民风”,所以也可将其归入待分析书证中。通过分析上述例证,我们发现,在所有形式为“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结构的书证中,“厉”后的名词都是直接受事宾语,体现了主语施加“厉”这一动作的对象,没有一例承担了“工具手段”的语义角色,即“厉”后所接名词不表示实现动词的手段。故陈奇猷所谓“用廉耻来鼓励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上古汉语中,如若想表达这个“利用某事物来鼓励人”的语义,都采用了“厉+以+NP”结构来实现,如:
(13)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大戴礼记•朝事》)
(14)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新书•阶级》)
(15)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淮南子•要略》)
(二)如存在与“厉”共现的特指对象,“厉”通“励”,反之则为“举”
在确定了“明主厉廉耻”是一个正常的主谓结构的陈述句后,我们继续通过例证(1)~(12)来分析“厉”的词义。
以上例证尽管形式上都呈现为“S+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结构,但是如果引入语义特征分析法,会发现“厉”在这些例证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义位,而这两个不同的义位,各自有自己的分布特征,是可以完全区分开的。
在“S+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中,“厉”可以通“励”,表示“劝勉,鼓励”,也包含有“(使之)高”义,《汉语大字典》中将这两个词义区分成了两个不同义项,实则不妥,因为“劝勉,鼓励”与“(使之)高”实际上是一个动作的过程和结果,如例(1)~(8),“厉”都表示了“励且使之高”的意义,通过分布时无法将其划分成两个义位。
我们发现,当取“鼓励”义位时,动词“厉”在作用于宾语这个抽象名词后,“厉NP”会指向一个固定的对象,这个对象成为了“厉NP”的最终承受者。即“厉”含有“+特指”语义特征,在句子中与一个被“厉”特指的“对象”语义角色共现:例(1)“厉”指向隐去的守城士兵;例(2)指向“女(汝)德”;例(3)指向被隐去的自己;例(4)指向“人主”;例(5)指向“群臣”;例(6)指向“宠臣”;例(7)指向被隐去的“诚”的主体,即跟随英豪的战士;例(8)指向其民之风。
而当文段中没有作为“对象”语义角色的成分与“厉”共现,特指谁最终承受了“厉NP”这个行为时,“厉”就只是泛指,语义特征为“-特指”,这时的“厉”表示“举、树立”,如例(9)~(12):例(9)中不存在与“厉”共现的“对象”语义角色,“厉”为泛指,“厉廉耻”即把廉耻树立起来给外界看;例(10)也不存在与“厉”共现的“对象”语义角色,“鬼不厉祟”即“鬼不举其祸祟”,无明确承受对象;例(11)“厉”也没有特指的对象,“厉威抗节”是树立其威信给天下看,后面的“当其前者”并非是“厉”的特指对象,而是属于“当”这个动词的管辖范围;例(12)中,“厉”同样只有宾语“义”,而没有特指的承受对象,故而也释为“举”。
因此,“明主厉廉耻”与例(9)~(12)中“厉”的分布特征一致,应取“举”义。
(三)“廉耻”常与“举”义动词相连,不和“鼓励”义动词连用
最后,我们分析本句中的名词性成分“廉耻”的结合能力。在上古汉语中,“廉耻”表示“廉洁的情操与羞耻心”,该词受“举”义动词支配。“举”义动词包括了“举”“立”“厉”“设”等,形成了一个同义词聚合。除了上文例(9)之外,还可举例如下:
(16)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属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韩非子•诡使》)
(17)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管子•立政》)
(18)圣人由近以知远,以万里为一同,气蒸乎天地,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文子•下德》)
(19)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淮南子•本经训》)
(20)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淮南子•泰族训》)
在上述例证中,当“举”义动词+“廉耻”结合时,皆表示“树立起廉耻心来”。进一步纵观先秦典籍语料,除了“举”义动词外,虽然“廉耻”也可以受一些其他动词如否定动词“无”等支配,但没有一个受“鼓励”义动词支配的例证,因而从“廉耻”的分布特征来看,“厉廉耻”作“举廉耻”解也为上选。
综上所述,通过对“厉”和“廉耻”的分布特征考察,包括语法结构分析和内在的语义特征分析,我们认为“厉”当作“举”,“鼓励”之说为非,而张觉虽然结论与我们相同,但其例证选择有问题——选择了用“高”义之“厉”的书证来论证其观点,更重要的是,其论证中没有细致的语法分布研究。要之,本句可翻译为:所以圣明的君主树立廉耻与仁义。传统认为法家一味地反对仁义,实际上其反对的是儒家提倡的某些与法治不符的仁义,而对于符合法治,尤其是能树立君主之势的仁义,法家则是大力提倡的,因为通过这种仁义,君主让渡部分利益,可以成功御下而行大事。
以上,我们考察词语的分布时,除了利用传统的“主谓宾定状补”外,还试图描写出与疑难词共现的成分具备了哪些语义特征,从而可以将对句子和分布特征的描写推向深入和精准。如此,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字词置换”问题,很多“新解”都对“字词置换”情有独钟,我们反对的并非是这种结果,而是反对预先设立结果,为之拼命寻找证据的做法——只要能够通过分布考察、语法分析证明A词出现在某个位置上,比起传世文献中不能理解的B词更加合适,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用A替换B。
二 “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解
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虚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韩非子•说难》)
本段中“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句因“交”义未辩而使该句难以文从字顺,前辈学者对“交”义及此句解释观点迥异,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改字而解。这其中又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改“交”为“久”解。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引《说难》,改述本文段为:“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6]二是改“交”为“史”解。顾广圻释此:“《正义》云:‘时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误,当作‘史’。本书《难言》篇:‘敏捷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7]王先慎也赞同此说。此解中“史”同《论语•雍也》中的“文胜质则史”,虚浮义。三是改“交”为“弃”解。陈奇猷认为:“交、久皆无义,‘交’当为‘弃’字之误,‘弃’与‘屈’对文。此谓米盐博辩则以为繁杂而弃之。作‘交’者乃因篆文‘交’‘弃’形近而讹。旧注以误文为训,失之。史迁引古籍,多篡改,此又因‘弃’误为‘交’,义不可通,遂改为‘久’。张榜本又依《史记》改为‘久’,非是。”[2]260简言之,陈奇猷因形近讹传而改“交”为“弃”,表摈弃。
其三,“交”为“驳杂”。蒲阪圆:“交,交杂也。”[5]199张觉否定了以上诸解,赞同日本学者蒲阪圆等观点,将“交”保留,释为“驳杂”。其依据为上下文关系,认为“拙”与“不智”义近,“不尽”与“怯懦”相承,“佢侮”与“草野”相类,所以认为“交”与“多”字义近相承[5]199。
我们认为当从司马迁观点,改“交”为“久”,即“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久之”。对先秦文献疑难句改字作解必须慎之又慎,改后之词的分布特征必须与原句语法环境相符,必须能够进入被改词所处的语法位置,才能成功进行置换。
(一)诸说中以情理论证或对文论证者,多不可从
谢希深之说增字解经,增一“猥”表纷乱,不仅未能通顺全句,反而为了自己的假设改变了句子的本貌,此法多不可取,正如王引之所言:“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8]
顾广圻以“史”替之,没有更多书证,只是引用了同书《难言》语为证,但其中“史”出现的语法位置和上下文语境都与本句不同,仅以此等情理上的推测入手,似不能作为诠释依据。
陈奇猷换“交”为“弃”,主要依据为缺少规范的“对文”。仅通过语意,可以出现在“交”位置上与“屈”对文的词语有很多,“弃”是程度比较严厉的行为动词,与“屈”这种较为委婉的词语也并不能做到陈氏所期望的对文。从语法角度来说,先秦典籍中连动结构“V1+O+而弃之”固有存在,但是可以存在于本结构“交”位置上的类似意思的词还有很多,如“诛”“杀”“退”等。如定需换词,比起后人的“弃”,或许从汉初司马迁之说更接近原书本义。因而陈奇猷据对文改为“弃”的观点当从疑。
张觉坚持此处为“交”,不换词不增字,从每个句子中前后用词相类似关系入手加以论证。分析张觉的类比,“不智”是“不聪明”,“拙”却为使动,表“使其屈抑不被重用”,《释名•释言语》:“拙,屈也。使物否屈不为用也。毕沅疏证:‘屈,当作诎。’王先谦补:‘物否屈不为用,即不利于人。’”[9]“怯懦”与“不尽”是情理语义上的相承,两句结构并不相同;后文“佢侮”与“草野”固然相类,但二者为并列关系,与上文句子结构不协,同时也是以动用法。所以张觉用于类比的诸词,实则不是一个层面,在语法功能上也并不协调。因此,单从对文和情理上认为交无误,尚缺少证据。
(二)“交”不能出现在句中此语法位置
首先我们通过审句例来分析本句的争讼点“交”,考察“交”能否出现在原语法位置上,是否需要被替换。
“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从句型上看,是为假设条件复句,“米盐博辩”为假设条件,后半句“则以为多而交之”为假设条件满足后产生的结果。承文意,后半句有主语“君主”被省略,“以为多”是述补结构,后“交”的宾语“之”则指代“米盐博辩”的“人臣”,因此后半句应该被识别为连谓句结构。也就是说在“交”这个位置出现的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使动、意动用法的不及物动词,在此句中为连动的第二个动作,前有一个表判断动作的成分,整句话语法结构描写为:“S+以为多+而V之”。
我们以“汉籍”为工具,穷尽考察了“交”在同时期文献中的分布情况。“交”在同时期典籍中作动词时多为不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表“交往、接触”,如:
(21)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左传•成公九年》)
(22)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23)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诸侯莫弗闻。(《韩非子•十过》)
(24)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犹未邪也?”(《吕氏春秋•观世》)
亦见作及物动词带宾语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语为单方,后接单宾语,表示“单方面与某人结交、交往”:
(25)食而弗爱,豕交之也。(《孟子•尽心上》)
(26)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管子•霸形》)
(27)秦不听,是秦、韩之怨深,而交楚也。(《战国策•韩策》)
另外一种情况是“交”前面主语成分为双方,表“交叉、交换、交往”:
(28)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左传•隐公三年》)
(29)大鋋前长尺,蚤长五寸,两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兑其两末。(《墨子•备城门》)
考察了同时代文献关于“交”的1898条书证后发现:首先“交”前罕有连谓结构,特别是“交”带宾语时,更是没有一例前置连谓结构。其次,不论“交之”前主语是单方还是双方,都具有“+互相”语义特征,表两方面之间的产生的“交往”“交换”,而这一义位出现在本句,则本句无法实现文从字顺。故“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中“交”缺乏语法合法性,不应出现在句中该语法位置上。
(三)“久”具有置换“交”字的分布特征
承上分析,既然“交”可能是一个误字,我们在寻找本字时就应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替换词在完成替换后,必须能让这个句子在语法上合法,语义上通顺;第二,替换词完成替换后,这个结构必须“验之他卷而通”,也就是必须满足语言社会性;第三,两个字需要在形体等方面有一定相似性。我们首先考察的备选字词置换方案是司马迁的更“交”为“久”说。首先“交”“久”字形也有所相似,更重要的是西汉与战国末年时代相近,且《史记》与《韩非子》作者地域也相近,不论从材料的易得性还是阅读的容易度来说,都是应该被格外重视的。
查之文献,上古汉语中“久”可以作动词表示“使某人某物长久在一个状态”,举数例如下:
(30)宋人伐郑。围长葛。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谷梁传•隐公五年》)
(31)皆习战也。何言乎祠兵。为久也。曷为为久。吾将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公羊传•庄公八年》)
(32)诸侯之师久于偪阳,荀偃、士匄请于荀罃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左传•襄公十年》)
(33)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孟子•公孙丑下》)
(34)愿王之使人反复言臣,必毋使臣久于勺(赵)也。(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
当“久”作为及物动词后加宾语时,这一结构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也屡有出现,此时“久”可作“灸”表“固定”:
(35)皆木桁久之。用器。(《仪礼•既夕礼》)
也可表“使某人某物长久在一个状态”义,如:
(37)士伯曰:“寡君以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左传•昭公廿四年》)
(38)吴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见。(《吴越春秋•勾践入臣》)
(39)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左传•宣公十七年》)
(40)轩骄之兵,则恭敬而久之。(《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五名五恭》)
(41)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新书•修政语下》)
以上诸例中,例(39)~(41),“久”之前都有一个前序动作,例(39)是“过而不改”,例(40)是“恭敬”,例(41)是“宜处”,三例都构成了或松散或紧凑的连动结构,与本文待考辨之句语法格式相同,同属连动结构中的后续动作,“久”前成分表一个前序动作或者看法,后带宾语,表示“使之滞留在一种状态”义。因此用“久”具有置换“交”的分布特征,在语法分布上具有可行性。
(四)以“久”换“交”可使文从字顺
如从司马氏之说以“久”置换“交”,“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就可译为“如说者如米盐一样细致地来辩说,就被(君主)认为说得太多太啰嗦从而使其滞留(而不用)”,即君主面对啰嗦的“说者”,往往采取置之不理也不用的态度,让其长期自己呆着。
实际上,先秦典籍中,表示因为一些原因,主语对象产生了某种看法或行为,然后让宾语对象滞留在某种状态这种语意的书证也较为常见。除了上述的“久”,还有与“久”同属一个语义聚合的“留”“止”等词,如:
(42)宫他为燕使魏,魏不听,留之数月。(《战国策•燕策》)
(43)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赵王之所甚爱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谋而入之秦。(《战国策•赵策》)
(44)楚王使景鲤如秦。客谓秦王曰:“景鲤,楚王使景所甚爱,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战国策•秦策》)
(45)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战国策•楚策》)
(46)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战国策•秦策》)
(47)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8)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与,子常三年留之,不使归国。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马,子常欲之,公不与,亦三年止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因此,用“久”置换“交”后,“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所表达的君主面对啰嗦说者的态度和行为,是可以说通的,能使句子做到文从字顺。
综上所述,基于语法分布特征,前后文语意通顺及字形相似,我们认为“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中“交”字应该用“久”置换。其中最主要的证据还是“久”可以完美地出现在“交”的语法位置上。除以上依据外,正如王力先生所言,“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耳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汉儒读先秦古籍,就时间的距离说,略等于我们读宋代的古文。我们现代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还是千年后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大家都会肯定是前者。因此,我们应当相信汉代的人对先秦古籍的语言比我们懂得多些,至少不会把后代产生的意义加在先秦的词汇上。”[10]时代相近的司马迁对《韩非子》此文的解释,或许比起后人的注解疏证要更为贴切一些;但是这种判断也只是在我们做了全面考察分布工作之后,作为辅助证据而存在的,因为它本身也属于语言系统外。韩非一生际遇坎坷,深感游说之难,每每游说,必考虑君主心理,言多则恐被视为迂腐而置之不理,言少则恐视为愚笨而弃之不用,故言之于胸,难以出口,因此他发出如此感叹是十分合理的。
综上两则考证,《韩非子》中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词句,我们从其语法形式入手,考察它们在同时代、近地域文献中的分布情况,以区别特征来分辨其语义,可以成功找到词义的“标志牌”,从而平定争讼。这一方法在先秦典籍疑难词句考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结合的研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