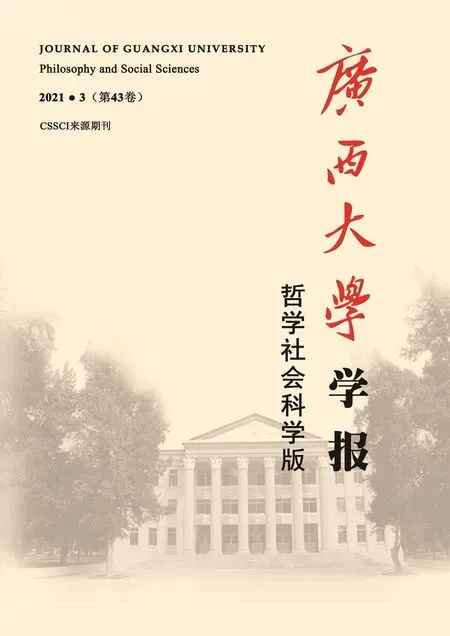INGO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的“本土化”路径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谢 舜,李岚睿
开放的社会系统下,组织发展目标、可支配资源、法律制度、社会文化、不同主体间互动关系等构成组织的行动“约束”。组织的行动真实地“嵌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并依赖于“行动场域”中的资源。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INGO)“外来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容易使其在东道国遭遇“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问题,治理实践受东道国特定社会情境的制约。组织身份劣势的克服与治理情境的差异,要求INGO遵循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本土化”行动路径。
一、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全球治理的纵深发展对国际及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对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全球及地区公共事务治理提出了现实要求。随着跨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INGO 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非政府组织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一类[1-2]。实践表明,INGO 凭借庞大的组织数量、先进的发展理念、成熟的项目管理技能、充裕的资金以及多样化的运作手段等优势,逐步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重要的驱动力[3]。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促使越来越多的INGO 进入东南亚,在区域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发挥重要作用。INGO在东南亚地区的治理实践涵盖自然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城市环境治理[4-5],扶危助困、教育培训、卫生医疗及生存条件改善[6-7],本土非政府组织发展指导、政府行为监督、人权民主促进等[8-9]。但INGO 在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组织身份合法性问题和治理情境约束问题。
从组织身份视角看,INGO 在东南亚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初始阶段,由于地域、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其在东道国的生存、发展将承担本土非政府组织无须面临的额外危害,例如信息缺失、合法性缺失及嵌入性缺失等,导致INGO在东道国遭遇与跨国企业组织相似的身份问题——“外来者劣势”[10-11]。因东道国具有歧视意味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INGO 容易被冠以“麻烦制造者”,被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自然地”或“理所应当地”贴上情报刺探、消极文化传播、意识形态对抗、干涉政权等负面标签。这种隐性的“外来者劣势”带来诸多危害,致使其面临物资、人力、信息、制度、社会关系等资源的缺失,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合法性缺失、社会网络缺失、管理冲突等问题[12-13]。克服“外来者劣势”成为各类跨国组织在东道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4-15]。
从治理情境看,面对东南亚地区特定的社会情境与治理实践“约束”,INGO 一般选择以下两种行动路径:一种是通过设立办事处、与政府直接合作、资助本土非政府组织等方式,以“主导者”身份在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开展活动,以资金援助、技术支持等手段操控民意、控制政治力量、引导政府行为,甚至输出西方思想,渗透西方民主[16-18]。如2015 年柬埔寨茶润水电大坝项目的停滞实为一起典型的INGO 操控本土非政府组织阻挠在建工程的案例[19]。另一种是,在“国家和政府确定的框架下”,INGO 以“服从者”的身份参与治理活动,以获得身份认同和合法性地位,避免遭受威权政体下政府的打压、限制及惩罚,选择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20-22]。如马来西亚政府为巩固自身民众支持基础,禁止INGO 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且服务对象范围仅限于中产阶级[23]。
从实践结果看,无论是“主导者”的行动路径,还是“服从者”的实践模式,都表现出治理需求与供给的背离,即治理主体间冲突、治理对象模糊、治理资源配置低效、治理目标偏离、治理成效有限等。在上述治理模式之下,东道国政府、INGO 及其他治理主体各自掌握的资源成为互相控制的手段。治理主体、治理资源与治理目标之间普遍存在对抗、内耗与冲突,应有的治理实践演变为“经济问题政治化、跨境问题人权化、环境问题极端化”等,被冠以“麻烦制造者”的INGO 在东南亚遭遇“治理失灵”[24-25]。
综上所述,组织身份带给INGO 的“外来者劣势”,使其在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初始发展阶段容易遭遇因信息、合法性和嵌入性缺失所导致的不熟悉危害、歧视危害等[26]。INGO 也未能有意识、有倾向地选择与东南亚特定治理场域相匹配的行动路径,“主导者”与“依附者”的参与模式导致治理低效。基于INGO 的组织身份劣势以及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治理情境,作为“参与者”和“外来者”的INGO 应选择怎样的行动路径?本文假设,一种遵循对象国特定治理情境且“资源互嵌”的本土化参与路径可有效克服外来者劣势并保证治理成效。
二、东南亚地区治理情境与INGO 的治理实践
(一)东南亚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境
东南亚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政党及政治制度多样,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多元,法律体系与执法机制各异。资源禀赋、政治环境、政府治理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INGO 治理实践的现实“约束”。东南亚地区的治理实践有其特定的场域特征。
1.治理机制的复杂性
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治理机制源于其多样化的政治体制与宗教文化。世界“种族和宗教博物馆”的特征和属性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治理机制[27]。例如印尼刑法体系由习惯法、伊斯兰法和荷兰法三者融合而成,民法体系以习惯法和伊斯兰法为主;马来西亚实行世俗法与伊斯兰法并行的双轨司法体系,伊斯兰法以宗教教义“沙里亚”为主要来源。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体系形成复杂的治理机制。
在越南,各类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都必须符合“第12/2012/ND-CP 号法令”,该法令涵盖了从设立、登记到管理的全部程序。针对INGO的管理更为严格,不仅要求具备来源国法人地位,还必须向越南国际非政府组织事务委员会(COMINGO)提交明确的业务章程、指导方针和发展计划,待委员会审核后方可进入注册程序。在获得注册证书、代表处注册证书和运营注册证书后才能开展活动。运营期间,须每6 个月向该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在越南活动的报告,并向越南人民委员会提供相关副本以供核查[28]。
2.治理主体与目标的差异化
东南亚区域的治理发展,正在“由单一状态嬗变至多元主体共同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的活动,一种政府将原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转移给社会,由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公私行为体共同治理的活动”[29],呈现出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中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各主体可能从各自道德立场、偏好出发,提出不同的利益诉求、治理目标和权责界限划分标准。例如,政府将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存在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的目标之差。如印尼实行地方自治后,政府“公共人”目标与少数追求个体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官员的“政治人”和“经济人”目标并行甚至存在冲突。企业则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组织兼有非营利性、独立性、自愿性,但也存在特定的群体利益偏向。个体的差异性更是多样化。由此,INGO 在东南亚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面临差异化的治理主体和治理目标。
3.治理资源的稀缺性
INGO 治理实践的开展依赖于资金、人才、信息、技术、设施等资源。但囿于各国经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INGO 在东南亚的行动面临治理资源的约束。国别上看,除新加坡、文莱,其余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尤其是缅甸、老挝、柬埔寨欠发达程度更高。人才和科技方面,新加坡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和较高的技术水平,其他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制约。印尼工业基础薄弱,科技落后,研究与发展投入少,科研人才匮乏,国际科技合作层次低,长期以来依靠进口技术和设备。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教育科技发展较为落后。老挝作为农业国家,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欠发达,财政经费有限,普通和高级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科技基础十分薄弱。柬埔寨政府虽然将教育视为优先发展项目,但国内至今未普及基础教育,而高水平人才的匮乏更使科技发展举步维艰。此外,信息、基础设施等治理资源也面临不同程度的现实制约。
4.治理需求的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推动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环境破坏、城乡发展失衡、社会保障等问题。在“经济发展至上”理念的推动下,该地区的大气污染、土壤退化、森林消失、生物多样性破坏、水资源浪费和污染等问题突出,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中心。印尼“烧芭”导致山火频发严重破坏森林资源,还引发了跨境烟霾污染问题。截至2019 年9 月16 日,“烧芭”已造成印尼约33.3 万公顷土地过火,并导致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部分地区长时间遭受烟霾污染,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航班停飞、学校停课等状况频频发生[30]。此外,东南亚地区地震、海啸、火山喷发、暴雨、洪涝等问题频现。人口增长过快、公平发展、性别平等、教育医疗、社会动荡已成为本地区面临的难题。如柬埔寨长期面临水资源短缺、教育水平落后以及卫生医疗条件差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教育权益迫切需要得到保障。复杂的治理机制、多元的治理主体、差异化的治理目标、有限的治理资源、多样的治理需求构成INGO 在东南亚的行动场域,治理活动受现实情境的约束。
(二)基于印尼的田野调查分析
2019 年 8 月至 12 月笔者对日惹特区(Daerah Istimewa Yogyakarta)和三宝垄 (Semarang) 地区4 个INGO 作了实地调研。通过调研笔者发现,上述INGO 不同程度地面临“外来者劣势”问题,尤其是在进入印尼的初期,组织身份劣势较明显。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以当地实际需求为导向,将实践根植于现实的治理情境之中。弱化或回避政治属性,以“参与者”的身份与政府、企业、高校、本土社会组织等构建良好的关系,将儿童权益保护、难民救助、残障人士赋能、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等全球性议题(global issue)置于本土情境(local level)中加以解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
1.SOS 儿童村概况
SOS 儿童村(SOS Children’s Villages,以下简称SCV),1949 年由赫尔曼·格迈纳(Hermann Gmeiner)创建于奥地利。SCV 在过去的70 多年间秉持“确保每个孩子在爱、安全和尊重中成长”的使命,通过教育、家庭强化、医疗和社区推广等方式在全球136 个国家开展活动,并设有2 000个SOS 儿童村设施,抚育了7.8 万多名儿童和青年,每年使大约200 万人间接受益,成为世界儿童救助非政府组织的典范。
目前,SCV 已在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开展数10 年运营,累计建立51个儿童村,并使超过30万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儿童直接或间接受益。
2.印尼SCV 访谈分析
2019 年 12 月 17 日,围绕“治理情境、组织身份、跨文化适应性、项目设定以及行动路径”五个主题,笔者在印尼日惹对印尼SOS 儿童村日惹负责人作了深度访谈。
(1)现实治理情境
2020 年印尼总人口2.74 亿,约占全球人口的3.51%,为世界第四大人口国[31]。民主革新以来,印尼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2010—2019年年均人口增长率1.31%。2017 年印尼全国15~19 岁女性生育率为36%,其中农村地区高达51%。2018 年印尼各省民政登记机构5 岁以下儿童在籍比例71.92%,近30%同龄儿童为“黑户”[32]。伴随早婚早育、高出生率、非法出生、贫困、家庭变故等而来的是弃婴、孤儿、流浪儿童、儿童抚养、免疫保健、教育、童工等一系列问题。2018 年印尼境内童工人数达290 万,印尼政府承诺到2022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工现象,但就目前形势看,童工问题依然严峻[33]。印尼儿童成长过程中对家庭关爱、父母陪伴、医疗保健、安全保障、持续教育、心理康复的现实需求是SCV 在印尼建立SOS 儿童村、开展运营、实施项目的前提。SCV 拥有的国际化运营理念、专业化服务技能、科学化管理模式、成熟化的运行机制以及良好的声誉,契合了印尼的现实需求。目前,SCV 在印尼运营9 个儿童村,为大约1 200 名孤儿提供了替代家庭式抚育服务,家庭强基计划(FSP)使近5 000 名贫困儿童受益,同时为2 556 名来自贫困家庭的父母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物资援助等服务。
(2)SCV 的“外来者劣势”与跨文化适应性
与印尼本土各类社会组织相比,作为“外来者”的SCV 面临环境不熟悉、信息缺失、关系缺失、合法性缺失以及嵌入性缺失等先天劣势,克服组织身份的劣势并提升跨文化适应力是现实问题。自然环境、“潘查希拉”(Panchahira)思想、INGO 注册及运营制度、地方政府规定、组织协会准则、宗教教义、文化习俗、社会认知、个体特征等带来的差异性与复杂性,需要SCV 主动适应。尤其在SCV 进入印尼初期,主动适应差异化的社会环境对合法身份的获取及项目的启动至关重要。
SCV自1972年在万隆连旺(Lembang,Bandung)建立第一个儿童村以来,十分注重组织身份变革,采取渐进式的“进化”机制,在雅加达、三宝垄、巴厘、弗洛斯、亚齐、美拉波、棉兰以及日惹设立并运营儿童村,前后时间跨度近50 年。50年里,SCV 逐步构建了印尼本土儿童救助领域专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身份,以良好的实践结果向公众诠释了组织的使命、价值和目标,呈现出与本土治理诉求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获取并逐步巩固组织身份的合法性,培养并提升组织的跨文化适应力。组织身份变革的举措保证了SCV在印尼运行过程中尤其是进入初期克服了“不被理解”“不被认可”以及“水土不服”等问题。
在后期发展进程中,SCV 重视“外来者劣势”的规避并强化组织的跨文化适应性,通过招募、培训、任用更多的本地雇员以强化组织的适应力。SCV 在印尼运行近50 年,并非一味地、被动地适应本地文化,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塑造该领域的文化。例如,推动政府进一步完善针对 INGO 的管理规定,呼吁社会关注弱势儿童群体,倡导多元主体投身公益事务。
(3)供需匹配与行动路径
印尼的现实诉求为SCV 参与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行性,组织合法性身份获取与跨文化适应力的提升为治理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但选择何种行动路径直接影响治理实践的成效。SCV 在印尼遵循“现实情景下的行动”(Kids orientation&Real action)原则,以SOS 儿童村为实践基地,将孤儿、留守儿童及缺乏关爱的孩子纳入儿童村的社区管理项目之中,同时将儿童所在家庭一并纳入社区服务项目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式抚育计划(Pengasuhan Berbasis Keluarga)、家庭强基计划(Program Penguatan Keluarga)和灾害应急响应计划(Tanggap Darurat Bencana)。
2015 年建立的日惹SOS 儿童村与印尼其他8 个城市的儿童村运行模式一致,儿童村中设立12~15 个家庭单元,每一个家庭单元包含1 名专职妈妈(Ibu asuh)和8~10 名儿童,专职妈妈负责家中儿童的饮食起居、保健、安全及教育,实行孤儿、弃婴家庭替代式抚育(family based care)。
家庭强基计划通过对日惹城区内沿河贫民区、北部火山区、南部海岸区等地的贫困家庭记录编组,分成10 个社区(community),定期在社区开展家庭儿童教育和家庭职业技能培训,并为贫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强化家庭经济基础,以此为儿童争取更多来自父母的陪伴、关爱和照料。SCV 为每一个社区派驻3~5 名志愿者,指导并协助社区开展活动,设置社区儿童学习室、小图书室、家庭轮流午托点、临时照看点,为家庭贫困儿童提供必要的关爱和守护。
灾害应急响应计划针对社区的儿童,尤其是小学阶段(Sekolah Dasar)的儿童,开展地震、火山喷发、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识别及自我保护的宣传和应急演练。同时,在交通安全、食物安全、卫生保健、紧急通信、避难所、早期创伤恢复、救助营合作与管理等方面给予儿童及其家庭必要的引导和帮助。该项目包括关爱留守儿童、临时关爱中心、儿童友好家园、家庭团聚、心理及社会支持五个子项目,SCV 致力于为日惹特区的弱势儿童群体提供系统性的帮助和守护。
(4)时空情境与项目差异化
日惹SOS 儿童村在家庭式抚育计划、家庭强基计划和灾害应急响应计划三个项目下开展活动,但具体活动内容根据具体受众对象及外部环境做出动态调整。灾害应急响应计划的实施会根据社区所在的地理位置、季节各有侧重。北部火山(Gunung Merapi)社区会侧重于火山喷发的常识宣传和应急演练,南部的黑滩(Pantai Parangtritis)社区侧重海啸的识别及自救,而日惹市区内的沿河社区(Sungai Code)则重点关注洪水灾害及疟疾防治。此外,一些项目的实施也会考虑到雨季和旱季,雨季会更多地实施有关饮水、疟疾预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活动,旱季则较多偏向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的项目实施。即使是在印尼,9 个城市的SOS 儿童村开展的项目也存在差异。亚齐会更强调关于海啸灾害的预防和救助,而雅加达则会关注交通安全、饮水安全。2004 年亚齐曾遭受严重的印度洋海啸袭击,雅加达是著名的“堵城”,城市水污染严重。
(5)身份劣势克服与资源嵌入
SCV 在印尼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其他主体互动,塑造良好公众形象,强化身份合法性,这是本土化的重要举措。SCV 作为“外来者”,身份是否合法直接决定其在印尼的生存、发展。为了获取在更广泛制度环境中的资源,克服“外来者劣势”危害,SCV 积极同政府机构、伊斯兰教协会、高等院校、本地社会组织、权威人士等建立并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通过设立社会实践基地、短期工作营、国际工作营招募本地及国际志愿者参与儿童村的日常活动。通过良好的社会互动,SCV 在印尼发展过程中获得政府批复的土地使用权,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获得J&T Express、DHL Indonesia 等大型企业的资金及物资赞助,同时得到了本地社会组织的支持,也获得印尼高校及研究院的智力支持。
(三)其他INGO 的访谈分析
除SOS 儿童村外,2019 年11 月至12 月,笔者在印尼先后对全球难民救助组织——耶稣会难民服务(Jesuit Refugee Service,下称JRS)、残障人士救济组织——劳工救助联盟(Arbeiter-Samariter-Bund,下称ASB)、贵格组织(Quaker)——美国教友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下称AFSC)作了调研和访谈。通过渐进式的发展,三个组织逐步规避了“异客”在“他乡”的身份劣势,并通过身份、信息等多重资源嵌入与政府等主体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目前,JRS 在印尼已累计为来自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缅甸等国的1 723 名难民及各类庇护寻求者提供了涵盖人身保护、心理辅导、紧急救助、儿童教育、社会倡议等服务。与移民局、海关等开展协作,为来自孟加拉国、泰国的非法劳工提供救助。ASB 在印尼日惹、三宝垄等4 个城市开展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赋能活动,通过增强社会包容性和风险适应力,减少残障人士生存的风险。2020 年4 月,ASB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实施了“仙台框架行动”项目(Putting the Sendai Framework into Action),为残疾人参与灾害治理赋能,消除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与歧视。1998 年以来,AFSC 在印尼先后实施了“青年促进和平计划”、贫困治理、灾后重建以及包容性宗教和环境治理行动。2019 年11 月13 日,AFSC在印尼亚齐、日惹和古邦实施环境治理项目,包括乡村清洁行动、塑料污染纪录片展播、气候变化对妇女影响论坛[34]。
三、治理情境的约束与行动路径的选择
SCV、JRS、ASB 及AFSC 的治理实践根植于印尼现实的情境之中,并将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置于本土情境(local level)中展开治理行动。在儿童权益保护、难民救助、残障人士权益保护和社会经济公平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通过考察其治理实践可归纳出以下特征。
(一)行动前提:治理情境的明确
治理对象的差异性、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多样性、治理机制的复杂性、治理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INGO 在东南亚治理实践的现实制约。SOS 儿童村实施的三大项目、JRS 对阿富汗难民和孟加拉国劳工的救助、ASB 在印尼和菲律宾开展的残障人士赋能活动、AFSC 推动的包容性宗教,无一不是在由特定的空间(印尼亚齐或日惹)、特定的时间(1998 年或者2017 年以来)、特定的对象(孤儿、残障人士或难民)、特定的诉求(儿童权益保护或残障人士灾害风险减少)、特定的机制(政府管理机制或社会互动机制)之下构成的行动“约束线”或“边界”之内开展的治理实践。与治理实践相关的每一个当下的现实情境即为INGO 在东道国参与治理的“场域”。任何行动都必须在场域内实现。对治理情境的明确是INGO 开展治理实践的前提。
(二)资源嵌入:治理共识下的良性互动
治理情境之下包含众多主体、诸多诉求。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自身难以拥有全部所需的资源,大量决定性的稀缺资源存在于组织外部环境之中,组织必须与其所依赖环境中的要素发生互动并将其内化[35]。组织在复杂环境中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关键,是获得并保住组织所需稀缺资源的能力。但囿于制度、文化等差异,INGO进入东道国后,“外来者”身份导致明显的边界,阻碍了信息交流,加大了东道国对INGO 合法性身份的认可难度。反之,合法性的缺失也阻碍了INGO 与东道国各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使INGO 无法嵌入东道国的信息网络之中,从而缺乏对东道国真实需求的了解。在“外来者劣势”的现实制约下,INGO 在东南亚地区难以实现维系自身生存和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的自给自足。无论是SCV、JRS,还是ASB、AFSC 都对其所在的治理场域中的资源产生依赖。
SCV 对印尼政府所给予的合法身份和行动准许的制度依赖,对J&T Express、DHL Indonesia 等企业赞助资金、物资的依赖,对伊斯兰教协会、本地社会组织、高等院校所提供的文化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的依赖。与此同时,SCV 也为包括印尼政府在内的其他主体提供了其所需的资源,例如为政府在儿童权益保护领域补充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履行创造契机,为本地社会组织及高等院校协作实践提供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主体各自拥有的资源并未成为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冲突内耗”的工具。基于“提升弱势儿童群体的福祉”这一共同治理目标,SCV 与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互嵌,跨越了身份边界并实现资源内化,被印尼公众接受、认可,即通过获取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克服外来者劣势以及优化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奠定开展治理的现实基础。
(三)治理成效:“本土化”行动的结果
治理情境的明确、治理资源的互嵌、治理行动的展开服务于治理目标。但治理实践有效与否、程度如何依赖于具体的、与之匹配的行动路径。上述四个INGO 在印尼实施具体项目的过程中,表现出与现实治理情境相匹配的“本土化”路径特征。SCV 对印尼儿童权益保护领域现实需求的回应,治理对象的界定,“外来者劣势”的克服,跨文化适应力的提升,差异化项目的实施,社会关系的构建,均发生在现实的行动场域之中,是对治理情景约束的回应。
2015 年以来,SCV 在日惹开展的家庭强基计划和灾害应急反应计划,按地理区位划分10个社区,差异化实施,既遵循了客观地理环境的属性(火山区、海滨区、城市内河区),又回应了治理对象的诉求(经济基础强化、灾害识别与自救能力提升)。这一遵循日惹特定治理情境的行动结果是,家庭强基计划使1 155 名日惹地区的儿童受益,灾害应急响应计划为在地震、火山喷发等事故中受伤的儿童提供了及时的关爱、陪伴、医疗、心理康复等服务[36]。
SCV、JRS、ASB 及AFSC 在东南亚成功地参与治理的案例表明:INGO 的“外来者”组织身份具有先天劣势;其治理行动须与东道国的治理情境匹配;在特定的治理对象与需求下,INGO既不是治理行动的“主导者”,也不是治理实践的“依附者”,而是现实情境下的“参与者”;治理目标一致下的资源互嵌可以实现优化配置,对资源的依赖并不必然导致治理主体间相互制约、冲突;治理资源互嵌可有效克服INGO 的“外来者劣势”并回应其他治理主体的诉求,形成共赢的参与治理模式;组织合法性获取与跨文化适应力增强,治理情境与行动路径相匹配,治理目标与资源互嵌相对应,共同促成良好的治理成效。
四、结语及启示
INGO 在东南亚面临复杂多样的治理情境,现实情境下不存在单一的“理性”或“有效”的治理模式(one-size-fits-all)适用于所有的治理实践。克服“外来者劣势”所带来的阻碍,INGO 应开展与特定时期和地区的社会化建构相匹配的行动路径。为此,“本土化”正是INGO 参与东南亚地区治理应当遵循的原则,通过制度、信息、物资、人力、社会关系等资源的嵌入克服“外来者劣势”危害,消除身份误解和曲解,获取与东道国制度规范和价值观一致的合法性身份,并保证治理效果的充分实现。
在全球治理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角色与国际地位逐步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修正者、建设者,甚至是供给者、创新者[37]。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逐步加大,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是中国“走出去”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面临合法性支持、核心能力培育、资源获取以及外部声誉建构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境外活动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缺乏、跨国运营管理能力弱、境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以及东道国舆论偏见等,阻碍了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
对此,可借鉴SCV、JRS、ASB 及AFSC 在东南亚地区参与治理的成功实践经验,遵循一种治理实践“本土化”的行动路径,即明确东道国的诉求、社会、市场、文化等治理情境,通过资源嵌入规避“外来者劣势”。治理资源互嵌,形成不同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多维度的信任以及互惠生态系统。由此,作为“外来者”和“参与者”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可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身份,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跨文化适应性,强化跨国运营管理能力,通过吸收、利用本地的资金、人力、物资、知识、信息等资源形成新的动力,不断巩固、提升根植于东道国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