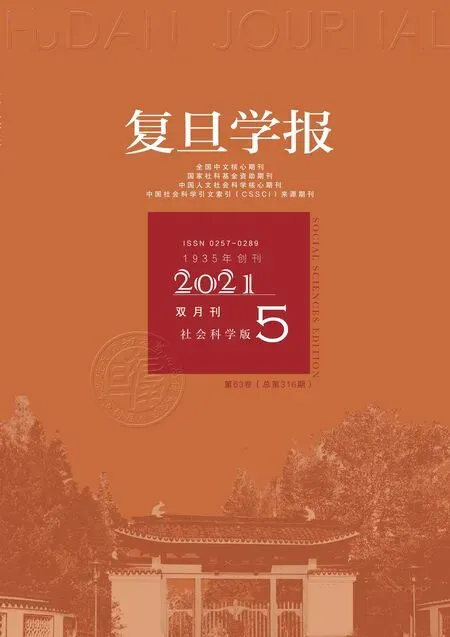追摹“圣人之道”:《续文章正宗》中的理事关系与文道关系
李法然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随着南宋理学的勃兴,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中存在的紧张与不稳定的状态愈发不被容忍。徐洪兴在描述理学发生的过程时,使用了“整合”(integration)这一概念。(1)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6页。如果说北宋理学草创阶段以整合异质文化为主,那么降及南宋,整合的对象便是传统学问中分裂出去的“训诂之学”与“文章之学”,从而消解知识世界中的张力与悖反。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一向被视作重要的道学家选本,真氏被评为“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2)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一《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6页。,其持论当最近朱熹。因而研究者也多力图从《文章正宗》中寻求具有理学家特色的文章学观点,即理学家以“圣人之道”对“文章之学”的“整合”。前贤的研究,总结出《文章正宗》“主理”“求正”“宗经”“尚雅”“崇古”等特色,(3)参漆子扬、马智全:《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孙先英:《论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审美价值取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等。以为此书理学色彩的表现。
作为《文章正宗》的续编,《续文章正宗》尚未见专门的研究。此书专选北宋文章,所谓“宗经”“尚雅”“崇古”便无从谈起;所选作家以“宋六家”为主,而最能代表理学特色的“北宋五子”却无一篇入选,则“主理”“求正”又如何体现?换言之,离开了《文章正宗》的解释框架,当如何认识《续文章正宗》的编选意图,是否落实了理学家文论,落实的效果又如何?窃以为可以从《续文章正宗》的篇章结构入手,推求其中所蕴含的理事对举的理学思想体系,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对文道关系的处理,以此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一、 正续之辨:从《文章正宗》到《续文章正宗》
作为《文章正宗》的续编,一般认为,《续文章正宗》专选北宋文章,是在时间上对《文章正宗》的延续。如明人胡松所作序中,便有“宋真希元氏忧之,乃即先秦两汉迄隋唐,录其文之粹,以正学者之习。……晩岁复取并世名儒之作”(4)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一《续文章正宗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62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481页。云云,即将《续文章正宗》之“续”,理解为入选篇目在时间上与《文章正宗》的承续关系。此外,此书所存三篇宋人跋中,倪澄与梁椅跋均称此书为《国朝文章正宗》,郑圭跋虽称《续文章正宗》,但开篇便有“国朝东都之盛”云云,(5)见真德秀:《续文章正宗》附录,《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94~197页。可见宋人对于此书的认识,也是着眼于时间上接续《文章正宗》的。
此外,关于《续文章正宗》与《文章正宗》的关系,或可作别解,即内容上“正编”与“续编”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两书的编纂过程中看到端倪。刘克庄为真德秀所作《行状》称:
又取周、程以来诸老先生之文,摘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汇次成编,名《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后世文辞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集录《春秋》内外传,止唐元和、长庆之文,以明义礼、切世用为主,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名《文章正宗》,凡二十余卷。(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四部丛刊初编》本。
可知在《文章正宗》之前,先有《诸老先生集略》。关于二者的编选宗旨,一称“关于大体、切于日用”,一称“明义礼、切世用”,大致相仿。而《集略》专收北宋理学先驱之作,则四库馆臣虽认为《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5页。,但从“谈理”的角度讲,《文章正宗》实是《集略》的续作,即在汇次理学文章之后,进而处理理学产生之前的文章。《续文章正宗》在时间上再次回到北宋,内容上则可以视为《集略》续作之续作,即既已向上打通先秦至于北宋五子的文章,再向下处理理学产生之后的非理学文章。
《文章正宗》虽然处理理学产生之前的文章,但其去取却以理学为标准。其主理而不主文,前人论述已多。如张履祥称:“至所选《文章正宗》一书,道理固是正当,文字终觉割裂。”(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四《训门人语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81页。顾炎武称:“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3页。四库馆臣总结道:“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如饮食惟取御饥,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弃;如衣服惟取御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第1699、1699页。与此相反,《续文章正宗》虽也标举“正宗”,却以入选当时已日渐被确立为古文经典的“宋六家”文为主。由此可以认为,《续文章正宗》是一部立足于理学立场,而面向古文传统的文章选本。
真德秀所作文章选本,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独特的文体分类。《续文章正宗》与《文章正宗》的关系,也可以经由文体分类的调整略窥一二。关于《文章正宗》,前贤已有充分的讨论。如钱仓水指出,此书“就文体分类来讲,却确乎是一个大胆的、极有意义的,甚至是雷电般地令人耳目一新的归并”(11)钱仓水:《文体分类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惊异于“四分法”的与众不同。而任竞泽则点出“四分法”的文体学意义:“唯有真德秀《文章正宗》‘四分法’,在分类上完全打破了以体类体裁划分类目的传统思维方式,而以文体的表达功能或者说表现方式来概括归并文类,从而包尽诸体,即吴讷所谓‘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12)任竞泽:《〈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较之《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在文体分类上的新变主要表现为:其一,取消“辞命”“诗”两类;其二,将“议论”类析为“论理”“论事”两类。
关于前者,四库馆臣给出的解释是《续文章正宗》实为“未成之本”(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第1699、1699页。。但此说犹嫌未稳。观真德秀自言《文章正宗》“辞命”类:“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至两汉诏册而止。盖魏晋以降,文辞猥下,无复深纯温厚之指。至偶俪之作兴,而去古益远矣。学者欲知王言之体,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而参之以此编。则所谓正宗者,庶乎其可识矣。”(14)真德秀:《文章正宗》卷首《文章正宗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既然收入“辞命”类文章的下限被定为两汉,自两汉而下皆被排除出“正宗”的范畴,那么专收北宋文章的《续文章正宗》不设“辞命”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此,《续文章正宗》在文体分类上的调整,或许出于真德秀有意为之。
至于《文章正宗》所设“议论”一类,真德秀云:“今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事之属,以为议论之首。他所纂述,或发明义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贬人物,以次而列焉。”(15)真德秀:《文章正宗》卷首《文章正宗纲目》。准此,《续文章正宗》中的“论理”类,大致相当于此处的“发明义理”之属;而“论事”类中,包括见于卷十七至十九的“谏争论列指切时病”“从容讽谏泛陈治道”,以及卷二十有目无文的“议论事宜反覆利害”“与公卿大夫陈论治道事宜”“议论古事得失”“辨论古人是非”(16)真德秀:《续文章正宗》目录,《宋集珍本丛刊》第105册,第641页。,正好与“书疏封事”“敷析治道”“褒贬人物”相对应。可见,《续文章正宗》是将“发明义理”的议论文章单独归为“论理”类,并提至全书之首;而其余的议论文章则统归于“论事”类。梁椅指出:“文以理为准,理到则辞达。公于论理一门最所留意。”(17)梁椅:《续文章正宗跋》,真德秀:《续文章正宗》附录,第195页。可见,这一调整也是出于真德秀本意。
这样,经过真德秀的调整,《续文章正宗》的文体分类显示出不同于《文章正宗》的格局,却可以在北宋找到渊源。苏轼在为欧阳修文集所作序文中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18)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而出于苏门的秦观则言道:
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19)秦观著,徐培均笺注:《韩愈论》,《淮海集笺注》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51页。
观秦观所言论理、论事、叙事,与《续文章正宗》完全一致;而苏轼所言“论大道”可对应“论理”,其余“论事”“记事”也与《续文章正宗》相对应。
从苏、秦二家对上述分类的具体解释,以及所举出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论理”(论大道)对应着儒学,“叙事”(记事)对应史才,“论事”对应吏能,而“诗赋”(托词)则对应辞章,四者均为士人安身立命所需的知识门类。四者的综合正好对应着“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体系,即“集三位于一身的”北宋士大夫的知识结构。理学发展至南宋,已经具备了统合四者的能力,至少在理学家的认识中确实如此。但在《续文章正宗》所承接的苏、秦二家的分类方式中,四者是被欧阳修与韩愈“成体之文”统合于一身的。二人正好是唐宋“古文运动”中前后相承的两位巨匠,可见这样的知识结构,可以以文章为载体加以呈现。
这样,《续文章正宗》作为文章选本,所面对的却不仅仅是文章本身,而是以文章为载体的宋人的全部知识。在理学家看来,重拾北宋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本应由道学思想体系完成。而《续文章正宗》虽立足于理学思想,却以古文传统中的经典文章承载上述知识结构。由此可以认为,作为“正编”的《文章正宗》,其编选意图在于以理学标准铨选宋前文章,而作为“续编”的《续文章正宗》,则意图寻求理学思想体系与宋代经典古文的契合点。
二、理一分殊:《续文章正宗》的理事对举结构
在《文章正宗》所分四类中,“议论”与“叙事”于古文写作之中应用最广,后人也多以此作为接受《文章正宗》一书的框架。如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指出:“读韩文,先钞读西山《文章正宗》内韩文议论、叙事两体,华实兼者七十余篇,要认此两体分明后,最得力。”(20)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七《教授程畏斋先生端礼》,第2928页。这一框架也被沿用于对《续文章正宗》的接受中,如前举胡松序,称此书“取并世名儒之作,分议论、叙事二体”(21)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一《续文章正宗序》,第481页。。但如前文所述,“议论”一类在《续文章正宗》之中已被析为“论理”与“论事”。如此,则“论事”与“叙事”中共有的“事”字,便与“理”构成了一组形上与形下的关系。正如郑圭所说:“夫叙事、论事而不先于理,则舍本根而事枝叶,非我朝诸儒之所谓文也,非先生名书之本旨也。”(22)郑圭:《续文章正宗跋》,真德秀:《续文章正宗》附录,第196页。显然,《文章正宗》的“议论/叙事”结构已经被打破,而“理”与“事”的关系在《续文章正宗》之中被突显出来。
《续文章正宗》将讨论道学义理的议论文章单独编为“论理”一类,并置于全书之首,可见对此类文章的重视。这类文章所收数量为全书最少,在所收王安石《推命对》之后,真氏有评语,称:“论理之文可取者仅如此。”(23)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二,《宋集珍本丛刊》第105册,第661页。可见数量之少,实因去取之严。去取的标准,则严格遵从唐宋儒学复古运动与理学思潮。以此书开篇所收欧阳修《本论》两篇为例。宋人每以欧阳修《本论》比附韩愈《原道》,如“观其词语丰润,意绪婉曲,俯仰揖逊,步骤驰骋,皆得韩子之体,故《本论》似《原道》”(24)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卷一,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8页。,又如“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25)陈善:《扪虱新话》卷十一,《全宋笔记》第五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87页。。可见,真德秀也是比附《原道》在唐宋儒学复古运动中的地位,以《本论》为反映宋代新儒学的压卷之作,而收录于《续文章正宗》全书的开端的。《本论下》主要言性善。欧阳修本不赞同言性,《答李诩书》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真德秀以《本论》收入正文,而于其后全篇附录了《答李诩书》,称:“愚谓公以世人之归佛,而知荀卿性恶之说为非,其论美矣。至《与李诩书》,其说乃如此,故附见焉。”(26)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一,《宋集珍本丛刊》第105册,第646页。可见,在《本论》与《答李诩书》之间,显然是以道学义理为标准进行了取舍。
理学家认为:“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27)陈淳:《北溪字义》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页。因此理须落实在事上,由事显现。同样,在文章学上事与理的关系也被强调,刘熙载便提出:“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28)刘熙载:《艺概·文概》,《历代文话》第6册,第5569页。事理并称,理穷于叙事论事之中。真德秀本人也十分强调理事关系。如其所言:“人之为人,受天地正气以生。故其心虚灵不昧,其于义理,自然有知。……此即良知也,所谓本然之知也。然虽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义理到极至处,亦无缘知得尽。”(29)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对此,徐洪兴解释道:“‘良知’不是义理之极致,因此人须以先验的‘理’去推求事物之理,以此来扩充心中之理,使达到义理之极致。”(30)徐洪兴:《道学思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61~462页。可见“事”既是“理”的反映,也是推求“理”的途径。《续文章正宗》中理事对举的结构,亦当如是观。
余英时指出,宋代的古文运动、政治改革与道学思潮之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儒家要求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3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45、875页。。如果说“理”是这一秩序背后的依据,那么“事”便是秩序本身。余先生同时表示:“我所谓‘秩序重建’是从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算起的。换句话说,人一生下来便置身于一层层一圈圈的‘秩序’之中,每一个‘秩序’都可以是‘重建’的对象。”(3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45、875页。观《续文章正宗》卷三至十所收诸墓志,上至元老大臣,下至妇人、处士,涵盖了家国天下的一切“秩序”。元老大臣、名儒文人与贤士大夫,皆有功业与著述,其事迹关乎治道,与“理”的关系较为显豁,不必赘述。在此重点关注处士、妇人事迹与“理”的关系。
欧阳修《连处士墓表》称:“其长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谨、礼让而温仁,必以处士为法……处士居应山,非有政令恩威以亲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谓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欤?”(33)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30、31、30、36、36、39页。王安石《孔处士墓志铭》称:“汝人争讼之不可平者,不听有司而听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于先生为耻。……盖先生孝弟忠信,无求于世,足以使其乡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尝为异也。”(34)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30、31、30、36、36、39页。兹举此二例,可见《续文章正宗》所收处士墓志,均为能独善一身,进而教化一乡者。王安石所作《王逢原墓志铭》言道:“士诚有常心以操圣人之说而力行之,则道虽不明乎天下,必明于己;道虽不行于天下,必行于妻子。内有以明于己,外有以行于妻子,则其言行必不孤立于天下矣。”(35)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30、31、30、36、36、39页。此言也可以作为上述处士墓志的总结,即真德秀选录处士墓志,是为了展现内明于己、外行于妻子之道,也就是道系于一人之身、一家之内与一乡之间的状态。与此相似,卷十一收入欧阳修《桑怿传》、曾巩《徐复传》《洪渥传》、苏轼《方山子传》与苏辙《巢谷传》,所记皆伟烈奇节之士,或沉于下僚,或居于乡里,或隐于山林,无奇功伟业,而有嘉言懿行。《洪渥传》云:“予观古今豪杰士传,论人行义,不列于史者,往往务摭奇以动俗,亦或事高而不可为继,或伸一人之善而诬天下以不及,虽归之辅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过矣。如渥之所存,盖人之所易到,故载之云。”(36)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一,《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44页。以“不过”亦不“不及”为参照,以“人之所易到”为标准,显示出与上述处士墓志所表彰的独善一身与教化一乡相同的旨归。
相比于一身与一乡,宋代女性的活动空间常被限定在闺阃之内,是齐家的重要承担者。邓小南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妇人不预外事,这在宋代被男女两性所认同。……宋代士大夫所做女性墓志铭,经常刻意强调女性相对于父母、舅姑、丈夫、子女的家内身份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37)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9页。《续文章正宗》所收妇人墓志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如王安石《永安县君蒋氏墓志铭》,称:
太君年二十一,归于钱氏,与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没,太君进诸子于学,恶衣恶食,御之不愠,均亲嫡庶,有鸤鸠之德,终不以贫故,使诸子者趋于利以适己。既其子官于朝,丰显矣,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而家人卒亦不见其喜焉。自其嫁至于老,中馈之事亲之惟谨。……不流于时俗,而乐尽其行己之道,穷通荣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学士大夫之所难,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难也。(38)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30、31、30、36、36、39页。
全篇所言,无非事亲、相夫、教子,与“乐尽行己之道”。篇后附录《答钱公辅学士书》,称:“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39)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30、31、30、36、36、39页。可见,墓志所记载的内容是王安石有意剪裁的结果。曾巩在《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中言道:“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达于天下,而女子言动有史,以昭劝戒。”(40)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30、31、30、36、36、39页。以齐家为先王之治之本,道出了真德秀编选妇人墓志的用意。
刘子健指出,南宋士人发展了儒学中“作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学以致知以及非精英主义的公众教育”,认为“只有成功地建立了道德社会之后,他们才有可能给国家注入新的动力”。(41)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南宋道学家的诉求由教化帝王转向教化乡里,于是闺阃之内、乡党之间的嘉言懿行受到了道学家的关注。上述对于妇人、处士事迹的选录,正与此相符合。
若再将视野放大,安居一乡的处士可以以善行教化一方,则主政一方的亲民官便可以以善政造福一方。这一点在《续文章正宗》“叙事”类中也有所体现。如欧阳修《泗州先春亭记》,“先叙其修堤,次饯劳之亭,次通漕之亭,然后归先春亭,而证以单子过陈,见其‘川泽不陂,梁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之说,谓皆三代为政之法,而张侯之善为政也”(42)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三》,《历代文话》第1册,第670页。。又如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载“本朝孙永复之,民赖其利”(43)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五》,第740、740页。、《越州赵公救灾记》载“救荒之委折备焉”(44)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五》,第740、740页。。此外诸如学记、兴造记、厅壁记,与诸治河、治湖、治井、修城、修门、修堤等记,或考论制度,或称颂善政,为百里侯、二千石之典刑。
由此,《续文章正宗》叙事类备载一人之善行,推衍至一家、一乡之间,再扩展至一方之善政。若再加之卷三至卷九所叙名儒文人、贤士大夫与元老大臣事迹,则构成了自修身以至于平天下的完整链条。前举刘克庄《行状》在记述真德秀编选《集略》《正宗》之前,尚有《读书记》一书:
《甲记》曰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记》曰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记》曰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丁记》曰出处语默之道、辞受取舍之宜,凡二卷。(45)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
四记之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外王”之学。(46)参见刘兵:《真德秀〈西山读书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31页。可以看出,《续文章正宗》理事对举的结构,正好与这套学说相呼应。正如朱熹所说:“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47)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高悬于上的论理文章与广泛铺开的叙事、论事文章,经由《大学》八条目产生了联系。至此,真德秀也通过《续文章正宗》的理事对举结构,找到了理学思想与文章传统的契合点。
三、 圣人之道:以“文”绾合“体”“用”的努力
宋儒刘彝有言:“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48)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一《文昭胡安定先生瑗》,第25页。这里所言“体”“用”,正好对应上文所言《续文章正宗》的理事对举结构。这里的“文”虽未必特指“文章”,但“文章”总是可以包含在内的。且宋代以后“文章”成为知识阶层最为重要的表达手段,故这一概念及其与体、用的关系,姑且可以借用。如余英时所说:“‘文’是一条历史主线,把‘体’和‘用’绾合在一起了。”(4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308页。这种绾合表现在《续文章正宗》一书,便是除在思想上以理学家“理一分殊”的理论框架,用承载道学义理的“论理”文章统摄“叙事”“论事”文章外,也试图在形式上统合古文传统中的经典文章与思想上的理事对举结构。
如前文所述,《续文章正宗》的文体分类可以在苏轼与秦观处寻找到渊源。但与苏、秦二家不同,此书没有单独设置对应辞章的“诗赋”或“托词之文”。在朱熹看来,“文”与“道”根本就是一事:“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50)朱熹:《朱子语类·论文》,《历代文话》第1册,第225页。真德秀显然接受了这一主张。如张健所说:“在《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系统中,并没有文章的位置。当程朱把文道关系置入德言关系架构中,文章就与《大学》的观念架构建立了关联。依朱子之说,《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明明德之事’,能‘明明德’,则‘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者必有文,因而文章的根本在修德。”(51)张健:《义理与词章之间:朱子的文章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因此在《续文章正宗》以《大学》八条目统合“理”“事”的过程中,也就没有必要另外为辞章设立单独的类目,而是直接以当时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宋六家文承载“理”“事”。从中可以看出,在真氏的观念中,“文”与“理”“事”并非是并列的,而是绾合二者的手段,是以理学思想体系统领的一切知识的载体。由此,以“文”绾合“理”“事”,可以视作《续文章正宗》寻求道学思想与古文传统契合点的另一层面。
既然文与道本为一事,那么文章的最高境界便是义理与辞章兼备,即所谓“畜道德而能文章”(52)曾巩:《曾巩集》卷十六《寄欧阳舍人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4页。。刘弇曾对曾巩表示:“如欧阳公之《本论》,王文公《杂说》,阁下《秘阁十序》,皆班班播在人口。”(53)刘弇:《龙云先生文集》卷二一《上知府曾内翰书》,《豫章丛书》本。《续文章正宗》“论理”类以《本论》开篇,而所收曾巩文章也多出自《秘阁十序》。可见上述文章不但在义理方面通过了“论理”类严苛的去取条件,且在辞章方面,在作品产生之初就获得了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吕祖谦评《送王陶序》,称:“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陈,此篇使得疏通不陈,窒塞处能疏通。”(54)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4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页。楼昉评《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称:“法度之文,妙于开阖,可以观世变。自欧、曾以前有此等议论。”(55)楼昉:《崇古文诀评文》,《历代文话》第1册,第497页。黄震也称《推命对》“文极工”(56)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六》,第768、772页。。可见,“论理”一类选文不但以严格的道学义理为标准,且又兼顾文辞的优劣。“论理”类以外,如《桂州新城记》“理正文婉”(57)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六》,第768、772页。、《抚州颜鲁公祠记》“议论正,笔力高,简而有法,质而不俚”(58)楼昉:《崇古文诀评文》,第498、505、482、490页。、《袁州学记》“议论关涉,笔力老健”(59)楼昉:《崇古文诀评文》,第498、505、482、490页。,均是文义俱佳的典范。
然而,“文”与“道”紧密无间的关系,在《续文章正宗》中有时会出现松动。如在苏轼《盖公堂记》之后,附录张耒《药戒》,称:“近世洪内翰景卢以此二篇相参较,以见其繁简优劣之不同。”(60)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二,《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57页。则完全是权衡文章之优劣,而无关义理之妥否。这一点,在处理文学性较强的记体文时尤为显著。叶适指出记文“如《吉州学》《丰乐亭》《拟岘台》《道州山亭》《信州兴造》《桂州新城》,后鲜过之矣。若《超然台》《放鹤亭》《筼筜偃竹》《石钟山》,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又关纽绳约之不能齐,而欧、曾不逮也”(6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历代文话》第1册,第279页。。所举诸篇悉数入选《续文章正宗》。此外如此书所收《相州昼锦堂记》,有“文字委曲,善于形容”(62)楼昉:《崇古文诀评文》,第498、505、482、490页。之评、《木假山记》有“首尾不过四百以下字,而起伏开阖,有无限曲折,此老可谓妙于文字者矣”(63)楼昉:《崇古文诀评文》,第498、505、482、490页。之评等。以上均为传统的古文典范,但未经使之符合道学标准的处理即被收入此书。在这里,《续文章正宗》直接面向古文传统,而未见到寻求与理学思想的契合点的努力。古文传统与理学标准显示出分立的状态。
不止是分立,古文传统与道学标准有时还会发生龃龉。在前引真德秀历数王安石议论之非,并断言“论理之文可取者仅如此”之后,又有“若其他文章,则盖有卓然与欧曾并驰而争先者,各见之别卷”(64)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二,第661页。之语。可见,真氏事实上允许于理不合但文辞可观的文章出现在此书中。例如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朱熹便认为义理不足道而文辞有可观:“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迁。”(65)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7、216、220页。但仅就辞章而言,此篇同样在产生之初便已经获得较大影响,据苏籀记载:“坡撰《富公碑》以拟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铭》《居士集叙》,公极赏慨其文,咨嗟不已。”(66)苏籀:《双溪集》卷尾《栾城遗言》,《粤雅堂丛书》本。且就朱熹指出的“首尾不相应”的弊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吕祖谦以为:“此篇曲折最多,破头说大,故下面应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远,下面未必言远,如一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夸。”(67)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下,第100页。所言与朱熹正相反。于是《续文章正宗》从俗,以辞章可观收入了这篇文章。又如《峻灵王庙碑》与《伏波将军庙碑》,也被认为义理不佳:“如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到得晚年过海,做昌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尼恍惚升天,见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之云,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云云,更不成议论,似丧心人说话!”“《峻灵王庙碑》无见识,《伏波庙碑》亦无意思。”(68)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7、216、220页。却也为《续文章正宗》所收入。甚至在道学家极为敏感的佛老问题上,真氏也会网开一面。苏轼《中和胜相院记》被评为“斯忠于佛者”(69)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四》,第711页。,其入选的意图,可谓与“重彼所以伤此”的《扬州龙兴十方讲院记》等篇正相反。
可见,当文辞确实可观时,无论是与义理离立还是龃龉,真德秀都会放开义理的标准而予以收入。义理标准的松动甚至使《续文章正宗》就文辞本身之优劣的判断,也常常与道学家的评价发生抵触。如朱熹评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其文气象不好”(70)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7、216、220页。,评《潮州韩文公庙碑》“初看甚好读,子细点检,疏漏甚多”(71)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6、226、213、216页。,评秦观《龙井记》“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发人意思”(72)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6、226、213、216页。。“气象”“布置”“实”均为理学家评论文辞的重要范畴,(73)如《朱子语类》评李觏文“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评韩、曾文“却是布置”,评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等。而“气象不好”“疏漏”“架空”的文章被收入《续文章正宗》,显然受到了古文自身传统的影响,如《仕学规范》评《赵清献公神道碑》:“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74)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三,《历代文话》第1册,第319页。《文章轨范》评《潮州韩文公庙碑》则称:“后生熟读此等文章,下笔便有气力,有光彩。”(75)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历代文话》第1册,第1052页。相似地,《六一居士传》在理学话语中被评为“意凡文弱”(76)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6、226、213、216页。“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77)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第216、226、213、216页。,可谓是文义俱不佳,而真氏同样予以收入。在此,其评文话语已经完全脱离了理学思想体系。
真德秀希望以“文”绾合“理”“事”,从而寻求文章外在形式与内在理学思想的契合点。但至此可以看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文”与“道”的关系发生了动摇,甚至对文辞本身的评判标准也在强大的古文传统下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妥协。从这一点上看,《续文章正宗》沟通文章道学的工作尚未获得全面的完成。
四、 余论:道学选本的转型
刘彝所谓“圣人之道”中“体”“用”与“文”的关系,正好对应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之中寻求理学与文章契合点的两个层面:其一,力图以“道”之“一”统领一切知识门类之“殊”,恢复北宋“三位一体”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从而在思想内容上实现理学思想对各类文章的统领;其二,整合以“道”统领的知识体系与“文章”的外在形式,从而恢复文道不分的理想状态。前者反映出道学思想体系,后者则是对文道关系的处理,这使得《续文章正宗》虽然面对古文传统中的经典文章,却又不失理学家的立场。在前一层面上,《续文章正宗》的文体分类与宋人知识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与此同时,其文体分类之中还隐含着理事对举结构,使对应儒学义理的“论理”类文章与对应其他知识门类的各类文章形成了形上与形下的关系,借由《大学》八条目的理论框架完成了在理学思想体系中对宋人各类文章的妥善安置。至于后一层面,也有朱熹“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之言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使“道”与“文”也构成一组逻辑上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但是,如此精妙的理论,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发生了动摇,在兼顾义理与辞章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古文自身强大的传统仍然与道学思想体系保持着离立甚至龃龉。
《续文章正宗》面对古文传统而力图以道学思想加以整合,这一尝试事实上渊源有自。王柏《鲁斋集》有《跋昌黎文粹》,称:“右韩文三十有四篇,得于考亭门人,谓朱子所选,以惠后学。”(78)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十一《跋昌黎文粹》,《续金华丛书》本。又有《跋欧曾文粹》,称:“右欧阳文忠公、南丰曾舍人《文粹》,合上下两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于考亭门人,谓朱子之所选。”(79)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十一《跋欧曾文粹》。可知朱熹曾经编选韩愈、欧阳修、曾巩三家文选。如前所述,朱熹持“文道一贯”说,那么上述选本可以视作朱熹本人对这一理论的尝试。然而,后人在继续这样的尝试时,也会面临相当的思想困境,这一点可以从真德秀的另一则材料中略窥一二:
汉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为尤盛,然其发挥理义、有补世教者,董仲舒氏、韩愈氏而止尔。国朝文治猬兴,欧王曾苏以大手笔追还古作,高处不减二子。至濂洛诸先生出,虽非有意为文,而片言只辞,贯综至理,若《太极》《西铭》等作,直与六经相出入,又非董韩之可匹矣。(80)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六《跋彭忠肃文集》。
此处虽然理义、世教与文章混融一片,但同时又隐然存在着等级差异。欧王曾苏仅获“不减”董韩之评,而濂洛诸子却非董韩可匹,三者之间高下立判。可见在朱熹之后,真德秀对于以道学思想整合古文传统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但两者在这里仍然可以并存,正好对应了真德秀所编的两部北宋文章选本,《诸老先生集略》与《续文章正宗》处理文道关系的方式。《集略》显然是以北宋五子的《太极》《西铭》等篇为道德文章的最高典范。如真氏本人所说:“圣人盛德蕴于中,而辉光发于外,如威仪之中度、语言之当理,皆文也。”(81)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一《问文章性与天道》。然而在《续文章正宗》中,真氏转而面对古文自身传统,以当世所公认的宋六家为“文”的代表,而力图以理学思想体系中以“道”统领的知识结构,即前一层面上已经获得的道学与文章的契合点,对“文章”进行整合。如前所述,这一尝试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留下的有关文道关系的困惑,以及文与道之间的巨大鸿沟,尚待理学家们进一步的探索,以寻求解决的可能。
南宋后期,颇具理学背景的罗大经直言:“‘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论后世之文也。‘文者,贯道之器’,此论古人之文也。天以云汉星斗为文,地以山川草木为文,要皆一元之气所发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绣,虽精妙绚烂,才可人目,初无补于实用,后世之文似之。”(82)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页。明显又回到了重道轻文的路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为“贯道”的“古人之文”留下了位置。在理学传承谱系中晚真德秀一辈的王柏同样热衷于文章选本的制作,编有“《勉斋黄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陈先生文粹》三十一篇”(83)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十一《跋勉斋北溪文粹》。,专选黄榦、陈淳文章,又编有《五先生文粹》,明人赵时春序:“不以名号其书,而直称之曰‘先生’者,惟濂溪周子、洛程伯仲子、秦张子、闽朱子为然……故并称之曰‘五先生’。”(84)赵时春:《五先生文粹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四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知所谓“五先生”,即“北宋五子”之周、张、二程四子,及南宋之朱熹。可见王柏所作选本,皆专以理学家为入选对象,标榜道学传承统序,正反映出南宋后期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方式。由此可见,在朱熹与王柏之间,道学家编纂的文章选本发生了一次转型,而德秀所编收录北宋文章的《诸老先生集略》与《续文章正宗》,恰好对应了这一转型的两端。在《续文章正宗》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之后,南宋晚期理学家开始编选标榜自我门户的选本,以“宋五子”取代“宋六家”,取消了“文”的独立价值,直接将“文”视为“道”的附庸。如此处理文道关系,较之朱熹一代理学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以避免与古文传统接触的方式,来求得在精密而自足的道学思想体系内部获得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