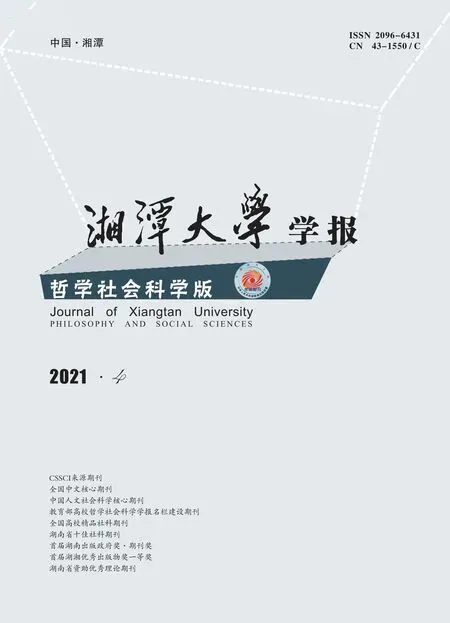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关系的理论逻辑*
——基于共产党创始人、先进分子早期妇女解放论述的考察
韩贺南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1)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启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理论与历史逻辑,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特色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关乎宏大旨趣,关涉妇女与党、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者的学术立场、问题意识,几经变化,此类介绍颇多,无须赘述。仅就近来研究观点的张力而言,确可深入探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特征为“合”与“同”,即合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与其同路同行。这一点国内外学界已有共识。然而,对此利弊得失的评介却观点各异。有研究认为,中国妇女运动具有体制化优势,也有观点质疑阶级解放对妇女问题的“遮蔽”。近年来,一些研究回避这些争论,着力于中国妇女主体性研究。但学理上的深入对话,尚需学界进一步做出努力。本文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如何理解男女性别属性,有哪些概念和观点;怎样理解阶级的涵义,如何认识妇女与阶级的关系。他/她们关于妇女解放的系统论述,多集中于1919年至1921年间。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首先在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下理解文本的意义,自不待言。其次在具体情境下理解文本旨意。关于文本产生的具体情境考据十分困难,需要仔细追寻。此外,当时理论纷争,阶级斗争环境险峻,文本要旨表达隐曲,须得仔细探寻。
一、共产党人早期(1)为了行文简约,本文借鉴学界一般说法,“共产党人早期”为共产党人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称谓。对男女性别属性的理解与基本观点
五四运动以前,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聚焦为某些领域。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1919年下半年至建党前后,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着重系统地阐述妇女解放,尤其是妇女运动性质、方向等重要问题。较多使用妇女(妇人、女人、女子)、妇女问题、妇女运动等概念。然而,在妇女概念背后包藏着性别概念,时称人的“属性”,即“性别属性”,或“男女两性”。这些概念的具体用途与意义,往往关涉妇女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问题。
(一)“属性平等”是民主主义精神“四要素”之一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制度,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最初的转变,不是绝然抛弃,而是有一个丢弃与抉择的过程。这一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有些仍以当时所谓现代民主主义精神为视阈,关注妇女解放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
《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2月)是李大钊第一篇系统论述妇女问题的文章。该文从人在社会组织中的个性发挥、机会与权利角度阐释了现代民主主义精神。他将性别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作为思考人们在社会组织中所处位置的一个维度,从而将性别纳入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分析视角之中,或可言之,他将属性(性别)平等作为体现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文中提到具有不同性别属性的人,应该受到平等对待,这一涵义即有今人所言的性别平等之初步涵义。李大钊此文开篇即明确地阐释了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人人都能够在共同生活的组织中,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诸方面机会均等,发展个性,享有权利。所谓“人人”,指无论何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1]410的所有人,其中的“属性”指性别,李大钊认为性别是人的属性。亦可理解为,人们在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中,不会因为民族、性别、阶级与地域这四个方面特征的不同而处于不同境遇,遭受不同对待,此为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体现。民族、性别、阶级、地域,或可称为“四维”视角,今人称其为“身份”。在这四个要素中,首位者为民族,性别位居第二,而后为阶级和地域。这四个要素的提出与序列,或可见当时李大钊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优先性、关联性的认识。在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下,民族问题当为首位;性别位居第二,亦另有深意(后文论及);阶级问题,当时正在探索之中;地域问题,亦被视为重要维度。
李大钊不仅提出了这一“四维”视角,而且据此分析、评价妇女参政问题。他认为妇女参政运动“是本着这精神起”。妇女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应该同男子一样,有地位、有生活要求,有法律权利。由此,他认为妇女参政运动是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体现,属性(性别)平等是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基本元素。
以上观之,李大钊在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中提出属性(性别)的概念,并初步提出了属性平等的主张,据此分析妇女问题。这些观点是李大钊此时民主主义思想在妇女问题上的体现。它是李大钊民主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亦可见,共产党人早期具有初步的性别认识与观点,是他们整体思想的内容之一。
(二)男女结合一体为“社会本源”
共产党人早期依据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男女性别问题,观点各异。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社会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李达从这一社会学角度阐释了男女两性结合对于社会的意义。
《女子解放论》(1919年10月)是李达系统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代表作品。根据学界对李达“早期生平与思想轨迹”研究,此文为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所作。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取留日官费生,“入东京第一师范数理科学习”[2]15。一年后,因国内变故,官费被取消以及身体原因,辍学回国。“一九一七年春季,李达第二次去东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3]15。此时,李达怀抱着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1918年5月初,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卖国反苏,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抗议。5月7日,学生在东京集会,虽多人遭警察拘捕,仍英勇反抗,后组织“中华学生留日救国团”回国情愿,“李达是救国团的主要代表之一”[2]20。1918年6月,李达再赴日本后,便放弃学习理科,攻读社会主义理论,研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师从马克思主义学者、经济学家河上肇,1920年8月回国。《女子解放论》一文是李达此次回日本一年多所作。
李达在绪论中运用社会系统理论,从人类繁衍的角度阐释了男女两性的结合是社会之“本源”的观点。首先,李达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实在性、相依性与相对性。他认为,社会是个系统的“实在”。它是个人的系统,每个人都是社会系统的一员;社会与个人相互依存。有个人才有社会,有社会方有个人。其次,男女结合为“个人”。李达关于个人的理解颇有寓意。他明确指出“男性与女性结合,成为个人”[4]15,即所谓个人不是指个体的男性和女性,而是男女两性结合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个人是“结合”与“分裂”的对立统一。男女两性结合出生新人,就是一个“结合”与“分裂”的过程。个人——男女结合,分裂——繁衍后代,又必有男女两性。再次,社会是系统的。除明确阐释社会构成与个人构成之外,李达强调社会的系统性特征。他表明,社会是“个人的有机体的集合体,即可称为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4]15。个人是社会单元,“男女两性是组织个人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个人是男女两性的集合体。社会与个人是大系统与小系统,大集合体与小集合体的关系。之所以论及男女两性的结合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旨在说明,民权社会,要以男女两性为中心。仅仅以某一性别为中心,就是虚假的民权。具体说来,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必以男女两性为中心,否则就是谬误,失掉了社会的真价值。在这里,李达在民权社会的视角下,将男女两性的结合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作为逻辑起点,阐释妇女解放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李达论述的逻辑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是由“个人”的不断“结合”与“分裂”而存在和延续的。所谓个人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分裂是指生育后代。个体的男性和个体的女性单独不能“结合”与“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女两性结合才成为“个人”。社会是个有机的系统,社会是大系统,“个人”是小系统。小系统健康,大系统方得强健。由此,为社会进化计,“个人”所包含的男女两性,必得优良和谐,这就要以男女两性为中心,妇女解放的意义也便在此。
李达关于男女性别的阐述,其逻辑起点不是个体的性别,而是开言即论男女两性的结合、繁衍。乍看起来是在谈人类的繁衍,其实不然。他一开始就赋予繁衍以“结合”与“分裂”的涵义,以社会存在与进化的意义。从而,男女性别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本质上是社会的,因为男女两性的结合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简言之,李达所谓男女性别是生理与社会一体的人的属性,是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基础。从而,也说明男女性别具有同等的价值,妇女解放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李达这时关于男女性别的观点,仍以民主主义为视角,借鉴了进化论、社会系统论,也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和合”的影响。他的男女性别的智识、妇女解放的主张,是他整体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男女气质的价值思考与评价
共产党人早期认为,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专制制度,也是男子专断制度。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在寻找改变专制制度的各种思想资源和实践方法过程中,将男女性别气质纳入视野。
关于男子气质与妇女气质的价值追问。 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在回应人们对妇女参政的意见时,直接运用“男子的气质”和妇女的气质概念,并对其价值评判提出新的思考。他在介绍美国妇女参政时,列举两种反对观点。一种认为,“妇人决一件事,往往不靠理性,单靠感情,所以让他们去做政治家,很不相宜”[1]411。另一种是对妇女能力怀疑。关于第一种意见,李大钊举出实例:“孟塔拿州有位女议员”“一时世间对他很有不满的批评”。具体情况为,当时美国对德宣战,决议时,两次叫她表达意见,她均不语,“第三次问他,他才哭着,颤声答了一个‘NO’字”[1]411。对这件事,李大钊一连提出五个疑问:“那些政治家的理性,都是背着人类感情的么?那些背着人类感情的理性,都是好的么?都是对的么?这个不忍的感情,都是错的么?都是坏的么?”[1]411首先,这里提出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是“背离”的还是相符的?即理性应不应该符合人类的感情,能不能使理性顺应人类的情感?李大钊文中的答案是肯定的。其次,是对理性的价值判断,“理性”不一定全部都有价值。背离情感的理性就不一定是好的理性。此外,就是对“感情”的价值肯定。这里的“感情”指决断事情“单靠感情”,有今人所谓感性之意。李大钊认为对战争“不忍”的感情不一定都是错的,都是坏的。无疑开启了对理性与感性关系,理性与感性价值判断的新的认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男女性别特质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以及对男女两性特质绝对肯定与否定的认识。
李大钊上述观点的思想来源或与中国传统文化刚柔并济、阴阳互补的思想有关,同时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女性优秀品质的深切认同。
关于男女特质的“自然均衡”。 李大钊于《妇女解放与Democracy》(1919年10月)一文中,在建立民权社会的重大主题下阐释妇女解放问题,直接提出、运用“男子的气质”和妇女的气质概念。该文提出,妇女解放是民主的必备条件。意为,妇女解放,妇女参与社会生活,民主精神方始建立。关于这一观点,李大钊从性别气质角度展开逻辑论述。他指出,男性气质以专制为特征,女性气质以平和、优美、慈爱为特质。而偏偏又是男子独占社会,所以男子的专制气质造成了社会的“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要使社会具有民主精神就要克服男性专制气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女性气质相与调剂,促使人类气质的自然均衡。要用女性气质调和男性气质,就要妇女解放,改变妇女幽闭在家的状况,使妇女参与社会。这里一方面表现出对女性气质的价值肯定;另一方面,提出了性别气质融合、优化的观点。从而,这一性别气质的微观视角开启了妇女解放,造就社会民主精神的逻辑思路。
(四)妇女的能力、智识与主体性
共产党人早期讨论妇女运动,针对时人的种种质疑,肯定普通平民妇女参与社会的能力,提出妇女的主体性问题。
当时,关于妇女及其妇女运动的评价,无论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女性能力的否定和质疑。针对这一问题,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其一,打破妇女能力低弱的看法,肯定妇女的聪明智慧;其二,指出了妇女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主张。当时倡导妇女解放,遇到的认识问题首先是对妇女能力的否认。李大钊在对美国妇女参政的具体考察中发现,在已经获得选举权的男人和女人中,许多妇女比男子更有独立判断能力。他举出实例:“考劳拉豆州有夫妇二人,各有各的投票权,他们所欲选的人,却正是反对党”[1]411,这里说明,妇女有自己的主见,并未与丈夫随波逐流。虽然“其妻所选举的人归于失败,选举后家庭的感情,并不以是生何影响”[1]411。他们各自行使选举权,并未因为妻子参政,或因为夫妻意见不同而影响家庭生活。此例说明,对妇女参政能力(选举权)的担心,以及对妇女参政影响家庭生活的说法不必要、不可信。以往,肯定妇女能力者,不乏其人,但多为赞许凤毛麟角的精英女性,而李大钊则为对多数平民女性能力的肯定。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此文对美国妇女参政的评论另有旨趣,须得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中国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此时妇女参政运动较为沉寂。而美国妇女参政已经开始,李大钊旨在以实例说明妇女具有独立决断能力,倡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此外,李大钊从女性问题应由女性自身表达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参政的合理性,进而提出了女性的主体性这一重要议题。李大钊言到:即便是关于社会制度、文化教育、法律习惯等方面,妇女的判断力较男子为弱,然而,关于妇女切身问题,“与其父兄夫友全不相干的问题,令他们自己也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难道不比由男子一手代办,把妇人当做一阶级排出政治以外妥当的多么?”[1]411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批评了女性被埋没在家庭和男人背后的现象,表达了在实践中将妇女作为独立个体,自我主体的观点。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亦须回溯当时妇女解放思潮。女子人格独立是其时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人格独立,要义为培养理性精神,做大群(社会)里独立的人。这是一种要求和期待。而对女性能力的肯定和自主性倡导则是一种主体性视角。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关于男女性别概念与观点的阐述,较多缘起为对具体问题、事件的分析与评价。其旨意均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或在重大社会问题,诸如现代民主主义、社会进化的视域下讨论妇女问题,从而言及性别,将性别从妇女概念背后引申出来,前文将“属性平等”作为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要素便可见之;或由妇女、性别谈起,关连重大社会问题,如前所论两性气质的均衡,抵御社会专制问题便是显例。
关于性别,运用“属性”,男女两性,与今人所用“性别”义近,而词不同;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词、义与今人大同小异,表述为“男子的气质”、妇女的气质,涵义与今人相同。且对“妇女的气质”予以较高的价值评价。男女性别属性是既有生理含义又有社会意义的复合概念。
二、阶级视域下的妇女与妇女运动
自1919年下半年,尤其是1920年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进一步探索与选择,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及先进分子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着重于从妇女、妇女运动的阶级分析入手,引导妇女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劳动阶级妇女运动中来。
(一)最先“为奴”的“妇女阶级
妇女的阶级,在理论上是当时妇女运动的核心命题之一,直接关涉妇女运动的方向、道路等重大问题。而在这一问题成为问题以前,人们比较关注妇女运动的合情、合理、合法性。妇女的阶级问题何以被提出,与两个问题直接相关。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二是当时救国救民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为共产党创始人分析中国社会,分析妇女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他/她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怎样分析中国妇女运动的阶级,其中的逻辑理路如何,许多论述可见其脉络。
1919年5至11月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巨著,还相继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真正的解放》等文章,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首先是经济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在经济上,主要是“有产”与“无产”,有产阶级拥有土地、资本等生产手段;无产阶级没有土地、资本等生产手段。政治上,有产阶级压迫、掠夺他人;无产阶级被掠夺、被压迫。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害”相反。关于阶级组织的改造,李大钊认为,“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5]481。以上阶级划分的标准,以及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为妇女的阶级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李大钊的观点,首先,妇女是半数人口,无疑是社会中的多数人;其次,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当为“不利阶级”,为阶级改造首要关注群体。
王剑虹在《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1921年12月)一文阐释了阶级的由来,认为阶级是因为物质的争斗而产生的。谈到:“人类因为受了物质的支配,社会上发生了抢夺、争斗的事实。结果,生出了种种阶级”[6]93。王剑虹此文隐约提出了妇女整体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看法。首先,她认为,人类社会初年,男性征服女性的时候,就出现了男子阶级和女子阶级。“男子是压迫阶级,女子是被压迫阶级”[6]93。她在文中没有详细阐释这一过程,但从文中大意可见接受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女性是最先成为奴隶的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早在1908年,《天义报》“第16至19卷的女子问题研究专栏中,第一次刊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的部分译文”[7]143。王剑虹此文发表一年以前,“恽代英于1920年在《东方杂志》摘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二章的内容”[7]144。当时,李达的《女子解放论》、李汉俊的《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1921年8月)都曾根据恩格斯的观点阐释过“女权不竞之由来”。王剑虹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源头,认为从当时妇女地位沦落的情况看来,妇女整体为奴,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前,时人的阶级概念带有封建宗法等级制的涵义,颇似今人的阶层。人们看待妇女的阶级身份,往往依据其父亲和丈夫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改变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对阶级的看法。首先是阶级关系的简单化。王剑虹谈到,“近代产业革命的结果,资本制度把阶级关系弄简单了。即是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个是有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6]93。阶级的核心涵义简单明了,即是否拥有财产与是否被压迫、被掠夺。根据这一标准,妇女整体是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一方面,妇女没有财产,没有资本;另一方面,当时对妇女解放的倡导,就是针对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和现实,许多事实足以说明妇女是被压迫、被掠夺的。
从当时的一些文本来看,王剑虹最早明确提出妇女整体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有一定的理论和历史逻辑的。此外,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女性先进分子首先提出这一问题,或可说明她们对妇女问题感受深切,解放要求强烈,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二)“平权”与“驱穷”:妇女运动的阶级差异
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及先进分子早期对妇女运动的阶级分析,主要关注不同阶级妇女运动的宗旨、目标与基本诉求,比较其异同,着重分析它们与救亡图存社会主题的关系。
陈望道的《我想》(1920年11月)一文,首先对妇女运动进行阶级划分。他将妇女运动(称“女人运动”)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第二类是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为“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第四阶级的女人运动为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其次,分析两种妇女运动的诉求。认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的目标是“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去的种种自由和特权”[8]102。用今人话语来说,即是基于性别的压迫与歧视。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8]102。再次,分析两种妇女运动的对象。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8]102。认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斗争的对象是男人,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斗争的对象是资本家。当时,人们对这些问题,不甚明了。陈望道曾经谈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种倾向即是以新旧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又“浑称为新,浑称为旧”[9]39,认为,“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9]38。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译稿,半年之后,发表《我想》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妇女运动进行了上述分析。旨在明确哪种妇女运动更合时宜,更有利于救亡图存。明确反对在现存制度下追求所谓男女平权,主张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的联合。
共产党人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析妇女问题,首先表现为,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阐释妇女地位的演变;其次,就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妇女及妇女运动。诚然,限于当时的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程度等问题,他/她们这时关于妇女和妇女运动的阶级理解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为基本观点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对第三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解过于简单,但将中国妇女运动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范畴。
三、阶级“根本”、妇女“优先”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机缘
怎样认识阶级与性别,如何理解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异同,妇女解放伴着劳动解放进行具有怎样的理论逻辑,在共产党人早期的许多论述中可见其基本观点。
(一)妇女解放的“优先性”
共产党人早期关于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论述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其一,唯其艰难,当为“首先”。 妇女解放优先性的观点,首先基于对阶级与性别异同的辨析。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中谈到阶级是可变的,性别是不可变的。“一切阶级都可变动”[10]90,不但可以变动,甚至可以消灭。说到底,阶级是个贫富问题。“富者可变为贫,贫者亦可变为富,地主、资主可变为工人,工人可转为地主、资主”[10]90。“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10]90。这里主要指生理性别的不可变。乍看起来没有明确指出性别的社会性,但已经感到基于生理性别的社会差别,即妇女群体所受压迫的深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认为“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10]90。因为性别不可改变,唯其艰难而要优先解决妇女解放问题。
其二,压迫深重,必得优先。 关于妇女所受压迫深重及其特殊性的问题,多有基于性别的,诸如来自性、生育乃至婚姻的种种事实说明,而在更深刻的理论层面上的认识,沈玄庐在《〈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1921年2月)中做了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言到“劳动者的找不到资本,正如妇女们的没有社会”[11]85。劳动者被资本家压迫,而妇女则没有成为“社会人”,没有成为构成社会的“人类”。妇女解放,首先要恢复其作为人类的成员,恢复其人的资格。所以妇女解放,使妇女成为人的问题必得优先解决。
其三,关涉种族存亡,理当为先。 共产党人早期对妇女解放的优先性认识,当与对妇女和种族关系认识有关。当时进化论、人类学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亦引起关注。李达翻译了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该著根据人类学家包芬(巴霍芬)、马克列南(麦克伦南)、莫尔甘(摩尔根)(2)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本文根据今人所熟悉的译法所加。的观点,阐述了人类由女性中心转变为男性中心的过程。发现这种转变初期,对妇女十分苛酷。书中引用社会学者斯宾塞的观点,如果对妇人的酷虐超过一定限度,“若对于妇人行无制限的虐待酷使,必至于灭种绝族”[12]428。这些观点对人们认识妇女与种族问题提供了历史教训,启发人们关注妇女与种族关系。此外,高畠素之还谈到,善待妇女,可以培养爱他之心。仍然引用斯宾塞的观点,说明“人类的历史中,最惨酷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妇人的待遇”“无论什么民族,其爱他的精神的平均程度,依妇人地位的高低可以推测而知”[12]428。这里从人类情感,从爱他之心的培养角度谈论社会、男人善待妇女问题。共产党人早期不仅注重妇女对于种族延续的重要作用,而且认为,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培养,当从妇女解放首先做起。可见,他/她们受到进化论、社会学理论的启发,而又对其改造和超越。
以上,基于人们性别属性的不可变性,妇女解放艰难性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地位的非人类化、妇女与民族存亡的关联性等认识,似乎大抵从某些方面呈现了共产党人早期对妇女解放重要性、优先性认识的理论逻辑。
(二)阶级解放为“根本解决”
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共产党人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妇女解放问题,着重探寻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寻求根本解决的办法。
“经济组织的变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阐释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解决“经济问题”“变动经济组织”。言到:“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3]55。此外,李大钊认为,要变革经济组织,解决经济问题,要采取阶级竞争手段。如果“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13]55。他指出“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13]55,即是不运用阶级竞争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在这里他明确提出,运用阶级竞争的手段改变经济制度,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李大钊主张运用阶级斗争手段推翻现存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妇女问题。 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1921年1月)一文中,着重指出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唯赖社会主义。他指出:女子问题“零零碎碎,没有系统”[14]144“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14]147。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根本解决妇女问题,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资本家没有分别,大家都要作工”[14]147,首先解决了妇女受资本家压迫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14]146,从而解决了男子压迫女子的问题。然而,离开社会主义,即便妇女走出家庭,也摆脱不了奴隶身份,只能是从家庭奴隶到资本家奴隶。
妇女经济独立只有消灭私有制一途。 李汉俊的《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1921年8月)一文,针对当时被人们所认同的妇女解放首先要经济独立问题,阐释了究竟怎样才能经济独立的观点。他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阐释了妇女受压迫地位形成的过程,指出,女子失去经济独立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产生了现存私有经济制度。所以,“女子要求经济独立,只有打破现在私有经济制度的一途”[15]306。这里已经提出要使妇女经济独立,就要消灭私有制问题。
合而“优先”。 需要明确的是,前文已述,妇女解放是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并不是用阶级解放代替妇女解放,也不是遮蔽妇女解放,而是在劳动解放的进程中优先解决妇女解放问题。简言之,合而“优先”。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妇女问题,针对妇女运动的诉求,研究如何才能根本解决妇女问题。基本沿着这样的思路:改变现存压迫妇女的双重专制制度,即男子专断和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首先改变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大致提出了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的路径。其中,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根本解决妇女问题,李大钊认为,经济基础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解决了。或可看作,根据当时第三阶级妇女运动的各种主张包括参政、职业、教育、法律等等来看,均可以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似有将性别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涵义,但没有明确提出。李汉俊则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运用妇女地位演变的历史规律,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方能根本解放妇女的问题。陈独秀则认为,社会主义消除了有产者压迫妇女的阶级基础,同时,社会主义价值观亦消除了妇女依附于人的观念。这些观点越来越明晰,妇女解放要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6]161。共产党人早期关于妇女解放道路的理论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开启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做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
结论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是在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下,针对当时妇女运动情况,回应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旨在把握妇女运动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第一,关于男女性别属性的概念与基本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性别概念与观点,是在分析妇女运动中的具体问题时被提出和应用的。或者说,男女性别属性是他们分析妇女问题的重要概念。首先,关于男女性别属性概念。共产党人早期的性别概念最初出现在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中。当时的用法为“属性”,即性别是人的属性。如前所言,李大钊认为在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中,不论何种民族、属性、阶级、地域之所有人都应该发展个性,享有平等机会和权力,谓之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在共产党人早期的性别观点中,李大钊首次提出“属性平等”的概念,或可理解为今人性别平等概念的最初形态。其次,关于性别气质。在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主义精神的论述中,出现了性别气质的概念,当时用法为“男子的气质”与女子的气质。男子的气质主要特征为专断、刚愎、冷酷,妇女的气质为平和、优美、慈爱;李大钊主张妇女解放,参与社会,使两性气质“自然均衡”,以抵制男子专断的社会氛围。再次,肯定妇女特质的价值。认为男子的理性与女子的感性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质疑理性为优,感性为劣的价值判断。最后,为妇女主体性的认同。认为妇女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应为自己切身问题做主,而不应该由父兄代言。
共产党人早期的男女性别属性概念与观点主要是在民主主义视域下,借鉴了进化论、社会学、人类学等科学理论,但在某些看法、观点上又有所超越。诸如,借鉴了社会系统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将男女两性的结合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子系统。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思考妇女解放对于民主社会建设的意义,认为真正的民权社会,应该以男女两性为中心。此外,他/她们的男女性别属性的观点,受到了中华民族“阴阳和合”“刚柔并济”的文化滋养。
第二,关于阶级概念的理解以及妇女、妇女运动的阶级问题。共产党人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妇女群体及其妇女运动。将有无财产及处于压迫或者被压迫地位作为基本标准,认为妇女从历史上就无财产,处于被压迫地位,妇女整体是被压迫阶级;将妇女运动主要分为第三阶级、第四阶级也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妇女运动。辨析其宗旨与目标的异同。认为第三阶级要辅助第四阶级妇女运动,将妇女运动的中心转移到第四阶级妇女运动上来。
第三,关于男女性别属性与阶级的异同。认为男女性别属性与阶级“有不同的事实存在”。性别是不可变的,阶级是可变的。妇女受压迫更加深重,又关系民族存亡,妇女解放应该首先解决,但唯赖阶级解放才能根本解决。妇女解放要走劳动解放的道路,在劳动解放的进程中首先解决妇女解放问题。
共产党人早期关于妇女问题较为系统的论述,集中在五四运动前后,尤其是1919年下半年以后。这一时期,他们开始逐步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价值肯定,传播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探讨并初步选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意识,理论来源,理论目标等诸多问题都受到特定历史环境影响。这些理论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提出妇女解放伴着劳动解放进行,开启中国妇女解放道路打下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