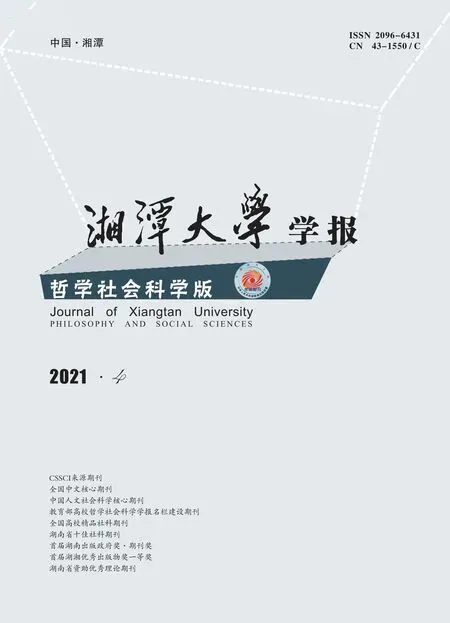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廖四平,战格格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
袁可嘉的诗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戏剧化论”(1)关于“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戏剧化论”的具体内容,参见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另参见常文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六章。“戏剧主义论”等内容。其中,诗的“本体论”即关于诗的“本体”的理论,主要论及了诗的“本体”“诗与非诗”“诗的语言”“诗的主题”“新诗的感伤”“新诗的晦涩”等问题;诗的“有机综合论”即关于新诗要做到“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的理论,主要论及了“现实”“象征”“玄学”“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等问题;诗的“艺术转化论”即关于诗的“生成”的理论,主要论及了“现实与诗”“政治与诗”“经验与诗”“诗艺与诗”等问题;诗的“戏剧化论”即关于诗创作要借用戏剧创作的方法、诗要吸收戏剧的元素的理论,主要论及了诗的戏剧化及其一些具体的方法等问题;“戏剧主义论”即关于要采用戏剧主义的观点来评论诗的理论,主要论及了诗歌批评及其方法、原则等问题。
袁可嘉曾明言自己的诗论“受到了瑞恰慈(又译为瑞恰兹、理查兹等——引者注)、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1]95,也就是说,在袁可嘉自己看来,其诗论受到了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从袁可嘉诗论的具体观点和文本来看,也的确如此。
一、袁可嘉诗论的具体观点与西方影响
袁可嘉的诗论几乎在所有的具体观点上都受到了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其中,在以下问题上的一些具体观点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
(一)“诗与非诗”
袁可嘉认为:“诗歌作为艺术也自有其特定的要求”[2]5,不能驱使诗与科学争“真”、与哲学争哲理的渊深,也不能用诗来代替传单、手榴弹,否则便使诗远离其本体而沦为“某种欲望的奴隶,工具”[2]85-86。袁可嘉的这些观点与瑞恰慈的相关观点颇为一致,如瑞恰慈认为: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或科学的真实——它所注重的是“合情合理”地表达其内容[2]37。而袁可嘉对瑞恰慈“情有独钟”,非常服膺——他认为:在西方,“批评以瑞恰慈的著作为核心”[2]3;他自己也属于瑞恰慈之类的“批评家”,即注重批评的“科学”性,把批评当成一种“单独”的“理智活动的作业”[2]143。因此,袁可嘉这些关于“诗与非诗”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瑞恰慈的影响的。
袁可嘉还认为:诗有各种不同的诗,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但好诗与坏诗、诗与非诗又绝对是有区别的,“我们取舍评价的最后标准是:‘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艾略特)”[2]7——在这里,袁可嘉是认同性地引用艾略特的观点的,因此,袁可嘉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二)“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
袁可嘉认为:从“主潮”的角度来看,现代诗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2]28以成为一种“包含的诗”[2]35,具有“高度综合的性质”[2]3。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所受的西方影响也具有“综合”性:
其一,受到了瑞恰慈的影响——瑞恰慈认为:诗可分为“包含的诗”与“排斥的诗”;“包含的诗”所追求的是“冲动的平衡”,而诗的本质是诗人的“整个心理状态,精神状况的心理学概括”[3]322。袁可嘉所使用的“包含的诗”这一概念本是借用于瑞恰慈,其关于“包含的诗”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瑞恰慈这一观点的引用和引申[2]35-36。
其二,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袁可嘉认为:艾略特的诗剧,如《大力士斯威尼》《大教堂中的谋杀》等及长诗《荒原》都表现了西方“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4]53。同时,艾略特认为,玄学派诗人注重运用“曲喻”——“曲喻”不仅为玄学派诗人所共有,而且作为一种风格的要素,使这些诗人自成一派;注重推敲锤炼、巧用心计地将辞格延长至极致;常常不满足于对比喻内容单纯的解释,而是注重思想的快速联想,将“最异质的意念”通过想象“强行栓缚在一起”并形成一个整体;注重将各种意象和多重联想通过撞击重叠而浑然一体;具有一种将任何经验吞噬的感受机制;17世纪以后,感受力出现“分裂”,之后一直没有恢复[5]31-32。袁可嘉的观点与艾略特的这些观点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受后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现实与诗”
在袁可嘉看来,现实既包括“外在的现实”,又包括“内在的现实”[2]44;诗要紧密地把握“现实人生”[6]60,并应包含、解释、反映“人生现实”,但作为一种艺术,诗又必须具有“诗底实质”[2]5。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一是明显地受到了奥登、艾略特等的影响:奥登曾在1938年有过中国之行,他在中国创作的《战时十四行》将现实题材用现代派手法加以表现,该诗对袁可嘉的诗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袁可嘉曾坦言自己所写的《上海》《南京》《北平》等诗歌受到了该诗的影响[7]1。同时,袁可嘉认为奥登和艾略特的诗歌“极度个人性里有极度的社会性,极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里有同样浓厚的理想主义的气息”[2]199,认可艾略特的“文化综合”和奥登的“社会综合”的观点[2]200-205——而这“两位诗人的现代主义诗艺都浸透有对现实的强烈关注”[8]87。
二是明显地受到了瑞恰慈、勃克等的影响:“袁可嘉对现实的关注,是主张现代诗的感受力应关注现实、包容现实;与现实主义诗学主张反映现实、再现现实是有本质区别的”[8]90,瑞恰慈的实用批评非常注重诗歌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作用,勃克力图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融为一体。
三是明显地受到了史本特、里尔克等的影响:袁可嘉所钦佩的对待现实的态度实际上只有两种,即“奥登、史本特(今多译作斯彭德)诸人对现代人生、当前社会展开正面的猛烈攻击”和里尔克的那种“足以代表现代诗人综合性的广度与深度”的对现实的沉思[8]91,“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所参考的诗歌范本显然是早期奥登的那种左翼色彩浓厚的现代主义诗歌”[8]86。
(四)“诗与经验”
袁可嘉认为:“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渲泄”[2]47,但“在生活里有生活经验与诗经验”[2]67,抽象的“说教”与宣泄似的“感伤”虽然都属于生活经验,也可能是诗经验,但不一定就是诗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意志只是一串认识的抽象结论”,常常用几个短句就足以把它清晰地表达清楚;情绪也可以靠几声呐喊“渲泄无余”[2]24,诗的经验虽然来自实际生活,但不就是也不“止于生活经验”;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转化或消化”的过程[2]160,“人的情绪是诗篇的经验材料”[2]61;艺术品的意义、作用全在于其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2]3,多数新诗“失败的原因”在于“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2]24;诗篇的优劣与否完全取决于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2]6。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首先,与艾略特相关观点有明显的一致之处:艾略特认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及集中之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诗人所应注重的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和“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没有的感觉”[5]7-8;“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最伟大的生命力和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9]3“思想对于邓恩来说是一种经验,它调整了他的感受力”[5]31-32。
其次,与瑞恰慈的相关观点有明显的一致之处:瑞恰慈在《诗的经验》中阐释过“经验”,认为艺术或诗的创造都具有调和最大量、最优秀的冲动的心神状态的功能,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
最后,与里尔克的相关观点有一致之处——后者认为:诗并非只是情感,而是“经验”[10]50;并要求将生活的体验转化为诗的经验。同时,就具体情况而言,中国现代诗人“诗是经验的传达”的理论,“更多的是通过冯至从里尔克那里继承而来”的。[11]110
因此,袁可嘉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明显地受到了艾略特、瑞恰慈、里尔克等的相关观点的影响。
(五)“诗的戏剧化”
袁可嘉认为:无论是就人生经验的本身而言,还是就作为诗动力的想象以及诗的语言而言,诗都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它所形成后的“模式”必定是戏剧的[2]34;同时,“复杂的现代经验”也不能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因此,“诗底必须戏剧化”便成为现代诗人的“课题”[2]47。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相关观点的影响:
其一,受到了勃克的影响:诗的“戏剧化”这个术语源于勃克——在后者看来,包括抒情诗在内的任何非情节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戏剧性结构”“人生冲突在作品中像戏剧展开并得到象征性的解决”[12]185-186。
其二,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艾略特认为,诗的价值并不在于感情的“伟大”与强烈,而在于艺术作用的强烈[5]6;一个抒情诗人“能为每个人说话,甚至能为那些与他自己迥然相异的人说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有能力在某一时刻使自己成为每一个人或其他人”[5]170;现代诗里既有诗人自己说话(或者是不对任何人说话)的声音,也有诗人对听众讲话时的声音以及诗剧的声音[5]240-254;伟大的诗都是戏剧的,“谁又比荷马和但丁更富戏剧性?”(2)艾略特语,转引自陈旭光《走向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论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成熟》,《学术界》,2000年第6期。[13]242
其三,受到了瑞恰慈的影响:瑞恰慈认为,“具有戏剧性结构的诗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想象”[14]273。
其四,受到了奥登的影响:奥登是“红色三十年代”中诗歌“戏剧化”尝试者中的代表之一;同时,他注重在诗中以机智、亲切和轻松隐藏关注现实的热情的方式抒情。袁可嘉称奥登是一个“有名的诗坛的顽童”[2]28,认为纯就诗题材接触面的广度而言,奥登绝对地超过梵乐希、里尔克及艾略特,“只要一打开他的诗总集,你便得钦佩他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2]27,赞赏奥登“对德籍犹太人,战时难民,及被压迫者的深厚同情”,明言“我们尤其不能忘怀他访问中国战场时所写的数十首十四行诗”[2]194。
其五,受到了维姆萨特的影响:维姆萨特认为,凡真正的诗均为复杂的诗,且“正是靠了其复杂性,才取得艺术统一性”[15]264“好诗的统一性与成熟性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我们在诗中所寻找并找到的那种统一性只有通过构思的复杂性才能取得”[15]265“美的统一和秩序……只能靠分歧而取得——只能靠某种斗争”[16]90。
(六)“想象逻辑”
袁可嘉认为:“想象逻辑”即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2]19,它具有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完全依赖结构上的安排”[2]37,强调诗歌组织的“高低起伏,层层连锁”[2]19,不太看重“常识意义的起承转合”[2]37,艾略特长诗中的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的片段便是运用想象逻辑创作出来的。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明显地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袁可嘉认为“想象逻辑”本是艾略特为击破传统的、狭隘的、平面的结构理论而基于经验而提出[2]37,并以艾略特的诗歌为依据具体地阐述了“想象逻辑”。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了柯勒律治(又译为柯尔立奇——笔者注)、瑞恰慈、克罗齐、玛里丹等的影响——柯勒律治认为:想象常常存在于“相反的不谐的因素的平衡调和之中;存同与异、抽象与具体,观念与意象,殊相与共相,新奇与陈腐,异常的情绪激动与异常的井然秩序的结合之中”[2]33;瑞恰慈认为:诗想象具有有机的综合能力,能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有条理的反应[17]103。袁可嘉认同柯勒律治、瑞恰慈的观点,并在论及“想象逻辑”时说:柯勒律治、瑞恰慈所说的“诗想象”实际上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以及法国当代哲学家玛里丹所说的“创造行为”[2]33。
(七)“戏剧主义”
袁可嘉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系统,“戏剧主义”主要有四种特点和长处:其一,其批评标准是“内在”的,而不是依赖诗篇以外的任何因素的[2]35;强调批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不是“作者的人格”[2]6——表现了“强烈感情或明确意志的作品也就未必成诗”[2]24。其二,强调诗的创造是一个连续的“象征的行为”,认为诗绝不是像写信那样——先“写好信(实质)”,然后“塞入信袋(形式)”[2]36。其三,十分重视诗的结构,认为诗中不同的因素产生不同的张力,各张力彼此修正补充、推广加深而“蔚为一个完整的模式”“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2]37。其四,它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分析的——与以印象为主的印象派及以各种教条为权威的教条主义等十分尖锐地对立;它常用的术语主要有“机智(wit)”“似是而非、似非而是”(paradox)、“讽刺感”(sense of irony)、“辩证性”(dialectic)……“讽刺感”即作者在指陈自己态度的同时,希望也有其他相反相成的态度能使之明朗化[2]37-39……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显然地受到了西方相关观点的影响:
第一,“戏剧主义”这一术语直接源于勃克——“戏剧主义”是勃克的AGrammarofMotives一书的中心术语[12]187,而就袁可嘉的诗论而言,“勃克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这位试图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融为一体的‘被奥登称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曾多次被袁可嘉提及”[8]90。
第二,关于“批评标准”的观点明显地受到了艾略特的相关观点的影响——艾略特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诗人只有一个特殊的工具——使种种印象和经验在这个工具里以种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相互结合,“许多对于诗人本身是很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在他的诗里尽可以不发挥作用,而在他的诗里是很重要的呢,对于他本身和他的个性也尽可以没有多大关系”[5]6,因此,“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5]4。
第三,关于张力的观点明显地受到了艾伦·退特等的相关观点的影响——艾伦·退特认为:诗的意义即其张力,即读者能在诗中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8]117;罗伯特·佩·沃伦将张力视为诗歌的结构的本质[19]181-182;布鲁克斯认为诗是矛盾的语言。
第四,关于讽刺感的观点明显地受到了瑞恰慈、艾略特等的相关观点的影响——瑞恰慈在《想象》中论及过讽刺感,认为有一种诗歌,如济慈的“你的嘴唇,滑溜的幸福”,是经不起以讽刺的态度来观赏的。因此,虽然容易受讽刺的诗不是最高级的诗,但最高级的诗总是具有讽刺的特点的[4]56。同时,袁可嘉关于现代诗“自嘲嘲人”特质观点的形成与艾略特诗歌的影响颇为相关[2]192-193。
除以上具体观点外,袁可嘉的诗论还有一些具体观点,如 “诗的本体”“晦涩”“现实”“象征”“玄学”“客观联系物”“远取譬”“思想知觉化”“批评”等,所受的西方影响也颇为明显。
二、袁可嘉诗论的文本与西方的影响
袁可嘉诗论在文本方面也受到了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
其一,大量地使用西方诗学概念。无论是从篇目的数量来说,还是从篇幅字数来说,袁可嘉的诗论都谈不上“多”或者“大”——总共才二十几篇、十几万字,但所使用了的西方诗学概念却不少,甚至称得上“多”或者“大”——有二三十个之多,如“客观对应物”“戏剧化”“文本的有机性”“想象逻辑”“最大量意识状态”等;对中国固有的诗学概念,主要是从西方诗学的角度来使用的,如象征,在袁可嘉那里,“主要指的不是波德莱尔的以‘契合’论为基础的那一套神秘主义象征学说而是后期象征主义以来的西方现代诗的一个特征。”[12]179-182
其二,大量地引用西方诗学话语或观点或西方诗歌。“《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共收入26篇文章,其中完全没有引文的只有两篇(《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和《批评漫步》),其余诸篇对于他人话语皆有引述。其中,最为袁氏借重的中外文士出现的频率分别为:艾略特73次,奥登34次,鲍特尔28次,马克思19次,瑞恰兹17次,叶芝15次,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14次,里尔克12次……史本特9次,亚里士多德8次,柯尔立奇、雪莱、布洛克斯……7次……安诺德6次”[20]199;而且,被引及的多为西方现代文论家或诗人——可以说,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现代诗学保持着同步对话的关系。同时,在展开论述时,用来作为论据的诗歌多为西方诗歌,而《新诗戏剧化》《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等诗论更是只引西方诗歌做论据。
其三,大量地论及了西方诗学家或诗人。袁可嘉的诗论论及的西方诗学家或诗人堪称为数众多——大致有艾略特、奥登、鲍特尔、马克思、瑞恰慈、叶芝、弗洛伊德、莎士比亚、里尔克、史本特、亚里士多德、柯勒律治、雪莱、布洛克斯、安诺德、柏拉图、贺拉斯、维柯、史达尔夫人、圣伯甫、泰纳、赫伯特·里德、克罗齐、玛里丹、肯尼斯·勃克、乌尔班、布拉克墨尔、利维斯、考德威尔等。
其四,在理论阐述的方式、方法方面,受到了西方学院派的影响,像对语义学方法的运用更是直接受到了瑞恰慈的影响。
三、袁可嘉诗论的西方影响与袁可嘉的创造性建构
袁可嘉的诗论虽然在诸多具体观点及文本上均受到了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但又不是西方诗歌的中国化理论总结或西方诗论或文论的中文翻版,而是袁可嘉在对新诗及新诗理论认真、严肃思考的基础上,“利用全部文化,学术的成果来接近文学,了解文学”[2]111、创造性地建构中国诗论的一种努力:
首先,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立足于中国本土。
其一,立足于中国现代诗歌。袁可嘉所关注的最主要的不是外来文化的“引进与模仿”,而是他所面临的创作现象——是新的文学现象激发起了他“思考的兴趣和解释的冲动”;他引述西方新批评的一些观点,如瑞恰慈关于“最大量意识状态”的观点,其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完整性,而是在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并试图“以此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变革”[21]122-123;新批评的理论在袁可嘉那里很大程度上演化成诗歌写作指导,“袁可嘉以这套理论召唤在艺术品质上以艾略特、奥登为楷模而又对中国现实有所干预的现代诗”[22]58。
其二,立足于中国现代诗学。总的来看,中国现代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诗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在袁可嘉的诗论产生之前,现代主义诗学主要受以法国象征主义为首的欧陆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并形成了相应的“晦涩”“不服中国水土”等缺点,从而失去了与现实主义诗学对话的基础,在诗坛上也未能被广泛地接纳。而袁可嘉的诗论虽广受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但其核心观点基本上“是以理查兹、艾略特、肯尼斯·勃克这三人的诗学观点为基础形成的”[8]87,即主要受以新批评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奥登等注重现实的诗学观的影响;这实际上既修正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晦涩”“不服中国水土”等缺点,又增加了西方诗学在中国传播的“品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诗学发展的路向。
其次,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融进了袁可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
袁可嘉的诗论虽然广受西方影响,但在接受西方影响时也融进了自己独特的体会和见解,因而实际上是对西方相关诗学的一种完善和完成,如对想象逻辑,艾略特、瑞恰慈的观点比较分散,且没有得到应有的具体论述;而在袁可嘉看来,所谓想象逻辑即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它可以结合不同经验,使意义加深、扩大、增重,它在艾略特长诗中表现为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断,或扩大某一行或某一意象的蕴义,或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或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引进……与艾略特、瑞恰慈相比,袁可嘉的观点及其论述都要集中而又具体得多。
又如,在瑞恰慈看来,能够实现“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包含的诗”“通过拓宽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由平行发展而方向相同的几对冲动构成”[23]226-227;而袁可嘉则将之联系到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上,强调“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21]123,这显然比瑞恰慈的观点周延得多——“把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同理查兹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学诗学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袁可嘉最突出的批评贡献之一”[8]88。
再如,“‘经验’一词虽说是瑞恰慈诗歌批评的关键词之一,但将‘人生’连接在‘经验’之上,则完全是袁可嘉的‘特殊命意’”[21]123——在新诗发展史上,虽然也有像冯至之类的人看到了经验与诗的密切关系,但多数只愿意承认生命冲动、感觉、感情、激情、情绪、神秘心理与诗密切相关;“中国新诗的‘经验’之论从初期白话诗歌时代就产生了,但是直到袁可嘉那里才完全进入到了‘艺术本身的逻辑’”[21]126:他不仅强调经验,而且毫不含糊地把“经验”同“热情”“说教”“感伤”“单纯”等“新诗的毛病”尖锐地对立起来……这对诗歌扩大题材的范围,即取“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2]4,无疑是具有理论支撑的积极意义的。
再次,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注重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建构。
袁可嘉的诗论虽然大量地使用了西方诗学概念,但“使用”本身更着眼于“建构”:“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压迫性输入之中,现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与诗学家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应付、消化外来资源方面”,因而未能有效地建构自己的理论,诗学概念也严重匮乏,“现代中国的几部体系完整的‘诗学’——包括朱光潜、艾青等人不无贡献的诗学——都未曾在推出新的诗学概念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虽然袁可嘉从不讳言自身诗学观念中所接受的外来痕迹,但他却总能自如地运行于所有这些外来诗学概念之上而予以新的组合和改造,并且形成自己的新的思想形式”,进而创造性地建构了“客观联系物”“新诗戏剧化”“文本的有机性”“想象逻辑”“最大量意识状态”“文本的有机性”“戏剧化”“戏剧主义”等一套新的诗学概念,从而“既与现代西方的诗学思想形成了对话,又奠基了中国自己的诗学批评概念。如果现代中国的诗家们能够有更多的袁可嘉式的自觉,那么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形式也就是大可期待的了。”[21]128
最后,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注重中西新诗潮的交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西方新诗潮和中国新诗潮交融、汇合的年代——当时,在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登的影响“所向披靡”;在中国,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后来的九叶诗人推动着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而走向中国式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中西诗交融而产生了好诗的辉煌年代。但截止于40年代中叶,诗歌理论明显地落后于实践,对西方现代诗论虽已有所介绍,可对西方和我国新诗潮的契合点还缺乏理论上的阐明”[7]2,袁可嘉的诗论,尤其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自觉地接受西方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关于西方和中国新诗潮的契合点的理论阐释,即主要是为了推动中国新诗潮和西方新诗潮的交融。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