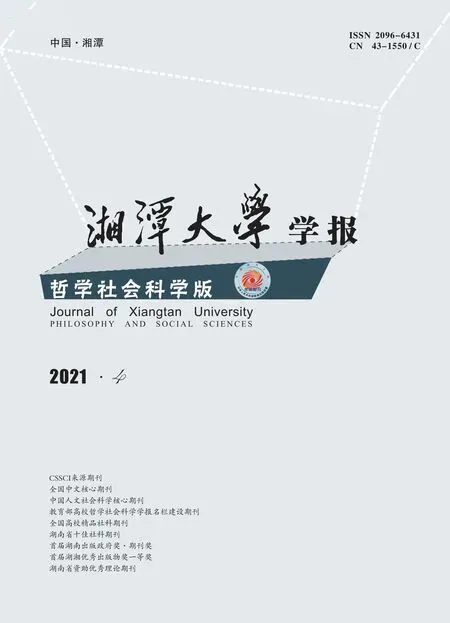加里·斯奈德诗歌之“不隔”*
罗 坚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关于美国深层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诗歌的形式风格特征,学界已有的研究大体是从西方的文学批评话语入手。如肯尼斯·雷克斯罗思认为,斯奈德的诗歌是反形式主义的,国际化的,直言其事,并且强调表现的瞬时性。鲍勃·斯特丁将斯奈德的诗歌风格概括为六点:“1.荒野,或东方背景;2.避免抽象,强调具体;3.简洁、有机的形式,常具意象性的诗行;4.运用俗语,尤其是口头语言;5.深奥难解的引用;6.偶尔带有情色的言外之意。”[1]22西方文学批评将理性与科学奉为圭臬,研究文学如做动物解剖实验。这种方式可以将文学作品层层分解,精细入微,然而其不足在于对文学作品浑融的整体性把握不够周全,对于文学作品“深层的意味和悠远的意境”[2]49把握不足。相对而言,中国文论话语在这些方面优势独具。笔者以为,斯奈德的不少诗作,都描写了诗人与自然怦然相遇后的瞬间直觉感悟,对自然意象的营造不假典故等外饰,情感抒发直接而不造作,意境悠远,充满生趣,简洁美好,语语如在目前。这正是王国维诗学理论“不隔”之要义。
一、王国维之“隔”与“不隔”的诗学观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姜夔的词时提出来的文艺理论观:“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继而论道:“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如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3]68-69。
王国维的这一文学批评观涉及三个方面,分别为“景”“情”与“意境”之“隔”与“不隔”。贯穿于这三个方面的是“主体心境”与“语言呈现”的格调与层级。“景”与“情”的融合则为“意境”,如“景”与“情”都“不隔”,则“意境”应为“不隔”。王国维又有“不隔”之“隔”与“隔”之“不隔”之说,应是指“隔”与“不隔”两极之中的中间状态,其定位只可感性意会。故朱光潜认为:“依我看来,‘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中见出。诗和一切其他艺术一样,须寓新颖的情趣于具体的意象。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4]52。诚然,心手相应,言语应心是“不隔”之诗的必然要求。
诗歌作品的“景”与“情”之“不隔”首先取决于诗人的“主体心境”。作家在创作时所取的心境,所持的文学立场与文化取向,都会影响,甚至决定其文学作品的诗学境界,自然会在诗中的“情”与“景”中体现。而影响作家的主体心境之最重要因素则在于作家的思想境界与文学品性之高低。故钱钟书指出:“按照‘不隔’说讲,假使作者的艺术能使读者对于这许多情感、境界或事物得到一个清晰的、正确的、不含糊的印象,像水中印月,不同雾里看花,那末,这个作者的艺术已能满足‘不隔’的条件。”之所以能做到“水中印月”,首先在于创作主体心境的澄明,品性的洒脱,同时具备高明的语言表达力与艺术呈现,才能实现作品的“不隔”。王国维所推崇的陶渊明、谢灵运、苏东坡等诗人都是骨格清奇之士,文学品性高洁,不为世俗所累,不为声名所羁,因此其文学作品的境界也是清明之至。相对而言,姜夔、黄庭坚等则略有逊色。就此叶嘉莹指出:“如果我们对于《人间词话》这种境界说的基本理论有了认知,我们自然便会明白静安先生所提的‘隔’与‘不隔’之说,其实原来就是他在批评实践中,以‘境界’说为基准来欣赏衡量作品时所得的印象和结论。”[5]251也就是说,“隔”与“不隔”都应放在文学作品的意境之中进行衡量。意境是作品所创造出的大语境,景的“不隔”与情的“不隔”融会出意境的“不隔”。意境的高下是衡量景与情的最终标准。
与其他几位学者不同,张节末从禅宗美学的角度论述诗歌之“隔”与“不隔”。他认为,如果文学作品能够在心与物之间呈现出澄明无碍的境界,则是“不隔”,如果心有尘埃,物为尘染,则五音混杂,五色不明,花非花,雾非雾,万事浑浊不清,则有“隔”之弊端。心物之间,关键在于心之清越、自在的禅境。“八风吹不动天边月”,佛性本真,于心不动,则竹现眼里,了无窒碍。于此,张节末认为:“所谓的‘隔’,是指禅者囿于情见、见闻觉知、语言等,给见性、悟理造成障碍,所谓的‘不隔’,是指超越的觉悟,它迅如霹雳电闪,不容思量拟议,是意通、见性、悟理。”[6]241由此,“具眼之人”以一双智慧的法眼直观现象,他写的景物自然“如在目前”,即为“不隔”。诗人如同悟入之禅者,以本能式的直觉,以刹那之间的凝神观照,放弃思量,摈弃杂念,甚至超越语言,从而得到直观之下的真知,由此“主体心境”生发而成的诗作自然“不隔”。
在具备澄明淡泊之心境之后,诗人还需具备将所观之景与所写之情形诸笔端的能力。从王国维的论断可知,写景时,语言需明白晓畅,使景色如雨后初霁,清新自然。在写情时,情感需一气呵成,沛然纸上,不可曲折缠绕,难以揣度。王国维认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可见,王国维所谓写景之“不隔”是指诗人在状写物态时,出乎自然,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柔妆束之态,辞采不妨俊拔,“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写情之“不隔”,是指诗人在表达情感时,要语言直接、明了、深刻,而不是以模糊、晦涩、迂回的方式表现。如此则“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因此,彭玉平指出:“在《人间词话》中,替代字、用事、典故一直是王国维反对的创作手段,因为它们负载了固有的意义,再加使用,意味着诗人原意的屈就和部分的流失。而不完整的表达带来的是意义的不完整”[7]186-188。关于所写之情,其“不隔”的内在原因在于,情绪状态是稳定、饱满的,明晰彰显的,由此在语言与情感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观照的关系。当然,如果在写情时需要用到某些意象,那这些意象的显现也必然是清晰的,并且与所写之情直接相关的,而且所有的修辞手段都基本被摈弃,仅以直白、清晰的语言呈现意象表达感情。
二、加里·斯奈德诗歌的中国道禅文化
加里·斯奈德的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禅宗文化影响,这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也形成了他诗歌“不隔”的美学特征。加里·斯奈德的诗作中,主要具备两种文化内因:其一为中国道家文化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其二为佛教禅宗文化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早在大学时期,斯奈德就深入研读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英译的《道德经》及他关于道家思想的英译著作,对道家的“道非道”“道法自然”“道生万物”“见素抱朴”“无为无不为”等核心理念都有独到的领悟[8]112-129。在《荒野践行》一著中,斯奈德这样阐述他对道家之“道”的理解:“它是无法分析的,不能归类的,自己形成的,自证自明的,嬉戏的,令人讶异的,无常的,非实质的,独立的,完整的,有秩序的,未经预谋的,随意呈现的,本身能印证的,坚持的,复合的,相当简单的。既是空的,也同时是真实的。有些情况下,我们可称之为神圣的”[9]153。斯奈德认识到“道”的本源性和整体性。《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0]2。斯奈德对“道”的解读,与老子关于“道”的终极性一致。在他摈弃西方基督教神学所构筑的形而上学传统之后,道家的哲学观更符合斯奈德的文化期待视野。通过对“道”的整体性观想,他既了悟“道”的哲学本体存在,又获知“道”在宇宙之中规定的秩序,同时还看到万物活泼泼的生机,因此它才是“嬉戏的”。
在整体性的观想之下,道家哲学视域中人与万物的关系对斯奈德影响深刻。道家美学的核心也是基于“道”。人处于万物之中,寰宇之下,以物观物,物我为一。叶维廉指出:“道家这一思域有更根本的一种体认,那就是:人只是万象中之一体,是有限的,不应视为万物的主宰者,更不应视为宇宙万象秩序的赋予者。要重视物我无碍、自由兴发的原真状态,首先要了悟到人在万物运作中原有的位置,人既然只是万千存在物之一,我们没有理由给人以特权去类分、分解天机”[11]2。道家的这一观点与斯奈德的深层生态观深度契合,因此被斯奈德融入自己的文学思想之中。斯奈德深层生态观的核心正是深度感知人与万物的关系,认识到众生平等,彼此相依,共生共荣,由此激发对众生,对地球家园的深度关怀。斯奈德在《万物村委会》一文中论道,“‘万物村委会’给予所有生物发声的机会,为他们提供空间”。毫无疑问,这其实已经意味着他在接受道家思想的同时,还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佛教的思想。他指出,“所有的我们如同溪畔的柳树,都有安身之地,也如同这个星球的流水系统一样,每两百万年穿行于各种形态,各个位置一次轮回。我们有限的身体与文化中必然的存在定当被认可为有价值的,正能量的。”[12]80
道家和佛教文化对斯奈德文学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自由旷达的诗学态度。如在阐述“道可道,非常道”的理念时,斯奈德认为:“它是指‘可循规蹈矩遵行的道路,一定不是精神的道路。’事物之真实不可能受路这种线形意象的限制。只有当‘追随的人’被忘却了,训练之意图才能达成。路是没有困难的;路本身并没有对我们造成障碍,它朝所有方向开放。”[13]150这就意味着,大道之行,不拘泥于狭窄的空间与思路,不要将“道”狭窄地理解为世俗之“道路”。要领悟大道之美,须要不拘泥于世俗法则,应顺应天道,自由旷达,纵情山水。为此他指出:“道家作家在研究自然(意为自然、自我、自我维护和开发)的过程中,在探寻人之本性、现象的黑暗内在时,主张清净无为、柔和、流动、明智地接纳。道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悖论,即热物理能量会流失,显然会永远消失:熵。生命的存在,似是为延缓能量消失、尽其用而采用的复杂策略。不过,所谓的‘精神’能量,通常只有在你学会‘放手’(放弃)、‘摆脱身心束缚’(成为过程的一部分)时才会增长。”[14]43斯奈德的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在题为“小径非小径”的诗中:
我顺着高速公路,开车疾驰。
在一个出口,下高速之后,
沿着公路行驶,
一直来到一条窄路口。
我开上这条窄路,
一直来到一条土路,
高高低低,坑洼不平。
我停下车,走上一条小径。
慢慢地,这条小径越来越模糊,
直到消失不见。
于是我走向旷野,
处处可行。[14]130
“处处可行”代表的正是对“道”的本质性体悟所达到的超拔而务实的境界,淡泊而自在,自由而超脱。相比于失范的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斯奈德在充盈着道家美学的心境之中写出的诗作,自然富有个性。
斯奈德对于文化一直秉持兼收并蓄的态度,禅宗与道家的思想在他的文化视域中自然融合,并与他先在的文化视野有效衔接,形成了他个性化的诗学观。在另一首题为“高品质资讯”的诗作中,斯奈德写道:
一生寻找,
如土中之虫,
如一只鹰。抓住线团,
扫描骨骼,
猜想道路所延伸之处。
老子说道: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吾所欲者为:
让这些风景,
直接回到这个地点,
于他们消隐之处,
回到我的时代之思,
旧的回路。
然而有一些道路带有彩色
空无
我们可自由而行了。[14]130
这首诗的前五行表述的是人类对于真知的探索过程。一生追寻,无数人、无数代的追寻,生活乱如麻,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直到老子说道:人类知道最多的事情须忘记。于是,回到现在的时代,领略“道”之妙处者,则处处可行。故钟玲指出:
此处他所引用的“老子”应该是《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此段之含义应是指追求道,追求真理,就要“日损”,不断地减却已经所学的方法,最后全部都已减却,就达到“无为’”的境界。在这境界中真的要做什么,则无不合乎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之意境。[8]42
虽然无法确认斯奈德此处所引的“老子”,是否一定是钟玲所指的道家“日损”的理念,但老子“忘掉已知”的观念,显然与斯奈德已有的文化观念正相符合。斯奈德早在大学时期就质疑西方的大学教育,认为只是给学生脑子里塞满无用的垃圾,而现代人类只有去除这些垃圾才能回归本源。他认为现代人类欲望太过强烈,为满足自己欲望无休止地掠夺自然,毁坏地球家园,而人类应该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这其实和老子的“绝圣弃智”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道家思想之外,斯奈德对禅宗思想也有深刻而独特的认识。斯奈德与佛禅文化渊源深厚。他学习与修行佛教禅宗多年,得到日本京都大德寺禅师小田雪窗的认可。斯奈德认为:“佛教的教诲是无常、无我、不可避免的苦,相互关联、空、无垠的思想以及实现的方式。一首诗,如同一种生活,是简洁的呈现,一体中的独特,一种完全彻底的表达,以及一种天赋”。对于“无常”“无我”与“空”等佛禅理念的深刻体悟,指引诗人达到超拔与洒脱的思想境界,形诸诗作之中则简洁而独特。斯奈德称:“佛教的理念与中国诗歌的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高雅隽永的简洁,我们称之为禅宗美学”。在斯奈德所体悟的禅宗美学中,他特别重视“当下”,如他所言,“一切都是当下”(“All is actuality”)。[15]115他认为,“关于‘当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它一直就在那儿。没有必要刻意提起与展示它。因此诗歌最终的主题也是深刻的普通。真正好的诗歌或许正是无形的,这些诗看起来并没有特殊的洞见,也没有非凡的美丽”[15]115。溯源禅宗文化,“当下”之理念来自“平常心是道”。《五灯会元》记载,“赵州从谂请教师傅南泉普愿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师曰:‘不拟怎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师于言下悟理。”所谓“平常心”,是指在平常生活中保持本心,本心圆满具足。普愿指出,不应在心中产生种种是非知见,因为任何一种知见都是妄觉,此即所谓“拟向即乖”。只要在日常洒扫中保持心行合一,以平静、从容的心态做种种平常小事,就能保持并体现自身的真如佛性。禅宗六祖慧能指出,“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16]78这一观点点明了禅宗修行的自由性,证实了在家居士获得悟入成佛的可能性,只要在与俗世尘缘相触的活动中“不染万境”,保持真如,平常生活即是道。
关于禅宗之“平常心是道”,斯奈德指出:“我的一首诗作是关于家里的许多小事情。这与我正在思考的一些想法非常接近,即思想与行为的合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正在扫地时,却在思考黑格尔,我的思想中便存在着一种身体思想的二元主义。但是如果我正在扫地时也在想着扫地,我就身心合一了。这时,扫地这一行为就不再细微了,关于扫地的心绪也不细微。于是扫地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情”[16]7。斯奈德对“平常心是道”的体认关涉般若中观的“不二法门”。如果他扫地时思考黑格尔,即是生分别心,是“二”非“一”,必然心生妄见。只有当他的思想与行为都集中到扫地之上时,身心合一,他的种种妄见也就消失了。在一次访谈中,他更加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禅的理解:“那是一种运用你的思想,并与他人一道践行生活的方式。它有一种与他人相关的风格,对日常工作有一种特别的关注。它重视工作,重视日常生活。它重视如“责任”与“投入”这样一些古旧的词汇。同时,它又没有规定外在的法则,因此你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它的基石。换句话说,它让你转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给你一本成果让你照章执行。禅是一种关涉“解放”的实践,而不是给予人们某种轻易的确定”[16]153。斯奈德了知禅宗的根本在于自己的内心,修行者需要通过不断地体悟自己的本心,才能获得开悟。这不是一个照章执行的过程,而是一个自我寻求的过程,其目的是自我心灵的自由与“解放”。“相由心生”。斯奈德对于禅宗美学核心质素的理解与体悟助他达到清净澄明的心境,去繁就简,专注当下,意在平常。由此诗人安贫乐道,身心宁静,创作心境安然自处,创作出的作品也与这一心境相符。
据上,斯奈德的不少散文和诗作以及文艺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中国道家文化和佛禅文化的深刻影响。斯奈德对道家文化和佛禅文化的深入领会与切身体验,形成了他融合道禅文化的独特生态诗学思想,从而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中自觉摒弃典故与象征,而直呈意象,直抒胸臆,简洁生动,意趣盎然,境界阔大,堪称王国维所谓“不隔”之诗学美之典范。
三、加里·斯奈德诗歌之“不隔”
从王国维“隔”与“不隔”的诗歌美学思想审视加里·斯奈德的诗,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具有“深层生态主义”的桂冠诗人,加里·斯奈德诗歌的重要美学特征即是“不隔”。这种“不隔”的效果,其实还深受埃兹拉·庞德领衔的意象派诗歌原则的影响。F.S弗林特在《意象主义》一文中指出,意象派的创作原则是:“1.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2.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17]150。斯奈德的诗歌创作正是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写景简洁生动,充分相信语词本身的力量,戒除繁复的修饰语,直呈景物,清新洗练,自然脱俗,语语如在目前。如其诗云:
山谷里烟雾萦绕,
五日雨来三日热。
枞子上树脂闪亮,
越过岩石和草原,
一簇簇新的苍蝇。
读过的东西记不起来了。
有几个朋友,但他们在城里。
我从锡杯喝冰冻的雪水,
越过高爽凝静的空气,
瞭望下间千里。[18]61
诗歌描绘高山上的宁静时刻,表达了诗人独居高山,自得其乐的宁静、恬淡之情。诗人在诗意呈现时,先将自然之境放在第一位直呈山中之境:山谷中烟雾缭绕,天气雨晴不定,树上树脂在阳光映照下闪着光亮,一群群新生的苍蝇飞起,越过岩石与草地。这样普通之极的风物,在他人眼里也许不值一提,可诗人却着意表现,没有任何形容词、修饰之语或修辞手法,体现出诗人无比寻常、淡然的心境。第二节,诗人作为这首诗中的唯一人格形象出场,心境澄明无碍,悠然地身处高山,远离人间,读过的书已无须记得,朋友都在遥远的城市里,但诗人有高山与众生作伴,所以并不孤独。他享受着高山上宁静的空气,与锡杯里的雪水,还惬意于眺望千里群山的辽阔风景。在这一节诗中,人格形象没有给予任何正面的表现,而是着力于呈现人格形象悠然自得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诗节中仅仅出现了两个形容词,即“冰冻的”与“宁静的”。这两个词并不使得诗意繁复,而是为了必要的叙述性呈现,是事物实质的表现需要。整首诗在写景和写情上都表现出“不隔”的美学特征,语语如在目前。同时,诗歌在语言和景物、景物和情感的贴合无间中营造出一种率真淡远的境界,使读者仿佛与诗人一道共处高山之巅,一起喝着雪水,一起从远离尘世的高山遥望。
斯奈德诗歌的“不隔”,与斯特丁所指的“强调具体,避免抽象”[1]22有暗合之处。“不隔”之说更为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只强调语言对自然物象呈现的具体实在,还强调意象的营构、情感的抒发,以及情景交融意境的营造之自然天成。在诗集《遗留在雨中》,此类诗歌作品颇多见到。如在题为“西部的宽阔道路”(TheBroadRoadoftheWest)之中的第一首:“BakersCabinonBoone’sFerryRoad”:
蛙鸣整夜,
白鸭三只,
在底下的池塘鸣叫。
暑热之中,暹罗猫的号叫。
滚烫的熨斗,烫得衬衣直冒烟气。
潮湿的柴火燃烧,
一边发出尖细的声响。
四只小猫,一个婴儿哭叫着。
在厨房炉灶旁的盒子里,
波特兰。[19]35
这首诗是斯奈德于1952—1956年间在贝克山担任防火瞭望员时创作的,表现的是瞭望站简陋的木屋里的生活。诗中所呈现的蛙、鸭等生物的状态都是极为简洁的,诗中的用词也很精到,动词性的词如“chant,yowl,spit,squeak,burn,squall”等,表达十分准确而贴切。正是这些关键动词使得装饰性的形容词、副词没有必要。诗中也完全没有使用象征、典故等倾向于将诗境导向晦涩与曲折的修辞格,只有两处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格,其指向也极为生动而精准。从心境上看,诗人安然处于高山之巅,寂静而欢喜。虽然天气闷热,生活清苦,却也乐趣无穷。诗歌呈现出“不隔”的美学境界。再如另一首题为“李树花飘落”(“Plumpetalsfalling”)的诗:
李树花瓣飘落,
樱花花蕾仍然坚硬。
喝着酒,
在花园之中。
女房主走出来,
在晨光之中,
拍打着一块小地毯。
无需多言,这首诗属于“不隔”之诗,读者如同和诗人一起坐在树下喝酒,看着周遭事物的种种发生,花瓣落下,坚硬的花蕾,以及清早起床的女房主。
以上诗作偏重写景,表现了斯奈德诗作在写景上不用典、戒修饰、重直呈的“不隔”的美学追求。而在偏于写情的诗作中,斯奈德同样达到了“不隔”的境界。在诗集《僻壤》中,他写道:
你搭便车一千英里,
从北方的旧金山来,
一路登山而来,直上一英里。
这个小木屋,只有一个房间,
玻璃窗作墙。
草地与雪野,山峰成百上千。
我们躺在睡袋里,
聊天至半夜。
拉索上的风声,夏日里的山雨。
次日早晨,我送别你,
直到峭壁边。
借与你我的斗篷,雨雾飘过页岩。
你顺雪野而下,
衣袂翻飞在风中。
挥手,最后一次再见,一半隐身于云雾。
继续搭车旅行,
直奔纽约。
我却回归我的高山 在远远的西边。
这首诗着重表现诗人与友人的深厚友情,但斯奈德并没有像李白在《赠汪伦》一诗中直抒胸臆,而是以极简洁的文辞客观展现了友人千里来访的过程。这首诗没有使用任何修辞格,而是直言其事,呈现了三个场景:友人千里来访,山巅小聚,依依惜别。每一场景都极为简洁,直指事件的关键与核心。比如在“千里来访”部分,诗人强调了三点,其一是友人来自千里之外,指明距离之远;二是友人来自大都市,来探望山野之中的朋友;三是诗人居处山巅,须直上一英里。三行诗,没有任何形容词、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只是极为直接、准确地呈示抒情缘由。在第二个场景中,诗人与友人在高山之巅小聚。同样没有任何修饰性的语言,只是点明环境:一座小木屋,一个小房间,玻璃窗为墙,刚好可以采光,亦便于欣赏风景。除此之外,就是绵延的草地与雪野了。居住条件显然极为简陋,但诗人与朋友却毫不在意,他们畅谈至深夜,伴随着风声与山雨,享受着相聚的时光。在第三个场景中,诗人送别友人,没有直接抒情,只点明几个细节:其一为送朋友至尽头,即“峭壁边”;其二为赠朋友以斗篷,以遮风雨,表明对友人的关爱;其三为友人依依不舍,云雾中最后一次挥手示别;其四为诗人与友人各自回归原点,友人前往纽约,诗人返回高山。整首诗歌摈弃了累赘、繁复的语词和直接的抒情,而代之以简洁、鲜活的诗意语言,呈现了友人来访的情状。然而友人之间心灵相通的长存深情,却如山中之风,弥漫全诗。这就是斯奈德写情之“不隔”的美学境界。
事实上,在斯奈德的多部诗集之中,如《砌石与寒山诗》《神话与文本》《僻壤》《山河无尽》《龟岛》等诗集之中,“不隔”的诗作普遍存在,“不隔”已经成为斯奈德诗歌的重要美学特征。
结 语
中国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有评论:“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枢,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20]12。在以悲秋为主题的三首诗中,韦应物、白居易、司空曙三位诗人的诗作都达到了“不隔”的诗学标准,相较之下,谢榛认为司空曙的诗作最为优秀,司空曙的两行诗不但做到了“不隔”,而且意境更胜一筹。可见诗歌之“不隔”虽然是衡量诗学品质的重要方面,但也只是诗学体系中的一环,诗作整体性的水平还需结合诗品、诗境等多重标准进行划定。同样,诗歌作品的繁简也是各有其势,须根据不同的诗人品性,不同的诗学追求采用合适的形式风格。如谢榛认为:“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若‘孔雀东南飞’、‘南山有鸟’是也”[20]4。相较而言,“不隔”之诗属于繁简之“简”。斯奈德的诗作中也有很繁复的,如《砌石》中的“T-2邮轮布鲁斯”、《观浪》中的“夜友”、《龟岛》中的“为伟大的家庭祈祷”等诗作。但总体而言,斯奈德诗歌作品之“不隔”的诗学特征确乎是其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赋予其诗作以独特的简素之美。“不隔”之美在他的多部诗集中的众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从诗学源头探寻,道家美学、禅宗美学等文化流派的核心理念对斯奈德“不隔”之诗学特征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中国诗学体系的“不隔”说观照美国诗人斯奈德的诗歌作品,有利于发现斯奈德诗作的独特审美内涵,也为我们用中国诗学话语解读西方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