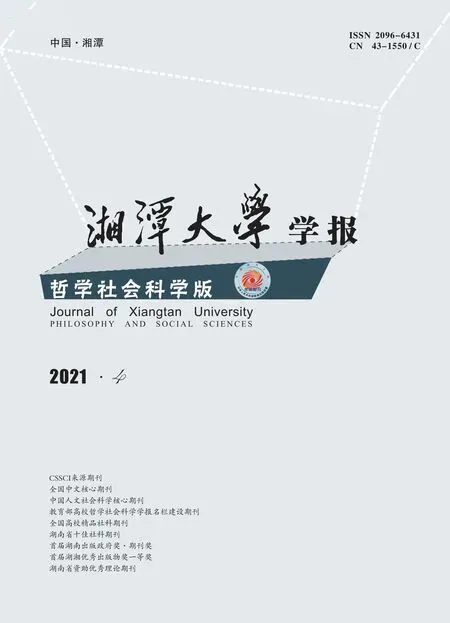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知识青年的《新青年》阅读与思想变革*
许高勇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元典,关于它的研究长盛不衰,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1]特别是《新青年》被接受的具体语境、受众与途径,乃至传播、变异的过程,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注意,尤其是广大的青年学子如何阅读乃至接受《新青年》的过程,还值得从传播史的角度做更深入的研究。[2]本文以《新青年》的阅读为中心,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探究青年学子与《新青年》相遇的方式,阅读《新青年》的心路历程,被《新青年》塑造的历史,即从阅读史的角度探讨《新青年》的阅读主体——“五四青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的对象“五四青年”,指的是“五四时代”的青年。具体言之,指的是阅读《新青年》进而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大体上指1915—1926年间的青年。
一、“新青年”的阅读历程与意识觉醒
1915年,陈独秀自日归国,期待在思想文化界有所创举,创办《新青年》,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3]六条准则作为时代对青年的要求,开始了中国近代的新思潮运动。应该来说,陈独秀于时代对青年的要求相当精准。《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志,青年成为《新青年》最重要的启蒙对象。《新青年》倡导“青春文化”,将“新青年”在“一种民族精神迟暮之感中被创造出来”,把“青年群体文化演绎成治国安邦的政治文化”,促进了“青年”意识的觉醒。[4]另一方面,《新青年》的这种启蒙受到了知识青年的欢迎,促使诸多的青年成为《新青年》的“阅读大众”。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得到了广大青年学子的阅读响应,许多知识青年成为《新青年》的读者,参与新文化运动,逐渐认同“新青年”的身份,开始接受、学习“新青年”这一角色。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青年”的这一角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在这里,可以列举诸多的例证。汪静之将是否阅读《新青年》作为评价青年进步或落后的标准。[5]292杨振声认为:“《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6]260从《新青年》中,青年初识其身处的时代,对旧道德、旧文学产生叛逆的“种子”,以青年的责任打破身上枷锁,冲出封建堡垒。
在《新青年》的阅读地域中,北京、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自然成为阅读的中心场域。1919年,北京成为新思潮中心,“新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等新式刊物的阅读,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殊为典型的是北京大学学生。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被一并带到北大出版,促使《新青年》向全国名刊迈进。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读者中,傅斯年、罗家伦、张厚载、张国焘、马非百、川岛等学生非常积极,他们不仅与《新青年》同仁之间进行互动,而且创办刊物,积极响应新文化思潮。傅斯年、罗家伦致信《新青年》,与《新青年》同仁讨论“文学革新”“青年学生”等问题,而且在《新青年》同仁的帮助下创办《新潮》,以此呼应《新青年》倡导的新思潮运动。傅、罗二人因《新潮》的缘故,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影响甚广,成为北京大学的风云人物,领导了五四运动,此后负笈欧美留学,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展演。
和傅斯年、罗家伦相类,张国焘亦是早期拥戴《新青年》的重要读者。张国焘非常留心《新青年》的出版,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随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白话文运动开始,“活文学出现”,《新青年》开始影响北大学子。对于张国焘本人而言,他是北大同学中“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对于《新青年》,他“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新青年》对张国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家庭方面,张国焘将其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他的父亲,后来所寄书刊多是《新青年》等新式书刊,“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在家庭婚姻方面,张国焘坚决抵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其二,张国焘和同学发起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以图实现救国理想。[7]39-42不同于《新潮》“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的宗旨,《国民杂志》同仁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研究学术”为宗旨,[8]以“救亡压倒启蒙”的旨趣成就了不同于傅斯年、罗家伦的人生样态。
相比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风云学生”,一些普通学子对《新青年》亦情有独钟。马非百参与了邓康组织的曦园,他们“尽可能地广为订阅”《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性报纸杂志,而且积极拥护“文学革命”,以致“读书谈话、思考、写日记,几乎都是《新青年》等刊物提出的各类问题”。[9]104-105川岛在北大求学时,对于新式书刊“都想去找来看,看不懂的也要硬看”。其中,“早就知名”的《新青年》属于必读刊物,“就贪婪地一古脑地吸取着”。[10]321从“知识资源”中汲取到“科学民主”“文学革命”“反孔非儒”等“思想资源”,为北大青年学子的思想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新青年》和师辈的感召下,他们走上了与旧思想、旧传统决裂,拥抱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除北京大学以外,其他北京高校学子亦通过阅读《新青年》而使其精神世界发生重要变革。在清华学堂,吴文藻因《新青年》“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进一步接触了一些新思想”。吴文藻比较赞同“胡适主张白话文的主张”和“罗素的社会思想”[11]391。这奠定了其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此后他开始投身于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程俊英通过李大钊介绍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对李大钊的《青春》《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教育尤为深刻”。通过李大钊的引介,程俊英接触到《新青年》,进而认同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程俊英希望“能看到全部的《新青年》杂志”,故其前往胡适家借《新青年》。在借得全部《新青年》后,程俊英“一口气从第一卷读到末卷,顿觉头脑清醒,眼睛明亮”,从而从孔子的“子曰诗云”的桎梏中爬出来,[12]52其精神世界从旧文化走向新文化,在五四期间为女子解放独立自由而走上街头,开启了中国女子干政游行的先例。由于阅读《新青年》中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吴文藻、程俊英等知识青年从旧思想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接受民主、科学、爱国等新思想,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就是这样不间断的阅读,造就了五四时代之“新青年”。
早期到达北京、上海的知识青年成为阅读《新青年》的主体,随后这种阅读吸引力影响到边缘的知识青年,促使他们不断地涌向北京、上海,构成《新青年》阅读史的重要环节。安徽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生苏雪林遇老师陈慎登骂《新青年》,反而使其注意到《新青年》,于是,她“零零碎碎借来了几本《新青年》”,读了以后觉得“其中议论新奇可喜”,但她没有真正意识到《新青年》的价值所在。及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抛弃了之乎也者,学做白话文”。[13]102-103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附小教师许钦文受了五四潮流的“激荡”,和同学、同事之间“互相借阅《新青年》、《新潮》等书刊,翻阅得破破烂烂了的,还要修补起来,从邮局寄来寄去。”此后,他从杭州到北京“去工读”。[14]147苏雪林、许钦文受《新青年》的影响,向往北京的文化氛围,促使他们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在北京接受新思潮的洗礼。同时,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创作并发表在新式刊物上,进一步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在一篇篇的白话文创作中,他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成就了俗世声名,乃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北京、上海的“新青年”受《新青年》影响可谓甚巨,而身处边缘的青年对《新青年》的影响也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阅读《新青年》,参与五四”,呈现出《新青年》阅读的地方回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新青年》等备受天津学生的欢迎。天津学生联合会每周举行学术讲演会,邀请新文化名人演讲新文化运动,促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在天津进一步拓展。[15]75诸祖耿在荡口教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之类的刊物,因和“一群进步青年接触”,他加入“锡社”。[16]299当五四的浪潮冲击到四川成都时,艾芜开始阅读《新青年》,且与阅读《新青年》的国文教员曾海门“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17]959-9631924年,聂绀弩在仰光做报馆编辑时,读到《新青年》,“发生兴趣”,进而对一系列的问题产生怀疑。[18]148-151这种阅读的先锋体验与时尚隐喻着新旧文化的更替,亦表明《新青年》在其观念变革方面埋下了种子,他们可以依托前已形成的书报信息渠道与观念基础,较为主动地做出反应,并给予偏于正面的理解以便能够为其找到合适的出路。同时,这种地方回响表明《新青年》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北京等阅读中心场域,诸多地方的知识分子都有丰富多彩的变化,他们也在敏感地寻找出路及寻求解决困扰人生的问题,《新青年》的“思想资源”正好提供了这种契机。
诸如此类受《新青年》影响的“五四青年”的阅读个案不胜枚举。由以上列举的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马步非、川岛、吴文藻、程俊英、苏雪林、许钦文、诸祖耿、艾芜、聂绀弩等的阅读体验来看,《新青年》在其早期生涯中扮演着启蒙读物的角色,阅读《新青年》促进了其“青年”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思考自我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他们开始求“新思想”,做“新学问”,行“新事情”。[19]
二、“知识青年”的阅读回响与“思想革命”
哈贝马斯强调:“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20]220针对《新青年》的分析,王汎森提出了“阅读大众”这个概念,他指出,《新青年》培养起“阅读大众”,从而运动起新文化。[21]93很显然,《新青年》提供的“思想革命”符合时代的需求,类似于一个个传声筒和扩音器,传递给了广大青年学子诸多的“知识资源”与“思想资源”,进一步影响了他们,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藤井省三所言“四合院共同体”的阅读机制。[22]19可见,《新青年》犹如一种“凝合剂”,将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聚合到北京、上海,聚合到革命的队伍。夏衍曾言,《新青年》不仅“在青年中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的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队伍”。[23]731这种阅读机制重大的价值在于拓展了《新青年》的“网络”,促进了青年学子的“合群”,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力。
从报刊可得性的角度来看,上海、北京的知识青年阅读《新青年》较为容易,呈现出中心“阅读”的景观,而地方性的青年亦不落后,呈现出《新青年》阅读的地方回响。这种中心的扩散与地方的回应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阅读景观,影响了诸多的地方青年学子。在天津,周恩来对早期《新青年》不甚留意,即使阅读《新青年》“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临去日本前,一位朋友送给他《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在赴日途中,周恩来阅读《新青年》后,表示“很是喜欢”。在日本期间,周恩来从严智开处得到《新青年》三卷全份,受到启发,觉得把“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24]当他再次阅读《新青年》第三卷时,“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25]34于是,周恩来“连着把前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其“从前的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愿从今日起,“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此后,他“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26]
在武汉,华中大学学生恽代英很早就开始阅读《新青年》。1917年,恽代英零星购买和阅读《新青年》,并对《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表示兴趣:
《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26]153
这表明恽代英关注《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但其并不认同《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至1919年,《新青年》成为其订购的杂志之一,并对《新青年》的认知逐渐发生改变。1919年4月,他就表明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26]528其后在给王光祈的信中就表示喜欢阅读《新青年》,皆因其“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26]624虽有夸大之嫌,但说明恽代英对《新青年》之喜爱。此外,《新青年》成为恽代英投稿之对象。1917年8月11日,恽代英“拟作文投《新青年》,借问前稿究竟。”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论信仰》两文在《新青年》发表。[26]153
周恩来、恽代英的日记,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他们对《新青年》的真实态度。不管是周恩来对《新青年》从“不甚留意”到“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的态度转变,还是恽代英一直“喜阅”《新青年》,代表着地方知识青年的阅读与对《新青年》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取舍。具体言之,他们对学术方面的内容没有什么回应,倒是对行动方面的内容有兴趣,因此,在地方新文化运动和转向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以强烈的实践感和使命感践行了《新青年》的“社会革命”主张,不仅推动了各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且以实际行动转向革命,拥抱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新青年》影响力较大的要属浙江与湖南。在浙江,由于浙江第一师范诸生的推动,浙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地方新文化运动的典范之一,其中,浙江学子杨贤江、施存统殊为典型。
杨贤江是浙江较早接触到《新青年》的读者。1915年底,杨贤江到大方伯图书馆阅《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对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自觉》一文产生了共鸣,并自奋:“我必须以己之志决吾之行,切不可存侥幸之想,又不可遇难而退,遭苦而悲,负虚此一生。”[27]193值得注意的是,杨贤江阅读《新青年》的地点大方伯图书馆是浙江省立图书馆,说明早期《新青年》已建立起省一级的市场,在省会城市可以较为方便地阅读到《新青年》。1918年3月,杨贤江再次阅读《新青年》时,对白话诗及文学革命颇为赞同:“《新青年》中白话诗,趣味隽永,精神盎然,读之可以清人思、娱人情。文学亦美术,但得人之欢心,价值即在其中矣。”[27]228在向友人推荐阅读的刊物中,《新青年》成为重点推荐的杂志之一,他表示《新青年》“盖有生气之杂志,虽论调不免趋乎激烈,易招一般人之反驳,然脱尽因循习气,扫除陈腐论调,另放一种光明,则该志之长也”。不特如此,杨贤江援引胡适《非留学篇》,希望“不贻恶感于人,亦以节用自家精力”。[27]321
不同于杨贤江较为容易地接受《新青年》,施存统接受《新青年》的过程较为复杂。1916年,施存统已接触到《新青年》,服膺于孔孟之道的施存统阅读《复辟与孔子》一文后,心中大怒,大骂陈独秀无礼,即弃书而走。但数天之后,因为“好奇心的冲动,要看看他究竟怎么样骂法”,遂重新拾起阅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从起初的一时兴起,到像阅读小说那般乐此不疲。再至1919年下旬,全然接受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的观点。[28]3681918年秋,施存统与其他同学在浙江第一师范组织“新生学社”,提倡新文化、白话文,反对文言文。[29]3651919年8、9月间,为推销国内各种进步报刊,施存统、汪寿华等人在第一师范学校成立全国书报代售处和书报贩卖处,贩卖各种新式书刊。
当然,杨贤江、施存统反映的是省会杭州《新青年》在地化的阅读,具体到《新青年》所形成的阅读影响机制,即如叶文心所言:“杭州之于北京,并不是省会之对中枢、边陲之于核心。杭州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并不为北京五四运动所涵盖。五四运动在杭州,比较之于北京,本身便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求变的讯息。这个讯息来自中国内地乡镇社会,而不只是对抽象理想的憧憬,所以表现出来的反传统性尤具激情。”[30]200-201这种地方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新青年》的地方扩散密切相关。这种文化扩散相当便利迅速,使《新青年》的影响机制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亦使杭州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现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新青年》呈现出群体影响力的另一地区为湖南,其中,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之时,杨昌济即注意到《青年杂志》。在阅读到《新青年》之后,杨昌济将《新青年》分送给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张昆弟等人阅读。他们聚集在天鹅塘,“经常在一起交流阅读心得,思考和讨论《青年杂志》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救国之情溢于言表”,[31]22从而“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32]241919年8月1日,张昆弟接到蔡和森从北京邮寄来的两本《新青年》。当阅读到“陈独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文章”时,张昆弟对反孔问题开始关注。[32]35-36张昆弟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时,“就去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老师的住处请教。”[32]29蔡和森对《新青年》每一期反复阅读,还经常和毛泽东、邓中夏等谈论《新青年》,思考和讨论《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而对墨子的学说发生强烈的兴趣。他更是指出:“《新青年》标榜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代表美国的精神,但陈独秀倾向社会主义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宣传社会主义了。”[33]30向警予是《新青年》早期“热心的读者”,此后又成为《湘江评论》“热心的读者”。[34]14在《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学灯》等刊物的影响下,向警予“寻找救国的道路”。[34]39-40丁玲在长沙周南女校时,教员陈启明将《新青年》介绍给同学看,并给学生讲“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个个的言论所鼓动”,其中,施存统的“非孝论”给丁玲的印象很深。[35]可以看到,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诸生,使《新青年》的主流话语经由他们的吸收和过滤进入湖南,使之不再是一个只流通于中心城市少数知识精英之间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毋宁也是一个“投机事业”。[36]
从浙江、湖南两个地区的例证可以看出《新青年》的在地化阅读与地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的关系,旨在从具体的在地化视角,从阅读史的角度来说明《新青年》如何从上海、北京这样的中心场域蔓延到地方,以及《新青年》给“五四青年”带来的影响与机遇。毕竟,《新青年》的阅读史是由各个地方、各个个体参与的历史构成的,从接受与传播角度关注思想和信息的社会层面,对某些地域、某些人如何接受《新青年》进行描绘,不但可以比较透彻地考察和诠释地方性或个体的问题,还可以为研究更大范围内的心态、思想及社会变化提供参照、经验与思考,展现或回应更为广阔层面的生活、思想、社会的互动和思想传统问题。
三、“革命青年”的阅读转向与实际行动
《新青年》对青年读者群的影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偏向学术的,主要是偏向于胡适的自由主义,他们以傅斯年、罗家伦为代表,在五四之后负笈欧美留学,归国之后仍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另一类偏向实际行动,主要是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像前文提及的恽代英、周恩来、杨贤江等,他们在五四之后以实际行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奋斗,诠释了革命青年的形象。因此,《新青年》的分裂代表着两类不同读者群的分裂,从此,青年读者走上了两条迥异的道路。
1919年,《新青年》刊发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学说批判》《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基本理论和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新青年》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孕育乃至催生了20年代的政党政治乃至意识形态,从而刺激各地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形成。1920年,《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使一批知识青年转变为革命青年,从《新青年》中汲取关于马列主义的知识成为许多革命青年的共同追求。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郑超麟的心路历程值得关注。1919年,郑超麟从一位经常看报的老先生那里得知五四运动,其思想开始变化。1919年底,郑超麟赴法勤工俭学,海上航行三十三天阅读《新青年》成为其触摸五四的最好例证。在船上,新思潮刊物《新青年》广受欢迎。对于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郑超麟表示不满,“大骂陈独秀”。但“《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他,“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内心则完全改变了”,三十三天的旅程让郑超麟“潜伏的个人意识觉醒”,思想也从“写日记骂陈独秀”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37]163-168从他的心路历程中可知,其转变经历了三个过程,由“反感”《新青年》到被《新青年》“吸引”,进而认同《新青年》的价值,然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可能更多的和赴法勤工俭学时的经历有关,但《新青年》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促使他吸收了《新青年》的“思想资源”,认知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迅速地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信仰体系,成为一名“革命青年”。
“革命青年”思想发生改变大多在中学学业阶段,而这种改变又与《新青年》的阅读联系在一起。随着《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社会青年群体被吸纳到各种革命网络中,阅读趣味所折射的革命思想有点类似于流行文化,使中小知识青年加入这种流行文化中不能自拔。[38]可以看到,诸多的“知识青年”在《新青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氛围中成为“革命青年”。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求学的刘少奇“在学校里可以随便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并且“校刊上还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评述国内外政治形势”,对刘少奇产生了很大影响。[39]19叶飞在厦门中山中学读书时,和同学互相“传看进步书刊,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其中《新青年》是叶最喜欢的杂志。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叶飞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之路。[40]8-9这些青年关于《新青年》的阅读史折射出中小知识青年转向革命具有共同的心路历程。《新青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表征着一种对社会秩序与生活世界的反叛,知识青年从阅读世界出发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进而加入革命的队伍。
由阅读早期《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反孔”等议题,进而到阅读《新青年》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知识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过渡。在学业的起步阶段,最新接触的读物往往对其人格和性情发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多地方中小学图书馆中有《新青年》等新式刊物,这些刊物为学生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知识资源,形塑了中小知识青年认知中国社会、想象未来的概念工具。黄克诚在湖南第三师范求学时,就已阅读到衡阳书报贩卖部出售的《新青年》等“革命报章杂志”,对新思潮发生兴趣。至1924年,黄克诚认真阅读《新青年》,渐渐认识到革命对改变中国的重要性,故参加国民党组织。至1925年,他又阅读了《新青年》中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开始接受“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决心寻找中国共产党”。[41]13-18张闻天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和同学在图书馆阅报室阅读《新青年》,他们“常常在课余饭后,聚在走廊上、宿舍里讥评时政,谈论‘改造中国’的问题。”《新青年》“对他的触动特别大,阅读《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常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张闻天“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从此发端了”。由于抵制旧式婚姻,张闻天“对旧社会已经从怀疑、不满进而否定、反抗了。他的志趣也从工程技术向社会问题转移”。五四之后,诸多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文章中,听到了无产阶级奏出的凯歌,看到了‘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于是,他转变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42]17-21求学阶段不仅是求知识,而且是明道理,而所谓的道理,即是将个体与国家、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式教育在中小学校的普及,使他们对国情多了一份认知。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使他们内心激荡澎湃,他们希望有所作为。因此,阅读报刊成为他们求知识、明道理的重要方式。从《新青年》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世界中完成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在实际行动中效仿马克思主义,以革命的激情投入中国的革命洪流中。
在“革命青年”的成长经历中,一些老师和朋友对“革命青年”的引领作用非常重要。郭廷以在开封二中时比较喜阅新式书刊。其师王芸青因和陈独秀熟识,陈独秀常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给王芸青,王芸青又因思想保守不愿阅读这些刊物,而将其借给郭廷以,郭廷以得以接触和阅读《新青年》。至南京后,郭廷以开始大量购买阅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据郭廷以的观察,“这时凡以新青年自居的至少要买几本这类的书籍杂志,以表示学问的渊博,而借以结交新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青年”成为时代的主流。《新青年》变为党的刊物后,“新青年”很容易读到《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宣传品,以至于“新青年”一窝蜂“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43]77-79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受王若飞和赵世炎影响,才开始阅读《新青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特别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44]15使邓小平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此后在苏联的那段时间,《新青年》成为邓小平每天自修之读物。[44]28张云逸通过好友介绍读到《新青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促使了他思想的“敏锐”和“深沉”。此后,《新青年》成为他必备的读物,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45]39-41左权在醴陵县立中学求学时,已秘密地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刊物,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46]67,并经常和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为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6]72诸如此类因阅读《新青年》而加入革命队伍的 “革命青年”的个案不胜枚举。对于《新青年》的阅读与接受,改变了这些青年的求学与人生轨迹。从他们相似的个体经验来看,以《新青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其将个人人生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上诸例并非个案,其出现的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和场景之相似,都可大致说明五四期间《新青年》从改变知识青年的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出发,为中国走向马克思主义浸染了一层鲜明的底色,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均能见到“革命青年”的身影,并清晰可见《新青年》普遍流行之观念在中国不断传承、复制与影响。
四、结 语
本文从“五四青年”的角度对《新青年》阅读史进行了考察,旨在揭示《新青年》在培养“五四青年”过程中的价值与作用。进而言之,《新青年》对“五四青年”的培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青年》创刊之初将新青年视为阅读对象,在《新青年》的文本阐释中亦注意到对新青年的培育,以此吸引新青年的阅读。《新青年》同人通过对“青年”的论述,阐释了“新青年”的真谛,发掘了“新青年”的价值,使青年终于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阅读《新青年》成为“五四青年”改造思想的重要方式,他们通过对《新青年》的仪式化阅读,其自我意识萌芽,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编织自己的“意义之网”。其二,《新青年》为“五四青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其所提供的“文学革命”“反孔”“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工具为“五四青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们将这些概念工具与思想资源运用到各个角度,形成了对《新青年》的不同解读。这种解读使《新青年》作为“知识纸”“思想纸”的价值与功能得到极大提升,从而营造了新型的阅读大众,使五四成为一个阅读的时代。
从“五四青年”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新青年》重要的阅读群体。他们对《新青年》的阅读“不但只是种技能而已,更还是一道寻求意义的途径”。[47]这种寻求意义的途径是个体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对于个体的成长来说,“五四青年”往往将阅读《新青年》视为“进步青年”的重要标志。他们从《新青年》中寻找“思想资源”,进而将自己形塑为“文艺青年”“学术青年”“革命青年”等,使阅读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以改革社会为己任”“以破除旧社会为担当”成为“五四青年”的共识。对于个体的思想认知来说,“五四青年”阅读《新青年》不仅是看杂志、学知识,更是一种日常仪式和精神洗礼。他们阅读《新青年》后对陈独秀、胡适、鲁迅新文化人士和新思潮的广泛认同,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对五四运动乃至革命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五四青年”对《新青年》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报刊、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