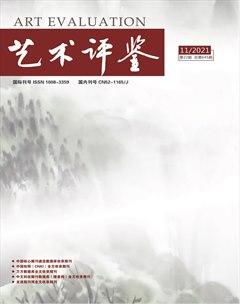科尔沁萨满仪式音乐中的节奏形态分析
摘要:乐器作为一种发声体,它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群体中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萨满教”是蒙古族最早的原始宗教之一,是古代文化的聚合体,具有综合的文化价值。根据萨满巫师手持法鼓,在进行请神、将神、送神仪式期间,所敲击的法鼓,以及法鼓环能够发出各种各样的节奏形式,本文选取贯穿于整个萨满仪式过程中的典型节奏型进行分析。
关键词:科尔沁 萨满 节奏形态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22-0054-03
从古到今,乐器在蒙古族各部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乐器不仅在民众音乐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在宗教仪式当中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也占据着重要地位。由此看来,乐器的文化属性随着用乐场合的不同,它的内涵和性质随着演奏群体的身份而发生重要变化。乐器作为一种发声体,它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群体中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蒙古族传统乐器在蒙古各部中以宴会中的表演呈现,但这些传统乐器在蒙汉杂交地区也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被当地民众作为重要的仪式道具来使用,是蒙汉人民在社会变迁与文化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音乐形式。
一、萨满仪式音乐
“萨满教”是蒙古族最早的原始宗教之一,自从成吉思汗建立汗国,萨满便成为国教,对汗国的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是古代文化的聚合体,包括了宗教、哲学、历史、民俗、天文、医学、音乐等文化内容,具有综合的文化价值,其影响延续至今。
内蒙古科尔沁地区,以及鄂温克、鄂伦春和布里亚特、巴尔虎蒙古人当中仍留部分萨满文化遗存,这些古老的仪式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空间逐渐失去生存地位,目前正处于消亡阶段。科尔沁萨满仪式文化被认为是蒙古族古老的萨满仪式文化最重要的继承体。科尔沁萨满仪式文化中,“萨满仪式音乐”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仪式举行时,萨满巫师手持萨满鼓,部分群众合起来演唱“请神歌”,召唤神灵,这一过程中音乐处于核心地位,而这些音乐的构成中主要以打击乐为主,并伴有人声演唱。
萨满(buge murgul)音乐是依附于萨满教存在的①,在萨满祭祀仪式过程中,萨满会穿着华丽的神服,腰间配着装饰的腰铃、铜镜、响刀等神器,手持神鼓,根据祭祀内容伴随着鼓的韵律,似说似唱地表述萨满神歌,身体也会随着节奏模仿动物的形态等等。据《多桑蒙古史》中的记载:“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茫,及神灵之附身也,则舞跃瞑眩,妄言吉凶……”②萨满音乐中由于以祭祀为主流,而鼓又是其中重要的乐器之一,因此诞生出了所谓的萨满神歌。在萨满祭祀仪式中,萨满通常会运用神鼓敲击出巨大的声响,希望借助震撼的声音来驱魔逐妖。应该说,萨满正是运用了神鼓宏大的音响效果来增添自己的勇气和力量,也给予妖魔鬼怪以威慑力。当萨满发现妖魔鬼怪时,会更加用力地击打神鼓,震耳欲聋的音响加之疯狂的摆动等,寓意着萨满帮助族人驱走邪恶,带给部族和平和希望。
二、萨满仪式音乐中使用的乐器
萨满在举办仪式活动时,使用一些特殊的法器或仪式道具。这些法器是萨满邀请天神时专门使用的,包括“萨满鼓”“法鼓环”“铜镜”“手锣”等,这些法器在仪式进行期间发挥着主要作用。
这些法器通过“请神”,将“神灵附体”,然后又通过“代神立言”和“还原”完成了神回归到人的过程。在神灵附体时,各种乐件大作,节奏也变得极为紧凑,这些音响混杂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空幻的效果。萨满的这种心理体验和情绪感受,都会借助于乐器和舞蹈传达给人。萨满教观念认为,神灵喜欢声音而鬼怪害怕声音。所以,萨满祭祀仪式中,激烈的鼓声和变化多变的节奏所代表的含义是不同的,而且演奏不同曲目时也会变化各式各样的节奏,应该说,这种击鼓节奏的差异就是用以表现先民的不同情感体验。
萨满巫师使用的法鼓是一种沟通神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乐器。法鼓的演奏,在仪式进行阶段,有着它特殊的功能作用,法鼓变化多样的节奏型中,构制着神灵的神秘、人的认同,表演中的歌声和持续不断的鼓声,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萨满仪式音声景观。而很多萨满师演唱的歌曲逐渐变成民间歌曲,或用器乐来演奏的器乐曲,而很多地方学者在搜集整理萨满祭祀音乐期间,发现很多古老的民歌曲调都来源于萨满祭祀歌曲。
法鼓环是萨满巫师在长期做法实践中由法鼓变化而来的一种乐器,外形似圆形的法鼓,中间镂空,四周镶嵌一些金属环。由于萨满巫师不能同时演奏法鼓和法鼓环,所以需要在仪式中加入其他巫师,以帮助完成演奏。据内蒙古科尔沁科左后旗巫师布仁巴图口述:“我从19岁开始跟随师傅走上请博的道路,刚开始只能给师傅拿乐器,师傅什么时候要法鼓,我就递过去。后来师傅教我演奏法鼓环,以配合师傅完成整场仪式。直到23岁师傅才教我演奏法鼓,我才能够独立完成请博仪式。”在萨满仪式过程中,法鼓是最重要的乐器。布仁巴图还说:“铜镜、手锣这两件乐器在我们日常的请博中基本不用,只有资历深厚的师傅在重要的场合才会使用。”由此可见,法鼓环、铜镜、手锣等作为主奏乐器的成员,配合演奏法鼓的巫师淋漓尽致地完成整个仪式。
三、萨满音乐中节奏形态分析
在内蒙古地区,萨满祭祀乐主要流传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当中。蒙古族将萨满祭司活动称之为“博·博勒呼”,将男萨满巫师称作“博”,女萨满师称作“伊图根”。早期的萨满巫师,不仅是一名医者,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很多萨满巫师能唱歌,还能演奏民间乐器,如口簧、鼓等。通過笔者的亲身田野,根据萨满巫师手持法鼓,在进行请神、将神、送神仪式期间,所敲击的法鼓,以及法鼓环能够发出各种各样的节奏形式,总的概括起来有九种节奏型。这九种节奏顺序可以归纳为五个阶段,即慢板—中板—快板—急板—慢板”。这种节奏型的设计安排与我国传统音乐的节奏流程不谋而合,所谓殊途同归。
萨满的仪式音乐分为三个部分,请神、降神、送神,各个阶段的乐器使用及其节奏有所不同。
(一)请神阶段
请神是第一阶段,“博”主要是赞美诗的形式,赞美长天生、吉雅其,唱诵时而晃动身体,节奏比较平缓,起伏不大。法鼓环敲击出每小节重音,法鼓在后半拍进入,然后以平均的八分音符xx xx连接,力度均匀。根据“博”唱诵的长度,重复演奏。赞颂结束时,以长音式的节奏两拍x-作为终止,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作呈示部分,即慢板部分。
接下来“博”以唱诵的形式,讲出要请的各路神灵的名字,语气平缓,带有敬畏之感,所以结构方整,节奏规整,变化较少,力度起伏不大。法鼓环以2/4拍的节奏,一轻一重x x敲击,象征着对神灵的召唤,法鼓以附点音符x.和八分音符x相以配合。力度随着博的身体变化和唱诵的进行稍有变换,情绪也逐渐激动,成为呈示阶段第二个部分的典型节奏型。
“博”的唱诵进入了尾声,请神即将成功,法鼓环第一小节以2/4的强弱拍子奏出,从第二小节开始只有强拍,弱位置的前半拍以休止符的形式和法鼓相配合。法鼓开始于急促的十六分音符xxxx,接着以规则的附点音符x.和八分音符x连接,仿佛预示着神灵即将到来,这个部分进入到中板,作为呈示段落的结束部分。
(二)降神阶段
作为降神的阶段,也是“博”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充当传话者的展开段落。作为快板部分,“博“随着神秘的歌声和激越的鼓声,舞步激烈旋转,摇晃身体。法鼓以八分音符xx xx和十六分音符xxxx的组合,敲击出激昂的节奏,法鼓环依然是以2/4拍典型的强弱节奏x x奏出沉稳规则的拍子,仿佛是神灵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天而降。
“博”在激烈的角色转换中不断加快步伐,增大肢体动作,变化频率也随之加快。为了能够给“博”动作上的声音支持,法鼓以附点音符和快速的十六分音符配合,法鼓环也加入快速的十六分音符,每两小节重复一次,共同营造出狂放奔放的气氛。这段也是整个仪式中的急板部分,也是高潮部分,音符紧密,力度强劲,声势浩大。
经过激烈的“决斗”,神灵终于降临,附体在“博”身上。前两小节,法鼓环用八分音符连续敲击三下,休止时用法鼓的两个十六分音符连接。后两小节,法鼓环只在强拍奏出两个八分音符,法鼓没有变化,依旧在弱拍的弱位置接龙。两件乐器以对答式的节奏配合,描述出“你说我听,我说你听”的场面,仿佛是神灵与人类的对话。
“博”作为神灵的附体,能够为百姓解决某些力所不能的事情。这段节奏是上段的延续,结构方整,法鼓环和法鼓以前起后应的节奏配合,构成一个层次分明、“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对答关系。法鼓环的四分音符演奏仿佛是神灵的诚恳询问,法鼓的八分音符仿佛是人们的认真回答,一个和谐的场景展示在众人面前。
(三)送神阶段
“博”治病驱魔完毕,就该将神灵送走,也就是送神部分,即慢板部分。法鼓在强拍以两个活跃的十六分音符和八分音符奏出,而法鼓环破天荒地的强拍休止,只在法鼓弱拍休止时以四分音符演奏,仿佛是为送走神灵做铺垫,这段结构方整,停顿分明,界限清晰。
这段为送神部分的典型节奏,“博”唱诵送神歌,祈請各路神灵回到深山继续修炼。法鼓以缓慢的四分音符连续演奏三拍,第四拍休止,而法鼓环只在法鼓休止的弱位置以相同的四分音符呼应,结构规整,音响弱化,节奏放缓。
这段类似于音乐作品的结束段落,是整首作品的总结。“博”恢复了本来面目,神智如初。第一拍法鼓和法鼓环以相同的八分音符奏出,第二拍法鼓环只奏四分音符,而法鼓环以十六分音符与之配合,相间交错,整段结构规整,界限清晰。
典型节奏贯穿于整个萨满仪式过程中,请神一般使用的节奏特点为,节奏平稳,结构规整,变化较小。降神阶段一般使用的节奏特点为法鼓和法鼓环不断变换节奏,情绪激动,声部密集,音响增强,是高潮部分。送神一般情绪从兴奋逐渐减退,力度也从强减退到弱,声部疏松,音响弱化。
文化始终处于变化当中,也始终作为一种变化体,在万千世界,适应着环境,塑造着自我。文化是交融的产物,音乐更是如此,那些流传几百年的传统音乐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被各民族人民接受、借鉴、创造和利用。北方草原历来就是多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区域,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各民族,在历史变迁和社会演变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草原文化,各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族音乐文化,汉族音乐文化也深深影响着少数民族。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双向流动中建构着民族音乐文化的多元结构体系,成为民族音乐文化交融后产生的极具特色的混溶性地方音乐文化品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及背后的社会文化,也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项目。
参考文献:
[1]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乌兰杰.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0.
[3]杨玉成.蒙古族科尔沁萨满仪式音乐的结构及模式[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4]秦建平.关于蒙古族民间器乐文化的几点思考[J].内蒙古艺术,2007(02).
作者简介:赵燕,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系列论文,项目编号:2014B062。
①徐嘉:《萨满神歌及萨满祭祀音乐文化研究》,《当代音乐》,2015年,第129页。
②(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