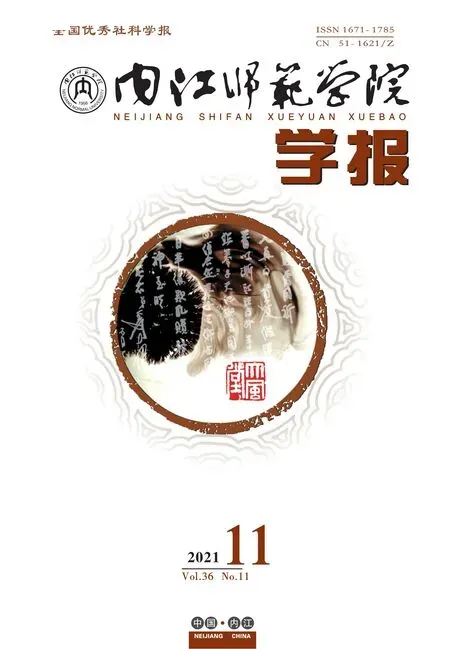张大千诗歌研究综述
曹 闽 川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7)
诗、书、画、印本相通,苏轼就曾在其《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盛赞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所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2],考之时代,以此四项推之近代,张大千可谓诗、书、画、印四绝。
张大千以画驰誉海内外,被认为是“终于让中华传统艺术在欧美艺坛大放异彩”的人物[3],是“五百年来一大千”[4],并于1958年被国际艺术学会公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5]。其实,张大千是“诗、书、画都戛戛独造”的大艺术家。张大千自己就曾说过:“穷年兀兀有霜髭,癖画淫书老更痴。一事自痴还自笑,断炊未忘苦吟诗。”[6]黄苗子认为,大千的诗歌“较之齐(白石)、徐(悲鸿),则功力更济”[7]。于右任在《题浣溪沙词·寿张大千先生六十》中说:“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8]谢稚柳也曾真诚地赞叹道:“今日读大千之诗若画,将无与东坡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非耶。”[9]给予张大千极高的评价,可见大千的诗歌在当时的影响力。
1980年代初,张大千逝世。学界对其的关注逐渐从绘画拓展到诗歌方面,其诗歌重新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学者们进一步挖掘大千诗歌方面的艺术成就,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张大千诗歌研究现状做一评述,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对张大千诗歌的进一步研究。
一、张大千题画诗研究
张大千一生中创作了七百余首诗词作品,其中大部分是题画诗[10]。他对于自己的题画诗曾有这样的论述:“吾画一落笔可成,而题署必穷神尽气为之,如题不好,则画毁也。”[11]因而,对于大千题画诗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多。郑雪峰从大千题画诗中“大部分是七言绝句,少部分是律诗,古体极少”的情况出发,认为“其艺术成就最高的当然也是七绝”。他着重分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题画诗作品,如《题荷花图》《题时装侍女》《题红梅》等,认为这些题画诗与画作珠联璧合,不但拥有“明确、深刻的主题”,同时“丰富了画的内涵,给人以更多的联想,是最好的画外音”[12]。韩晓光从张大千题画诗的家国情怀和艺术匠心入手,分三个方面详细阐述,即家国之思的情感载体,爱憎分明、淡泊名利的人格追求,以及对艺术的不断探索与创新。至于张大千题画诗呈现出的形神兼备、动静相映、诸觉交融、化实为虚、正侧结合等艺术特色,韩晓东的研究尤为清晰精辟[13]。刘宏《人格理想的诗意表达——浅析张大千的题画诗》一文则以题花鸟画诗、题山水诗、题人物画诗三个方面对大千的题画诗进行了精要的剖析,在探讨张大千题画诗的特色、分析其创作精神的同时,结合大千某些时段的特殊时代背景,对题荷花、题《南岳图》、题《贵妃扶醉图》、题《庐山图》四首诗歌进行了仔细地分析,论证了大千题画诗体裁多样、不拘形式、风格多样的特点,给人以直观的感受[14]。申东城《张大千诗歌与绘画关系析探》以大千题画诗为研究对象,寻找大千诗歌与绘画之间的关联[15]。他认为,思乡、漫游、体物、戏剧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大千诗歌与绘画的秒合,大千善于化用前人诗句,效法古诗文意、体式,多用古典入诗,这是其国画拥有深厚底蕴的不竭源泉。文章将张大千题画诗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关照,全面而系统,又注重对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同时采用了列表例举等方式,给我们思考张大千诗画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面,这是我们研究大千题画诗应该首先留意的。肖体仁的《论张大千题画诗的美学蕴含》一文以美学的视角统观大千的题画诗,对大千题画诗呈现出的诗歌意境与绘画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他认为,大千的题画诗“既富有一般诗笔难到的绘画美,又充盈着绘画难以抵达的诗意美”,是一座“蕴含深广的富矿”[16]。而其随后的《墨落能生万壑云——张大千题画诗的艺术特色》一文则着眼于大千题画诗体现的“补画之所不足或画之所不到”的特点,即化静为动,诗意飞扬;巧妙比喻,生动形象;俚语口语,诙谐风趣;叠声重字,音节明亮,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大千题画诗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路与材料[17]。朱丹、曾晓舸《张大千题画诗的修辞艺术》一文则着眼于张大千题画诗中常见“用典”,概括出其典故的出处,即历代文人佳句、上古神话、历史典籍、民间神话传说等[18]。此外,还对张大千题画诗中的譬喻、拟人、对偶、双关等辞格有所提及,角度新颖,为研究大千题画诗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王益《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张大千题画诗管窥》一文将现代美学主张和中国传统的生命意识观念相结合,对大千题画诗中诸如鸟兽虫鱼、山水泉瀑、花果松竹等生态题材进行探究,总结出大千题画诗中的生态美感(自然与自然物、人与自然、万物一体),认为张大千的题画诗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下的生态意识追求”[19]。而他随后与汪羽旎、沈穷竹的《试论张大千花鸟虫鱼类题画诗的生态意趣与审美张力》一文则又集中目光于大千题画诗中的“题花鸟虫鱼诗”,通过对花、鸟、虫、鱼的分而述之,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大千题画诗中的花、鸟、虫、鱼世界不仅充盈着生机、活力,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嬗递,是“民胞物与”语境下的生态审美的“爱意呈现”[20]。这篇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大千题画诗在生态美学方面具有的超前意识,率先肯定了大千题画诗中具有的浓郁生态审美意趣。潘先伟在《论张大千绘画诗词的主体性哲学精神与审美意蕴》中认为张大千的绘画诗词“不仅是画面的注脚,更凸显了绘画的意境。他的诗歌文辞质朴、内蕴沉稳、题材丰富、感情真挚、意境优美、立意深刻,往往与画面交融,蕴含着张大千的主体人格精神追求,将儒、道、佛传统文化精髓融会贯通,有着丰富的审美张力,表达了张大千主体性的生命哲学精神追求”[21]。至于夏中义《故国之思与泼墨云山境界——论张大千题画诗的心灵底蕴与其绘画的互文关系》一文则运用“以诗证画”的方式,以《泼墨云山、题泼墨云烟图、庐山图(之一、之二)》四首来印证大千的青绿写意三绝,又回顾大千题画诗中大量出现的关键词“故山”,从而点明驱动大千泼墨云山的原动力乃是“故国之思”,最后论述以《庐山图》为代表的题画诗“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翻盆自笑顽”正是其诗魂境界的最终完成[22]。该论文重视对诗歌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人物心境变化的分析,以“文献——发生学”的角度来解读大千题画诗及创新水墨境界的内驱力的原因,为研究大千题画诗又开一新天地。周于飞《谈张大千题画诗词中的隐括》一文对大千在题画诗创作中运用的隐括手法进行品评,认为隐括的手法对于提升大千题画诗的思想内容和开阔艺术境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3]。同时,通过其隐括内容,可以看出大千对于李白、苏轼、白居易等前贤的敬慕之意。周文从小处(创作手法)着笔,由小见大,为大千题画诗的更全面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点。
二、张大千咏花(竹)诗研究
张大千在咏花诗上不但体量大,而且咏花的种类繁多,在中国的诗坛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相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涉及的相关文章有许克福《名人与梅花拾趣》、郭伟《张大千荷花系列禅意研究》、张艳芳《张大千的梅花诗》、段汶利《又谈“诗画一律”——论张大千梅花的画意与诗情》、齐小刚《张大千咏花诗研究》、杨倩、张建锋《张大千咏竹诗的情感特质、艺术传承与创新》《论张大千竹画与竹诗的融合之美》等。
梅花性贞,是卓尔不凡、孤高独立人格的象征。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大多对梅花是有好感的,这已无须赘述。许克福列举包括北宋林逋、元代王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在内的九位名人与梅花的轶事,尤其对大千“梅痴”称号多有提及,记叙了其访竹园买梅而不得的事情,颇具趣味。郭伟立意于张大千“荷花系列”画作中展现的禅意,对于张大千绘荷的相关理论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此文虽不是对大千咏荷诗的专题分析,但其文对大千咏荷诗的首次提及并做了相应的分析,这是研究大千咏荷诗首先应当留意的。张艳芳对大千先生敦煌、巴西、日本、美国、台北等的一生行迹进行了解析,指出大千在各个时期、地段、年岁与梅花的不解之缘,同时直口称赞这些梅花诗“字字锤炼,丽句清词,堪称一绝”,是大千坚贞品格的体现。段汶利所谈及的“诗画一律”其实就是探讨张大千梅花诗中的诗画关系,文章说“梅花以绘画的形式统合了大千诗意的情感世界,也展现了画家非凡的艺术才华”,确实也是应得之语。齐小刚则是首次将大千的咏花诗当作一个整体来观照,齐文细析大千诗歌文本,抓住大千咏花诗的最大特征:数量大、种类繁。这篇文章一是深究文本,对大千咏花诗的取材对象、品类、数量进行了详细统计,从文献的角度精确展现出了大千咏花诗创作的整体面貌;二是对大千咏花诗的审美景观也结合相关文本进行了阐述;三是分析了大千咏花诗的三点成因。齐文不仅论述用心,引用有据,并且在论及“咏花诗审美景观”时“以花比德”的提法也颇为恰当契合,而且文采独具,可堪细读。《张大千咏花诗研究》一文是研究大千咏花诗为数不多的优秀成果,其可资借鉴之处,实不在少数。杨、张二人《张大千咏竹诗的情感特质、艺术传承与创新》则落脚于张大千46首咏竹诗,透过大千咏竹诗来窥见蜀竹意向在大千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即“品格、乡愁的重要表达”。此外,本文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蜀竹的历史渊源,梳理分析了张大千诗歌中对传统竹意向的沿袭及新意的体现,探讨了张大千创作咏竹诗所处的文化大背景。《论张大千竹画与竹诗的融合之美》认为大千的竹诗与竹画浑然一体、完美融合,表现了意境之美、乡情之美、林盘之美,认为竹林敏茂的四川是大千艺术素材和灵感的源泉。
三、张大千怀乡诗研究
大千一生漂泊,50岁以后,先后侨居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在外流浪长达30年,饱尝了游子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漂泊之苦,因而其后期的诗作大多充满了思国怀乡、念友思亲的感情。大千诗歌中浓郁的家国之思也是近些年研究者对他诗画艺术成就进行深入探析的艺术渊薮。
邱笑秋先生的《梦与帆——张大千诗词初探》认为大千的怀乡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50年代移居印度大吉岭是“避乱去国”,50至60年代先后旅居南美、美国则是“移居隔尘”,晚年定居台北则是“欲归而不得”[24]。邱文立足大千三个时期的诗歌文本,深入浅出,令人信服。李永翘先生的《张大千怀乡诗评介》[25]84一文对大千寓居、游历各地时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诸如《无题》《怀祖韩兄妹》《赠友》《致友》等怀乡诗)进行了评析,认为大千50岁以后,思国怀乡、念友思亲成了大千晚年艺术创作中不可更改的总主题。他结合大千诗歌文本,认为大千的怀乡诗是“(大千)整个诗歌艺术甚至整个艺术创作中最晶莹璀璨的一环!”[25]86同时也是大千晚年诗歌创作的主流,特别是后期的诗歌,完完全全表现了一个海外游子对于祖国母亲的“苦苦依恋”,是大千纯真情感的深切体验,是其苦恋故山的晶莹之泪的凝聚。李永翘先生因为亲身编注《张大千诗词集》,因而对大千的诗歌创作的理解自然是很深刻的。肖体仁、廖品端《万里归迟总恋乡——张大千怀乡诗简论》一文则层层分析张大千,以“看山须是故乡亲”“挂帆归日是何年” “挥毫蘸泪写沧桑”三句大千怀乡诗作为行文结构脉络,从大千大力写故乡山水、大力写梦中诗、大千怀乡诗的诗意呈现三方面来表现大千对故乡的极致怀念。肖、廖二人的论文同时还摘出了大千诗歌中感情真挚、绘声绘色、以口语入诗等三方面特点并作了逐一讲解。文章说“诗歌是讲究语言表现的艺术, 而张大千似乎并不怎么注重诗的语言技巧, 其语言却颇具特色, 自有个性”[26]291,认为大千怀乡诗中“那浓浓的乡愁, 深深的思恋, 弥漫于记游写景、题画咏物、酬赠应答等各类题材之中, 杜鹃啼血, 长歌当哭, 时时撩拨着海内外无数游子柔软的心弦”[26]292,是颇为贴切的。申东城《张大千思乡爱国情怀三变探微》[27]126一文将大千诗画、言行当作参考标准,考察其漂泊羁旅一生的游踪,探析大千乡土情怀演变的三个阶段。申文将大千一生分为游居留学(17岁-52岁)、离乡去国(52岁-79岁)、归居台湾(79岁-逝世)三个阶段,并深入分析了大千家国情怀三变的原因,即一生的丰富游历、多变的时代政治及个人对传统的固爱三个方面。申文不仅指出了大千酷爱传统、学习传统的为诗特质,还有意识地去窥究大千怀乡诗所独具的特殊属性,大千“血液中永远奔流着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思想独山岐山、兼济天下的情怀”[27]129,认为这是其家国情怀不断深衍、变化的内在动力和诱因。申文深入浅出,重视大千“思想艺术成长的真实过程”,对于我们更真切了解大千思乡爱国诗歌的艺术风格特征有很大的裨益。
四、张大千其他诗歌研究
第一,从地域角度的研究。杨倩《论张大千的蜀中画与蜀中诗》[28]21一文探讨了大千在抗战时期的蜀中十年艺术创作活动,尤其是诗歌作品、绘画作品。杨文历数大千在蜀地的游历史实,得“四川江山之助”的大千诗歌风格从早年的“诗古”转向师法造化,由“风雅有余、韵味略浅”逐渐变得朴实自然而真率豪放。杨文深深服膺于大千蜀中诗神韵气度,认为“心与自然的圆通” “真实真切的情感”的艺术创造实为大千蜀中诗歌、画作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因而杨文最后总结“蜀中十年,是张大千诗歌创作的转折点”“蜀中山水无疑孕育了张大千的诗情,让他的蜀中诗别具风采”[28]23也是可信之论与应得之语。黄群英《张大千诗词创作的巴蜀情怀研究》[29]一文认为张大千诗词创作的巴蜀情怀主要体现在“借巴山蜀水寄托情思”“借怀人抒发对巴蜀的情感”“借体物张扬对巴蜀的感情”三个方面。大千诗词中的浓烈张力正是其内心中的巴蜀情怀所赋予的,大千一生漂泊羁旅他乡,对故乡的思念也便体现在他对亲友的思念、对自然万物的书写之中了。黄文充分肯定了蜀山蜀水对于大千诗词创作的重要意义,也充分认识到了巴蜀情怀在大千诗词赏析中的不可或缺的价值。
第二,佚诗辑补。刘振宇《成都新发现的张大千轶诗》[30]新补大千诗稿4页7首(第1、2首重复,实为6首),并从佚诗风格、书法风格、落款时间等分析出了具体的创作时间,2-5首书写时间应当是1944年2月,1、6、7首书写时间应当是1944年8月。刘文以张大千年谱、现代笔记学、现代心理学等原理对大千此6首佚诗进行了细致的考释,究其年代、探其背景,有理有据,推琢可靠。刘文所辑补之佚诗,均为《大千诗文集编年》《张大千诗文集》所未曾收录之作,对于后学者研究大千诗歌有着极大的裨益。
第三,伪作辨析。殷晓燕、王发国《〈张大千诗词集〉部分诗词作者考辨》[31]对李永翘先生编著的《张大千诗词集》中收录的一部分非大千先生所作的诗歌进行了辨析。殷、王二人振叶寻根、沿波讨源,通过认真考索,得出五十余题画诗、词、对联及断句,系为前人所作而误收于《张大千诗词集》中。殷、王二人在论文中指出了原诗的作者、出处书名、题目,也比较了异文及介绍了原作者的事迹,加了按语和编者说明,简洁直观,使得读者一目了然。殷、王二人从伪作辨析的校勘学角度入手,辨析了误入大千诗词集子中的伪诗,对于更好地研究大千诗歌、恢复对其诗词艺术的正确认识有着积极的作用。王发国、戴丽松《张大千临抚赵子昂〈马上封侯图〉之题识诗文考论》共四篇,分别为“白阳山人题后考论”“巴西邓文原题跋考论”“赵子昂款识考论”“张大千题识考论”,对张大千部分诗词的作者、标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还对李永翘编《张大千画语录》附载的大千所用之钤印误认做了纠正,[32]对于我们更客观而深刻地了解大千诗词创作的真实面貌有很大的帮助。魏红翎的《张大千诗词校勘》则是通过对《张大千诗词集》三个版本的比较,对包括《夷陵三游洞》《江山雪霁图仿右丞真本》《病目看云感赋》在内的二十八首诗歌(《题青灯课子图》有两首)的一些用语用字进行了校勘和辨析[33]。
第四,其他角度。周于飞《从张大千看守正体诗词创作的价值》[34]则别出心裁,从大千诗歌中的“守正”特征出发,分别从大千诗歌的创作主题、艺术特征两方面来论证“守正体”诗人的诗词创作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大千诗歌体现的“雅正”特征正是其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结果,周文在以大千诗歌为探讨样本,正是对“守正体”诗人诗词创作的一种肯定。在文章中,以《大千夷陵三游洞》《春娘曲》《初试软片隐形眼镜戏赋绝句(四首其四)》《观己卯闰七月二十七日为某君所画扇是日日机大炸梧州》四首诗歌来详解“守正体”之艺术特征,同时略举他例加以佐证,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大千的“守正体”诗词创作正是对诗词创作主流传统的继承与回归。而对大千诗词创作的分析,同样也能为如何评价“守正体”诗词提供文学史意义上的参考。
五、结语
张大千的诗歌是一处未被大多数学者注意的富矿。前人以丰厚学养进行研究探讨的,大多是大千在绘画方面的巨大成就,而对于大千同样名世的诗歌创作倒显得不那么热忱了。
事实上,在大千绘画艺术上的探究已经较多,对于大千诗歌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千诗歌巨大的数量、丰富的题材乃至于蕴含其中的思想感情和其研究成果并不相称。纵观现有的成果,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大千诗歌进行研究。
一是“向深挖”。大千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因而其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自然是经得起推敲和深究的。对大千诗歌的研究要秉持着打“持久战”的思维来,而不能仅仅是抱着“蜻蜓点水”或“打游击战”的态度来做。要回归传统的研究诗词的态度,对于大千诗歌中的创作主题、历史背景、思想感情、特殊的去国经历等进行综合的考量,要系统而不要细碎,要细致而不能大概,要追根溯源而不能点到即止,要创新深刻而不能旧饭重炒。例如大千诗歌中的爱国主义主题的探析、大千诗歌中的“故山”情结、大千诗歌中的“梅花”情结、大千的怀乡诗研究、大千的纪游诗研究等。大千的诗歌能做的选题太多,但无一例外都需要学者摒弃浮躁和功利主义,转而安神静气地去认真阅读文本,同大千对话,从而找寻其中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二是“向外求”。大千的诗歌多为题画诗,而中国传统本就有“诗画一体”的观念,因而绘画艺术与诗歌创作的学科交叉研究也成了大千诗歌研究的重要方向,诗画互证的研究方式也须得为学者所注意。此外,大千也是一位深谙佛道哲学的艺术家,大千的诗歌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之处,因而研究大千诗歌,应当要有学科交叉的勇气,又要有融合传统与新知的胆量,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碰撞才能激起学术的火花。相较于中国传统的画家、诗人,大千有周游欧美的独特经历,因而他的诗歌所承载的内容思想较于前人更丰厚,他诗歌中所描绘的异域风情、近现代事物、当地历史掌故等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这需要研究者跳出传统的圈子,将视野投放到海外去,更新耳目,从而得出新的观点来。
相较于层出不穷的大千绘画、书法研究成果,着眼于大千诗歌研究的文章就显得有些“零星”了。然而,随着大千文化的不断传播和学者们对大千艺术成就的重新回顾,我们仍然可以在各种场合欣喜地发现学者们对大千诗歌愈来愈烈的关注。无论如何,对大千诗歌的研究会持续深入下去,也会有更多突破性的认知出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