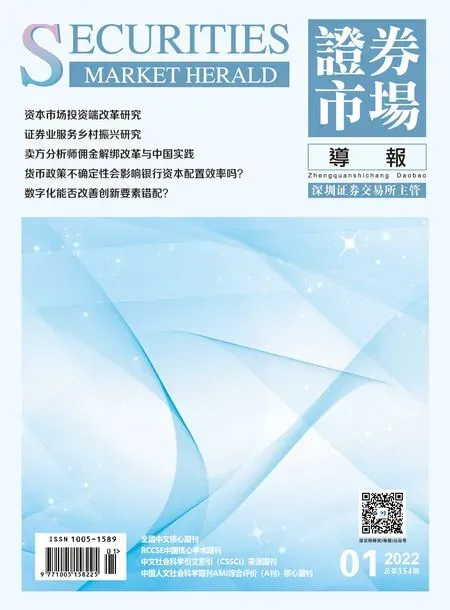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行为指引制度研究
吕昊 贾海东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2.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中长期资金“压舱石”作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也对“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和方式”作出明确要求。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助力科创企业成长、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一环。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实践表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价值与理念有待进一步优化、更新,亟需确立一套以行为指引为基础的规范制度。
一、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面向
通常认为,机构投资者擅长信息挖掘和投研分析,其有效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实质性提升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出于此考量,我国长期推进机构投资者发展和培育工作。以保险资金为例,自2005年批准入市以来,截至2021年1月,用于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保险资金高达29554亿元人民币。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初步具备,特别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基金管理公司代表基金对外行使投票表决权工作指引》对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基金公司表决权行使等做了集中规定,夯实了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也在增强,部分机构投资者已制定了参与公司治理的目标与原则、组织与实施、参与策略等相关内部制度,其中有些机构已对外公开披露或正在考虑逐步公开相关制度,头部公募基金公司清晰地认识到其作为机构股东具有参与被投公司治理的责任,部分机构已成立或正在筹划专门的ESG投委会作为相关事务决策机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方式不断丰富,投资机构一般通过实地调研、投资者说明会、电话、邮件、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等多种渠道行使质询权和建议权,少数机构通过推荐董事、监事人选参与治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也取得一定效果,对于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减少“内部人控制”、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的积极作用正日益显现。
近年来,A股市场境内外投资机构持股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A股市场境内专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17.26%,境外机构投资者为5.04%。但与美国等境外成熟市场比较,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总体仍较低,缺少在上市公司治理方面有较大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同时,机构投资者的数量不多,且投资业务、投资策略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此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也影响到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A股市场日均换手率较高,持续波动问题并未得到改善,追逐热点、炒作概念依旧盛行,长期投资现象并不明显。总体来看,我国机构投资者培育存在量、质双重提升空间。
结合实践情况看,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参与公司治理方面还存在着总体积极性不高、参与制度不规范、披露不充分、参与手段有限、参与质量较低等问题,反映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三重困境。
其一,部分机构投资者开始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但大多数尚处于“搭便车”状态,积极性总体不高。据统计,公募基金中行使投票权的占87.5%,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协商的占21.25%,提出议案、行使股东提案权的占5%;私募基金中行使投票权的占50%,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协商的占13.9%,提出议案、行使股东提案权的占8.3%。相较质询权及建议权,机构投资者普遍积极行使投票权,但难以投出反对票,和境外机构相比很少与上市公司沟通关于议题顾虑和异议,更不会对外公开投反对票的理由。实践中,部分上市公司对于投资者建议和问询不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构投资者的主动性。
其二,在践行股东积极主义的机构投资者中,存在创造价值的案例,但也大量存在转移、破坏价值的案例。部分机构投资者道德底线低下、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利用杠杆资金进行并购,谋求公司的控制权并过分追逐短期收益,忽视所代表投资者所能承受的风险、忽视公司长期发展价值,忽视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三,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明显,信息挖掘能力、投研分析能力存在较大差别。伴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基金经理队伍建设不均衡现象明显,部分机构投资者的噪声交易、风险控制、选股能力同个人投资者相比没有明显优势。实证研究发现,绩优基金表现出对个股特质信息、公司基本面信息的关注与挖掘,同时具备卓越的投研分析能力,践行了理性投资与价值投资理念;但绩劣基金主要关注市场有形信息和非基本面信息,投机行为明显。这显示出机构投资者发展的不均衡,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创造价值与破坏价值并存的现象。
二、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规则不足
上述困境的形成不仅与机构投资者自身缺陷有关,也与理论界对机构投资者培育的偏颇理解密切关联。在我国资本市场迈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改革逻辑已然转向。在新范式下,理论与实践对机构投资者之于资本市场的压舱石功效认识深刻,但对机构投资者之于上市公司的价值还在逐步认识过程中。倘若将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价值称之为外部价值,对于上市公司的价值称之为内部价值,则机构投资者的价值应当是内外部价值的统一,且核心逻辑应表现为“因为内部价值的有效实现,所以外部价值才得以彰显”。在现代金融环境下,公司的外部融资深受内部治理的影响,资本市场外在地表现为证券法制,却内在地体现出公司法制,即“公司法制与证券法制均应当以完善公司治理为切入点”。反观当前的机构投资者培育措施,均是从发展及稳定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没有触及到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底层逻辑,激励与引导制度严重不足。
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培育措施大致可概括为三种:其一,通过政策松绑促进银行资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其二,通过制度设计强化长期资金与基金公司的合作;其三,引导资本市场开展长期考核。首先,松绑长期资金入市的限制能够显著提升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积极性,从数量上改变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但数量上的提升并不能保证在质量上培育出优质的机构投资者,甚至还会由于监管尺度的放松加大机构投资者扰乱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宝万之争即为例证之一。其次,强化长期资金与基金公司的合作确能为信息挖掘能力强、投研水平高的基金公司带来充足的资金来源,但无法规制那些关注公司非基本面进行投机的机构投资者,市场上仍然充斥着大量不合格的伪机构投资者。最后,引导资本市场开展长期考核确为一项好的制度,有利于克服机构投资者的短视行为,但长期考核应当关注机构投资者自身能力还是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尚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长期考核结果的市场指引功能有待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总结来看,上述措施依旧未触及机构投资者价值实现的底层逻辑,也未聚焦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激励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针对我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公司的特殊情况,理论界尝试“尊重现实,确立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藉由控股股东信义义务予以规制。然而,信义义务是否能适用于机构投资者尚缺乏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构建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中小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同途殊归”。美国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适用有严格的范围限制,被定位为大股东压制下小股东寻求法律救济的可用而非唯一渠道。在我国,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更多指向的是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尤其是在证券监管“追首恶”语境下,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直接指向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中小投资者应当承担的义务。但过分强调责任追究,容易忽视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应有的责任边界。在此种倾向下,“立法会对控股股东的行为给予特殊的约束,不仅消极地要求控股股东不得为某些行为,还会积极地要求控股股东为某些行为”,这将会给公司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带来更大的阻碍。
三、行为指引制度契合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
破解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困境,需要从完善公司治理规则体系、丰富参与治理的方式方法、营造相关市场生态、提高参与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施策,宜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引入行为指引制度,构建具备一定约束力的促进型法律制度。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指引是由监管机构、交易所或者行业自律组织(基金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等发布的倡导性文件,是规范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软法,能够克服传统硬法“单向度治理”扼杀尚不成熟事项的弊端,避免落入“一管就死”的窘境。
(一)行为指引制度的性质
其一,行为指引是一种行为规范。有观点认为软法不具有强制力,因此不是行为规范。但是,该行为指引是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客观行为进行引导与评价,而不是泛谈机构投资者的主观道德,明显不同于道德软约束。通过市场化、规范化的指引、评级和评价机制,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客观行为予以量化和可视化,反映机构投资者的声誉价值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辅助投资者作出更加科学的投资决策。可见,软法性质的行为指引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量化声誉价值和辅助投资决策三种途径具备了规范性和约束力。
其二,作为软法的行为指引具备相当的弹性空间,有利于实现灵活约束。机构投资者具有非常明显的异质化特征,对冲基金与指数基金所表现出的股东积极行动就明显不同,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差异明显。基于此,针对特定类型的机构投资者量身定做适合其特征的行为规范制度尤为必要,而不能采用平铺式的统一规则。行为指引所具备的任意性条款将极大促进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而不会因规则的僵化扼杀其积极性。
其三,行为指引的实施强调共识机制的构建。行为指引更注重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主体之间的开放包容性,通过对话、协商等途径,真正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达成一定的利益平衡,起到正向引导作用。一方面,行为指引表现为一种软约束力。通过舆论导向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道德约束机制、文化伦理机制等软约束,实现行业内的自律与规范。另一方面,行为指引还表现为一种硬约束力。通过对参与公司治理行为的量化分析,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实质性影响上市公司的利益,因而具备了硬约束力。即行为指引通过构建上市公司、监管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共识机制,使其具备了制度硬约束力。透过软硬双重约束力的协调配合,培育机构投资者自愿、自觉遵从公司治理规范的意愿与能力,契合培育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制度的初衷。
(二)行为指引制度的逻辑
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的运行机理在于深入践行股东积极主义,通过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特有问题的分析,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激励与规制措施,从而防止机构投资者不作为或乱作为。
随着公司治理的“纵向”代理成本不断降低,管理层越来越负责,上市公司的积极股东可能越来越多地转向针对其他群体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同时,积极股东为了不与“搭便车”的股东分享利益,开始大量从自我交易、内幕交易或者其他非共享回报模式中获得私人利益。传统“纵向代理理论”(vertical agency costs)逐渐分离出当前“横向代理理论”(horizontal agency costs)。
另一个层面,机构投资者是否采取积极行动,以及采取何种程度的积极行动,是利益权衡的结果,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下的理性行为。传统意义上,股东欲通过改善公司经营以提高自身回报,通常会增持股份甚至谋求收购上市公司来实现控股,进而直接推行自己的治理方针,这就是Manne于1965年提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然而,股份增持需要耗费巨大财力,公司收购面临严格监管,成本不断上升,绝对控股变得较为困难,因此,利用持有的股份作为推动变革平台的方式应运而生,即“公司影响力市场理论”(market for corporate influence)。为此,应当立足于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差异进行规则设计,笼统的、格式化的股东权利并不足以激励机构投资者,更不足以规制机构投资者。
(三)行为指引制度的域外实践
行为指引制度发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的尽责管理准则制度(Stewardship Code),是一种约束、规范和引导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纲领性指导原则,由投资者自主决定是否受准则的约束。目前,全球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本地区的尽责管理准则。为了窥探准则背后的制度原理,本文对此类规则进行了归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全球地区性尽责管理准则一览(截至2020 年12 月)
纵观上述21个国家/地区所发布的24份指引,特征较为明显:(1)行为指引的目标指向明确,内容不断丰富,重点提及了七项内容:stewardship(出现16次)、monitoring voting(出现2次)、shareholder(出现3次)、responsible investing(出现4次)、guidelines/principles/framework(出现10次)、institutional investors(出现9次)、governance(出现3次)。自英国Stewardship Code开始,无论其他国家或地区行为指引名称是否使用stewardship的表述,其行为指引的目的均确定为“尽责管理”。但是,随着行为指引制度在全球的不断发展,各国家/地区所发布的行为指引内容不断丰富,朝着负责任投资、绿色投资、公司治理以及机构投资者等细化方向延伸。(2)行为指引的定性多为原则性框架,一般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随着行为指引制度的丰富发展,部分国家/地区开始在行为指引中加入principles/guidelines/framework等表述,以示行为指引的非强制性特征和原则导向型监管属性。关于行为指引的实施路径方面,域外大多数国家/地区均选择了非强制性规制,机构投资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受规则约束,按照“遵守或解释”原则(comply or explain),机构投资者应当尽可能遵守规则,若未能付诸实践,能作出解释即可。(3)行为指引的发布主体主要集中在监管机构(占比50%),其次是行业组织(占比37.5%),第三方相对较少(占比12.5%)。作为行为指引的发布主体,监管机构与非监管机构各占一半,一定程度上说明行为指引的性质并非纯粹的软约束或者硬约束,而是兼具“激励”与“规制”色彩。
对于尽责管理守则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以英国为例,部分研究认为,Stewardship Code通过倡导ESG投资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了资本市场投资理念的转型。亦有学者以公司股价的表现来研究尽责管理守则实施效果,认为准则的制定虽然不能保证公司的行为符合机构投资者的最佳利益,但准则是董事会治理意图的信号,也是投资者判断董事会未来行动的基准,因而能够更好地实现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良好互动。但亦有学者认为尽责管理守则的最大贡献在于使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角色合法化,除此之外并无实质性功效,甚至有可能造成股东民主意识觉醒后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的混乱。
四、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的具体面向
(一)行为指引制度的着力点
其一,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应当从约束“控制权”转向规制“影响力”。机构投资者奉行“组合投资”原则,力求降低成本与风险,一般不会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用相对较小的股份,借助自身在信息、专业知识以及谈判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在公司中的影响力是其常用手段,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鉴于此,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的规制起点应当转向对此种“影响力”的制约,以期引导机构投资者合理合法利用影响力参与公司治理。
其二,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应当以培育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目标,并构建激励与规制相统一的指引制度。通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充当资本市场“压舱石”并促进资本市场有序运转是机构投资者的核心使命。为此,应当在激励与规制相统一的基础上引导机构投资者积极进行价值投资,构建促进型法制而不是单向度地进行规制。
其三,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指引既应当区别于信义义务规则的具体设计,同时也应当借鉴信义义务的规则意旨。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应当设定为任意性规则,以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传统过分严格的信义义务不利于机构投资者践行股东积极主义。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的本质是限制其从事利益冲突的行为,若能保证委托人与公司利益不受损失,过分严格的信义义务反而会限制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行为,降低效率和股东积极主义的价值。因此,关于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的规则设计,应当以任意性规则为主,强调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自愿约定。
其四,补强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的规范约束机制,从“信任基础”的维护与“共识机制”的强化入手,厘清行为指引的职责面向。机构投资者的信任基础部分来源于法律规则的创设,部分来源于委托人对受托人道德品质、专业能力等主观上的肯定,还有部分来源于共识机制的构建。上述信任的三个来源,均需要在制度规范层面予以适当转化,将行为指引的规范后果细化为信念责任、审议责任、行动责任与后果责任,并辅之以信息披露、审慎标准、过程控制等来维护信任基础。
(二)行为指引制度的具体内容
具备约束力的促进型法律制度,一方面需要为调整对象设定行为边界,起到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为调整对象设立普遍性的豁免机制,使被调整对象能够通过解释得以免责进而保护其积极性。基于此,宜将我国的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界定为非强制性规制,确立“遵守或解释”的基本原则。“遵守或解释”原则在欧盟公司法与证券监管中居于重要地位,并被欧盟监管者认为是提高市场透明度、披露市场参与者战略活动的首选监管工具。该原则最大的优点在于实施的灵活性,能够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间接的协调机制,从而促进投资者相互谅解各自的不同主张,弥合不同类型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鸿沟与意见分歧。概言之,“遵守或解释”原则契合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面向,同时能够通过间接协调机制最大限度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质量,是我国在构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指引制度时应当确立的基本原则。
培育基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机构投资者,是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的目的。而此目的的实现,有赖于股东权利行使这一基础事实的实现。因此,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指引制度,应当以股东权利(尤其是投票权)的行使为核心规则,构建以机构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为核心的行为指引制度。
其一,细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具体规则。无论是基于“影响力”还是基于“控制权”参与公司治理,作为公司股东,机构投资者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是最基本、最主要的途径,为此需要明确以下三方面内容:(1)投票义务。机构投资者应当负责任投票,典型如相关国家和地区出台的行为指引所规定的“负责任投资”(responsible investing)。要求机构投资者设立专门的投票委员会或者与独立的投资顾问合作,除非客观原因无法投票,机构投资者均应当参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并积极行使投票权,同时严格限制并规范代理投票行为(proxy voting)。(2)投票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应当向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自身的底层投资者披露投票结果、投票程序以及投票权的行使记录,并定期向行业组织或监管机构报送格式化的信息披露表格。(3)投票标准(voting policy/guidelines)。投票标准有两层含义,制度层面的含义为机构投资者事先制定的,针对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和不同性质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如何表决的指导性文件;实践层面的含义是机构投资者具体行使投票权时所考量的因素。一般而言,机构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定位等相关因素,制定程式化的指导性文件以规范其投票行为;同时,实践中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变通实施,但应当具备可信的实践标准予以支撑。
其二,积极探索机构投资者与公益股东的协作模式。面对当前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困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普通小股东身份出现,但却达到了普通中小股东难以企及的行权维权高度。作为公益股东持股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不仅具备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还具备带动其他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功效。探索机构投资者与公益股东的协作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1)通过投资者教育、积极行动示范等措施促进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当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承担着中国投资者网及网站配套微信公众平台等的运营维护工作。中国投资者网是由中国证监会管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具体承建和运行维护的公益网络服务平台,是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政策、法律法规宣传的重要窗口。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也积极推动与证监会派出机构、交易所、行业协会、证券公司、媒体等的合作,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资本市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同时通过示范作用,带动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有效的公司治理。(2)有助于解决当前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足之痼疾。由于公共属性以及法律特殊授权,公益股东虽持股较少但影响力较大,容易带动剩余股东积极参与,有效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同时,公益股东本身并非追求一定时期内收益的最大化,其代理成本与积极行动成本均较低,激励机制较健全。为此,宜通过公益股东的良好示范,有效带动剩余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从而弥补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
行为指引制度的规则体系应当具备一定程度的层次性,可分为基础性条款与特殊性条款。
基础性条款明确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基本行为,是机构投资者参与所有类型公司治理时均应当遵守(或解释)的条款。主要内容包括:(1)投票权及其他股东权利的行使规则。(2)对上市公司的监督规则。(3)与上市公司的私下沟通及私人参与规则。(4)关注目标公司治理原则的分歧。域外指数基金通常采用“检查框治理”(check-the-box governance),即将目标公司的治理安排与一般治理原则进行比较,重点关注其中存在分歧的部分。(5)利益冲突的处理规则。机构投资者应当充分说明在践行积极行动时如何处理可能面临的利益冲突;同时,在机构投资者作出“亲管理层投票”时,应当解释投票行为的合理性。
特殊性条款是部分机构投资者在特定情况下需要遵循的指引规则,需根据法律环境、监管要求以及上市公司自身情况设置不同条款。具体包括:(1)集体行动条款。集体行动困境是公司的固有难题,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方可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因此,集体行动不宜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基础性条款。(2)升级措施条款。明确机构投资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捍卫股东权利,以此起到指引与威慑的双重效果。(3)消除治理分歧条款。在发现治理原则的分歧之后,机构投资者通常并不会致力于消除该分歧,因为,此种主动消除分歧的行为是一种敌对甚至是对抗的行为,会为自身带来较大成本;同时机构投资者认为,消除治理原则的分歧并不能使其获益,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
五、结论
尽管各国和地区资本市场均提出要培育长期主义的机构投资者,但囿于法律传统与现实背景的差异,具体践行路径必然有别。步入新时代,我国资本市场改革逻辑已然发生转向,更加注重对投融资端的改革与创新,培育基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并引导其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紧抓机遇,围绕核心问题解决主要矛盾,构建契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的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
然而尚需明确,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是一个开放且不断发展的规则体系。作为软法,行为指引制度虽不一定直接具备硬约束能力,但核心作用在于形成规则的“普遍性共识”,通过声誉机制及信任机制达到激励与规制融合的目标,同时也并不排斥硬约束的存在。此外,应当发挥极具我国特色的公益股东制度。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应当始终以“激励与规制并重、软约束与硬约束共存、公权力与私权利互补”为指导,构建契合我国资本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特点的行为指引制度,不断调整、持续完善,以期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
注释
1. 参见田利辉, 曹龙杰. 私有信息优势还是投研分析能力?——绩优基金与绩劣基金信息挖掘行为比较分析[J]. 证券市场导报,2021, (3): 50-51.
2. 参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1年1月保险业经营情况表[EB/OL]. [2021-03-05].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69471&itemId=954&generaltype=0.
3. 数据来源于公募基金季报、央行、银保监会以及信托业协会官方披露。参见华西证券. A股投资者结构全景图深度剖析(2021Q3).
4. See Chalmers J, et al. The wisdom of crowds: mutual fund investors’ aggregate asset allocation decision[J]. 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 2013, 37(9): 3318-3333.
5. 参见陆静, 邱于航, 秦大超. 公司创新投入对股票特质风险的影响——基于有中介调节效应的检验[J]. 证券市场导报, 2021, (12): 48.
6. 参见孟庆斌, 吴卫星, 于上尧. 基金经理职业忧虑与其投资风险[J]. 经济研究, 2015, (3): 115-130.
7. 有学者总结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逻辑为:以2013年为界,之前的改革逻辑是从融资企业角度出发的资本市场改革逻辑,之后是从投资者角度出发的资本市场改革逻辑。参见邢会强. 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逻辑转换与法律因应[J]. 河北法学, 2019, (5): 26-39.
8. See Santella, et al. Legal obstacles to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ctivism in the EU and in the US[J]. 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2011, 23(2): 257-307.
9. 参见赵万一, 高达. 论中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协同完善与制度创新——以公司治理为研究视角[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4): 143-144.
10. 参见赵旭东. 公司治理中的控股股东及其法律规制[J]. 法学研究, 2020, (4): 99.
11. 参见朱大明. 美国公司法视角下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本义与移植的可能性[J]. 比较法研究, 2017, (5): 50.
12. 同注11。
13. 同注10。
14. 参见王建文. 论我国构建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J].比较法研究, 2020, (1): 95.
15. See Sergakis K.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ply or explain” principle in EU capital markets[J]. Account. Econ. Law,2015, 5(3): 233-288.
16. See Chava S, et al. Managerial agency and bond covenant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3): 1120-1148.
17. See Robert P. Venture capital, agency costs, and the false dichotomy of the corporation[J]. UCLA Law Review, 2006, 54(37): 42-45.
18. See Henry G. Manne, 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5, 73(2): 110-120.
19. See Cheffins B R, Armour J.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by hedge funds[J].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11, 37(1): 51.
20. 从上述表格也能发现,实践中澳大利亚和印度也选择将行为指引作为强制性规则,通过硬约束规范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
21. 就制度是如何生成的,制度发生学提供了两条解释路径,即斯密、门格尔、哈耶克的“自发演化生成论”和康芒斯“理性创设生成论”。本文认为,兼具激励与规制性质的行为指引制度,是在环境自发演化下,法律的一种理性创设。
22. See Young S. Lessons from the UK stewardship code[J].Business Law Review, 2016, 30(2): 9-35.
23. See Picon A, Rubach M J. Does good governance matter t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the enact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lin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6, 65(1): 55-67.
24. See Chiu H Y. European shareholder rights directive proposals:a critical analysis in mapping with the UK stewardship code?[J]. Era Forum, 2016, 17(1): 31-44.
25. 参见尹迪. 责任投资趋势下的养老基金信托责任[J].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4): 109.
26. 同注15。
27. 同注23。
28. 美国对于此制度应用较为成熟:美国证监会规定凡在美国注册的投资顾问公司,需要在当年8月底前,向SEC提交N-PX表格(即SEC Form N-PX),共同基金及其他各种注册投资公司需要在表格中填写自身代理投票的情况,并提交给证监会。
29. See Ian R A, et al. Passive investors, not passive owner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21(1): 111-141.
30. 同注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