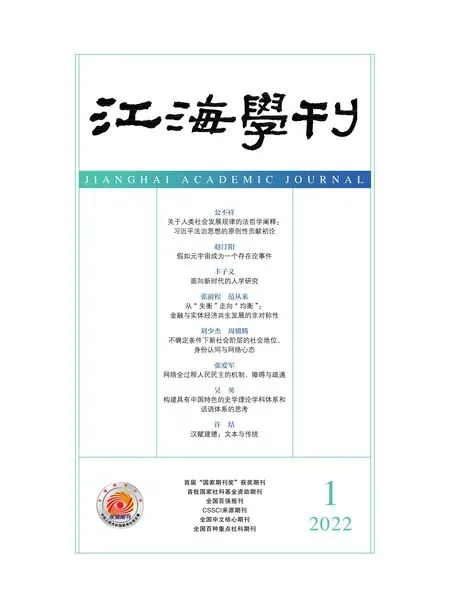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
——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
王卫平 潘伟峰
清朝建立以后,继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政策,重视荒政,建立养济院,对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民给予较大的关注和关怀。由于王朝甫建,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政局不稳,清初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民间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沿袭明末以来的惯性,表现出自发散在的状态。这种情况在雍正上台以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变。
如何理解雍正倡设慈善机构的“上谕”?
《清世宗实录》载有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初十日上谕:“谕顺天府府尹: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司其事者,乐善不倦,殊为可嘉。圣祖仁皇帝曾赐额立碑,以旌好义。尔等均有地方之责,宜时加奖劝,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壮及游手好闲之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长浮惰而生事端。又闻广渠门内有育婴堂一区,凡孩穉之不能养育者收留于此,数十年来,成立者颇众。夫养少存孤,载于月令,与扶衰恤老,同一善举,为世俗之所难。朕心嘉悦,特颁匾额,并赐白金。尔等其宣示朕怀,使之益加鼓励。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也。”这个诏谕透露出来的信息如下:首先,康熙年间的民间慈善事业处于自发状态,对于这些既有的民间“好义”之举,康熙只是“赐额立碑”,予以荣誉表彰,并无实质性的政策举措;其次,雍正皇帝对于普济堂、育婴堂等由民间社会创办的慈善机构抱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对于民间人士扶老救孤的慈善举动予以鼓励与提倡,不仅要求“时加奖劝”,更有“特颁匾额,并赐白金”的奖劝行为;再次,普济堂收养“老疾无依之人”、育婴堂“养少存孤”均属“善举”,因而号召各省督抚、地方有司“劝募好善之人”,在人烟稠集之处推广施行。因此,这个“上谕”可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即一改过去任由民间自生自灭转为政府提倡、推动。由此清朝的民间慈善事业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慈善政策的转变自有其契机。从资料来看,雍正上台当年(1723)八月初似乎曾召集朝臣召开过一个工作务虚会,征求各位大臣对治国理政的意见,要求“各抒其欲言”。(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设立社仓史料》(上)“詹事府詹事鄂尔奇为仿古制设立社仓事奏折”,《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詹事府詹事鄂尔奇提出的设立社仓建议得到大臣们的响应,从而成为雍正的决策依据,在全国渐次推广。(2)《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八,雍正五年六月初一丙戌上谕有谓:“朕之举行社仓,实因民生起见,又诸臣条奏者多言之凿凿,是以令各省酌量试行,以观其成效何如。”《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879页。与此相同,雍正二年发布鼓励各地兴办育婴堂、普济堂的上谕,也应与此次会议有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的《清代设立与管理育婴堂档案》收录一则《翰林院侍讲学士戚麟祥为请敕各省开办育婴堂等事奏折》,时间不详,编选者仅指为“雍正朝”。关于戚麟祥的信息,仅知其为浙江德清人,康熙己丑(170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值南书房,精通数学,“世宗嗣位,尤重之”,后以事谪戍宁古塔。(3)光绪《吉林通志》卷一一五《人物志四十四》。但同书称戚麟祥为乙丑(1685)进士,考之《词林典故》《浙江通志》等,此说有误,应为康熙己丑进士。从奏折内容判断,此奏应是在雍正元年八月至二年四月期间所呈,为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的依据,其中有谓:“窃臣至愚极陋,滥厕词林,仰见皇上聪明天纵,旁烛无疆,又兼言路广开,刍荛毕献,凡民风吏治无不纲举目张,岂复有一得之愚补助万一。但臣本迂腐,近于妇人之仁,谨列三条,仰尘圣览。京师有普济堂、育婴堂二处,首善之地,王化所基,既有善信奉行,复有贵官施舍,一年存活大约以数千百计。外省州县未尝无其名目,亦尝建有屋宇,使为民父母者开诚劝谕,设法救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有不可行之理。伏乞敕谕各省大吏,奖励各属,或捐己俸,或劝输助,或罚赎小罪,各照京师式样,遴民之殷实良善者,使主其事。所谓文王施仁,必先四者,实恺悌之一端也。至于三年奏绩,亦请以此事编入考成,定州县贤否,果有实心爱民者,量加升擢,则四海之大,所全必众,而天恩浩荡,遍于茕独矣……”(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设立与管理育婴堂档案》(上)“翰林院侍讲学士戚麟祥为请敕各省开办育婴堂等事奏折”,《历史档案》2015年第2期。奏折所言,恰与雍正二年闰四月上谕的内容一脉相承,应是雍正“上谕”的源起。试想,如果此奏是在雍正二年闰四月上谕发布以后所呈,岂非多此一举、自讨罪责?
但是,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十日上谕发布以后,我们没有看到如同社仓建设一样的反应。在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鄂尔奇呈上推行社仓的奏折后不久,雍正即密谕各省督抚渐次推行,而各省督抚等在随后的三四年中纷纷上报社仓建设情况,雍正帝在他们的奏折中也不嫌其烦地予以鼓励和指导。然而,对于建设慈善机构的情况,数年之内各地方督抚等官员的奏折中却甚少提及。接任仅一个多月的湖北巡抚法敏可能是响应最为积极的官员,他于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的奏折中表示欲于汉口设立普济堂,“商之司道,各官皆乐于为善,劝谕商民,亦皆踊跃从事”,“现在举行,俟稍有就绪,另行奏闻”。但雍正的反应似乎并不积极。据夫马进所查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宫中档雍正朝硃批奏折》有雍正硃批“方到任,何必做此沽名吊誉之举。既举也罢了”一语,并说:“此固极善之政,亦只可帮助,令好善者成,百姓自为之。若官做,则不胜其烦。恐招集远来无依之人,倘力不能,有害无益。”(5)[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2—423页。但笔者查阅的《清世宗宪皇帝雍正·硃批谕旨》第十六册第31页所录雍正硃批,未见“方到任,何必做此沽名吊誉之举。既举也罢了”一句,批语也与夫马进所录不同:“此举固属善政,但只可劝导众善良民自为之,汝等协助则可。若做成官事,既不胜烦,且恐招集远来无依之人过多,至力不足时,反令贫民失所矣。”两种说法措辞不同、语气有别,但大致意思相近。尤其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初八日两江总督赵弘恩奏称准备动用盐规银建设育婴、普济善堂时,雍正认为“好,应为者”,但又说此不过是“道婆之政,非急务也”。学术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夫马进认为,“在雍正帝看来,类似于普济堂建设这等事,只不过是‘道婆’那样最下等的而且是女人们应该做的事,而绝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或者是对国家承担着重大责任的政治家们应该干的事”,“不是国家必须大力推进的重要课题”;(6)[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423页。梁其姿也认为,“在雍正心目中,这些慈善组织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只是表达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妇人之仁’”,“就算积极如雍正,也不过是象征性地推动地方善举,以宣示朝廷德政,而心底从来没有把此事看作重要的政策来推行”。(7)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98页。换言之,两位学者均认为雍正其实对于民间慈善事业的推行并不重视。
对此,王大学不以为然,认为“传统观点需修正”。他从河南、山东两省善堂建设数量遥遥领先的角度,认为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认识雍正朝慈善组织建设过程尤为重要,雍正对普济堂和育婴堂建设的态度是依靠民间力量,不希望官方过多介入。在两江总督奏折上批示善堂是道婆之政而非急务,是因当时江苏的重点是清理亏空。(8)王大学:《雍正朝慈善组织的时空特征及运作实况初探》,《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就江苏而论,王大学的观点固然值得重视,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说明雍正为何对湖北巡抚法敏回复设立普济堂不过是“沽名吊誉之举”的态度。
雍正对待慈善事业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欲正确理解雍正皇帝在慈善组织建设问题上看似消极乃至矛盾的表态,应首先弄清以下三个问题,即雍正对于民间慈善的态度如何?雍正推动善堂建设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雍正二年闰四月上谕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雍正对于民间慈善的态度如何?从史料记载可知,雍正对于民间慈善活动一向较为重视,多方鼓励。康熙时期,政府包办救荒济穷事务,少有动员民间力量进行慈善救济的举动。到了雍正年间,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动员好义富民协助政府救济越来越受重视,如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针对京城饥民丛聚、冻饿不堪的情况,雍正帝在要求五城御史加强巡视、留心照看的同时,指出“若有好义之人,容其栖息者,不必禁阻”,(9)《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清实录》第七册,第576页。鼓励民间好善之人参与到救助饥民的工作中来。雍正七年(1729)三月,他还专门诏谕内阁,号召民间人士积极从事慈善救助事业,谕旨中说:“直省各处富户,其为士民而殷实者,或由于祖父之积累,或由于己身之经营,操持俭约,然后能致此饶裕,此乃国家之良民也。其为乡绅而有余者,非由于先世之留遗,即由于己身之俸禄制节谨度,始能成其家计,此乃国家之良吏也。是以绅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实者,实为国家之所爱养保护,则本身安可不思孳孳为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奢侈糜费,固非所以善守,而悭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有曰孝友、睦姻、任恤。可知公财行惠、任恤之义,与孝友而并重也。盖凡穷乏之人,既游闲破耗,自困其生,又不知己过,转怀忌于温饱之家。若富户复以悭吝刻薄为心,朘削侵牟,与小民争利,在年谷顺成之时,固可相安,一遇歉荒,贫民肆行抢夺,先众人而受其害者,皆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后,官法究拟,必将抢夺之贫民,置之重典,是富户以敛财而倾其家,贫民以贪利而丧其命,岂非两失之道,大可悯恻者乎?朕为此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如此,则居常能缓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亲睦之心必笃,岂非富户保家之善道乎!从来家国一理,若富户能自保其身家,贫民知共卫夫富户,一乡如此,则一乡永靖,一邑如此,则一邑长宁,是富户之自保其家,犹富户之宣力于国也。况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种福果于天地之间,子孙必常享丰厚,岂不美欤!著各省督抚,将朕此旨,通行该属之乡绅士民人等共知之。”(10)《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九,雍正七年三月,《清实录》第八册,第32—33页。雍正提倡《周礼》孝友、睦姻、任恤之道,要求地方邻里之间缓急相助、有无相恤,告诫富裕之家,当懂得守望相助之道理,“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济贫即是保富,家保则国宁。
同时,雍正多次下旨,对于民间好善之举进行表彰与奖励。如《清世宗实录》载雍正九年(1731)七月乙酉谕内阁:“如各省乐善之家,有能存恤周济者,该地方官酌量轻重,赏给花红旗匾,最优者,详请题达,给以顶带,以示鼓励。”十一年(1733)五月己丑谕内阁:“朕于直省地方偶遇灾祲,即为之寝食不宁,蠲租发粟,截漕平粜,多方抚恤,务使贫民无一不得其所。又念各该地方,虽或收成歉薄,岂无盖藏丰裕之家?伊等谊笃桑梓,休戚相关,若各人量力乐输,既可以展其睦姻任恤之情,亦可以为恤灾扶困之助。是以曾经降上谕,通行劝导。然亦听绅衿士庶自为之,不相强也。近闻直省地方,捐资周急,好善乐施,颇不乏人。此诚乡邻风俗之美,亦人心古处之一验也。此等良善之人,应加恩泽,以示褒嘉。著各该督抚留心体察,秉公确访。其捐助多者,著具题议叙,少者,亦著地方大吏给与匾额,并登记档册,免其差徭,以昭朕与人同善之至意。”在民间慈善方面,应“听绅衿士庶自为之”,不可强迫。对于好施之人或乐善之家,官府不仅赏给花红旗匾、给以顶戴,还可以具题议叙、免其差徭。由此可见,雍正大力倡导民间发扬古来传统,邻里互助,积极鼓励民间力量从事力所能及的慈善救济工作。
第二个问题,雍正推动善堂建设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在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的上谕中,雍正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求地方官“宣示朕怀”,即宣传雍正对京师普济堂、育婴堂赐匾赐金的举措以及由此反映的鼓励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从而“使之益加鼓励”;二是“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即通过各级官府的倡导,调动民间好善之人的积极性,在各地推广发展慈善救助事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举办民间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官府只起倡导的作用,而一切事务均由民间社会自行办理,此即雍正三年九月六日硃批法敏奏折中所说,“此举固属善政,但只可劝导众善良民自为之,汝等协助则可”,以及雍正七年六月四日硃批山西巡抚宋筠奏折中所强调的“(举办育婴堂、普济堂)此二者须劝导乐为,不必强之”的原因。如果结合同时期开展的社仓建设情况来看,这一点当更为清楚。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鄂尔奇上呈推行社仓的奏折后不久,雍正即密谕各省督抚渐次推行。在此过程中,雍正多次指示,社仓应令民间自为,官府除了善为劝谕、倡导外,不宜干预具体事务。他在给各省督抚的密谕中说:“社仓一事,甚属美政,但可行之于私,不可行之于公。”(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页。此后又不断加以强调,如雍正二年四月十三日在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折的硃批中说:“社仓一事,朕谆谆告尔听民自为,严束属员,不可逼迫。近日闻得百姓因此事甚怨畏,尔虽欲速成邀前番之奖,奈今日水落石出何?前已有谕发来,尔可协同两抚严查不肖逢迎欺隐属员,再速安百姓之疑,皆令知原为百姓,并非为仓谷。即丰年出旧入新之勤公行一两年,百姓知其力而乐为方好。”(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设立社仓史料》(上)“湖广总督杨宗仁为报湖广地方秋后全部建成社仓等事奏折”,《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再如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丑,“谕直隶各省总督巡抚等:社仓之设,原以备荒歉不时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烦扰,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为奉行之道,宜缓不宜急,宜劝谕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13)《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九,雍正二年闰四月,《清实录》第七册,第308—309页。并且明确要求“一切条约,有司毋得干预。至行有成效,积谷渐多,该督抚亦止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使社仓顿成官仓,贻后日官民之累”。(14)《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八,雍正二年四月,《清实录》第七册,第304页。在雍正看来,康熙时期几次试行社仓均无成效,其因主要在于“官办”,官办导致善政“行之不善,致滋烦扰,官民俱受其累”。所以,社仓、善堂建设应充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在慈善事业应由民间去办这个问题上,雍正的态度是十分明确并且贯穿始终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雍正二年闰四月上谕的意义?梁其姿认为“1724年(即雍正二年)诏令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1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98页。事实真是如此吗?夫马进曾对沿海六省的善会善堂情况作过初步统计,结果表明,各省的情况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尽管存在经费差异等问题,但从各省善会善堂的数量变动以及设置时间的曲线图来看,雍正年间均处于上升发展期,尤其山东、河南、广东的情况更为明显。(16)[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661—701页。王大学的研究表明,“雍正朝之前江苏和浙江清代慈善组织最多,雍正朝结束后数量最多的是山东、河南,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山东、河南、山西和福建。福建、山西善堂绝大多数建于雍正二年,官方强力推动”。(17)王大学:《雍正朝慈善组织的时空特征及运作实况初探》,《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从梁其姿本人根据方志资料对清代育婴堂所作的统计数据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全国育婴堂总数为422个,其中顺治朝3个,康熙朝93个,雍正朝160个,乾隆朝166个。(18)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259—270页。由此可知,雍正二年闰四月劝谕各地兴办育婴堂、普济堂的上谕,对于清代民间慈善组织的涌现与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所谓“1724年诏令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的说法难以成立。
如何理解雍正所说慈善乃“道婆之政”?
雍正对于发展民间慈善事业抱持积极的态度,并且通过上谕的形式予以推动,取得明显的成效。那么他为何在硃批谕旨中又说创建育婴堂、普济堂不过是“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呢?这一点恐怕还需要从总督、巡抚的工作职责方面去理解。
作为封疆大吏,清朝的总督、巡抚负有守土之责,全面管理地方事务,所谓“身任封疆,事无巨细,皆尔之责”。(19)《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二○,“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镇海将军署理江苏巡抚何天培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253页。但各种事务又有轻重主次之分,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对此应能充分把握。雍正曾对苏州巡抚陈时夏有过这样的批评:“汝自莅仕以来,盗不能缉,吏不能察,承追二百五十万钱粮不能完二十分之一,苏郡城内大开铜铺而不能禁止,筑堤濬河工程迟误而不能劝惩,于刑名案件则一味姑息,其余不职处不可枚举。惟能令戏班减少大半,缎铺关闭数十座,僧道数千百人还俗,祠庙数处改为书院。在汝意以王道变化风俗,但不知实有益于民生处何在?”(20)《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一下,“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苏州巡抚陈时夏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669页。作为巡抚大员,陈时夏回避缉盗察吏、追征钱粮(江苏拖欠钱粮的情况最为严重)、禁止铸铜、兴修水利等主要职责,而热衷于禁戏班、关缎铺、令僧道还俗、改祠庙为书院等易见成效但对民生未见得有多少实际益处的末务,从而让雍正颇感不满。现实情况是,陈时夏的作为并非个例。当时的督抚大僚们大多庸碌无为,缺少进取心和责任心,往往将主要精力放在简单易行而又能捞取名声的小事琐事上,而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难事则避而不理。雍正六年(1728)正月二十九日在硃批陈时夏奏折时对此现象再次提出批评,并要求督抚大僚深谋远虑,能“于远大留心”,多行大事要事难事:“览所奏,何琐屑猥鄙至于如此!果肯秉公正色如鄂尔泰、田文镜,于地方上兴大利、除大弊,令百姓沾永远之惠,国家享悠久之福,其功与能岂此二三万金所能酬答耶!假若庸碌无能,沽名钓誉,甚至误国殃民,即取用此数千金亦属过分。朕前面谕汝者甚明。今此奏令朕如何批谕耶?据云一一亲手登记,纤悉无遗。诚如此,何暇办理政务?况江苏事繁,一日之光阴无几,一人之精力有限,专于细小者,必致遗误大者要者。多有人论汝见小不识大体,今览此奏,果不缪矣。譬如逸盗不捕而严约奢靡,铜赌不禁而驱逐娼优,类斯者不可枚举。舍本而趋末,避难而谋易,无非沽名而已。人心不服,虽令不从也。诚能将大者、难者,力图数事,俾令行禁止,人咸感畏,其余些小易办之事,只须出一告条,若不各各遵奉,朕知必无是理也。……身为大臣,但当于远大留心,几许银两多寡增减,有何关系?”(21)《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一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苏州巡抚陈时夏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659页。解读雍正上谕及硃批谕旨可知,雍正最为重视的督抚大僚职责乃攸关国计民生之事,所谓“总理军务、粮储、刑名、钱谷、营伍、汛防等事”,(22)《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三六,雍正十一年十月,《清实录》第八册,第745页。具体而言,包括地方蓄积、稳定粮价、缉匪靖盗、察吏安民、劝导百姓力田务本、完纳钱粮、兴修水利等。如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四日广东巡抚杨文乾奏折硃批,“相机调剂,系尔等封疆大吏之专责……地方蓄积为第一要务,刻不可忽”;(23)《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九上,“雍正四年四月十四日广东巡抚杨文乾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464页。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江西巡抚布兰泰奏折硃批,“督抚为封疆大吏,全在察吏安民、抚辑地方”;(24)《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二下,“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江西巡抚布兰泰奏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717页。雍正十三年(1735)闰四月初十日江南总督赵弘恩奏折硃批,“安民之道,惟以缉匪靖盗、察吏训兵为根本要务,余皆枝叶边事也”。(25)《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二一六之五,“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十日江南总督赵弘恩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5册,第596页。不同地方、不同阶段的要务可能有所不同,工作重点需视情况而定,有时候防匪也只能算是第二等重要之事,如硃批镇海将军署理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折中说:“果地方上文武官弁,根本不失……朕意惟以察吏治、整营务为先,百凡务本为要,防匪犹属第二义也。”(26)《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三,“雍正五年四月初四日镇海将军署理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7册,第59页。至于关税一类更属小事,硃批陈时夏奏折中说:“关税原系责成巡抚办理之事,无论如何题请皆可,但身任封疆,统率群僚,不能信托一人、威服一人,甚至税务小事,皆欲亲身料理……国计民生大事如何办集?”(27)《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一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苏州巡抚陈时夏奏折硃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666页。在雍正眼里,防匪、税务都难称地方紧要之务,则办理善举自是属于“舍本而趋末,避难而谋易”的“沽名”之举了。由此可以理解,雍正硃批对于法敏、赵弘恩等人办理善堂的态度先是肯定,“好,应为者”,“此固极善之政”,但同时又说此乃“沽名吊誉之举”,不过是“道婆之政”罢了的本意。
显而易见,雍正与康熙对待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存在重大区别。雍正上台不久,即一改此前放任的情况,于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彰鼓励民间扶老救孤济困的好义行为,并要求地方督抚推广设立普济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取得明显成效。学术界因雍正在回复地方督抚的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而认为雍正并不重视慈善事业,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雍正的态度既积极又明确,而在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有其客观原因。雍正的这一“上谕”可以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