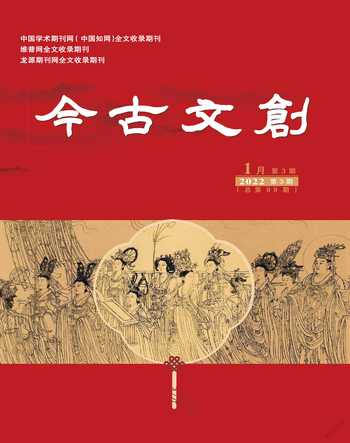《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观表现研究
【摘要】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系统阐释了文化属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人格等问题,一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介绍了豆豆及其创作的《遥远的救世主》,其次分析了《遥远的救世主》的精神理念,最后论述了《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观,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遥远的救世主》;精神理念;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3-0007-03
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由豆豆所著,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在该本小说的封面上,作家出版社如此评价道:这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佳作。作者以类比的手段阐释了中国文化对“尘世”的热情远超“天堂”,并对文化属性进行了深入探究,以期阐明中国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强烈追求与西方文化对宗教理念的情愫有着相斥相容的关系,由此也彰显了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的鲜明风格。
小说的主人公丁元英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商界规律,这使得一群企图谄媚高人以获得成功的音响发烧友将他奉为“神”;另一个主人公芮小丹,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特别的她,在与丁元英陷入爱情后想要的礼物也十分特别,这份“礼物”是丁元英对贫困村王庙村展开的“扶贫”帮助,更是一种觉悟,一种对文化观的深思[1]。
《遥远的救世主》的主要情节即是围绕芮小丹向丁元英讨要礼物展开的,并通过形形色色人物思想的相互碰撞、融合,最终聚焦于“文化”上。小说对中国文化、宗教文化、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将对其文化观表现进行思考研究。
一、豆豆与《遥远的救世主》
豆豆,原名李雪,著名女作家,同时也是油田年轻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死比活着容易》于1993年发表在天津《小说家》杂志上,同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后转入中国石油作家协会。
作者同时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早年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好朋友李红英,而李红英不论是其思想品德,还是其人生观、价值观都对作者产生了极大影响。1990年,李红英定居欧洲,在那以后李红英陆陆续续向豆豆寄送了很多参考资料,以向豆豆分享令她陌生的国外生活。
豆豆于1995年展开对长篇小说《背叛》的创作,并于1997年完稿,2000年《啄木鸟》杂志对《背叛》进行了四期连载,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翻拍成电视连续剧,至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豆豆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同时被翻拍成电视连续剧《天道》,广受好评。
在《遥远的救世主》中,作者凭借她的创作才能,带领读者对一个有机的、无形的、未知的世界进行了一探究竟。豆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作家的品质,《遥远的救世主》主题睿智、简约,一气呵成地传达了佛学的光耀、不蓄意,引人深思。男女主人公独特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之间令人万千感慨的爱情故事,最终造就了一种超然背叛的意志。
二、《遥远的救世主》的精神理念
和其他财经小说相比,《遥远的救世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鲜明的精神理念。首先,《遥远的救世主》的无相观。《遥远的救世主》主人公丁元英智高在无相,“以佛的无相观照人世的有相,故是实相,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丁元英的影响下,芮小月、肖亚文也表现出一定的预见能力。
为实现小说的无相观,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衬托手法。小说中,女主人公芮小丹美丽善良聪明、思想独立,作者在描写她不凡的才貌时,在运用常规手法进行刻画的基础上,主要是依托有强烈雄性文化而认定女人难养的丁元英,由排斥到接受,然后到尊重,最终到尊敬的巨大反差进行衬托的[2]。相同的,丁元英的“神”也离不开芮小丹、肖亚文、韩楚风等人物的衬托,以及刘冰、林雨峰等人物的反衬。除去在人物刻画方面,故事情节、场景叙述上,也运用了大量的衬托手法。比如,各式各样的音响效果相互衬托,有格律诗公司与乐圣公司的实力相互反衬,等等。
其次,《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属性决定论。《金刚经》中提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人处在有界之中,便要遵循有界的规律,这一规律即为文化属性决定论,对强势的文化十分推崇。林雨峰在叶晓明之上,叶晓明又在王庙村的那些村民之上,他们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形式。而丁元英则更是超过有界范畴,这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财经小说中人物所秉持的商战理念。在《遥远的救世主》中,文化属性决定论实现了与全面情节的有效融合,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语言艺术化处理这一叙事技巧的运用。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大众对文学作品的语言认识不断加深,并产生各不相同的感悟,有的读者向往回歸人性,有的读者则获得哲学思辨的启迪。《遥远的救世主》叙事有条不紊,有张有弛,文字朴实无华,基本没有过多的赘述,并展现出入木三分的思考,以及自然的行文风格,给人以和谐融洽的感觉。同时,小说中每个人物所设置的语言都与其人物性格相符,不会显然突兀。也正是因为小说语言运用得恰到好处,让经该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道》对小说中的语言进行了完全沿用,即便是小说中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语言电视剧也以人物独白的方式进行了展现,似乎脱离了小说中的语言将使得小说原本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难以得到充分表达。
再次,《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自觉观念。在文化属性的影响下,人物得以实现自明。《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并不是替人冒险的“神”,他心怀普世仁爱,但并不掌控他人的命运,而是在他人陷入迷茫时,给予一番指点,而命运改变与否最终是掌握在人们自己手中。小说中关于“杀富济贫”终究能收获成果,一方面是因为丁元英提出了一个好的策划思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人们为追求命运扭转,为创造美好生活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小说中的冯世杰、叶晓明、刘冰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丁元英身上,但因为他们品性、心性、眼光的不同,最终迎来了不同的人生结果。反派人物林雨峰虽然也十分聪明,但同样弄不清楚该种唯物史观,他始终未能清楚认识到,自己为何会输给一群村民,并且到生命最后也未能认清“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的道理。这一思想理念既是小说中每个人最终归属的逻辑使然,同时还对读者的心灵带来极大震撼。
三、《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观
(一)救世主文化
“救世主”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感谢上苍”“皇天在上”等便是一种对“救世主”的期盼;西方基督教则宣扬上帝创世说,是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虽然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中的救世主文化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它们无不是根植于人类思想中的一个共同要素——期待救主,也就是当人们每每遭遇险境时,总是期盼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抑或超出人类本身的外部力量以让自身脱离险境。这一文化的本源是过去人类对大自然、对鬼神等的崇拜,但这同时也是受人类早期社会生产力不足、思想观念落后等因素影响,人类对大自然强大力量所形成的一种敬畏之心,并表现出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3]。
而千百年来,绝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并且在各类典籍中,都难以找到有关于“救世主”救世的记录。在《遥远的救世主》中,在几个音响发烧友听到丁元英关于组建音响公司,帮助王庙村致富的计划后,叶晓明信誓旦旦地说道:“丁哥一来,我们哥儿几个的前途就有救了。”丁元英不以为然,说道:“有了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救了。”在丁元英看来,救世主根本就不存在,倘若要讨论救世主这一话题,则反映客观规律的文化即为救世主。对应到小说中的形势,救世主就是看清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人必先自救,而后救人。丁元英也清楚地自知自己救不了贫困的农户,自己所能为王庙村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认清市场经济的生存之道,并且只能是他们自己救自己。小说的最后也是果不其然,完全将丁元英奉为救世主的几个人物都没有落得好的结局,而王庙村贫困农户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最终在脱贫致富道路上获得了成功。
《遥远的救世主》也试图通过此让读者知道,世上并没有救世主,人只有靠自己,或者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救世主”。
(二)强势文化
《遥远的救世主》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进行了系统解读。首先,对于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是弱势文化,在小说中,丁元英如此界定:强势文化即为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文化,弱势即为依赖强者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
《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便属于一种强势文化的体现,在欧洲学习干工作期间,丁元英受到了西方文化中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等的极大影响,相较于中国文化中所崇尚的人情世故,他更注重讲规则、讲事实。
作品中,无论是丁元英所从事的金融活动,还是他组织的王庙村扶贫计划,无不秉持的是客观事实,讲求基于对市场规律、法律法规等的掌握运用,进一步开展相应的计划行动,而遵循客观规律,凡是讲求实事求是,也是丁元英收获成功的重要原因[4]。
而如前文所述,将丁元英奉为“神”的冯世杰、叶晓明等人,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体现,他们秉持趋炎附势、破格获取的思想,不付诸行动,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他们的悲惨结局,无不是该种弱势文化属性的最终宿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升至国家、民族层面亦是如此,小说中丁元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抨击,他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5]
简言之,丁元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有一定的弱势文化属性,以此影响了中华民族对强势文化的承载、积淀。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已基本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并且同时随着进入近代由先辈们所掀起的一次次文化反省、革新运动以来,中国人不断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摒弃,并在其中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显著增强。
结合《季羡林先生纵谈东西方文化》而言,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在他看来西方文化表现为“战胜自然”“一分为二”等内容,这同时是二十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体现。而伴随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随之而来的是生态污染、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合二为一”等文化观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广泛推崇。由此表明,中西方文化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属性,与此同时,无论是哪种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唯有秉持客观规律方可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方可成为真正的强势文化[6]。
(三)中西文化碰撞
在作者及读者看来,《遥远的救世主》是一部高层次作品,尽管受众面不广,但小说探讨的问题及设想解决问题的对策,对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上,《遥远的救世主》中也进行了多个问题的探讨。
首先,在中西方爱情观碰撞方面,丁元英作为一个极品混混,他同时是一个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实继承者、无私叛逆者,对经济、文化、人性有着深入理解;芮小丹作为一名正义的警察,她同时是一个生长于莱茵河畔的独立思考者,敢爱敢恨。两者有着相似的不被德国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经历,但他们的爱情观截然不同。
丁元英在遇见芮小丹之前,他几乎已经放弃了爱情,他尊重女人的同时,也十分懂女人,并希望能于女人保持距离。而芮小丹的出现,让丁元英不得不用自己的灵魂去感悟她的圣洁[7]。芮小丹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爱情主义者,在这个奇女子面前,悟道者丁元英迷失了自我,两个独立的个体在爱情中到了相互无法割舍的地步。
其次,在中西方道德观的碰撞方面,小说中在丁元英父亲重病时,由于丁元英较为偏激的思想表达,而引发的兄弟反目与母亲不解,这其中反映的“养儿防老,正确与否”的问题,不仅引起了读者的争辩、反思,还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中国文化崇尚以家国为本位的道德取向,而西方文化则推崇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取向。丁元英所崇尚的道德观与他人存在一定差异性,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他提出,不愿将父亲的痛苦、尊严作为自己孝顺的体验,并认为倘若父亲过了病危阶段变为植物人,应当拔了父亲的氧气管,以了结父亲的痛苦,丁元英的这种思想行为,对于生长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下的人们而言,显然显得十分极端,但也存在其中的道路,倘若置父母的痛苦不顾,去刻板地履行孝道,实则是徒有虚名。“养儿防老”观念正确与否,中国传统观念是父母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就应当为父母养老送终,并赋予爱的美名。无论实际情况是什么,中国传统观念中始终流露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心态,若是不然便反目成仇,这也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导致的,属于是一种劣根。中西方文化存在极大的差异性,除去体现于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另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来也需要相近的价值观支撑[8]。
四、结束语
通过《遥远的救世主》可以了解到,世上根本没有救世主,人们要想得到命运的眷顾,唯有依靠自己。中西方文化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唯有建立起相互间的和谐共处关系,方可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獻:
[1]任文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遥远的救世主》解读[J].语言文学研究(下旬刊),2011,03(27):12,14.
[2]裴安齐.初探“心本源”——论《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属性[J].社科纵横,2013,12(28):279-280.
[3]池永文.宗教情怀与世俗理想交织中的英雄叙事——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的文化解读[J].小说评论,2011,02(06):120-122.
[4]涂露柔.浅谈《遥远的救世主》文化观的呈现[J].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6,12(07):14-15.
[5]张晓茹.《遥远的救世主》中会话的含义——从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角度分析[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 27(06):62-65.
[6]胡星.心路何由到“天国”——《遥远的救世主》文化观的呈现[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6
(01):13-17.
[7]张艾晨.天国之恋的倾情演绎——解读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的爱情绝唱[J].名作欣赏,2017,584(24):
135-136.
[8]陈静.从电视剧《天道》中追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源头[J].青年文学家,2017,10(30):190-191.
作者简介:
张岩,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