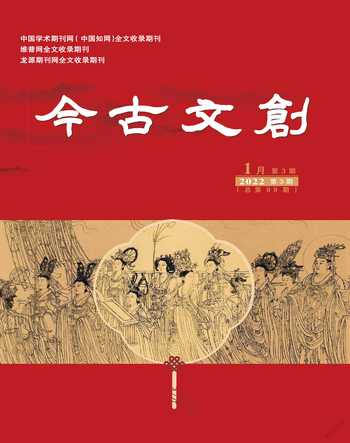浅析《文心雕龙》中“神思”的概念与方法论
黄静
【摘要】《文心雕龙·神思》篇列《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重点论述了创作思维中的想象问题,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其中“物我合一”“苦思”说等理论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本文从“神思”概念的界定入手,结合当时“魏晋文学自由说”背景,分析其具体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内涵与外延;魏晋文学自由说;物我合一;“迅思”“覃思”;虚静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3-0010-03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多无体系,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体系完整的著作实属不多见。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它通过研究先秦至齐梁各体文章的写作并总结为理论体系,系统论述了文章的本质起源、文体和创作、发展与流變等诸多方面,论述之全面、影响之巨大,如鲁迅所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如今学者看待《文心雕龙》,大部分把它归为文学理论著作一类,不过严格划分来说它的论述的范围较文学甚广,内容涵盖了文学在内的诸多类型文章,既有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章表奏启等公文及应用文。
一、“神思”一词概念的界定
在确定一项事物的概念时,通常需要弄清楚它的“内涵”与“外延”。《神思》篇列《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它讨论的是写作启动阶段的构思和想象的问题,在全书中占比较突出的地位。对于篇名“神思”该如何理解,历来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一种相对普遍的解释为“神思”就是精神和思维,也有学者把它确定为神奇的思想,还有的说法认为“神思”既不等同于想象或灵感,也不等同于艺术构思、形象思维等,应是灵感来临或获得灵感时的文思。①由此看来,对内涵的界定取决于它是并列结构还是偏正结构。而再精确一点,对“神”的意义界定是几种说法的差别之处所在:是“精神”还是“神奇”抑或是当“神”来时呢?为了精准的要求,对它的辨析就尤为重要了。
(一)内涵界定
开篇“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开门见山地指出“神思”的“思”一字在本文的界定即文思,此句的前一句“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是直接引用于《庄子·让王》的句子。他对“神思”的特征做了初步的描述,称这种思维的特征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还应注意“文之思也”这个描述,这是对“神思”概念的补充,意思是这里所谓的“神思”,其实就是写作的思维。写作是写作活动中的“精神思维”,是写作的动力,相当于兴趣,或者说是当前语言的灵感和想象。
“神”经过全篇的梳理可以被理解为灵感或想象,并列结构初现端倪;而后面的“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是受《庄子》“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的启发,好像更印证了这种看法:构思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人的主观想象能与客观物象交接融合;行文最后,“神用象通……物以貌求”,“神”与“物”是对照的两种事物,与“神”作为名词这一属性遥相呼应。由此而论,“神思”一词的解释似乎偏向于并列结构。然而从第一段看来,“神”是包含于“思”的,两者并不是平等的并列关系。
再来看看第二处运用:“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与第一段相比,本段对“神思”的含义和操作特点进行了更详细、更生动的解释和描述。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对“神思”这个词的使用非常正式,而且作者的解释也相当清楚,说明他所谓的“神思”是有特定含义的。根据之前的描述,可以知道,他所谓的“神思”,尤其是写文章的思维,是一种高度兴奋和活跃的非理性思维状态,无法自主地控制。
因此对于贺天忠先生“灵感来临或获得灵感时的文思”这一内涵界定,笔者深以为然。
(二)外延范围界定
内涵得到确定后,再来界定它的外延。再说到文思的重要性时有一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这句对“神思”的外延有清晰的界定。创作伊始文思充沛,可写成却发现大打折扣。刘勰认为,“思”“意”“言”三者顺序关系中文思处于首要位置。创作三个阶段中,第一步是文思要活跃,其后是根据文思来确定立意的成型,接下来才是文本的表达输出。在这个阶段中的“思”处于发动机的地位,如没有“文思”则没有接下来一系列创作活动。而这个“思”通达全篇理解为忽然而至的文思,后面由“意”到“言”中所产生的一般意义的思考活动则不在此范围之内。
二、《文心雕龙·神思》对文学创作的方法论意义
确定“神思”一词的概念之后,接下来具体分析其在文中的描述呈现。
后人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提出的重要理论之一就是“魏晋文学自由说”。早在上古虞舜时期,作为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中国就产生了“诗言志”的诗学主张。此时的“志”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伦理观念等多方面元素,本质是将这些元素化为内在情志,通过诗歌外化表达出来;在随后先秦两汉时代,这种思想被伦理纲常观念深深影响。文体创作风格逐渐偏向政治伦理的教化作用和群体性、功能性的强化作用;而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式微,道教玄学兴起,魏晋南北朝的文风又逐渐回归到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和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评价:“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②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如此背景下,刘勰提出“为情而造文”的观点,这无疑对文学创作思维带来一种清晰的提升和凝练。
前文提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一部出色的文学评论,同样对文学创作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一)“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
首先,来理解刘勰所言“物”的范围。可从《物色》篇窥见全貌。在《物色》篇,刘勰对自然之“物”做了详细的描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其中,“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清晰地概括本段内容:情感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语言通过感情来抒发。在刘勰眼中,山川风物、春华秋实皆能引起情感的迸发和共鸣,自然之“物”被具体化、生命化。
除自然景物作为感情寄托之“物”外,刘勰把社会生活的物感作用也引入其中。在《辨骚》中描写屈原的部分:“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山水”“节侯”同样说的是自然景物对情感抒发的作用,而“情怨”“离居”则专指社会生活的影响。综上所述,“物”可以包含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环境两方面要素。
开篇“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运思状态,开宗明义地描述思想感情与外界事物并驾齐驱。此时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割裂的状态;随后则进行更加形象和详细地描述:“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其中“规矩虚位,刻镂無形”意为将无形的、不可捕捉的思想和灵感化为可捕捉的、可规划的实体,进行意象的加工和成型,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一种情感寄托于自然万物的状态,其中“满”“溢”表现了寄托的深入性和充分性。通过将无形化为有形、寓情于景,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与风云并驱”的境界。
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对境界有这样的形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③而此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不失为一种“高格”。在后人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运用也是比比皆是。如李白著名的《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与“山”是平等的交流对象,我既是山,山即为我,浑然一体,符合王国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界;而杜甫在《春望》借景物表达强烈的悲痛愤慨之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此时花鸟仿佛知我心事、与我同悲,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不谋而合。无论是哪种物我合一,“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③。
(二)“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的后天积累习得
在《神思》中,刘勰明确指出积累、研究和训练对于成文的作用:“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这四步分别为通过积累学问来储备知识,通过斟酌文理来丰富才能,通过周密地观察体会来彻底观照、深入探索,通过不断练习和推敲来使文章华美。这样才能做到庖丁解牛,胸有成竹。这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提出的后天要求;而在随后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中,刘勰强调对于文思的“顺其自然”:需要涵养心神,训练方法,勤加积累与练习,不要强思苦索;注意写作的文采,掌握好写作的规则。其中“术”即为前文提到的后天方法。文思汹涌而来时,从容应对;而文思阻塞时,不必苦虑勉强。
(三)“迅思”“覃思”的先天禀赋差异
正如人们熟知的那句“天才那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后半句经常被忽略“然而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往往是最重要的”。除了强调可靠后天积累和训练得到的方法之外,刘勰认为先天禀赋也是文思创作的重要决定因素。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他发现人的文思有迟缓和敏捷之分,把作者划分成“骏发之士”与“覃思之人”两种,并举例来印证:司马相如口吮着笔,直到笔毛腐烂文章才写成;扬雄写完文章后,因用心过度而憩睡,却被噩梦惊醒;桓谭由于苦苦思索而害病;王充因思虑过度而气力衰竭;张衡用十年工夫研磨撰成《两京赋》;左思撰写《三都赋》则用了十二年时间。这些著作有些虽说篇幅巨大、用时过长,根本还是因为作者先天才思迟缓;淮南王刘安在一个早上就写成《离骚赋》;枚皋接到诏令立即就能创作一篇赋;曹植铺开纸张创作,速度就像口诵文章一样;王粲拿起笔来创作,仿佛在默写昨晚就已经构思好的文章;阮瑀靠着马鞍,在马上就能写成一篇书信;祢衡草拟奏章在宴会上撰赋,均须臾而成。虽说都是短篇、用时少,根本原因还是作者先天才思敏捷。
关于刘勰对才学的定论,可追溯到《事类》篇:“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其中,才是指先天禀赋,学即为后天习得。才为主,学为辅。但俗话说“笨鸟先飞”,后天的积累可以作为先天禀赋不足的补充和弥补,他认为两者相辅相成,各有裨益。“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无论是文思敏捷还是迟缓,如果想要完成,都需要积累广博的学识和长时间的练习;所以在构思下笔时,先天或后天任何一方面的不足都可能出现“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思路阻塞的人,苦于内容贫乏,辞藻泛滥的人,苦于华丽杂乱而无内容;针对这两种情况,刘勰提出了解决方法:“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因此,广博的积累就是解决内容贫乏的粮食,中心一贯就是拯救文辞杂乱的药方。这样就有助于文章构思了。
由此可见,刘勰认为在文学创作构思方面,先天禀赋和后天积累是并驾齐驱、缺一不可的。
(四)“虚静说”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提到如何解决思路阻塞这个话题时,刘勰发出了“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感慨,也因此引出一种备受后人引用和热议的“虚静说”。“虚静”一词在我国古代的哲学等意识范畴中屡被提及,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美学的重要理论。作为哲学中的“虚静”,它不仅为道家所讨论,也为儒、法、佛所探讨。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管子·心术》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韩非子·扬权》说:“执一而静”“虚以静后”。它是先秦时期的普遍认识,涉及人格修养、思维方式、宇宙论和认识论。这些认识对后来文学美学中虚静论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更直接、关系更密切的,还应该是以老庄学说为主。而刘勰将它延伸到方法论的运用中,从众多思想理论基础上加以再创作,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虚静思想。
前文提到,文中若干处描述都脱胎于《庄子》,不难看出刘勰受庄子和道家理论影响颇深。刘勰在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分段总述后紧接着“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意思是在酝酿构思时应该抛弃杂念意为作文构思时需要摒除杂念,身心沉静、并且集中注意力。而达到如此程度的做法要点就是,清除意念中庸俗的东西,使神志、思路保持纯正。不难看出,后半句是前半句的具体做法和陈述。而后句正是向《庄子·知北游》致敬:“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
刘勰指出,作家思维的内容在时空上是无限广阔的,写作的思维活动与作家自身的情感以及外界事物的形象密切相关。这种说法在古代文学中比较常见,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切景语皆情语”。而在讨论怎样保持思路畅通这个话题时,他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志气”与“辞令”两个方面。“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从志气这一点切入,提到了解决文思堵塞的办法,就是“虚静”说。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曾提及,刘勰定义写作当为“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意思是应该在从容不迫、放松性情、舒适自由的状态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这跟他在“神思篇”中认为“骏发之士”有迅思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同篇也曾提出另一种创作的状态——“烦而即舍,勿使壅滞”,表明他也曾经经历过写作阻滞、烦躁的阶段,经历了创作的曲折和艰苦后,刘勰通过辩证的思考提出“清明虚静”的创作状态就尤为难得。他深刻而独特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贺天忠:《“神思”是灵感来临的文思——对〈文心雕龙〉“神思”的认识》,《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45页。
②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120页。
③王国维:《人间词话》,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第40页。
参考文献:
[1]贺天忠.“神思”是灵感来临的文思——对《文心雕龙》“神思”的认识[J].湖北大学学报,2004,(4).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3]刘美森.《文心雕龙·神思》的写作思维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