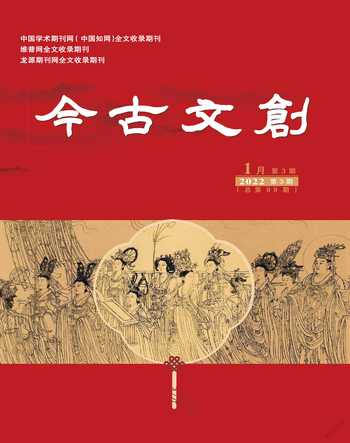《酒神的伴侣》中家庭的重要性
【摘要】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中,家庭以及其对城邦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家庭、村坊、城邦是三种不同的社群共同体。家庭是城邦形成的第一阶段,在个人德性的培养和城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文本着手,分析主要人物对家庭的态度及其与家庭的关联,探索家庭的重要性在剧中的体现。
【关键词】《酒神的伴侣》;家庭;德性;城邦
【中图分类号】I54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3-0020-03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 ①。社会性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包括他和父母、妻子、朋友等的关系,也包含他和同邦人的联系,因此个人的社会性可以在城邦的政治性生活中得到实现。但是,城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城邦内部包括家庭与村坊。家庭是第一阶段的社群共同体。当单个的家庭需求无法通过自己的独立活动来得到满足的时候,家庭开始聚集,村庄随之出现。由若干家庭联合而成的村庄最终再次通过联合构成了城邦。所以说,家庭可以说是城邦起源的基础和前提。
在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这一部剧中,几位主要人物,狄俄倪索斯、卡德摩斯、彭透斯、阿高厄,其实都是属于同一家族的亲人关系,他们是父女、母子、爷孙、表亲,但是他们对于所属的家庭和家庭关系的态度又各有不同,最后导致了每个人物不同的结局。家庭这一元素的重要性也因此在该剧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一、家庭空间与个人德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提到过家庭生活对个人德性的塑造。他认为,家务重在“人事”“人生的善德”以及“自由人们(家族)的品行”②。家庭空间所构成的社群生活可以促进善德的形成。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类,在他的德目表上,伦理德性包括“节制、勇毅、慷慨大方、大度、正义”等,理智德性包含“明智、智慧”等。③
在《酒神的伴侣》中,家庭对个体的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进行了空间划分。离家的狂女和彭透斯失去了德性,无家的狄俄倪索斯代表了德性的缺失,而离家后复而归家的阿高厄在剧末却似乎恢复了部分德性。
(一)离家与德性缺失
剧中最先离开家的是以阿高厄为代表的忒拜城邦内的狂女。“卡德墨俄家族的全体女后裔,所有女子,我都使她们疯狂,离家出走” ④“她们被狄俄倪索斯逼得发狂,抛下机杼和织梭”。本来应该是在忒拜城邦的家中劳作的妇女,离开了家庭这一空间,来到家庭之外,进入山林,成为酒神狂女。
她们表面看起来“秩序井然”,但是离开了家庭、脱离了城邦政治生活的狂女们实则是进入了一种前政治的自然状态。首先,她们不用劳作,可是这种不劳作的生活状态会导致其人性的败坏,最终会成为赫西俄德笔下从黄金种族到黑铁时代的堕落。其次,她们的行为表现出一种反人性的特点。“这些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抛下婴儿”,不管不顾自己滞留在城邦家中的孩子,离开家庭,“有的把幼鹿或野狼崽子抱在怀里,喂给它们白色的乳汁”。最后,她们的身上更是体现出了一种残暴的兽性。她们的暴力不加区分,把母牛扯成两半,把壮牛撕成碎片,把孩子从别人家中抢走。阿高厄最后手撕亲子彭透斯的剧情更是将狂女的暴力和失序推向了极致。因此,离开了家庭的女人们成了没有德性的酒神狂女,在家庭之外的空间中,她们过着一种没有节制的败坏的生活。
剧中最后一位离开家(或王宫)的人是彭透斯。作为忒拜的王,彭透斯在一开始始终坚持抵制狄俄倪索斯这位新神,但在欲望的诱使下,彭透斯的王者血气逐渐消失,他跟随狄俄倪索斯化作的异乡人离开了王宫,离开了家,前往狂女所在的山林。在《王制》中,柏拉图按照地位高低依次排列理性、血气和欲望。他认为,血气处于理性和欲望这两极之间,代表了人性的复杂和含混,“可在理智的劝谕下趋向更高的德性,也可能在欲望的诱惑下沦为欲望” ⑤。于彭透斯而言,当他位于家庭空间之内时,他是充满政治血气的,试图凭借武力来对抗酒神和酒神狂女:“事不宜迟!(向卫队长)速往厄勒克特莱城门;命所有持重盾的兵士和快马骑兵迎敌,以及所有挥着轻盾的兵士和手拨弓弦的射手”向狂女和酒神进军。但是,经爱欲催动,他的政治血气逐渐丧失,狄俄倪索斯的劝言使他一步一步走向家门(宫门),最后走出家庭(王宫)。
即使在他的身体还未完全踏出家庭空间(地理空间)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离开了家庭。譬如他在得知自己的母亲及其姐妹们也成了酒神狂女之后,决议“要把她们逐出山”“还要把她们捆在铁网中,即刻制止这邪恶的狂欢”,把她们“卖掉”或“拥为家奴”。说这话(把自己的母亲卖掉或拥为家奴)时的彭透斯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吗?还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完全不重视家庭和亲情?他更像是早已从家庭的心理空间出走,才显得这般冷酷绝情。
如果说这时是强烈的政治血气让他不顾血缘亲情,没有德性,那么后期政治血气逐渐丧失的彭透斯则在德性的缺失方面变得愈加过分。在第四场的宫中,彭透斯把自己“托付”给酒神,任由他为自己整理女装,他的血气已经开始向欲望投降。当彭透斯之后穿着女装“穿过忒拜土地的中心”,向全城展示自己,进入山林窥探酒神狂女之时,他已经完全被欲望捕获。离开了王宫之家的彭透斯最终不仅失去了血气,也失去了向理智的德性靠拢的机会。
(二)归家与德性觉醒
如果说“离家”和“无家”象征个体德性的缺失,那么“离家”后的“归家”则体现了德性的复归与觉醒。在剧的结尾部分,手撕亲子的阿高厄下山,“行色匆匆入宫”,她重新回到城邦,来到王宫,回归家庭。对于阿高厄来说,重新进入家庭空间也是她理智得以恢复的开始。在父亲卡德摩斯的循循诱导下,疯狂的阿高厄逐渐恢复神智,重新建立灵魂的人伦秩序,她的“心境变得跟先前不一样了”“变得清醒点了”,灵魂“比先前更清明、更透亮了”。
卡德摩斯接下来的话试图让阿高厄回忆起她和家族的关系:“卡:你在歌声里进的是什么样的人家?阿:你把我交给厄克西翁,人们说他是龙牙变的。卡:那你在这家族为你丈夫生育的儿子是谁呢?阿:是彭透斯,我和他父亲结合所生。”
卡德摩斯在这里的提问让阿高厄觉醒,“家是其真实自我的所在地,不是作为狂女,而是作为曾在其中养育家庭的女人” ⑥。身体已经回归了家庭的物理空间的阿高厄,在父亲卡德摩斯的引导下,重新正视并接受自己和家庭的关联,抛弃自己的狂女身份,回归了家庭的心理空间。而这样一种重回家庭的过程也正是阿高厄远离狂女时期的欲望和不节制,重拾理智的过程。她看见了自己怀里的脸,那不是一头狮子,“我拿的是彭透斯的头”。阿高厄认清了自己在酒神崇拜无节制的爱欲和暴力的驱使下杀害自己的儿子的真相,认识到了这一真相的“不幸”,具备了分辨是非的神智,她不再是酒神盲目的崇拜者,她明白“狄俄倪索斯毁了我们”。
因此,对于阿高厄来说,回归家庭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将自己的存在重新和家庭挂钩的过程代表着她的理智回归和德性觉醒。虽然这一回归的真相是不幸的,但是德性的觉醒对于这不幸的女人来说已是幸运,回归家庭之前的疯狂的阿高厄才是杀子而不自知的真正的不幸。
二、家族与城邦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家庭还是部族,结合形成城邦,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⑦。于城邦而言,这是其本质要求,而这一要求的实现,却是基于若干家庭或部族的结合。在酒神进入忒拜的前哲学时代,“最古老的”等同于“最好的”或“最自然的”,而在城邦形成的早期,最古老也最繁盛的一族血亲是家庭最自然的形式。因此,“血缘和‘家庭’在公共政治中的影响力” ⑧获得承认,家庭和血缘共同体的古老与否也就成了现实中衡量城邦政治共同体优劣的一种礼法尺度。因此,同为社群共同体,家庭不仅是城邦形成的第一阶段,被包含于城邦之内,更是与城邦相辅相成。如果忽视了家庭这一元素,那都会给城邦以及个人带来巨大的伤害。
在《酒神的伴侣》中,忒拜的新王彭透斯忽视家庭,为了消除酒神崇拜对忒拜城的影响,不惜下令抓捕自己的母亲,把她卖掉或拥为家奴。彭透斯将自己等同于城邦,把城邦置于家庭之上。相反,忒拜的老王卡德摩斯极其重视家庭荣耀,他相信狄俄倪索斯是宙斯之子,愿意加入酒神崇拜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凡人家族和神产生联系,给家族增加荣耀。比起忒拜城邦的守护者,老王卡德摩斯更像是家族荣耀的守卫者。
酒神狄俄倪索斯在处理家庭和城邦的联系时,则变得更为变本加厉。和剧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不同,狄俄倪索斯来自外邦,带着复仇的目的来到忒拜城。狄俄倪索斯并没有位于忒拜城邦内的家,他的母亲早亡,他是一个不属于家庭空间内部的异乡人。他虽然没有家庭,但却借着家庭的借口进行他的复仇计划。在开场中,狄俄倪索斯批判赫拉对其母亲塞墨勒“永不泯灭的肆心”。但是实际上,是塞墨勒坚持要看宙斯的真身才引雷自焚,塞墨勒才是拥有“肆心”的那个人。然而,狄俄倪索斯故意将“肆心”嫁祸给赫拉,指责赫拉作为神对人实行的不义。他进一步指责现任忒拜的王彭透斯“与本神作对,奠酒没我的份,祈祷时也从不提我”。塞墨勒的姐妹们更是诡计多端,夸口中伤酒神,说他不是宙斯所生,而是“塞墨勒跟某个凡人有了私情,却把这失身的罪过推给宙斯”,为此宙斯杀死了说谎的塞墨勒。因此酒神来到忒拜,“要证明自己是神”,要“替母亲塞墨勒辩护,通过向凡人显示,她为宙斯所生的是一位精灵”。他惩罚母亲的姐妹们,使她们发狂离家,并强迫所有忒拜女子成为自己的信徒,他“率领狂女们一起战斗”准备攻克忒拜城。
通过对赫拉和彭透斯的指责,这位外邦新神假借家庭之名行报仇之事,为自己来到忒拜城传播酒神崇拜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而家庭和城邦之间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联,狄俄倪索斯对家庭这一要素的轻视(实际上仅仅是在利用)导致了后续城邦的毁灭。
酒神崇拜的一大特点是对限制入会这一观念的摈弃。因此,酒神崇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秘仪,后者对入会资格需进行严格考核。而人们只需要穿上恰当的服装,加入跳舞的队伍,就可以成为酒神的崇拜者。在酒神崇拜中,人人平等,没有限制,不分地域。酒神从外邦而来,其崇拜又在忒拜城邦内部传播,城邦界限被隐化。
更重要的是,狄俄倪索斯在剧末向卡德摩斯发布了一则神谕:忒拜城邦的建造者卡德摩斯将和妻子(“哈耳摩尼亚,阿瑞斯的女儿”)一起“化作蛇形”,“驾着牛车,统领外邦人”,组成无数的军队,洗劫神托所,亲手毁灭自己的家庭、城邦和传统,并摧毁其他众多的城邦。在这则神谕之中,包括忒拜城在内的所有城邦的毁灭,使得整个世界出现了没有城邦的局面,城邦的界限被彻底消除。城邦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是一种“拥有自我生命的自然创造物(a natural creature with a life of its own)” ⑨,它不是因人的需要而生,不是人类需求的创造物。因此,城邦具有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统治的德性(ruling virtue)”是好人和好公民所共有的德性,但是,好公民还具备“被统治的德性(ruled virtue)” ⑩。
换言之,好公民的德性(包括治人的德性和治于人的德性)只有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才能够形成。而新神(即酒神)却完全无视城邦的这种特性和本质,以及其对个人德性养成的重要作用。在酒神狄俄倪索斯统治下的“世界城邦”,企图在毁灭所有的城邦的基础上创建永久和平的“福佑之地”,这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因为其內的公民是没有德性的。因此,狄俄倪索斯的没有家庭限制,且不受城邦所限的酒神崇拜也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由酒神狄俄倪索斯统领的世界城邦,是通过由卡德摩斯带领的野蛮的战争所实现的,并在战争带来的和平中完全释放个人的自然欲望,如同文中酒神狂女们在基泰隆山上毫无区分的暴力和劫杀,极端的民主制带来了极端的血腥,战争带来的和平也就无法保障安全。
三、结语
城邦包括家庭,家庭是城邦形成的第一阶段。在城邦中,德性的养成是实现个人优良生活的重要前提,而德性的培养又有赖于家庭。作为社群结构,家庭对其中的个人的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在家庭的地理和心理空间内,个体收获节制、明智,离开了家庭,个人就会发狂,甚至遇难。同时,家庭空间的重要性和城邦界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裨益。任何重家庭轻城邦,重城邦轻家庭,轻家庭轻城邦的行为,都对个人生存和城邦发展毫无益处,要警惕家庭与城邦二者割裂的危机。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19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7-38页。
③姜丽:《社群、良制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观的核心义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4页。
④欧里庇得斯著,罗峰译:《酒神的伴侣》,引自《酒神与世界城邦下卷:〈酒神的伴侣〉笺注》,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⑤罗峰:《王者的血气—— 〈酒神的伴侣〉中的彭透斯解析》,《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85页。
⑥西格尔著,罗峰编译:《家庭、城邦与山:〈酒神的伴侣〉中的空间轴》,引自《自由与僭越——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绎读》,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
⑦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3页。
⑧贺晴川:《从家庭到城邦的政治教育——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之谜》,《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8期,第18页。
⑨Wayne H.Ambler,“Aristotle's Understandng of the Naturalness of the City.”The Review of Politics 47.2(1985),
P.169.
⑩Peter L.Phillips Simpson,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P.145.
作者簡介:
顾世一,女,汉族,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