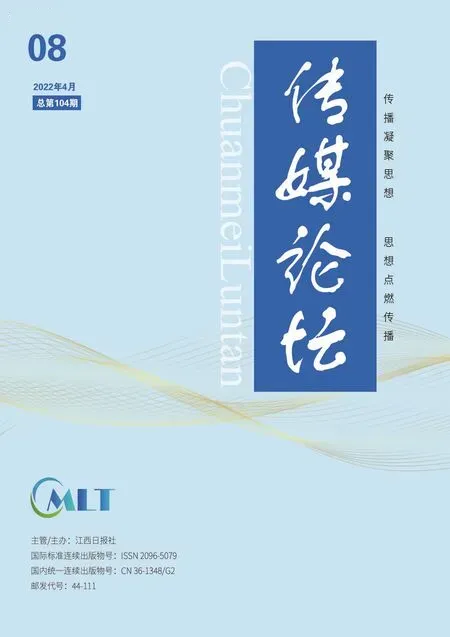《第一炉香》的女性形象与悲剧底色
宋瑞雪
作为纸上电影的张爱玲女性文学,富有极强的视听通感,天然就适合电影视听语言的改编,形成不同媒介记录的文化记忆。对张爱玲文学作品进行电影改编共发生了6次,分别是:《倾城之恋》(1984)、《怨女》(1988)、《白玫瑰与红玫瑰》(1994)、《半生缘》(1997)、《色·戒》(2007),《第一炉香》(2021)。其中许鞍华是对其作品进行影视化最早和尝试最多的导演,《倾城之恋》最早将其唯一喜剧式结局的作品搬上荧幕,《半生缘》呈现了爱情悲剧和人生际遇的叹惋,《第一炉香》讲述了女性出走之后面临的困境。无论是文字文本抑或是影视文本,张爱玲与许鞍华都以其作为女性的视角深描女性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呈现出特定时代下女性的形象及命运,以男性参照出时代下女性的被动处境。
2021年由许鞍华导演,王安忆编剧的影版《第一炉香》上映,讲述了女学生葛薇龙为留港继续学业投靠姑妈梁太太,最终被梁太利用成为交际花并与花花公子乔琪乔结婚成为妓女的故事。以《第一炉香》为例,对这样几个问题进行追问:影片呈现了怎样的女性形象?造成此类命运悲剧的女性形象原因是什么? 影片又是如何呈现悲剧的审美底蕴呢? 并以此来思考不同时代下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当下女性生存境遇。
一、时代困境下出走的女性形象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演讲了《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影片《第一炉香》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意识觉醒的女性反叛父权,逃离父亲统治的旧家庭。但是她们出走后仅供选择的也就只有堕落和回来两条路。为什么?因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2]。《第一炉香》通过描绘出走的女性形象,即挣扎谋生和卑微谋爱的女性,回答和探讨了时代困境下娜拉出走后的故事。影片塑造的女性形象有以下五类:以葛薇龙母亲为代表的旧式封建家庭的女性、以梁太太为代表的走出旧家庭的女性、以葛薇龙为代表的接受教育的新式女性、以周吉婕为代表的接受西式教育的殖民地混血女性,以丫鬟为代表的受人摆布的女性。这些女性都以找到一个好归宿为最终人生目标,其中出走的女性有两位梁太太和葛薇龙,二人展现了当时女性出走后艰难挣扎的求生和谋爱之路。
(一)挣扎谋生的女性
五四时期出走后的女性不想回归旧家庭,就只有挣扎谋生这一种可能,但是可供女性谋生的道路太窄。相比于影片中所呈现的男性形象:拥有财富的司徒协、拥有社会地位的乔诚、浪荡公子哥乔琪乔、出国留学的卢兆麟,女性总是以依附者,即符合社会性别体制下的形象出现:照顾起居的奴仆、撑牌面的姨太太、多才多艺的讨好者、温顺的被包养者、能够挣钱的妻子、出卖色相的妓女。两性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极大悬殊,使得出走后的娜拉谋生格外艰难。她们只是从一个家庭出来,逃离结果有两种:最终回归另一个家庭,把自己异化为色相市场的商品才能活下去。女性如果不走这条路,那就只有恋爱、结婚,建立新家庭。[3]而梁太太和葛微龙作为出走者就是这样两种结果的写照。
梁太太作为走出旧家庭并与原生家庭关系破裂的女性,与旧家庭的决裂和出走行为并没有使她获得自由,而是戴上人生的另一副枷锁走进了婚姻,遂成为另一个旧式家庭的传统女性。影片在展现薇龙与乔琪结婚留影时,混出头的梁太作为薇龙家长庄重地站在人群中,闪回了当年她远嫁富商做姨太时的卑躬屈膝——封建礼教束缚了她结婚时的着装及行动,她不仅没尊严,也无法满足那旺盛的情欲,直到丈夫下葬,开始了骄奢淫逸的日常。但要满足奢靡日常并非易事,而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男人成了她的猎物,为了欲求和享乐甚至不惜搭上自己侄女的青春。
以葛薇龙为代表的接受教育的新式女性,离家原本是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和将来谋生做打算;因为摆脱了自己的家,这是最终的断奶:正是在这时,她经历了被抛弃引起的一切焦虑和自由带来的眩晕。[4]一开始的薇龙未经世事一心向学,两个关键点使她改变初心:第一,司徒协用手镯把她和梁太镣铐住。第二,病愈后薇龙准备离港,拿自己的竹布衫与华服难以抉择,此刻她的人性已被物化难以回头。对于薇龙来说,即使顺利完成学业未来也仅仅是当个薪资微薄的教员,奢靡享乐的交际生活使得她沉迷于人生捷径,从此走上依附之路。在司徒协的物质供养下,她活在被男人支配的荫蔽下,从而丢掉自我的独立性——过上了一边忙着为丈夫弄钱,一边替梁太弄人的婚后生活中。
(二)卑微谋爱的女性
女性接受了教育鼓足勇气走出去,有了人生飞扬一面,但出去之后呢?在她面前并未有别的出路,也唯有谋生谋爱自求安稳。《第一炉香》除了刻画出挣扎谋生的女性形象外,也为我们细描出卑微谋爱的女性形象——情欲旺盛的梁太,为爱堕落的葛微龙。
梁太在丈夫死后开始了自己的纵欲生活,年老色衰的她一边对老男人百依百顺,一边又渴望年轻男人的身体,养了两个青春正茂的小丫头替她吸引男人,侄女的到来也列入了她寻求欲望的计划。在乔琪乔与葛微龙趁着夜色私会温存的同时,采用交叉蒙太奇细化填充了此刻二人的缠绵与深夜梁太惊醒后点烟冥想的内心孤寂,形成了对照;强化了一个并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现状,且深夜欲火旺盛但孤独无依的女性形象。葛微龙从一个一心求学的女学生,沦陷为灯红酒绿的社交场里姑妈谋爱的工具,到堕落为爱而放弃学业和正经工作,还要为梁太太弄人,给丈夫弄钱,“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留住”丈夫是一门职业。[5]迈出家门的女性,貌似获得了自由,却也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基本需求,葛薇龙只能奔忙于交际生活,却难逃最终青春被埋葬在梁宅的覆辙。那些在时代中挣扎着的娜拉们,也只能走向自己貌似主动实则被动的弯路。对葛薇龙来说也只有在湾仔集市上微笑道出那句“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儿?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女性被时代压抑着,连追求爱情都是一种隐没到内里的卑微和人生命运的无奈与苍凉,影片结尾一改原著小说中薇龙坐在车里饮泣,葛微龙想让沉默的丈夫表达出来同等分量地爱,自我流露出对丈夫的爱和抱怨地呼喊:“我爱你——个没良心的。”丈夫的爱就像燃烟的火星一样——开始来得热烈,结局只剩下黑暗中的对婚姻的满不在乎。葛微龙寄托于男性的卑微谋爱行为,如同蜜月时飘摇的小船上她手中握住的冰块一样,这不同于年少发烧时握住父亲镇纸的坚实且冰凉的玻璃球,谋爱带给她的只能是冰化水后的无法掌控的人生命运,婚姻也像这只飘摇不定的小船,并不能给她带来理想中安稳的生活。
梁太太从“谋生”到“谋爱”,葛薇龙从一开始的“谋生”到“谋爱”再到“为爱而谋生”,她们都没有获得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即便是爱情也难以给出走的娜拉们指出一条生存和成长的阳关大道,她们一直在崎岖的羊肠小径里步入歧途。影片只是呈现女性出走后所需要面对的现实世界,却并未对造成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原因进行分析。
二、时代困境下的悲剧底色
《第一炉香》通过对女性命运“悲”的叙事讲述和悲剧审美内涵的升华,表现出时代困境下的悲剧底色。我们通过探讨造成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原因和影像美学中审美内涵的分析,也能对当下女性所面临生存困境进行反思。
(一)父权制下作为附属品的悲剧命运
女人之所以变成《第二性》中的他者和男性附属品,是时代并未提供给女性应有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必然受到制约,造成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原因,并不仅是女性自身,还有以下两点:男性的主动导致作为“他者”女性的被动处境,时代挤压女性的生存空间。
第一,男性的主动导致作为“他者”女性的被动处境。女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另外一群人的作用,那就是男人,[6]女性是被造成的。以父权制为代表的男性家长气质,不仅仅占有政治、经济和生活资源,还束缚女性身体和精神发展,要求女性服从于父亲,丈夫和兄弟。这也就有了《第一炉香》故事发生的原因:葛微龙因父亲对家庭经济权的掌控,不再支持自己香港的学业,于是来到姑妈处求接济。男性对其命运和人生走向掌握着主动权,男性以父亲、包养者、暗恋者、丈夫的社会身份出现,他们参与抉择了葛微龙之后的人生走向。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这不仅会伤及女性,也伤及了男性自身,如乔琪乔作为儿子被父亲看不起。葛微龙无论是作为女儿、被包养的情妇、妻子,都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父权制将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7]作为“他者”(第二性)的女性相比于拥有社会地位的男性处于被动处境,于是丢掉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姑且将“出走”作为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出走后的代价说明女性的社会意识,即她们对自我所受到的压迫并未真正觉醒。因为面对谋生和谋爱,“葛微龙”们并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出走后的发展空间和主体性获得对她们来说太过艰难。因此回归家庭的葛微龙不仅要面对着丈夫的不忠,还要混迹于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进行谋生,甚至面临年老色衰后被男人抛弃的危机。
第二,时代挤压女性的生存空间。这也体现在国难时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上。“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绝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产,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胁她,使她奴役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8]个人际遇的兴衰荣辱,与生存空间的逼仄和广阔,都与时代境遇紧紧相连。家庭条件一般的卢兆麟成为梁太新欢后可以继续出国深造自己的医学学业,影片尽管没有交代他的后续,但可以想象学成归国后的他将拥有更好的机遇和人生前景。而葛微龙的人生选择是结婚。男性在公共领域活跃,女性可选择的出路只有回归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并依靠男人。选择与不专情且没有经济能力的乔琪乔结婚,注定两人的关系不平等。而她的谋生之路靠着年轻,多才多艺和色相,只剩下被司徒协包养去堕落这一条路走。影片结局给我们呈现了湾仔集市上被两个英国大兵架着走的雏妓,她们是时代困境下女性在艰难空间中生存的写照。
(二)影片悲剧的审美底蕴
《第一炉香》尽管不似西方酒神颂呈现出一种崇高的悲剧感,但却有一种东方含蓄式的隐喻,即人生难以托付的苍凉韵味。正如德索所言,真正的悲剧并不解决冲突,它只能让人们看到,在世界上、生活里存在着无论如何都无法平衡的矛盾。无情的命运总是无法消除那些罪过与天真。影片悲剧的审美底蕴体现在影片细节刻画中:坟墓般的别墅装潢,注定了住在里面女性前途被葬送;而梁太就像那只雄孔雀标本死物件一样,尽管外表保养得当,但内里清楚自己青春被葬送后的毫无生气;养在花盆里鲜红的杜鹃花隐喻着命运被掌控的年轻女仆;月亮在影片中除了交代时间的作用外,这一圆月意象并不象征着美好、思念与团圆,它象征着乔琪乔与葛微龙私会所达到的关系顶点,之后二人关系将月满则亏;司徒协的手镯隐喻着男性对女性的选择所导致女性的被动处境。受教育的女性选择做出走的娜拉,她们同样面对着走后生存的难题。女性在见识过世界的奢华与享乐后,难逃物质化的诱惑,因此像葛薇龙这类极其普通的上海市民阶级的女子大抵是回不去旧日的生活了。在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并且受挫时,时代困境下无助的她们只能依附于男人,能走的路只有姑妈的覆辙——她被人支配的命运是基于不幸、基于自身与世界的不和谐、更是基于张爱玲对普通女性人生命运与情感归属苍凉悲悯底色的洞察。
三、结语
《第一炉香》选择张爱玲初露文坛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进行改编,呈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转型社会,这些受到教育的旧式小姐在转变成新女性的失败——女性意识并未真正觉醒。呈现出时代困境下狭小的女性生存空间。伴随着1995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使得用女性眼睛看世界得以流行,也加速了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等议题的讨论和提案项目的实践。尽管张爱玲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早有觉察与审慎,其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剧底色和人生悲凉的况味;但两性不公平导致女性生存的困境,一直是时代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女性应当拥有自己的独立性,走出去,拥有广阔和包容多元性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将归宿寄托于稳定的家庭。《第一炉香》回答了无论过去抑或当下,女性出走需要面对的生存困境,但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尽管女性主义正在经历全球第四次浪潮,但是女性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依旧是女性主义讨论的永恒话题。通过对影片所塑造挣扎谋生的女性形象,或许可以引发当下更多关于女性处境的思考:性别的刻板印象、两性职业公平、经济收入对比,婚姻法的合理性等。当下女性主义的文化思潮影响着两性,女性意识也有了反压迫的践行,出走后的女性可供选择的机遇并非如鲁迅所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她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因此,《第一炉香》不仅仅是把女性话题再次带入人们的视野,同样它也可以让我们思索过去导致女性悲剧形象和命运的原因,从而反思当下及展望未来两性平等及女性赋权的措施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