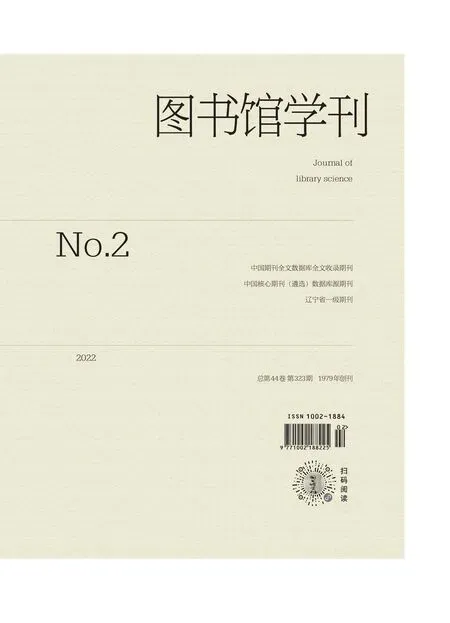钱存训先生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
富 洁
(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钱存训先生是著名的书史、印刷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他学识渊博,造诣深厚,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在青年时代便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职于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皆有出色的工作表现。1947年,钱先生以交换馆员的身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进修。在美期间,他钻研学问、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取得了图书馆事业的辉煌成就。虽然久居美国,钱先生却始终胸怀祖国,自称永远是北平图书馆派出的馆员。他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特别是图书馆界的交流上,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1 图书馆工作业绩
1.1 北平图书馆的对外联系工作
1932年,钱存训先生经校方推荐至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1937年,钱先生接受袁同礼先生邀请,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主任,后转任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办事处是保存北平总馆重要藏书的分馆之一,收藏有全套科学及东方学期刊1万余册,甲、乙库善本古籍5000多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和金石碑帖数百件[1]。钱先生既要监管珍贵的善本藏书,还要负责搜集和抢购图书、出版发行《图书季刊》、北平总馆的对外联络和交换等工作。《图书季刊》创办于1934年,内容包括论著、书评、书刊介绍、学术消息等专栏,深受学界欢迎。因战争原因,其一度停刊。1939年复刊后,大部分稿件的评论、校对、印刷和对外发行均由钱先生负责。新版《图书季刊》每年一卷,每卷四期,恢复发行后立即收到中外机构和私人的千余份订单。战乱年代,印刷和发行工作十分艰难,在多数图书馆学期刊停办的情况下,钱先生始终坚守阵地,为国内外学者传递出中国图书出版及学术活动的信息。
1941年初,上海局势日趋紧张。为保善本免遭战火涂炭,袁同礼先生决定将珍贵善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待战争结束,再接运回国。由于善本种类繁多,遂从中挑选出2720种,3万余册,共装成102箱,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宋、元、明、清历朝内阁大库的旧藏,是北图善本中的精华[1]。最初由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试寄了两箱,后因日方干涉,不能续寄。直到当年9月,钱先生与海关外勤的张先生建立了联系。在张先生的协助下,钱先生用手推车将余下100箱善本运送至海关。1942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102箱的善本书籍全部到达华盛顿,即将开始摄制胶片。5年后,国会图书馆将摄成的缩微胶片赠送中国的图书馆3套,其余被世界各国图书馆收购,供各国学者研究参考,具有弘扬中华文化的深远意义。钱先生在乱世中甘冒生命危险,维护图书馆利益,抢救国家文化遗产,体现了图书馆员恪尽职守的责任感和爱国爱馆的高尚情操,实为同侪楷模。当时的教育部特令予以嘉奖并颁发奖金。199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向钱先生颁发“杰出贡献荣誉奖”,表彰他在抗战时期运送善本的光荣事迹。颁奖仪式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举行,人民日报社、美联社等中外媒体记者到场采访。有位美国记者问道:“你为什么冒生命危险做这件事?”。钱先生回答:“这是馆中交给我的任务,当时并没有考虑其他问题”[2]。朴素平和的话语,成功却不居功的气度,正是默默无闻、恪尽职守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吾辈用心体会效法。
1.2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图书交换工作
1947年,钱先生接受芝加哥大学邀请,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工作学习,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1949年,钱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任教,并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馆长一职延续至退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扩大到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钱先生身为图书馆负责人,考虑到教学和研究的需要,重点加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资料的搜集。20世纪50年代,在中美尚未建交的背景下,钱先生率先与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即使在文革时期、国内出版物停寄的情况下,他依然向北图邮寄书刊,从未间断。中美建交后,北京图书馆领导为此安排向钱先生表示了感谢。钱先生从远东图书馆荣休之时,芝加哥大学负责管理学术资源的副校长致函祝贺:“你献身中美两国图书馆事业五十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无价的传统”[3]。
2 图书馆界交流活动
2.1 中美图书馆代表团实现互访
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打开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政府间交往的新局面。随后中美公私团体开始互相访问,中国图书馆代表团是少数访美的学术团体之一。1973年9月,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率领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展开了对美国的访问。代表团考察了美国图书馆的行政工作和服务设施、现代新科技对图书馆的应用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的最新情况,行程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歇根、俄亥俄、芝加哥、俄克拉荷马及旧金山等地。由于中国图书馆界是首度访美,主办方对于接待工作十分谨慎,事先安排了各地区的负责人,并召集负责人到华盛顿参加筹备会。钱先生作为芝加哥地区的负责人,前后两次赶往华盛顿,一次是为商讨本地区的日程安排和接待工作,另一次是参加欢迎宴会。10月份,中国代表团到访芝加哥。在钱先生的安排下,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总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及东亚图书馆[4]。
1979年,钱先生随美国图书馆代表团回访中国。美国代表团的访问为期两周,行程有北京、西安、上海、南京和广州5座城市。访问北京期间,钱先生在首都图书馆做了题为《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沿革与发展》的学术报告,来自首都图书馆界的1200余人收听了报告,报告后附有近百所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名单。时逢文化部拟办中国对外出版贸易总公司,推广国内书刊出口。中国对外出版贸易总公司委派王福时先生现场收听了报告,并进行了详细地记录。会后,总公司致函钱先生,请他帮助推广书刊出口。当时全美的东亚图书馆每年约有一千万美元的购书经费,经费的大部分用于采购中文书刊。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只能由香港和日本的代理商购入。间接的购书渠道不仅费时,且收入数量、种类不全。钱先生向中国对外出版贸易总公司介绍了这一现状,并建议该公司到美国参加书展,让美国的学者和图书馆人员能够直观地了解中国大陆的出版情况。总公司赞同钱先生的建议,请他出面代为办理。1982年,钱先生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成立了中国出版服务公司,并出任公司董事长。总公司每年选出两千多种学术性书刊交由中国出版服务公司参加书展,并在展后处理展品和接受订单。中国出版服务公司成立于中美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时期,成为了连接中国大陆出版界和美国学术及图书馆界的纽带。通过它的联系,中国的出版界了解到美国学术界的图书需求,扩大了在美影响力,拓宽了书刊发行渠道。美国的学者了解到中国的出版情况,采购了科研所需资料。钱先生此举惠及中美,受到了双方的欢迎和称赞。
中美图书馆代表团的首次互访结果圆满,收获颇丰。通过初步的业务考察和学术交流,中方学习了美国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美方了解到了中国图书馆的现状和发展意向,为日后进一步沟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钱先生在中美图书馆界的访问活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见证了中美两国文化界、图书馆界从隔阂走向交往的历史。
2.2 学术会议
随着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的逐渐恢复,钱先生与国内图书馆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便利。1984年,“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丹麦、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学者出席。讨论会设立数学与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学史、生物学史、技术史、冶金学史、综合研究7个专门组。钱先生担任了技术史组主席,主持本组的演讲和讨论,并宣读了题为《欧洲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的论文。论文阐述了“欧洲的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是受中国印刷术的启示和影响,并非独立发明”[5]的观点,内容精辟,论点鲜明,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辉煌成就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起到了交流学术、增进理解的重要作用。
1984年11月,钱先生应邀参加在中国台北举行的“古籍鉴定与维护研讨会”。研讨会采用“教学兼讨论”的形式,目的是培植古籍维护鉴定方面的人才。参会学员约有30余名,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钱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两场专题演讲。第一讲的题目为《欧美地区古籍存藏现况》,主要讲述欧美收藏与汉学研究渊源及发展、收藏特色及重要性、欧美各国中文藏书简介、北美图书馆近况、古籍的定义及维护建议[6]。第二讲为《中国历代活字本》,阐述了活字版的重要及特点、中国活字版的起源及传播、明清两代活字本的发展、研究活字版的问题等[7]。钱先生的演讲生动精辟,学员们从中获得了常规教学中接触不到的知识。研讨环节中,学员们兴趣盎然,每每发问,授课专家讲解详尽,相互讨论。此次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培植人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预期目标。
3 捐赠藏书
1979年,钱先生向北京图书馆赠送了清代高士奇的精写本《江村书画目》。该书收录了534件晋唐至清初的书画作品,是研究书画鉴赏和从事美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访问上海时,钱先生代表芝加哥大学向上海图书馆赠送了有关新科技和计算机的西文图书553种、600余册,并赠送个人收集的韩国在1966年发现的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复印件及相关论文、报道。这一发现曾震惊世界,韩方企图借此改写雕版印刷的发明史。我国正值文革时期,学术界与世隔绝。钱先生将此信息及时传递给国内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协助了国内学术界展开行动,捍卫我国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
2006年,钱先生向母校南京大学捐赠183箱书刊,其中图书约4700册,期刊70种近千册[8]。这批赠书是钱先生多年珍藏,包括中国文史、社科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一些欧美、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出版的全套书刊。2007年,南京大学将钱先生的赠书存放于新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并命名为“钱存训图书馆”。南京大学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是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同其他学科的发展交流,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指导研究工作,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9]。钱先生的赠书行动正好符合研究院的办院理念。在钱先生的带动下,他的好友门人纷纷踊跃捐赠藏书,作为“钱存训图书馆”的补充。接受赠书是图书馆完善藏书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久的将来,势必有更多的海外学者受此感召,加强与国内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的联系,推动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发展,促进中美图书馆及图书文化的交流。
4 文化史研究
钱存训先生对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浓厚的兴趣,著述颇丰。譬如《第一次中美出版品交换》(First Chinese-American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一文,其主要是钱先生依据偶然间发现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恭亲王奏折研究所得。其内容大概是美国政府请求交换书籍,清政府起初不置可否,后来挑选1000册图书赠送美国政府。他根据奏折中的人名年月,在美国档案局找到了当年美国国务院与驻华公使来往的15件公文。后又根据这批公文,写成《第一次中美出版品交换》,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文章以确凿的史料,还原了中美两国首次图书交换的史实,考证了中美政府间的文化交流结缘于1869年。1867年,史密斯学院通过美国国务院驻北京使馆向清政府总理衙门请求交换图书,未获回复。之后,美国农业部派特使到中国获取农业物产资料。美国特使带来了美国蔬菜、五谷、豆类的种子和农业、机械、采矿、地图等书籍,希望与中国交换同类书籍。总理衙门在等候同治皇帝谕旨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再度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申请获取道光年间的户籍调查资料。在美国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总理衙门选购了《皇清经解》《五礼通考》《钦定三礼》《医宗金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骈字类编》《针灸大成》《梅氏丛书》《性理大全》10种书籍,约1000册回赠美国政府。1869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劳文罗在卸任致词中说:“希望将来两国有更多人士能够阅读彼此书籍,增进彼此了解”。1876年5月美国公使的公文显示,中国政府的全部赠书应在1876年或以后到美。钱先生在文中指出,1869年的图书交换虽然数量有限,但开创了两国政府间文化交流的先河,意义非凡。如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量举世闻名,两国能通晓彼此语言的人才数倍于前,图书交换应是今后两国吸收彼此文化精髓,丰富彼此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渠道之一,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10]。
图书交换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政府间的图书交换更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清政府的赠书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库的始祖,也是美国图书馆入藏最早、规模最大的中文书籍。钱先生成文前,国会图书馆和主持国际交换的史密斯学院均无当年中国政府的赠书记录。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国会图书馆的认可,弥补了历史记录的缺憾,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的材料依据。1969年,为纪念中美图书交换100周年,国会图书馆特在Whittall Pavilion议会厅举行了展览,并将钱先生的文章放置于特藏书库,供读者参考。
2004年,钱存训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顾问。2009年,钱先生向国图赠送手稿及签名图书。2012年,钱先生参与了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文本中国”研讨会。2014年,钱先生致函祝贺《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2015年4月9日,钱先生因病离世。钱先生的一生,与书结缘,学贯中西,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对“文化交流”有着深切透彻的理解,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界交流、增进世界人民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