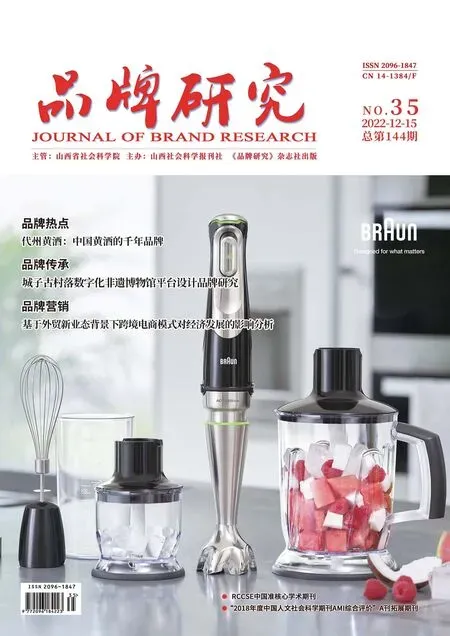虚拟偶像粉丝群体的内容共创与文化实践研究
——以虚拟偶像团体A-SOUL为例
文/王彪 王新惠(北京工商大学)
随着VR、人工智能、全息影像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以此技术为依托的虚拟偶像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并吸引了大批粉丝的追捧。技术赋能和市场催化使虚拟偶像的现实形式不断拓宽,发展为虚拟主播、虚拟歌手、虚拟代言人等多种门类,并在交互性和体验性方面完成了实质性升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虚拟数字人综合评估指数报告》指出,中国虚拟数字人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2000亿元,比2018年同期翻了一倍,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2700亿元。2022年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化虚实交互体验,国家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虚拟数字产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资本的青睐,虚拟偶像产业在经历了萌芽、探索后,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本文的研究案例A-SOUL于2020年出道,是字节跳动和乐华娱乐共同打造的虚拟艺人团体,人设定位为来自元宇宙空间“枝江大学”的五位性格各异的女大学生,分别是贝拉、向晚、嘉然、乃琳和乐珈。不同于初代虚拟偶像初音未来、洛天依等完全依赖电脑技术合成声音和虚拟形象,A-SOUL则是通过全身动作捕捉技术、捕捉真人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在保证视觉模型超真实虚拟形象的同时,实现与粉丝的实时互动。凭借与粉丝群体间真诚、亲密的关系,A-SOUL经过两年的发展,一跃成为国内虚拟偶像圈的顶流。
一、A-SOUL粉丝群体的内容共创方式
“与以前把媒体制作人和消费者当作完全分立的两类角色不同,现在我们可能会把他们看作是按照一套新规则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参与者”。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已经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内容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在A-SOUL创立的初期,留下了大量的内容空白供粉丝参与和填补。在商业运营的过程中,A-SOUL的运营方发现,粉丝群体的内容创作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因此粉丝的创作价值得到运营方的认可,创作热情被激活。通过内容共创的方式,粉丝群体逐渐由内容创作的边缘位置走向中心。
(一)形成与虚拟偶像的“拟社会关系”
传统偶像的经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由经纪公司或娱乐媒体共同建构人设,偶像再通过人设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的建议一般不会被偶像背后的团队认可和采纳,难以对偶像人设造成实质性影响。而且,在事实上,粉丝也没有想要改变传统偶像人设的基础动因。与传统偶像不同,A-SOUL的粉丝群体则被赋予了充分的内容创作空间,且在A-SOUL背后的经营团队也极其重视粉丝的内容创作,并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技术支持。为了降低创作的技术门槛,鼓励粉丝创作的积极性,A-SOUL团队主动分享了虚拟偶像的基础模型,使得粉丝可以利用这些基础模型,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期待塑造偶像的形象。《今夜不会停止》就是粉丝通过A-SOUL成员贝拉、向晚和珈乐的基础模型创作的原创舞蹈单曲,不需要过于专业性的技能,就能参与内容共创,填补了由于高技术门槛限制无法参与内容创造的空白。
偶像与粉丝之间存在一种“拟社会关系”。粉丝参与虚拟偶像的人设塑造,通过内容共创的方式打造符合自己期待的偶像人设,并借助相关媒介平台与偶像进行深层互动,从而与偶像建立了一种虚拟的社会关系。这种虚拟社会关系的建立,源于粉丝自身的心理需求。以Z世代为主的粉丝群体,在新媒介技术的环境中成长,面对诸多的学业、工作和生活压力,他们习惯于在网络世界中寻找逃避现实、排解压力的方式,从而获得情感上的安慰和补偿。而虚拟偶像的高度娱乐化和参与式的内容生产方式,为粉丝提供了想象空间中的新鲜的情感体验,与虚拟偶像建立情感联系,既满足了观感上的愉悦体验,又满足了心理上的沉浸式陪伴。
(二)符号化的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
虚拟偶像的主要受众是Z世代群体,他们在新媒介环境中成长,更注重自我,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表达欲。他们更容易接受虚拟形象的传播方式,借助虚拟偶像的内容生产彰显自我价值,区分自己与他人,并通过与虚拟偶像相关的内容生产获得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相关理论,大众在以符号为媒介互动交流中产生对意义的认知和把握,交流的对象包括客观环境、其他个体或群体以及内向自我等。在互动的过程中,适应环境、交流意义并产生自我认知,其中,符号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中间介质的作用。在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中,存在着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化传播方式。粉丝群体往往通过赋予虚拟偶像或群体自身符号化的专属称谓,表达对“他者”或自我的身份认同,小作文创作是二次元粉丝圈层中的常见现象,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最廉价最简单的情绪发泄方式和自我调侃方式”。
(三)群体狂欢式的造“梗”文化
“梗”原本指具有讽刺或指涉含义的笑点,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含义不断延伸,任何词句、短语、事件都可能成为“梗”。“梗”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赋予过程,具有多义性和不稳定性,不同的人、不同的经验背景,对“梗”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虚拟偶像的粉丝圈层中,造“梗”体现为一种群体共同参与的意义生产过程和话语方式。
根据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在群体狂欢仪式中,群体成员的个性和普遍存在的规则和秩序消失,呈现出一种狂欢式的集体趋同心理。这种现象在虚拟偶像的直播弹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直播弹幕往往表现出同质化、情绪化的鲜明特征。比如,A-SOUL的粉丝群体经常通过弹幕造“梗”的方式与虚拟偶像互动,造“梗”活动一旦引发群体效应,全体粉丝都会通过弹幕、评论等方式参与进来,呈现出大量同质化的全员狂欢式的内容输出。例如经常出现在A-SOUL直播弹幕中的“哈哈鬼”,是用来嘲讽那些在网络社交中,只会使用“哈哈”作为回复的网络社交能力偏弱的现象,随着这个“梗”的流行,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演化成乐观面对生活“无论发生什么,每天都是哈哈哈哈”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造“梗”,既是一种娱乐化的自我表达,也是一种在达成共识后的群体狂欢。
二、A-SOUL粉丝群体的文化实践研究
亨利·詹金斯认为,新媒介环境下的粉丝既是“文化盗猎者”,又是“勇于争夺文化权利的斗士”。从文化实践的角度看,他们拥有文化生产和实践的方式和技巧,不满足于被动接受媒介提供的信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生活经验,“盗猎”、汲取原文本中的意义,并构建新意义。因此,A-SOUL的粉丝群体既是虚拟偶像商品的消费者,又是文化内容生产的参与者。
(一)生产内容的排他性:构筑圈层文化壁垒
在虚拟偶像的粉丝群内部,对“他人”的判断标准不是地理位置、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属性,而是根据能否理解群体中独特的语言风格、表达方式,那些无法理解或误解的人群则被排除在圈层壁垒之外。文化壁垒的形成,有助于保持自有文化的独特性,但阻断了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扩大了认知鸿沟,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不同群体间的误解与矛盾。
虚拟偶像从属于亚文化体系,与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壁垒,具有天然的属性特征,同样是粉丝群体自主建构的结果,他们通过生产独特性的区隔性文化符号,把自己与主流文化隔离,使两种文化之间缺乏正常的沟通交流。这种情况极易造成主流文化对虚拟偶像圈层的偏见和刻板印象。通过对A-SOUL粉丝群体的观察,他们把虚拟偶像崇拜视为抵抗孤独、表达自我的方式,对外来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情绪,这种抵抗情绪投射在内容生产上,则表现为通过大量排他性内容的输出,这种方式虽然满足了粉丝群体自我认同、彰显自我价值的需求,但难以获得圈层外群体的理解和认可,可能有招致标签化和污名化的风险。
(二)融合与碰撞:跨圈层的文化传播
粉丝群体排他性的内容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文化壁垒。但在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虚拟偶像圈层无法做到完全把自己阻隔在大众文化之外,相反的,表现出与主流文化之间不断交融的趋势。这种趋势实际上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形成了新型的泛二次元文化圈层。与二次元文化相比,泛二次元文化圈层的圈层范围更广,且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界限更模糊,甚至表现出一种重构主流文化的能力。
虚拟偶像的粉丝,在最开始的时候常见于动漫圈层、游戏圈层的爱好者,这些群体成员有着相似的二次元文化属性、审美偏好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具有排他性质的群体性圈层融合。但这种初始圈层形成后,则表现出不断向外延伸、扩展的趋势。以A-SOUL的粉丝群体为例,其中有些粉丝自发地在各圈层中为自己崇拜的虚拟偶像引流。他们在为自己的偶像引流的过程中,把圈外人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作为吸引他们的信息点,“欺骗”他们点进去,从而达到帮助自己的偶像吸引流量、赢得关注的目的,引流的范围包括手游圈、私人朋友圈和公共社交平台等多个圈层,在粉丝群体的自发引流中实现了圈层之间的交流、融合。
(三)收编与规训:资本入侵二次元文化圈层
伯明翰学派认为,主流文化面对亚文化的挑战,自然不会放弃自身的权威,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会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对亚文化的收编。在虚拟偶像产业中,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产业红利初现,资本纷纷入局这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虚拟偶像在资本支持和技术赋能下,视觉呈现更加真实、梦幻,体验性、沉浸感越来越强,技术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完全依靠粉丝自发的内容生产获得自身的主动权面临着一系列困难。
高技术门槛限制了粉丝的内容创作。A-SOUL的全身动作捕捉技术、3D呈现技术,细节甚至可以精确到手指、发丝。这些技术的高门槛属性,导致A-SOUL的粉丝虽然在A-SOUL团队那里获得了基础的生产模型,但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限制,使得他们创作的内容与专业团队相比还是具有较大差距,造成在技术型的内容创作方面,他们还是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与此同时,A-SOUL的运营团队还通过设置规则和奖励机制的方式,限制粉丝的内容生产行为。例如,A-SOUL的“二创激励计划”,就明确表示粉丝的原创作品要“积极健康,符合主流价值观”,鬼畜等非主流作品均被排除在外,粉丝群体原本自发的内容生产模式,被资本规训后,难以保持原有的创作激情。
三、A-SOUL粉丝群体双重身份的迷思与应对措施
A-SOUL粉丝群体的内容生产获得了官方团队的认可和支持,被赋予了极大的创作空间,这造就了他们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又是商品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在两种身份之间转换,通过内容共创获得群体认同和精神满足,通过商品的消费行为表达对偶像的关注和热爱。但面对消费文化、资本市场、大众文化等多重压力,他们无法做到游刃有余,有陷入被资本操纵、自我迷失的风险,应正视这些问题,探究解决方法。
(一)搭建与主流文化沟通的桥梁
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在维护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应主动跨越圈层壁垒,寻求与主流文化的沟通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消除自身的刻板印象和文化隔阂。长久以来,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类,打上异质化的标签。其实,这种异质化标签的实质是双方缺少沟通交流,彼此缺乏了解所致。因此,应该设法增进彼此了解,消除圈层壁垒。比如,A-SOUL官方就曾编制过一部《枝江方言词典》,用来科普A-SOUL专属的流行语,帮助圈层外群体理解,促进文化融合;或者,在内容上可以创作一些关于生活、情绪方面的内容,这些感受是相通的,有助于获得大众的共鸣。
(二)防止丧失理性的自我迷失
技术的加持,赋予虚拟偶像“超真实”、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给予粉丝内容共创的权利和空间。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游离,通过个人主义的内容生产塑造符合自己期待的“完美偶像”,实质也是在塑造“完美自我”。在这种内容共创机制下,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甘愿把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沉迷于虚拟的“元宇宙”之中,丧失了在现实世界中正常生活、社交的能力;为了彰显自我价值、获得群体认可,他们盲目地进行炫耀性消费,为支持自己的虚拟偶像,上演了一次次狂热的“粉丝群殴”,导致虚拟偶像市场乱象丛生。事实上,所谓的“完美”虚拟偶像并不存在,它们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娱乐于人的媒介工具。因此,应理性看待虚拟偶像现象,把握自我的现实价值,才能防止自我迷失和自我异化。
(三)警惕资本操纵,掌握内容生产的主动权
“资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亚文化的收编,亚文化也一直在进行着反收编”。只有掌握了内容生产的主动权,才能抵抗资本操纵,保持自身的独立发展,而参与内容共创活动就是抵抗资本入侵的重要方式之一。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可以通过主动地内容生产抵抗资本的操控,甚至可以利用资本的资源为自己服务,掌握内容生产的主动权,反制资本的收编企图。比如,在A-SOUL的“二创激励计划”中,虽然A-SOUL官方设置了参与机制和规则,但粉丝群体也能通过这个活动,获得内容创作所需的偶像基本模型和来自主创团队的资金支持。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在面对资本的收编时,只要方法得当,是具有一定反收编的能力的。
与以往单纯依靠数字电脑技术驱动虚拟形象的方式不同,A-SOUL是通过全身动作捕捉技术和3D呈现技术,在虚拟成员的背后安排了真实的演员角色,实现了与粉丝实时、真实的沟通交流,成为目前极具代表性的虚拟偶像团体。A-SOUL的粉丝群体在虚拟产业的受众群体中具有鲜明特征,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虚拟产业受众群体的表现特征。A-SOUL的粉丝群体在内容生产能力和积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粉丝群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并通过与官方团体间合作的内容共创活动,表达自我、反哺偶像。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群体获得了内容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身份之间的游离,使得他们有陷入自我迷失和异化的风险,应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