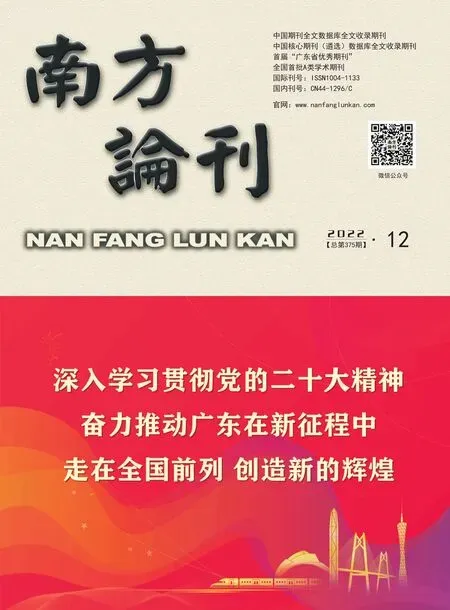中国传统家风的文化载体探析
潘子檬
(南开大学 天津 300350)
作为中国传统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家风,是以血缘天性为隐秘牵系的亲亲之情为依托,以伦理秩序所确定的长尊幼卑为前提,通过一代代言传身教、躬行实践,形成植根于日用常行的“规范”的家族风范。自2022年正式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的“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1]既凸显了家风于现代社会建构的重要意义,同时也隐含着对传统家风深入剖析的必要性。以传统家风的文化载体为视角,将耕读、家学、家训作为家风的三维文化载体,系统分析无形家风与有形载体间的影响进程与作用效果,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新时代传统家风的文化传承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耕读:传统家风的场域载体
耕,治生之本务;读,荣身之常道。农耕与读书相伴,进而形成“耕读并举”“半耕半读”的生活状态,已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高洁志向追求的表征;文化活动与农业活动的结合,使耕读文化的身份得以澄明。
(一)耕与读
“人类文明的起源无疑地是以农业为先导的,农业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先决条件,农业文明本身就是初始意义上的文明。”[2]以农耕为例,在早期社会,四民分业理论严格限制了职业与阶层的流动,“农分田而耕……士大夫分职而听”[3](P495)的社会背景使农耕成为农人世守之业,鲜有士人躬耕陇亩。经过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4]的思想观念为“耕”赋予了“道”与“德”之意涵,原本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耕作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内涵后,便成为承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行为,具有更为普遍和深刻的社会道德意义;科举制度的兴起打破了“农农、士士、工工、商商”[3](P374)的预设和前提,耕与读的普遍互通性使得职业分野的界限变得模糊,并产生相互转化的通道,经过传承与淬炼,最终形成了耕读为本的文化传统。
(二)耕读与士人
耕读文化之所以在中华文明中熠熠生辉且恒久不衰,关键在于其自身内在包含的两个元素——耕与读,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作用力下创造出来的内驱力。农耕哺育了众多读书人,根植于日用常行的农耕体验阐发了超越文字的思考;士人则借助自身文化素养的优势,以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理认知反哺农耕,同生产工具等其他生产因素共同促进农业发展。以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为例,在土地兼并之风盛行的北宋时期,由于大地主势力多逃赋税,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分化日益明显,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富国强兵,变法图强,王安石发动系列变法对策,无论是以国家贷款帮助农民耕作的“青苗法”,还是核实土地数目好坏,进而保证农民的土地数量的“方田均税法”,这些“中央——地方”管道式对接的变法核心均是其农耕思想的体现。正是自幼出身于农耕家庭的实际生活体验,土地改革成为其政治抱负中至关重要的内容,这种颇具农耕色彩的政治抱负也终于在农民生活改善、国库充盈等现实成就中得以实现。对于农耕的反哺,则集中体现在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农书,它们均出自具有丰富农耕经验的学者之手,将农业精神凝汇于普通百姓易读易懂的农耕技术、农耕方法中,延续了农耕文化的种子。总之,“耕”与“读”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它们相互补益,相辅相成,也正是这一哺一反的循环合力促成耕读文明源远流长。
(三)耕读与家族
家族,是实践耕读文化传承的社会载体。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耕读文化本身作为家族崇尚的价值取向,家族成员希望借助这种“内圣”的修身途径达到“外王”的功夫和境界;另一方面,由于家族自身经济基础的迥异,“外王”的终极目标在世家大族和寒门士族中具有不同体现——前者致力于清、慎、勤的品德培养,后者则更偏向于为官出仕的明确目标。原本的世家大族物质支撑较为充裕,生存压力较小,从事劳动生产也并非生活必须。官宦家族更希望通过耕读,培养家族成员清正廉洁的高洁品德,将“仕宦之法,清廉为最”[5]的观念视为出仕之目的;培养谨言慎行的良好作风,认为家庭成员“非法不言,非道不行”[6](P98)的个人行为与家族荣誉和传承直接关联;培养勤劳节俭的家庭美德,以勤劳之“立”保证开拓,以节俭的“续”保证传承。而对于寒门士族来说,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完善,出身寒门却中举入仕之人不再是寥寥无几。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7]寒门之人愈来愈有机会建立新的世家大族。科举制度一方面给予其光明前途,从而可以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和家族本身具有诸多不稳定性,荣华风光可能一朝倾覆败落,读则“兼济天下”,耕则“独善其身”,[8]构成寒门士族传承的两种现实需求。
(四)耕读与家风
家风,是家族耕读文化传承的集中表现,传承千年的耕读文化是传统家风的原始场域,形成了以耕读为本、诗书传家为理想追求的家风范式。南宋诗人陆游曾对子孙后代指出“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9]的人生道路,在陆游提出的三种人生道路选择中,复能为农为上选,杜门穷经为中选,安于小官为下选;他将“吾家世守农桑业,一挂朝衣即力耕”[10](P184)的经验与情怀濡染于“更祝吾儿思早退,雨蓑烟笠事春耕”[10](P200)的字里行间,以诗书为载体传承以农为乐、勤力稼穑的淳朴家风。此外,诗书传家的家族理想仍然被许多士族所重视。《颜氏家训》有言:“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11](P97)家族中唯有志者,方可历经磨难后最终成就士族的事业,而“志”的关键在于立读书志,传承门第之风。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才有了“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11](P99)的劝诫,子女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自然致力于养身心,取科名,继家声。
耕与读的内在契合是在家族这一社会载体中实现的,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代表家族精神气质之魂——家风,这是中华文化扎根于家族内部的写实,也是将农业文明融于血缘天性,进而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现实基础。“耕读传家”四字,呈现了耕读并举的社会理念、隐耕进仕的生活选择以及伦理规范的行为准则,一锄一笔,勾勒着中国古人的文化气质。
二、家学:传统家风的活动载体
家学是家族世代相承之学,是中国古代世家大族世代传承、赓续家风的基本向度。作为传统家风的一种具体外化形式,家学围绕家庭范围内的授读、训育等有形的教育活动展开,共同交织成无形的家庭精神联结,成为传统家风的外在凭借。家学作为家风彰显的文化事象,内在包含对思想道德的培养、对文化濡染的达致、对文辞技艺的培植三重意涵、三种特性。
(一)世德家风:道德元素核心化
所谓核心化,是指一些士族家族在普遍遵循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对某一道德元素有所偏向和侧重,将这一道德元素作为传袭世代的重要内容,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门第之风。在以仁、义、礼、智、信为最高道德标准的传统社会历史背景下,家族内部以某一道德元素为起点,扩充其范围进而构建彰显门风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传统,颇具家风传承和家族兴旺等积极的现实意涵。
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勤劳节俭作为家庭美德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方面,可以维系共同奋斗的稳固家庭关系,建立起“两种生产”所必需的家庭财富;另一方面,能够承续个人的德行臧否,成为决定家庭成败兴衰的关键要素。司马光家族有着崇尚世家节俭的德性先风。司马池“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12](P3395)的清廉自守的入仕之德,及“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12](P3394)“不饰厨传”[12](P3395)的质朴淳厚。司马光以自身作为孝友忠信,恭谦正直的垂范,教诫子孙保持节俭的德性,做到“不役于物”。司马光认为,以节俭为指导的德性教育应成为家范的精神内核,“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13],奠定子孙后代的责任践履的善道基础。司马康谨记其父坚守节俭风尚的处世原则,一生廉洁自立,以俭朴自持。宋哲宗曾为过世的司马光立神道碑,赐予司马康两千两白金,而他“以文正公葬皆官给,碑已具,固辞。”[14]司马光家族重视对代际成员节俭德性的培养,将节俭这一道德品质作为家风外在显现的核心。这既对当世世家大族作出先锋垂范,又成为后世个人、家庭及社会一洗浮华之风的长鸣。
(二)世仕家风:仕途知识功名化
在以“选贤任能”为基本向度的传统社会政治生活里,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成功造就了士大夫阶层这一兼具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这一古老而常新的领域打开了一条新通道。一方面,科举制将意义深刻的“至公”思想落实到制度设立、人才选拔等环节,扩增招贤人数的同时打破身份差异的拘囿;另一方面,随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抱负得以有生根之土壤,“仕”与“学”的紧密结合使劝学之习蔚然成风。但从唯物史观加以辩证地审思,科举制度的实行也造成士人“官本位”等功利观念的膨胀。其一,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由于身份限制的放松,寒门子弟试图摆脱贫苦生活、挤入社会上层的理想有了制度保障,于是唯科举是尚,只为求取功名、一举中第;世家大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以家族势力为根基进入仕途的机会,只得改变清谈玄学、专攻学问的“纯文化”生活模式,同诸士人一并踏入一纸程文定去留的科举浪潮。其二,从家族本身来看,由于科举取士在官吏选拔方式中占据主流地位,为官入仕又与家族命运休戚紧密相关,于是在家族内部衍生出两种出仕旨趣:一是以传承家族的实际利益;二是传承为官入仕的家学思想,这使得仕途知识的学习不可避免地朝着功名化的趋势发展前进。
(三)世艺家风:文辞技艺专业化
所谓专业化,是指在家族内部以“父兄之教”的形式,将文辞技艺付诸于代际成员,从而形成通文达艺的学理形态,使一个家族一代数人或多代数人均能专注于辞章之学或艺术追求,进而发展为家族职业的文化事象。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极度崇文的社会背景下,文辞技艺的家学延续,一方面能作为学术能力的补充,影响个人的仕宦成就与家族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在家族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同时,可以增强社会认同,进而转化为社会地位的有力支撑,实现由“文章学业继家声”到“名誉压群英”[15]的理想境界,形成兼具家学、理想抱负、社会声望在内的相互促进的文化传承体系。
依托于文辞技艺的家学形式,往往始自家族创始人或家族中某位具有较高艺术造诣的人物。例如,杜甫作为家族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先是师从祖父杜审言,承其诗体诗风;而后创新体式实现超越,将诗歌家学发扬光大;继而希冀于家族晚辈传承诗学,认为文章是进身的正途,教育后人“文章实致身”,[16](P63)他采用“觅句新知律”[16](P1202)的教育方式、营造“续儿诵文选”[16](P827)的教育氛围,对家族后代进行技艺培养和环境熏染,真正实现“诗是吾家事”[16](P577)的艺术自觉。因此,文辞技艺的家学所及,是家族精神的淬炼与彰显。正是基于共同的思想认知,孔子以一人之力开创“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6](P657)的家族经学、司马迁穷毕生精力开启“驰骋数千载,贯穿百家作”[17]的家族史学。
总体看来,道德元素核心化的家学,以彰善瘅恶的内在信仰孕育出众多德行家族;仕途知识功名化的家学,以“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追求培养出诸多学术家族;文辞技艺专业化的家学,以世传家业的职业理想打造出闻名的文艺家族。概言之,正是世德,世仕,世艺的三重维度构成了家学的三重意涵,使得家学传承异彩纷呈;也正是家学活动的有形开展,才成为无形家风彰显的外在凭借,从而有力推动家风的传承。
三、家训:传统家风的文字载体
家训以血缘天性的亲亲之情为依托,凝聚和传承道德精神,借助尊长权威实现道德精神的内化与实践,具有集规范性、针对性、原则性于一体的特点。家训是家风的文化符号,家风是家训的理想维度。可视可见的文字成为通往渐渍家风的理想路径。家训以其特有的文字载体实现自身的独特价值,文字本身的稳定性与家族文化的可选择性共同构成家训的特性:跨越时空的稳定性与随时代变化的灵活性。
(一)家训的稳定性:传承家风常道
文字载体赋予家训跨越时空的稳定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家文化中合理的精神内核。在传统家文化的家训传承与家风传颂过程中,一方面,家族内部各成员以家训为遵循,形成具有高度相似性和同构性的家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再建则予以传统家训信条中永恒价值者新的使命,穿透古今文化因子碰撞的迷雾,构成绵延不绝的纵向传承关系。
以家训作为家族内部的行为摹本为例。众多家族后代在塑造自身德行操守时,模仿父祖长辈中之贤良者,借助文字载体以继人之事续先辈之遗风遗德,这便是家训跨越时空的稳定性的第一种形态。明朝丘普的丘氏家族闻名于世,第三世核心成员丘普,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与职业能力为参照,培养子孙继承家族主业。丘普在长孙丘源幼年之时,发现其有着继承医学祖业的潜质,因此教导其“承吾世业,隐而为良医”[18](P60)。稚孙丘濬则幼承祖训,做出从儒的人生选择,曾在《可继堂记》中记述,虽然“不知先祖之言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厉自持,不敢失坠。”[18](P61)这种外在的训诫敦促化为内在的信仰载体,化为丘濬孜孜不倦追求济世的力量源泉,终成就这位“有明一代,文臣之宗”[19]明代理学名臣。
以家训中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为例。探究传统家训中的永恒价值,即挖掘穿越时空而延续的家训文化要素。对我国家训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纵使每个时期的家训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与重点,家训之间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不尽相同,但贯穿始终的道德主线和根本宗旨则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意蕴,这便是家训跨越时空的稳定性的第二种形态。文化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应该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民族之间的差别尚未消失之前,维护民族独立是至关重要的”。[20](P307)只有在科学真理的指导和立足中国国情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族主体意识进而实现辩证的综合创造,才能“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20](P306)随着家庭建设、家教建设、家风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重要作用的日益凸显,具有民族性意涵的家训文化要素,“存在的价值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作为一种社会亟须的能量而不断增强。”[21]
(二)家训的灵活性:焕发家风活力
家族文化的可选择性赋予家训随时代变化的灵活性,不断纳入新元素使家训与时俱进、长盛不衰。在社会背景更迭与家族选择差异的共同作用下,一方面,家族后辈对家训内涵加以再处理、再审视,使家风在具有同构性的同时,仍适应时代需要,保证家族繁荣;另一方面,由社会变革引起的治家观念和治家方式的更新,使家训内容随之演变,在永葆家训生命力的同时焕发家风活力。
在秉承某一家风信条的前提下,根据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迁、更迭与演变以及家族的动态发展,家族会不断调整和更新家训观念。颜氏家族历代子孙秉承祖风,“忠义为节”向来是颜氏子弟共同恪守传承的家风,但对实现“忠”却有着不同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选择。颜氏三十五代孙颜之仪犯颜进谏,隋文帝予以“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22]的赞誉。颜之推则认为“无多言,多言多败”。颜之推三经世变,身仕四朝,正因为深受时代浪潮更迭之苦,他才更能明白在历史洪流中保全家族整体运数的不易。因此,“稳定”胜于“煊赫”这一思想便成为颜之推安身立命的为官宗旨,并为后人定下“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11](P347)甘居中游的出仕原则。颜真卿对“忠义之节”有着新的理解。面对安禄山叛军之时首举义旗、直指宰相元载蒙蔽圣听、在生死关头视死如归,都表现出颜真卿没有囿于颜之推以大义为前提所提倡的“平和不争”的为官之道,而是以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文化精神诠释颜氏家族的忠义家风。
家训的灵活性还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家训侧重点不同。从隋唐至明清,社会从业观念嬗变与实践演进大体呈现出读书致仕——治生训诫——经世致用的特点,历代家训对此多有反映。“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乐徽之际”,[23](P250)自兴科举之后,读书致仕成为从寒门到贵胄全社会各家族的择业追求。宋元时期,政权的稳定统一与水陆交通的开拓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契机,以“治生”为主要内容的家训开始大量涌现。“士”与“治生”的绝对界限已经模糊,有人认为,读书入仕之人“尤应砥砺表率,效故人体天地育万物之志”,[23](P444)读书习儒并不是唯一的职业选择,那些曾经被轻视的职业被纳入可选择的范围,是社会择业观上的一大进步。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使绅商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商贾家训的繁荣成为择业观念转变的外显。这一时期的择业观变化有二:一是提倡学习杂艺及科学技术知识,二是官商一体、儒商结合的群体变化,《营生集》《士商要览》等家书的出现,体现了商贾家训成为中国传统家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训的稳定性是对时空范围内之恒价值的世代传承,灵活性是不局限于文字形式的现实生动体现与历经千年历史更迭对部分观念的再处理和再审视。需要指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从来没有尽善尽美的思想和制度,无论先辈所著家训文本如何完备,也难以实现全知全能。集成家训的最终旨趣是家风的传承与弘扬,进而发挥家庭建设在社会建构、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唯有将依托于家训文本中的哲思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充分挖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旧邦新命”。
四、结语
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家风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壤似乎已经消失殆尽,其存在与发展似乎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但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新时代如何正确看待和继承优秀传统家风,正确把握传统家风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家风的场域载体、活动载体和文字载体的三维探讨,有助于深刻理解传统家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将传统家风镶嵌于新时代新社会的崭新社会环境中,使其在保留合理文化内涵的同时,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