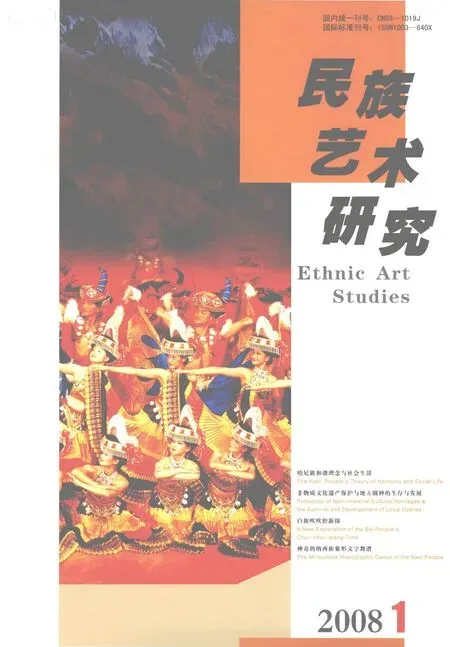仪式音乐研究
胡晓东,彭小峰
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关键词之一,“仪式音乐研究”尚属年轻,但广泛意义上的“仪式”及“仪式音乐”却有着极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自从人类基于对某种原始力量或信仰的崇拜而促发的一系列固定行为开始,仪式就已经诞生,而伴随这些固定行为而产生的一系列音声行为,则被视为仪式音乐的最早存在。学者们关注仪式及其音乐,是因为它反映了执仪者或仪式参与者内心深处的原发观念或思维模式,而这正是探究人类社会文化结构模式,尤其是原始结构模式不可绕开的重要维度。因此,追溯并考索“仪式音乐”的源流及其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厘清国内外学界“仪式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思其当下存在的问题,是全面认知民族音乐学学术史与思想史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进一步建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并最终建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一、仪式音乐研究及其发展历程
仪式音乐(Ritualmusic)是源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语境,在特定的仪式场域或仪式表演语境中生成,为渲染仪式气氛,对仪式参与者的身心施加相应影响,以达到特定的仪式文化功能的一种音声形态。国外关于仪式音乐的研究最早基于民族学或人类学者对仪式的研究。意大利学者加斯特(Theodor Gaster)认为,神话是对原始神的行为“叙事(narrate)”,而仪式又是此叙事的“扮演(enact)”。①Gaster,Theodor.MythandStory.Numen2.1954.Thespis:Ritual,Mythand Dramain the Ancient Near East.Reviededition.NewYork:Harper&Row.1961,p.207.显然,加斯特对于仪式音乐的认识受到了神话学的影响,认为仪式音乐是对神话的表演。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J.G.Frazer)认为,仪式是民间信仰的实体与核心结构,人们通过仪式营造气氛,并在仪式表演中创造各种音乐环境以获得心灵的慰藉。②[英]弗雷泽(J.G.Frazer):《金枝》,徐育新、张泽石、汪培基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弗雷泽看到了仪式音乐在表演语境中的功能性,认为仪式音乐在仪式表演中起到营造气氛,使人们获得心灵慰藉的功能。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认为,仪式就是一种“文化表演”,是对信仰的展示、实现和形象化。③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York:Basic Books.1973,p.113.加拿大仪式学家格兰姆斯(Grimes)以“仪式化”来泛称仪式活动,他将“仪式化”定义为:“活性的人所演绎的形式化体态行为。”④Ronald L.Grimes,Bgehinningsin Ritual Studies.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61-62.格兰姆斯的定义是将仪式音乐作为一种行为来阐释,他所提出的仪式是泛化的,并非特指宗教,可以看出学界对仪式范畴的认识愈发宽泛。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Bauman)把仪式“表演”看成一种“特定的、艺术的交流模式”,“是一种语境性(contexts)行为”,并传达着与语境相关的意义。⑤[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8页。鲍曼将仪式音乐看作是一种交流模式,并认为仪式音乐行为跟仪式信仰(观念)、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文化身份有着很深的联系。从以上各位学者对仪式音乐的定义来看,他们均是从自己的研究角度以及学科属性出发,围绕仪式音乐的象征、功能、行为、表演等内涵特点进行定义。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仪式音乐的认识是受到了不同时期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如弗雷泽是早期人类学家的代表,所以他对仪式音乐的定义带有明显的早期人类学的思维,格尔兹对仪式音乐的认识显然是受到了阐释人类学核心观念的影响。格兰姆斯的定义受到“反神学”思潮的影响。
仪式音乐研究是仪式学与民族音乐学两个学科交叉影响下发展而来的一个研究领域,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宗教学术会中举行的首届“仪式研讨会”中提出。目前,学界对于仪式音乐概念的界定并未达成一致,原因就在于“局内”与“局外”视角的差异。曹本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将仪式音乐称为“音声”,他认为“音声”指的是“一切仪式化行为中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对局内人有特定意义的近音乐和远音乐的声音,包括一般意义中的‘音乐’”。⑥曹本冶:《“声/声音”“音声”“音乐”“仪式中音声”:重访“仪式中音声”的研究》,《音乐艺术》2017年第2期,第11页。曹本冶的定义兼顾了“局内”与“局外”两个不同的视角,拓宽了仪式音乐研究的范围。但是,我们感到曹氏对于仪式音乐的定义似乎太过宽泛,比如乐器不小心掉落的声音,是否算是仪式音乐呢?为此,薛艺兵将仪式音乐限定在“艺术效应”“社会价值”“文化归属”这三大特性之内。⑦薛艺兵:《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33页。薛氏的定义是从仪式音乐的功效出发,将仪式音乐框定在对仪式产生作用的声音这一范围。但是,薛氏的定义涉及到了仪式音乐作为传统音乐所具有的共性的一面,而未顾及其因与宗教文化相关而具有的独特个性。⑧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409页。因此,杨民康从仪式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含义和同一性含义两个方面来对仪式音乐进行界定,认为仪式音乐信仰体系是仪式音乐区别于其他传统音乐的重要因素,仪式行为、音乐表演以及音乐艺术形式是与其他传统音乐相一致的要素,这些要素加起来的总和才是仪式音乐的概念。杨氏对仪式音乐的定义是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进行的,既关注到了带有信仰体系的仪式音乐,也关注了不带信仰体系的泛化的仪式音乐。
对于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需要将其置于历时的语境中,探寻不同时期的仪式音乐研究的特征,对仪式音乐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仪式音乐研究的历时性内涵必将是一个开放、动态、不断被填充的系统。
从整体上看,国内学界关于仪式音乐研究大致可分为早期的音乐资料集成、中期的音乐形态分析以及后期的民族音乐学探究三个时期,从中可以看到仪式音乐研究由单纯的形态研究到文化探讨的发展历程。
(一)早期:音乐资料集成期
早期的仪式音乐研究主要是对佛教、道教、基督教音乐的零星记录,其做法大多是对仪式音乐进行记谱。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未有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他们只是把仪式音乐当作一般的民间音乐来记录。在这一时期,杨荫浏先生对宗教仪式音乐的记录相对较为全面。他记录的仪式音乐主要有道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家祭孔四大类,出版了《锣鼓谱》《苏南十番鼓》《十番锣鼓》等成果。除了宗教仪式音乐的记录研究以外,他还率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前往湖南收集民间音乐,最终出版了《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在报告的附录中就有对孔府丁祭音乐的记录研究。除了杨荫浏先生以外,刘天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对佛教仪式音乐进行了搜集整理,著有《佛曲集》。20世纪40年代末,原晋绥解放区文联音乐部的亚欣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开始进行初步的收集工作,此次搜集整理涉及五台山青庙、黄庙及“八大套”等传统佛教仪式音乐的记谱。
(二)中期:音乐形态分析期
音乐形态分析期是学界对仪式音乐进行广泛的整理,并辅以音乐形态分析。这一时期的收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官方发起,分省、市、区进行民间音乐的全面普查,并编撰了全国性的“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全国的道教、佛教等仪式音乐就被大规模地收入了“十大集成”之中。除了“十大集成”中对仪式音乐的广泛搜集整理外,很多学者也对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寺庙、道观的仪式音乐进行微观深入的研究。他们不仅对仪式音乐进行记谱整理,还对记录的乐谱进行调式、音阶、曲体结构、旋法分析。对仪式中的乐队、乐器、乐谱、曲牌进行阐释,对仪式的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如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杨久盛《辽宁千山佛教音乐》、甘绍成《青城山道教音乐研究》等著作。这一时期,学者的眼光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单个点的分析,他们将两个点甚至多个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如张鸿懿《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研究》、甘绍成《青城山道教音乐与外地道教音乐的关系》等。
(三)后期:民族音乐学探究期
民族音乐学探究期是受西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吸收仪式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符号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将仪式音声置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探究仪式音声与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学界将目光投向民间仪式音乐,如巫、傩、节庆仪式等,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及其博士团队(薛艺兵、张振涛、杨民康、臧艺兵、刘红、杨红等)的仪式音乐研究推动了仪式音乐民族音乐学探究期的形成。曹本冶提出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的三元理论结构模式,由此形成了仪式音乐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和他的博士团队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实践研究,产生了系列成果(《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西南、西北、华东、华南等地域卷)。学界还吸收了宗教学、仪式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符号学的理论方法,产生了“现象文本”和“生产文本” “深——表”结构分析、组合与聚合、阈限期等研究方法。
二、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
20世纪末,仪式音乐研究开启了“中国化”进程。其中,较为有影响力、规模较大的是曹本冶及其学术团队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从1993年开始,曹本冶及其团队对国内部分地区的代表性仪式音乐作了调查研究,产生了《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华东卷、东北卷、西北卷)等系列成果。此后,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在仪式音乐研究的领域继续探索,他们结合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进行实践研究,推动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进程,对构建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以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人类学与仪式音乐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借助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基本情况,提出了“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三元理论结构模式,以及“近—远”“定—活”“内—外”三个基本性的两极变量的思维方法。我们看到,曹氏的仪式音乐研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模式的影响,他结合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特点对梅式的研究模式进行改造,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中国化”。同时,曹本冶及其学术团队成员以及其他学者以梅里亚姆的“三重模式”以及曹氏的“三元理论结构模式”“三个两极变量思维”为方法基础,进行实践研究,产生了系列学术成果,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曹本冶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与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将道教仪式音乐分为核心、中间、表面三个层次,对其固定因素与可变音素进行剖析,采用“近—远”“定—活”“内—外”的思维方法,是对他所提出的方法论的实践。周凯模的西南彝族仪式音声研究,在“思想—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结合西南彝族仪式音乐的案例,提出了“道—行”合一的研究理念。周氏还将“道”分为了“道型”“道性”“道义”三类,细化了曹氏的研究模式。但是,他对方法论的反思主要来源于对彝族仪式音乐的研究,这样的方法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不论是梅式的“三重模式”,还是曹氏的“三元理论结构模式”都没有关注到仪式音乐的功能性,所以,杨晓在曹氏理论的基础上,将研究延伸至仪式音声的功能层面,在其南侗正月祭萨仪式研究中,探讨了仪式音声如何构建天人观念和社群结构。
(二)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
在表演理论研究的观念影响下,形成了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的新范式。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旨在揭示并阐释仪式表演过程中,执仪者脑海中的音乐文化观念模式如何经由表演转化为一系列音声景观与符号表征的过程。如杨民康《海南黎族道公祭祀音乐表演民族志——以杞黎“招财”仪式为案例》,探究黎族杞黎支系的传统道公祭祀“招财”仪式音乐文化的“表层与深层结构”及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萧梅的《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认为“仪式内涵之所以能够通过音声‘进行可感知的系统表述’,是因为其‘规律性和可预知方式中的重复行为’在展演结构和音声属性上形成了特有的制度,并被其文化群体所感知和共享。”①萧梅:《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第32页。萧氏所说的“制度性音声属性”也可以看作是仪式表演中的“文化模式”。胡晓东《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通过观察并分析瑜伽焰口仪式表演中所呈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象征符号和符号表征,分析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是在佛教“三密合一”、阈限等观念下的仪式戏剧表演。②胡晓东:《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3—112页。此外,路菊芳的《彝族诺苏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体系的衍变关系》(2021年)、李纬霖《跨界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中、老、缅、泰傣仂原始宗教仪式表演中的赞哈演唱为例》(2019年)皆是此类成果。如今,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将“上下文情景网络、历时研究、多点动态、跨地域”③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第2—3页。等理念加入其中,丰富了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研究理论。这些反思,都是基于“中国化”实践中的问题所提出的,故推动了仪式音乐研究方法论的“中国化”进程。
(三)语言学、符号学与仪式音乐研究
受符号学、语言学的研究观念影响,国内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仪式音乐分析方法。如杨民康的《论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深—表结构”思维与分析方法》一文,采用结构语言学的“深—表结构”分析,探究出仪式音乐民族志的“深—表”分析方法。可以看出,杨氏提出的“深—表结构”分析法,是对曹本冶“两极”分析思维的进一步拓展。他的《傣族佛教安居节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特征》一文,借鉴符号学中的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角度,分析了傣族佛教安居节仪式及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特征。仪式音乐的互文性研究也是受到符号学、语言学的启发,对仪式音乐的“现象文本”和“生产文本”进行分析,如赵书峰《湘中民间仪式音声的“在地化”与互文性研究》,探究湘中民间仪式音乐中互文性与“在地化”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关注了互文性和“在地化”现象的文化背景(移民),进一步拓宽了仪式音乐研究的视野,弥补以往仪式音乐研究对语境的忽视,是将国外理论“中国化”的体现。
(四)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
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就是探究仪式音乐作为感知个体认同的媒介和途径,以及作为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是如何对族群认同的形成与维护起到作用。如胡晓东关注云南少数民族杂居区的仪式音乐认同,根据少数民族杂居区仪式音乐认同功能的多元复杂性,将音乐认同分为族群、区域以及国家三个层面。①胡晓东:《族群·区域·国家——彝、哈、傣、苗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三重文化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6期,第26—33页。张林的《新宾满族节日音乐文化建构的认同差序特征》(2020年)也属于仪式音乐认同的分层研究。赵书峰在老挝优勉瑶婚俗仪式音乐研究中,将音乐认同与跨界族群结合,发现老挝优勉瑶在瑶族语言与神圣性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多强调族群身份的差异性诉求,而在世俗性婚俗音乐方面彰显其对老挝主流文化的主观认同,形成仪式音乐身份的二维并置特征。②赵书峰:《跨界族群与音乐认同——老挝优勉瑶婚俗仪式音乐的身份问题研究》,《中国音乐》2021年第3期,第71—79页。魏琳琳在蒙汉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中,探究蒙古族人如何通过节庆仪式音乐表演,表达一种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甚至一种“思乡情结”,建构一种民族音乐的“想象的共同体”。③魏琳琳:《蒙汉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地方性与族群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44页。可以看到,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大多是对正在被发明和构建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进行探究,与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实际情况进行结合,实现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
(五)身体理论与仪式音乐研究
学界对仪式音乐中的身体的研究是对西方学术话语中的“缘身性”理论的借鉴,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征的把握,以及对曹本冶“思想—行为”互向研究模式的反思后所提出的。以往学界在仪式音乐研究中关注仪式如何表达观念,忽视了身体的能动性,所以,萧梅在曹本冶“思想—行为”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提出缘身实践既是思想(信仰)的外化,也是思想的原动力,是填补鸿沟的中介。④曹本冶主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页。她在广西魔仪的研究中,对魔的身体为何成为神的容器和执仪的法器以及身体技术的能动性进行探究,并认为缘身体验属于曹本冶提出的仪式音声中听不见的声音的范畴。⑤曹本冶主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页。在本土实践过程中,萧梅发现了身体对于中国传统仪式音乐乃至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性,所以她在方法论上借鉴了“缘身性”理论,进一步对曹本冶的“思想—行为”互向模式进行了发展,对曹氏提出的“听不见的声音”的探索,促进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进程。
(六)仪式学与仪式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界借鉴仪式学中阈限期的研究范式对仪式过程进行阐释。如胡晓东《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域中的梅山文化研究——以湖南梅山文化区仪式音乐为例》,将整场还家愿仪式过程分为阈限前期、阈限期和阈限后期三个阶段。在阈限前期与后期,仪式结构的内容较为松散自由,用乐方式与音乐形态较为多变,而处于阈限期的仪式结构及内容较严格稳定。⑥胡晓东:《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域中的梅山文化研究——以湖南梅山文化区仪式音乐为例》,《中国音乐》2019年第4期,第19页。以往的仪式音乐研究注重对仪式文本的“两极”进行探究,而仪式化过程较少关注,也就是说以往的仪式音乐研究更重结果,至于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变化过程少有提及。所以,仪式音乐的阈限期研究正是基于本土研究的反思,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音乐与迷幻与阈限期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萧梅《音乐与迷幻》一文,探讨仪式中音乐对迷幻的产生,以及对“人—神”之间过渡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仪式结构的关注。
三、仪式音乐研究对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
仪式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与其他种类的传统音乐在仪式行为、音乐表演、艺术形态等方面有着同一性,而且它与其他传统音乐类型结成“核心—中介—外围”环链,贯穿了传统音乐由内向外展示的表演活动过程。①杨民康:《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第22页。仪式音乐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学界结合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民俗学、仪式学等理论方法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进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进程,推动了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以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学界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特点进行总结,对外来的方法论进行改造,对改造过的方法论进行实践,在仪式音乐研究的观念、学统、方法层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次,仪式音乐研究对中国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体系的“塔层结构”②杨民康:《论音乐民族志理论范式的塔层结构及其应用特征》,《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125—137页。构建有着重要作用。仪式音乐研究不仅仅是民族音乐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它还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集大成者。它通过对国外理论方法的吸收、融合、发展,形成了由观念层、学统层以及方法层构成的方法论“塔层结构”。在研究观念层,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主要源于梅里亚姆的“文化中的音乐”以及“音乐中的文化”的学术主张,形成“思想-行为”互动研究观念。仪式学中关注仪式结构化过程的理念。民俗学中关注“表演”的理念。除此之外,符号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都影响着仪式音乐的研究观念。在学统层方面,曹本冶提出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三元理论结构模式”以及“两极变量的思维方法。”受语言学影响,产生了“深-表结构”思维与分析方法。借鉴符号学中的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角度,分析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特征。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模式”与“模式变体”分析法。除此之外,互文性、文化认同、阈限期等研究理论方法均在仪式音乐研究中得以运用。在方法层面,中国学者总结出了“四度三音列”“音腔”“板式变奏”等分析法。故仪式音乐研究形成了方法论的观念层、学统层与方法层“塔层结构”,构筑了中国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体系,推动了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四、仪式音乐研究的问题与出路
(一)仪式音乐研究的问题
在既有的仪式音乐研究中,国内学者大多借鉴外国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未归纳总结本土仪式音乐特征,导致了诸多问题,主要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两个方面。
1.认识论方面
仪式音乐的认识论是指通过仪式来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起初学界将仪式音乐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去探究它的律、调、谱、器、曲等形态,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学界仅仅看到的是仪式音乐的艺术性。后来,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人们试图通过仪式音乐来看个人信仰、社会与历史。仪式音乐逐渐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窗口,逐渐以一种新的视角来透过仪式看人的宇宙观与社会价值观。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认识大多处于一个共时的层面,历时动态层面几乎未有涉及。仪式音乐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共时的信仰体系、社会价值观,而且还反映一个族群的历史发展,反映一种动态的社会变迁。除了历时动态以外,共时动态也是仪式音乐一大特点。总之,透过仪式音乐,我们不仅要看到共时的宇宙观、价值观,还要通过仪式音乐来看到历时和共时层面多点动态的族群文化变迁,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的。
2.方法论方面
20世纪初,仪式音乐研究迎来了新的局面。自曹本冶提出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三元理论结构模式,以及三个基本性的“两极变量的思维方法”以来,学界就开始结合多学科视角,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仪式音乐研究结合。虽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拓宽了仪式音乐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些理论的运用仍处于探索期,很多理论直接用于仪式音乐研究,并未经过一定的改造。所以,方法论层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法论的“中国化”还有待加强。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语境的缺失。不论是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模式,还是曹本冶提出的“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三元理论结构模式都没有语境化,故使用曹氏的理论进行实践研究的一些成果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仪式音乐研究成果大多是微观研究方法,很少有宏观性的研究。对于仪式音乐,族群内部的深入研究是一个角度,那么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仪式音乐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在方法论上缺乏关系性、动态性视野。
(二)仪式音乐研究的出路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仪式音乐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出路在于借力“新文科”背景,对仪式音乐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方法等方面进行重新审视,构建起新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体系,从而推动仪式音乐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新文科”理念强调学科交叉,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合;强调切实解决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强调中西平等对话,文化尊严与自觉、自信。这样的理念于仪式音乐研究大有裨益。
1.进一步厘清相关学术概念
目前,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笔者认为,仪式音乐研究概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无标准答案可言,这也是“新文科”理念所提倡的开放性的体现。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学界对仪式音乐研究认识的更加深入,仪式音乐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等等都在随时代而变化,所以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概念去对仪式音乐进行界定。我们看到,早期的仪式音乐研究主要是针对佛教、道教、基督教的仪式音乐进行研究,十分强调仪式的信仰体系,而现在,仪式音乐的研究扩展到了巫、傩以及节庆仪式,信仰体系在这类仪式中并不明显。所以,从仪式音乐研究对象的变化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学界仪式音乐认识的变化。故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是在不断构建的,需要我们从一个动态的视角去把握。
2.采用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对于当前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是“以仪式化音乐表演为对象和路径,借以观察和揭示人们在其音乐表演活动中如何经由和利用仪式表演行为,将观念性音乐文化模式转化为音声表象的活动过程和结局,并辅以必要的描述性、规律性、阐释性分析和文化反思。”①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第11页。它关注仪式的活态表演,注重表演中的交流、展示或展演等社会性、文化性的一面。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方法论正好可以解决以往的仪式音乐研究方法的诸多不足之处。首先,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弥补了以往研究的去语境化的问题。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不仅在“经度”上探讨仪式音乐的表演行为如何与观念性文本和口传音声文本之间发生怎样的“承接”和“反馈”的横向联系,而且它还结合历史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将仪式音乐置于历时的语境之中进行研究,形成“共时+历时”的研究理念。其次,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强调多点、动态性研究,弥补了以往仪式音乐研究单点、静态研究的不足。总之,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既继承了以往仪式音乐民族志的研究理论方法,又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了反思,这些新的反思,正是解决目前仪式音乐研究问题的对策,也是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体现。
结 语
仪式音乐研究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更是一种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借鉴了西方人类学、语言学、仪式学等学科理论,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进行实践研究,实现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认识论、方法论上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新文科”背景的引导下,重新审视仪式音乐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方法等,同时从多学科视角切实解决当前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构建新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体系。另,笔者认为,我们还可采用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关注活态的仪式表演,探究仪式表演中的交流、展演等社会性、文化性的一面。结合历史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将其置于历时的语境中,形成“共时+历时”的研究观念,促进仪式音乐的多点、动态性研究。
仪式音乐研究在观念层、学统层、方法层方面正不断壮大,汇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诸多方法论,在“新文科”核心理念的引导下,未来的仪式音乐研究一定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在历时与共时之间,静态与动态之间,定点与多点之间,对仪式音乐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这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乃至对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推动力。
——读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