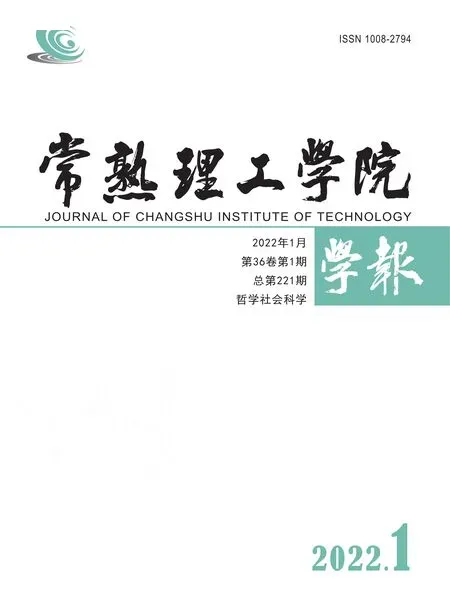民间宝卷婚变主题初探
纪亚兰,王定勇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一、婚变主题溯源
古代社会,人们重视婚姻关系,以婚姻为“人伦之本”,与“天地之道”相契合。[1]13而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谓之婚变。实际上,“婚变”不仅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的破裂,还包括未婚男女违背口头婚约或盟誓的情况。从历史角度追溯,稳定的婚姻结构最早建立于周朝。自周始,官方参与到适婚男女的婚嫁大事中来,政府设置专门管理男婚女嫁的官员,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了起来。在此之前,夫妻之间解除婚姻关系较为自由,遵循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的原则。[2]99战国《仪礼·丧服》[3]487中以“七出”之条规定了休妻条件,同时主张了丈夫在婚变中的主导权利。在以夫权制为主导的婚姻下,“婚变”多以丈夫施行的“休妻”作为标志,因此遮蔽了妻子逼休或者要求和离的情况。除法律规定的出妻条例外,真实案例中亦有“妻不肯安心过活”,或丈夫另有新欢、无故婚变的情况。但无论是丈夫另结新欢,还是妻子不安于室,写休书的权利只有丈夫拥有。
事实上,“休妻”与“弃夫”故事从先秦时期便有记载,自《诗经》中妇人哀怨悲吟“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4]90后,婚变的哀怨旋律便在文学作品中长盛不衰。《汉书》有买臣妻羞于买臣“讴歌道中”行为请求离去的记载。与之相似的还有东晋时期的王欢,他的妻子因丈夫贫困不事生计而希望休离。汉魏六朝乐府《白头吟》《有所思》等作品更是细腻描写了婚变中的女子百转柔肠、郁结于心的情感。自唐科举取士以来,中下层士子获得进身之阶,一旦金榜题名,便彻底改变命运。于是,书生始乱终弃和发迹重娶的社会问题成为传奇小说的热门题材,映现出当时社会的婚姻问题。婚变题材的创作于宋代文学中尤为突出,弃妇诗在这一主题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代之以南戏、宋杂剧、院本等通俗文学。说话、鼓词、稗官野史、轶文传说更是以其通俗性在民间影响甚大。宋代有《王宗道休妻》《李勉负心》《王魁三乡题》等典型的负心婚变剧。明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收录的剧目中有六分之一是负心婚变剧。元代文学中婚变主题尤为突出,在现存的三十余部表现婚恋题材的元杂剧中,有近三分之一以婚变为主题的作品。[5]南戏受众以民众为主,婚姻题材故事更是具有绝对优势。钱南扬在《戏文概论》中总结:“在已有的二百多个南戏剧目中,以婚姻为题材的约占三分之一以上。”[6]111-120至明清两代,通俗文学进入大发展时期,婚变主题在各类文学中仍处于突出地位。在以百姓为宣讲对象的宝卷作品中,婚恋题材同样占比不小。“婚变”对稳固的传统婚姻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人们都期待负心变节者遭受严重惩罚,因而“婚变”故事成为民间教化的重要素材。因此,当婚变主题故事进入宝卷后,展现出来的就不再是仅供消遣娱乐的儿女情长,而是极具宣教意味的百姓人生,其表现出来的文学性虽不如小说、话本、戏曲浓厚,但对当时的婚姻观念的反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二、宝卷中婚变故事的类型
目前学界对宝卷中婚变主题的探索未有整体的研究成果,但针对具体宝卷文本已有不少分析和探讨。《白马宝卷》中,熊子贵因不堪妻命强于自己愤而休妻。妻子未犯七出之条而无辜被休,穷命丈夫无故休掉有福气的妻子,这个故事非常典型。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将该休妻故事归纳在841A “乞丐不知有黄金”型婚变故事中。[7]249伊藤清司将婚变故事称为天婚故事,并将其分为三类:“破落型的初婚A型”“孝养型的初婚B型”“再婚型”。[8]35-39江帆先生又将婚变故事细分为三种类型:“贫妻型”“丑妻型”“灶神来历型”。[9]25-28依据婚变时婚姻关系的状态,我们可将宝卷中的婚变故事分为未婚情况下的悔婚型故事和已婚情况下的休妻型故事。
悔婚型宝卷又可分为男方主动悔婚和女方主动悔婚。男方悔婚多以男主角打破婚约为主。《兰香阁宝卷》中落魄书生得美貌女子庄珍容资助考中进士,后贪图荣华富贵,改娶大财主丁进士之女为妻。[10]91-92女方悔婚多为女主角的家长回绝婚约(多以父命为主),女子多表现出忠贞不二的个性。《百花台宝卷》中,莫桂将女儿月贞许配给扬州李文俊,后李文俊父母双亡,家道中落,李文俊投靠莫家,莫桂便起赖婚之意,使李文俊在莫家做仆,百般凌辱。月贞得知此事,资助李文俊逃出莫家,上京赴考高中,二人终成眷属。[10]10悔婚型故事中,悔婚多发生于男女双方家庭地位和财产状况产生差距的情况下,一般是在门当户对之时定下婚约,一旦一方门户败落,便出现悔婚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宝卷中悔婚型故事虽多以团圆结局,但故事中的男女在应对悔婚时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使故事能够以团圆收束,男主角悔婚后多因外部压力或舆论而悔悟,与女方重修旧好;女方悔婚,多以男方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后再续姻缘作结。若男方犯下毁约的过错,只需悔悟并重订婚约便可躲避舆论谴责;至于女方悔婚所承担的后果,却往往是悔婚之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可见当时的婚姻契约对男女双方的不平等。
休妻型故事宝卷不仅包含夫休妻,亦包括妻休夫类型。以男子主导的夫休妻型故事又有形形色色的休妻情状,根据动因的不同可将休妻分成主动休妻和被动休妻。主动休妻型故事除较少的妻子犯七出之条的情况外,多是男子贪慕权势富贵而舍弃糟糠之妻。《绣红灯宝卷》《陈世美宝卷》最为典型,丈夫攀权之后厌弃妻子,抛下旧妻,另娶新人。这类故事皆因男方品性问题而休妻。此外更多的是外界压力导致男方休妻,如《新出绘图金枝宝卷》《佛说王有道休妻宝卷》《张德和休妻宝卷》等,皆因丈夫误会妻子与人有染而休妻,但夫妻二人的感情未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因此,宝卷中夫休妻型故事亦可从二人情感的破裂程度对其进行划分。从本质来说,丈夫因权势富贵舍弃糟糠之妻,夫妻二人情感破裂,即便后来的团圆结局亦无法掩盖丈夫变心变节的事实;而因外力干扰导致的休妻,在一定程度下反而成为夫妻二人情感的考验,一纸休书成为见证二人情感坚贞的情书。
若说被逼休妻是迫于无奈的话,丈夫被妻子逼休则是对男权主导下的婚姻观念的挑战。在当时的社会公序良俗规范下,这类妇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像抛弃旧妻、另娶他人的男子一样得到翻案的机会。因此,《朱买臣宝卷》与《紫荆宝卷》中逼离的妇人多被塑造成无赖泼妇的形象。宝卷宣讲的夫妻关系仍以家庭和睦不离弃为主题,故事中的女性一旦出现动摇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的行为,必然会被贬低甚而污名化。《东厨宝卷》中,张大刚、范三郎、范婆最终都得到玉帝的封赠,只有丁香不曾受封,理由就是丁香“一女嫁了二夫君”;后经丁香苦苦哀求,才封了个“墒沟姑娘”的名号。“墒沟”意为临时开挖的田间排水的浅沟,从此甚为牵强的名号亦可看出丁香一女二嫁所受的嘲讽和贬斥。再如《朱买臣宝卷》,“买臣休妻”故事在此前流变过程中多塑造买臣妻良善的形象,但在宝卷中,买臣妻再嫁后不仅克夫,而且好吃懒做,拖垮再嫁夫,在买臣衣锦还乡后又厚颜求和而被惩治,最终无颜苟活,投河自尽,尸体亦无人问领。宝卷故事对逼休的妇人不仅在品性上进行打击,写她们爱财、好吃懒做、泼皮无赖,不知廉耻;而且从命理上否定这类妇人,用“丧门星”“孤煞星”等词以达贬低之意。
三、婚变主题的程式化结构
分析宝卷中的婚变主题故事,可总结出一套程式化的结构。根据已划分的婚变故事类型可总结出以下的结构模式。悔婚型宝卷结构:嫌贫爱富悔婚——女子守节——男子发迹/悔悟——重订婚姻;休妻型宝卷的结构为:妻子不贤/贫贱/丑陋/误会休妻——受天谴/误会解除——丈夫寻妻——再婚(夫妻团圆),男子美人在怀,名利双收。这些故事数量众多,内容五花八门,但情节结构却比较简单,且多有重复。这些重复的情节不仅是改编自其他题材故事的结果,亦具有融入了民间故事想象痕迹的共性。如因故事曲折性的需要,宝卷所展现的婚姻变故中,男女双方必然需要有所行动方能挽回婚姻。就女方而言,在交通、通讯都不便捷的古代,女子欲寻找分离的丈夫必要踏出家门,而女子出门不便,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女扮男装就成为宝卷中常用的克服困境的叙事手段。《苦节图宝卷》中,秀才张彦受婶婶钱氏挑拨,误会妻子白玉楼与人通奸而休妻,并将其赶出家门。白玉楼被钱氏卖给江夏,后白玉楼女扮男装逃命脱险。张彦发现误会妻子后离家寻妻,途中被昆山县江边刘太翁的女儿蕊莲看中,与之拜了天地。白玉楼逃亡途中化名张彦,女扮男装接住了驸马之女的招亲绣球后悄悄逃跑,途中遭一对夫妻打劫,被剿匪的金驸马救下并认了干女儿带回驸马府。张彦虽与蕊莲结婚,但日夜思念白玉楼,趁夜逃走。蕊莲女扮男装改名张彦寻找夫君,寻夫途中助金驸马逼降贼寇。蕊莲被驸马相中,招为女婿并被点为武状元。白玉楼以自身遭遇绣成一幅苦节图张挂于驸马府,被中了状元的张彦看见,方知白玉楼在此。皇帝知其间屈情,做主将蕊莲、白玉楼、驸马女儿秀云许给张彦为妻。钱氏后悔不已,撞地而死。至此,张彦与白玉楼、蕊莲、秀云拜堂成亲,天子敕赐“苦节图志仁勇”金字牌匾,一家团圆。[11]685-707故事安排了两位女子变装寻夫的情节,并在寻夫途中屡得机缘,变装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此外,还有男变女装。《玉连环宝卷》中,男主角的假冒者被其岳父谋杀,男主角为了阻止女主角改嫁,着女装混入应徽府,成为女主角的丫鬟,直待女主角出嫁前欲自尽才自行披露身份。[12]5785-5887
宝卷婚变主题程式化的结构在纷繁复杂的人物、背景下几乎保持了同一性。其与才子佳人型故事程式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更多源于宝卷宣讲的特点。宝卷所阐述的是“善行”,在家庭生活方面总结起来就是“家庭和睦”,它是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世代相传并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宝卷的教化性,造就了其创作形式与故事结构的固定的模式。[13]123-131在娱乐功能上,其目的在于吸引观众,同时亦在重复不变地反映当时社会对婚恋关系的态度以及对圆满结局的憧憬,更是民众对婚姻变故进行挽救的体现。
四、宝卷与戏曲婚变主题的异同
宝卷中的许多故事与戏曲所演故事重合甚多,甚至有些故事便是从戏曲演化、改编而来的。现存“婚变”题材的戏曲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如《琵琶记》《御碑亭》《芦花记》《王员外休妻》等戏曲故事皆被跨文体重新演绎。这些故事虽然在人物、情节上一脉相承,但由于所载文体不同,相同的故事在宝卷和戏曲中亦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首先,题材内容上的差异。宝卷通常集中笔墨于关键情节的走向,故事发生的场景变化颇多且复杂;戏曲则更加注重对某一场景环境的渲染,文学气息较为浓厚,情节更为细腻。如《朱买臣宝卷》中,从朱买臣被逼休妻、故妻再婚至买臣发达回乡、故妻悔恨而死,情节的发展是宝卷宣讲的重点,并无其他枝蔓。而《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则照顾到故事发展的细枝末节,包括买臣妻如何埋怨买臣一事无成,如何逼休,买臣如何进京赴考,如何高中,都一一顾及。
其次,人物形象上的差异。宝卷宣讲的人物形象更加扁平化,正反两派人物性格单一,符合故事角色性的发展,不做多重的性格分析。戏曲则有意识地塑造多面化的人物形象。以“朱买臣休妻”为例,戏曲中的买臣妻不是贪财懒惰之人,她深爱丈夫,不愿与丈夫分离,却希望丈夫能登科中举,因而不得不用激将法逼迫丈夫上进,戏曲中买臣妻的心理是矛盾冲突的;而宝卷中的买臣妻则是嫌贫爱富的恶妇形象,她不仅渴望富贵,而且凶悍刁蛮、好吃懒做,与戏曲中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同一婚变主题在宝卷与戏曲中发生变化,主要源于戏曲与宝卷对生活的不同表现,因此导致其主旨与题材内容、人物形象的差异性。虽然戏曲和宝卷皆以满足社会百姓的消遣娱乐为主,但戏曲主要传达的是对美满的男女情爱的向往,期盼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戏中追求的婚姻爱情美满是让每一对痴男怨女都能终成眷属,因而故事情节都围绕男女主角展开,痴男怨女亦仅此一对,所有笔墨皆为这一对男女服务。男女主角重修旧好、恶人们得到惩治便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团圆结局,故而戏曲中的主角们一定是正面角色,即便婚姻中有短暂变故,最终仍以浪漫团圆收束,其对民众婚姻观念的影响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对比戏曲,宝卷本源于寺院俗讲,讲唱内容以佛经故事和劝世文为主,目的是宣讲佛教教义、劝人积德行善,具有强烈的教化民众的色彩。即使清代中后期民间故事进入宝卷,使得宝卷故事平民化,其本身仍保留了劝世的特性,开卷偈和卷终颂词都保留了宝卷的劝善仪式特征。因宗教对下层民众有强大的震慑力,一般民众对于具有宗教性质的宣讲更加虔诚,他们在听宣卷的过程中,在享受故事的意趣的同时亦接受了教育。[14]95-100因此,宝卷即以第三视角讲述婚变故事,将孰是孰非作为宣讲重点,致力于让故事中有情的得偿所愿,成为眷属;有义的加官晋爵,流芳百世;作恶的遗臭万年,恶有恶报。由此可见因果观念对当时民众婚姻态度的深刻影响。
宝卷中的婚变主题是婚姻爱情主题下的分支,但体现在宝卷中几乎就以婚变故事为主体了。“宝卷宣讲的是伦理上的夫妻二人的团圆,这是一种偏向功利性的团圆结局。故而男女方的重修旧好是有现实的条件支撑下的圆满,是建立在利益或者舆论上的婚姻承诺。”[15]160在双方未完成婚姻之前,男女双方都需经历考验,使得男方功成名就,提高社会地位,成为一个好丈夫;而女方则要坚贞不渝,从一而终,忍耐刻苦,成为一位好妻子。如此,宝卷婚变主题渲染的便不再是才子佳人感天动地的爱情,而是符合伦理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整体而言,宝卷本身的教化性质,使得进入宝卷的婚变故事发生了质的改变,即注重教化,不再强调爱情的浪漫与美好,体现了从社会、伦理、家庭的角度强调因果报应以及夫妻双方对婚姻的忠诚、对道德操守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