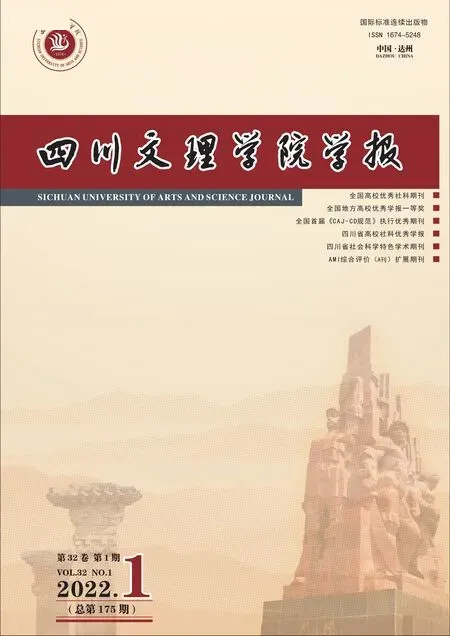石黑一雄小说的不可靠叙述
——以《长日将尽》《远山淡影》为例
胡显茗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1331)
石黑一雄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这样说到:“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如此看来,他的回忆是为了“解构回忆”。在他的作品《远山淡影》《长日将尽》中,这种自我欺骗式的第一人称回忆,呈现为典型的“石黑一雄式”的不可靠叙述策略。不过,国内学者对此策略的讨论,由于对不可靠叙述理论本身理解的偏狭,多显不恰切。
赵毅衡先生认为,不可靠叙述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一致,包括“全局不可靠”和“局部不可靠”。前者指文本叙述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可靠的地方,后指个别词句、个别段落、文本个别部分表现出“局部不可靠”,这样,叙述者的叙述就可能一会儿可靠,一会儿不可靠。[1]可以确定的是,石黑一雄不少小说的“不可靠叙述”,并没有延伸到整个文本中,只是在整体可靠的叙述中偶尔有部分的语句、文段等不可靠,即局部不可靠。下文就来分析这些局部不可靠叙述的具体表现及其功能。
一、碎片式的模糊回忆
小说《长日将近》主要是以管家史蒂文斯对亲情、爱情及事业的回忆构成。三十几年的经历,短短六天旅行中回忆,他的叙述并不完整,常常通过一些位于当下时间点的事物、事件断断续续地引发出来。先看史蒂文斯关于他父亲的叙述。他们俩都是管家,他也曾将父亲视为“伟大管家”学习,但年老的父亲来达林顿府工作的经历却是借肯顿小姐的信说出来。“如果这回忆令人痛苦,敬请谅解。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我们俩一起望见令尊在凉亭前来回地蹀躞的情景,他低头看着地上,就仿佛一心想找回他失落在那里的某样珍宝。”[2]64这回忆让他痛苦是因为,在这凉亭附近,他父亲在服务过程中竟然当着客人的面摔倒在地。这一摔,既摔掉了他的工作,摔掉了他“伟大管家”的头衔,更让他的生命提前走到尽头。这种突然出现的碎片式回忆表明,史蒂文斯非常抗拒这段回忆——要不是这封信刚好提到这里,他根本不会回忆起这次事故。事故发生后,他的父亲身体受到伤害,不能再从事热爱的管家工作。这对他来说,异常残酷与痛苦。然而,史蒂文斯作为儿子,不但没有宽慰父亲,相反给以冷漠。之后,在见父亲最后一面和为贵宾服务两者中,他选择了后者,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史蒂文斯认为这样做是一名伟大管家应该做的,这明显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冲突,叙述也就变得不可靠。
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那尚未开始便已结束的爱情,也同样用了碎片式的模糊回忆。在回忆他和肯顿小姐的关系时,他经常陷入一种记忆混乱的状态,他记得某件事情、某个场景,却不记得原因。当史蒂文斯反复思量他和她关系恶化的原因时,始终没办法完全确定。他认为关系的转变是由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也许是他不让她知晓名字的那本“感伤的罗曼司”,也许是两人关于人生目标的一次不愉快谈话,也许是她收到姨妈死讯后,他在工作上的刻意挑刺,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另外,他记得自己站在后廊上听她哭泣的场景,记得自己内心升腾出来的一种类似怜惜和心疼的感觉,却不知道原因何在。他也曾多次猜测,猜测她是因为姨妈(像母亲的人)的去世而哭泣,随即又自我否定,认为张冠李戴了。他又猜测她是答应了他人的求婚而哭泣——实际上,她是为史蒂文斯不肯接受自己的爱而哭泣。这些记忆是他在旅行过程中时不时想起的,呈碎片状,模糊性的。正是这些模糊的碎片回忆,既显露了他对她的爱——他渴望能改变过去,渴望两人的关系能够恢复如初,又使他之前所说的两人只是工作关系经不起推敲。因而,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远山淡影》也是写悦子短短五天里回想大约二十年前在长崎的往事。文本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悦子对日本生活的回忆,里面出现了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女二人;另一条线是悦子与小女儿妮基在英国的生活。两条线的展开相互交错缠绕,诸多回忆模糊混乱。据悦子的回忆,读者会认为佐知子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母亲。她固执、自私,待女儿万里子非常不好,明明说“我是个母亲,我女儿的利益是第一位的”,[3]70却不顾女儿意愿将她带去美国。而悦子,是一个怀着孕的善良温和的母亲。两相对比,读者自然会觉得悦子是一个远比佐知子负责任的母亲。可真是如此吗?直到文本结尾,悦子翻出一本有照片的老旧日历,才将她自己伪造的身份揭露,“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3]151之前叙述的,明明是怀着孕的悦子和佐知子、万里子母女一起去港口郊游,万里子玩缆车非常愉快。此时,印象中的万里子突然变成了景子, 读者由此恍然大悟,原来悦子是在讲自己的故事,[4]佐知子这位不负责任的母亲原来就是悦子本人。读到这里,读者肯定也开始怀疑,悦子之前的叙述就一直可靠,难道没有一点痕迹透露她的真实身份?其实不然。叙述者在很多叙述语言和细节中都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试举一例。景子自杀后,悦子在散步中偶遇了景子和妮基的钢琴老师沃特斯太太,当沃特斯太太问到景子的消息时,悦子却说她搬到了曼彻斯特,最近没有她的消息。其实,那时景子已经死了。她这样说给别人一种景子还活着的错觉——悦子在现实这条线中都能够自欺欺人,她的叙述会可靠吗?
细读文本可知,虽然悦子的回忆较零碎,也依旧能察觉她和佐知子的相似之处,发现两人实为一人。两人生活习惯相似,不太合群,不愿意刻意对他人表现出友好,都讨厌流浪猫,谈话时都会习惯性忽视万里子。两人经历相同,都离开日本去国外:佐知子生性自私,不管不顾去了美国,悦子本分传统,竟也离开家庭去英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悦子说服万里子去美国时, 她说了两遍:“你要是不喜欢那里, 我们就马上回来。”[3]142这里的“我们”让人怀疑,怎么会是“我们”,去美国的分明是佐知子和万里子,和悦子这个旁观者有什么关系?此时,悦子已经模糊了自己和佐知子的界限,二人已融为一体。读者可以猜测,当时悦子带走景子时也曾这样劝过她——恍惚间,她似乎回到了当年她对景子说话的时刻。佐知子本是悦子回忆中塑造的另一个人物,与她毫不相干,是她自己的回忆暴露了真实的自己。当然,悦子是位聪明的叙述者,她善用周到的回忆策略包装自己的叙述,试图让叙述显得可靠,但再精巧的设计也有一些漏洞,暴露了她叙述的不可靠。
综上可以看出,碎片式模糊回忆,是不可靠叙述的一种天然表现形式——回忆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确切知道,叙述者可以在回忆里随心所欲,如果读者不仔细阅读,就很容易被叙述者精心设计好的回忆套住。与《长日将尽》中的叙述相比(史蒂文斯的回忆叙述,多数还是可靠的,比如他能力出众、经历非凡等),《远山淡影》中的叙述策略更富艺术意味,现实的、正常时间这条线的叙述几乎是可靠的,而悦子假装记忆错乱的回忆,则像一个叙述迷宫,极需读者的叙述智力去领会。
二、自我欺骗的心理
《长日将尽》中,史蒂文斯一方面宣称自己以曾经在达林顿府工作为荣,为自己能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达林顿勋爵服务而深感骄傲,另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多次否认与达林顿勋爵的关系。史蒂文斯在旅途中遇到一名管家,当被问及是否曾经受雇于达林顿勋爵时,他却说自己受雇于美国绅士约翰·法拉戴。当法拉戴的朋友威克菲尔德夫妇访问达林顿府时,史蒂文斯也坚决否认他曾为勋爵服务过。这是一种典型的伪装与自我欺骗。但是,当别人批评达林顿勋爵是排犹主义者时,他又会为勋爵辩解,认为这是污蔑之词。然而他在回忆叙述中又说“我记得他指示我不要再给某个定期上门募捐的当地慈善组织捐款,因为其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都是犹太人组成的’。”[2]188而且勋爵还命令他解雇了两位并无过错的女仆,只因她们两个的犹太人身份。虽然史蒂文斯为此找了不少的理由,甚至把这些“小事”当作“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不可否认这些行为就是反犹太行为,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史蒂文斯之所以不愿承认达林顿勋爵是排犹主义者, 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一位“伟大的绅士”,自己也就不再是为“伟大绅士”服务的“伟大管家”。[5]叙述者这种自我欺骗的叙述,显而易见与隐含作者的道德感及判断不一致,是明显的不可靠叙述。
同样,史蒂文斯也以这种自我欺骗的心理对待爱情。明明他和肯顿小姐互相爱着对方,他却囿于一些名声荣誉的身外之物,牺牲了这段珍贵的爱情。肯顿小姐是深爱过史蒂文斯的,她为他送过花,煮过可可,还有每日的傍晚晤谈,多次明里暗里地表达对史蒂文斯的爱。虽然,史蒂文斯的自我陈述中很少透露出爱意,他总是自我欺骗,将一切解释为工作的需要,读者依旧能从文本细节中感受到他那份压抑已久的爱意。首先,他对肯顿小姐来信过度解读。虽然信中无一处表明她会回来工作,但他却将此视为外出旅行的真正原因,并在旅行中时常温习、反复琢磨这封信,达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其次,他对肯顿小姐的称呼。虽然肯顿小姐早已嫁人,他却不肯称她为本恩太太,他无法忘怀的是共事的肯顿小姐,而不是嫁做人妇的本恩太太。他还认为肯顿小姐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很快将会恢复为肯顿小姐的身份。最后,在肯顿小姐嫁人之后,他还通过相关的书了解她的婚后定居处。足见其恋恋不忘。然而,在这么多的事实面前,他仍旧自欺欺人,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出于工作考虑,“男女关系对于整幢宅第里的秩序是一种严重的威胁”,[2]66谈恋爱会影响他成为伟大而有尊严的管家。直到小说的最后,他才直接展现了爱意,不再自我欺骗。当他再见到肯顿小姐,终于认清自己的真心,勇敢地表达了爱,“的确——我又何必再遮遮掩掩?”[2]310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他和肯顿小姐永远不可能了,“在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2]310无疑,叙述者这种表里不一的叙述,是会受到隐含作者的批评的,批评叙述者的不诚恳、不磊落。换言之,史蒂文斯对爱情的自我欺骗,使其部分叙述不可靠。
《远山淡影》中,悦子的自我欺骗则不同,她假借佐知子的身份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减轻自己的内疚感和罪恶感。[4]当年她不顾大女儿景子的想法,带着景子去了不熟悉的英国。结果景子无法适应外国的生活,只能自我封闭,最后自杀。景子的继父认为她“天生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3]76并且认为这种性格是从景子的生父——二郎那里继承来的。景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又怎么能够获得理解和关爱。而身为母亲的悦子却并不能保护女儿,在那个家庭中,同样作为一个新移民者的她也只能保全自身。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中,景子终于不堪重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她而言,可能是一种解脱。不仅景子的继父对景子有着这样的偏见,连英国整个大环境都对景子的自杀也有着偏见,不止一家报纸报道的全部内容都是:“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3]6仿佛因为景子是个日本人,所以她就会自杀,没有一家报纸去了解她自杀的真相。唯一知情、也唯一对此怀着歉意的,可能就是她的母亲,不管不顾把她带到新环境的母亲——悦子。但悦子不敢直面自己的过错,她不敢承认就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一念之私,导致女儿自杀。所以她选择了自我欺骗,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佐知子,而自己则扮演了一个和佐知子截然不同,也就是和曾经的自己截然不同的身份:关心孩子,以孩子的利益为重,担心小小的万里子会因为陌生的环境而出现心理问题。这些都是曾经的悦子没有做到的,她渴望在她虚构的故事中弥补一切遗憾,抚平一切伤痕。在故事快要接近尾声时,悦子第一次直接将自己的过错赤裸裸地摊开来说“可是你瞧,妮基,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3]145她这样坦白自己过错的做法的确获得了妮基的理解,妮基安慰她:“别傻了, 你怎么会知道呢?而且你为她尽力了。您是最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人。”[3]146不管小女儿妮基是否知道母亲故事中的“佐知子”就是母亲本人,悦子的目的达到了。她知道骗局终会被揭露,却仍旧选择这种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只是因为她想要解脱,想要求得内心的一丝平静。
《长日将尽》中,史蒂文斯自我欺骗,他骗自己、骗大家达林顿勋爵没有什么过错,达林顿勋爵没有反犹太倾向。其实他也清楚,达林顿勋爵真的做错了事情,他成为了纳粹的爪牙,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但是他却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他“伟大管家”头衔带来的荣誉就会随之而去。所以他宁愿将自己变成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也要选择自我欺骗。《远山淡影》中,悦子自我欺骗,她不敢承认自己的过错,不敢承认景子之死与自己当年的决定脱不开关系。但是她又想要解脱,想要把这些事说出来。所以她编纂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她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安慰,也获得了重生。这种自我欺骗的方式,也是叙述者逐渐不可靠的表现,这是叙述者为了达成自己的一些目的,自愿变得不可靠。
三、重复强调的语言
《长日将尽》《远山淡影》两部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策略,除上述两种外,还包括叙述者在回忆的过程中,用一些重复强调的语言作为支架。也正是这种文本形式上的不可靠,让读者窥探到叙述者的一丝不可靠,开始反思自己的意识状态,想要挖掘真相。
《长日将尽》中的叙述者有明显的语言风格。首先,叙述者喜欢用“特别指出”“准确的说”“我必须重申的是”“特别强调的是”这类反复表肯定的语言,反而让人质疑这件事情的真相。要是叙述者对自己说的话十足肯定,会自然而然叙述,不会用很多表肯定的词反复强调。这种强调,相反暴露了其多数时候的不确定与不自信——似乎只有自我肯定后,别人才会肯定他。其次,叙述者喜欢用过多的破折号,一句话中常常有三四个破折号,破折号起解释、强调的作用,或表犹疑心理,不断的强调、犹疑。这似乎贴合史蒂文斯模仿绅士的语言风格,一种端着的态度,让人感觉不自然和做作,或者表示他的对回忆之事的犹疑不决。再者,叙述者在同一句话中的用词常常比较繁杂。例如《长日将尽》开篇第一句,“看来,这些天来一直在我心头盘桓的那次远行计划越来越像是真的要成行了。”[2]3“越来越像”一词弱化了话语的稳固性,“真的”又加强了语气,又弱化又稳固,既充分强调又前后矛盾,侧面反映了叙述者史蒂文斯叙述的不确定与不可靠。“我忍不住想立刻又毫不含糊地坚决否认我的雇主强加在我头上的这种不实的动机”。[2]17“忍不住”程度稍轻、是想法,“立刻”表肯定、速度,“毫不含糊”含否定的肯定词、再次表肯定、速度,“坚决”又表肯定和坚决的态度。多个词语连续表达肯定的想法,实际正是一种强调,强调对于史蒂文斯而言又是一种不可靠的表现。最后,叙述者会多次重复同一句话。例如:在父亲弥留之际,史蒂文斯反复说“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2]128只为了自我安慰,给自己一个可以离开的理由。同样,在肯顿小姐告诉史蒂文斯她答应了他人的求婚时,他也是重复一句相似的话“我真的必须马上回到楼上去了”,[2]282以掩盖自己此刻内心的无措与翻滚。
《远山淡影》中,悦子(或者说回忆中的佐知子)同样有自己的语言策略。其一,多用一些重复的语言。如:当万里子失踪时,佐知子反复说“没什么担心的”“没必要担心”“你不要担心”,有一种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感觉,也让人怀疑佐知子是否真的疼爱在乎万里子。当悦子和佐知子初次相遇交流时,佐知子在短短篇幅内两次称赞悦子“我肯定你会是一位好母亲”,这与真实世界中悦子的形象不符。其二,常用模糊不肯定的语句。比如:“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3]128“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3]31除此之外,“记不清”“不记得”这类语句也出现过不止一次。这些含糊不清、指代不明的用语,都能够反映出叙述者悦子本人某个阶段叙述的不可靠。连叙述者都不相信自己的叙述,读者又怎么敢全部相信。其三,叙述者喜欢埋下伏笔,后文又会再现这个伏笔。例如万里子口中的“那个女人”,她一直说自己能够看到她,说她就在河岸对面,实际上河岸对面并没有人居住。后来揭晓真相,这个女人早都死了,在溺死自己的婴儿之后自杀了,这一幕被年幼的万里子看到并记在心里,留下阴影。不仅如此,之后佐知子为了带走万里子,又把万里子最爱的小猫淹死了,动作和淹死婴儿的那位母亲一模一样,更加深了万里子内心的恐惧,给她带来了永远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这也能够解释为何长大后的万里子,实际就是景子会早早结束自己生命,除了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也有幼时心理创伤的影响。
赵毅衡先生认为,符号发出者构成谎言有三种类型:“明知真相而不说真相,或说出真相却没有被当做真相,或明知真相说的不是真相也让接收者不必当做真相。”[6]本文讨论的两个文本的叙述者都采用了第一种,文本借此揭示了某种值得玩味的人生体验:人们往往通过欺骗式的回忆叙述缓解人生的种种不幸与痛苦。不过,这两个文本也以上述三种局部不可靠叙述策略,隐含了隐含作者正面的价值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