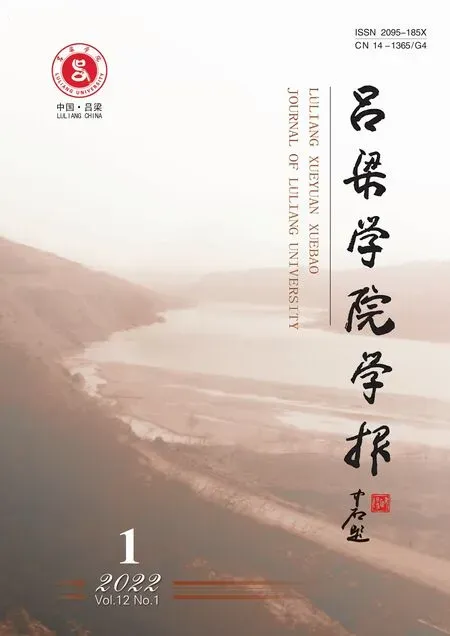荀子论道心关系
张焕君,梁瑞强
(1.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2.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部,山西 太原 030000)
人们对荀子核心的理解,历来被视为是礼,但其间亦有不同。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说,“吾尝博观周秦诸子,而深疑百家言主术,同归于执本秉要,清虚自守,莫不原于道德之意,万变而未离其宗。”[1]36在张舜徽看来,如果想深刻了解先秦诸子,就必须对其所论之“道”有所了解。《淮南子·齐俗训》也曰:“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2]183由此看来,淮南子亦认为道德为各家之核心,各家的道德之论犹如日月,其它皆以之为标准。只有理解了各家所谓的“道”,才能真正把握诸子的精义,对其有深入的了解。
荀子为诸子之一,故而道亦是其核心概念。“荀卿广陈人主任人而不任智之旨,以阐扬无为之意,谓为百王之所同,儒者之所谨守,则道德之论,由来远矣。”[1]38张舜徽认为,了解了荀子的道,也就为全面了解荀子打下了基础。他认为荀子的核心是道,而唐君毅先生则认为是心。“荀子整个政治文化之思想,全不能由其性恶观念以引出。则谓荀子之思想中心在性恶,最为悖理。以吾人之意观之,则荀子思想之核心,正全在其言心。”[3]73在唐君毅看来,荀子思想的核心,在心不在道。
那么荀子思想的核心究竟在“道”还是在“心”?其心道之间又是何种关系?
一、荀子论道
张舜徽言:“千载下儒生所争论不休者莫如‘道’,‘道’之一字,在古书中随处见之,而其含义,又各随时代有浅深广狭之不同。盖有先秦诸子之所谓道,有孔门之所谓道,有两汉儒生之所谓道,有魏晋南北朝谈士之所谓道,有唐代韩李之所谓道,有宋明理学家之所谓道,有清初颜李之所谓道。学者生于后世,上窥先民立言之旨,期于不失其真,则必以先秦诸子之见还之先秦诸子,以孔门之见还之孔门,以两汉人之见还之两汉,下观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人之书莫不如此,虚心静气以求真是之归,庶乎其有得也。”[1]30研究荀子之道,亦须以荀子之道还荀子,不可以别人之道加之。
《劝学》为荀子第一篇。其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4]7
由以上引文可得:第一,关于学的性质,学与不学是人和禽兽的区别所在。学,便是人;不学,便是禽兽,故说“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由此,学便成了人的本质,不学的人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第二,学的方法。起初是阅读经典,而后要践行礼的内容。“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读礼是为了行礼,所以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总之,是由理论而实践的。第三,学的阶位。人之生都是小人,经由学进升为士,然后再进升为君子,最后成为圣人。故说,“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第四,学的内容为诗、书、礼、乐、春秋。这些典籍的特点是博、敬文、中和、微。这些都是先王传下来的大典,如果将这些典籍都学完,天地之间的事物也都了然于胸了,故“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但了然于胸还只是理论上的知,还未化为行,只有外化为实践,才是学成。外化为实践就是“至乎礼”,能“止乎礼”则是“道德之极”,完成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由小人到圣人的蜕变。
荀子将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一个完整的学的过程是由理论而实践的,即“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即“道德之极”。道德之极,即由诵诗、书、春秋而行礼(乐)得以完成。分为两个层面:道和德,道属理论的层面,德属实践的层面。道之极是穷尽天地间万物,“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4]11。 《说文解字》曰:“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5]1在这里,一便是道。道需落到实践,荀子在谈到文武周公时说,“道岂不行矣哉!”[4]68道之极之行,便是德之极,便是实践,礼的实践,先掌握天地之道,然后躬行礼德,最后成为圣人。道德之极是理论和实践都达到最高水平,二者统一于圣人。
由此可知,荀子之道偏重于理论层面,是“天地之间毕”的道,是对天地之间万有的认识,是对宇宙大全(1)参见金岳霖先生之《道论》,他在绪论中说:“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说道为万有或宇宙,含有了金先生所讲的两种情况。的认识。
道首先是一与异的统一。《劝学》说,“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学者的任务,是谓能一。一在这里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即使……一,是使万物一。万物为小一,具体的一;大道为大一,贯通的一。道之一,便是万物的本质;道之异,便是万物的现象。使……一,便是将对万物的本质的认识和对万物的现象的认识统一起来, 做到“伦类通,仁义一”。
道又是常与变的统一。一与异,主静;常与变,主动。《解蔽》曰,“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可见道有两个方面:常和变。常,即道的本体;变,即道的化成。体常,即体察道之本体;尽变,即穷尽道之化生。唯有体常,才能尽变。体常和尽变是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由其不变之常,方能衡量万物之变。“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何谓衡?曰道。”[4]263道是万物的标尺,任何事物都能由道衡量。因为,道是不变的万物的本体,只有本体才能成为标准,变因其变,不能成为标准。“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执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4]262用、俗、法、执、辞、天等,都是道的一面,是道之变,故不能成为衡。
不论主静还是主动,都属于空间的范畴。道不仅有空间性,也有时间性。道不仅是万物之衡,也是古今之衡。“道者,古今之正权也。”[4]286杨倞注曰:“道能知祸福之正,如权之知轻重之正。离权则不知轻重,离道则不知祸福也。”杨注此处仅以祸福释道,略嫌狭隘。《非相》曰:“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4]286杨注曰:“古今不殊,尽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异情乎?”“以道观尽物之理。”站在道的高度,古今自然不殊,故曰“类不悖,虽久同理”。
荀子也说,“须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备,曲容备物之谓道矣。”[4]249事、成、文、备皆是道。道不尽有其体,还有其用。《淮南子·泛论训》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2]214道为圣人所由,常而不变;事为圣人所为,变而不常。荀子所论之君道、臣道便是大道之用。《仲尼》曰,“道岂不行矣哉!”[4]68即道之体落到事上而言。
如此,荀子之道是一和多的统一,是常和变的统一,是古和今的统一,是体和用的统一,是宇宙的本质和宇宙万象的统一,是宇宙大全。
二、荀子论心
荀子之论心,离不开其论性、情、欲。何为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4]274性为人生而所有,所以是“天之就也”。天之就,故不事而自然,事即人为刻意,不假人为刻意,所以是天之所成,天然。何为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是不动者,其动者为情,具体表现为好、恶、喜、怒、哀、乐等情绪。天然之性没有实际内容,故“情者,性之质也”,其实际内容为情。但是仅仅有情还不能化为行动,欲才是情的行动,故说“欲者,情之应也”。欲和情之间的关系是,“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4]284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是:性为不动者,乃天之所生;情由性而出,是喜怒哀乐等情绪,但是还未化为行动;欲是由情而化生的行动,如饿的情会导致吃东西的动作。三者关系也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表示:性为大海水,情为波浪,欲为浪花。由静而动,由内而外,逐层显现。那么性情欲三者和心之间的关系如何?“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性为不动的天然状态,情因性而显现为喜怒哀乐,但情不尽是合理的,如怒火中烧之后的泄愤(泄愤已成为欲)便不应当。故情的出现需要心的抉择,合理合适的情可以由欲表现为行动,非理的情则不可以由欲而表现出来,此处判断合理与非理则需要心,心是判断情之是否合理的法官。性无善无恶,是天然如此;情有善有恶,故需要抉择;欲由情而出,故有善有恶。心可抉择善恶,是情-欲的阀门(2)荀子说:“(心)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明显地将心作为情-欲的把门者,视其情况而决定其去留。。这样,性、情、欲、心就被分为两部分:心是理性的部分,性情欲是感性的部分。(性虽无善无恶,但情欲由其而出,故亦归为感性。)在荀子这里,理性部分高于感性部分,“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治乱由心而决定,由情-欲只能走向乱。
故心又分为两种状态。《解蔽》中说:“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於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在荀子看来,盘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静止不动时,“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一种是微风吹过,受到外在的影响,盘中之水就不能映现人的真实面貌。心如盘水,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这样的心,是“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另外一种情况是:“小物引之(心)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心的两种情况也可以说是心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动占主导地位,一个方面是被动占主导地位。在主动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善的;在被动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人的选择可能就是错误的,恶的。也就是说,心分为动静两种,主动占主导地位的心是静心,被动占主导地位的心是动心,也即所谓的枝心。
静心是“神明之主”。何谓神?《不苟》曰:“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4]28又说“尽善挟治之谓神”[4]84。何谓明?“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在论及神时,不能离开形;在论及明时,不能离开理。在论及形、神、理、明时,又都离不开“诚”。诚是仁、形、神、化的前提,也是义、理、明、变的前提。只有做到诚,才能静心,才能发挥心善的一面。那么,何为诚?刘台拱曰:“诚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以成始则《大学》之诚其意是也,以成终则《中庸》之至诚无息是也。”[4]28此处之诚就成终而言,所以是《中庸》之诚。《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朱熹注曰:“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6]12诚是自成,即物之成为自己。《说文解字注》曰:“诚,信也。”[5]92信,也就是所说的言辞与事实相符。以“信”释“诚”,即事物实际的状态要与应该的状态相符,故“诚心”即是“成心”,使心真正成为心,使心成为真心。由此可知,虽然荀子区别了心的动静两种状态,但其侧重点在静心,也即真心上。诚心是心应该保有的状态,枝心只会干扰诚心,使诚心隐遁,所以需要摒弃枝心。只有在诚(静)心的状态之下,人才能定是非,决嫌疑,发挥心真正的作用。
三、荀子论心与道的关系
以上分别论述了荀子的道和心,那么道心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正名》曰:“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4]281在荀子看来,心是道化为现实的工具和依靠,道是天下治乱的标准和关键。所以说,“治之要在于知道。”那么“人何以知道”?“曰心。”心是道的工宰,能知道而行道,使道显彰于现世而非隐匿于幽冥。心是道和治之间的桥梁和媒介。通过心,道可以为人所认识;人认识了道之后,追随道可以达到治的目的。如果没有心,道既不可被认识,也不能由道而治。
道离不开心,心也离不开道。可是心何以知道呢?曰:“虚壹而静”[4]263。
“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荀子看到,心能藏,但是也能虚,虚和藏相对,人要用心之虚求其藏,也只有虚才能藏,虚比藏更为重要,心之虚使人能“不以所已藏者害所将受”。正是因为心能虚,故不会形成成见去阻碍将要接受的新事物,而成就人心能藏的作用。这是道心关系的第一层,重在虚,偏于归纳。“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满即是藏,一即是所藏。心之能一,是与心之能两相提并论的。心之能两,即心“能兼两一而知之,更不以此一害彼一”的作用。两即是多,一即是统一,是心的综合功能。心能知两,是指心能认识很多事物,并将其统一。这是心道关系的第二层,重在壹,偏演绎。统一于何?曰道。将认识的万物统一于道,即是“壹”,心就自然达到静的境界。《说文》曰:“静者,审也。”心之受物是按事物本来的样子而受,如静水之照面,对事物的认识是其本来面目的反映。故“审”是将事物认识得清清楚楚,又不混淆。这是心道关系的第三层,即知道,也就是融贯。
人能知道,还能行道。人如何行道?“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4]268心之静,即是心完全沉浸于所知的道之中,与道合一,也可以说是无心。因其无心,所以心之所行便是道。这是心能行道的缘故。进一步而言,心的虚、壹、静的功能同时出现。心虚之时,即是心壹、静之时,由此类推。由心的虚的功能,故能藏,而所藏与心可谓合一,合一则静,所以心之虚、壹、静同时兼有,虚、壹、静三而合为一。因心的虚、壹、静,所以能成就心的大清明,大清明的心即能对万物认识无余,这时,万物便是此心了。人心得到这样的大清明之时,就是知道的时候,道与心,融而为一,故所行无不是道。
不论知道还是行道,皆需要人真心的显现,真心显现,人便能知道行道,故关键还在于对心的修养。如何养心?曰诚、曰恭、曰乐。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4]28此处之诚,依刘台拱之意,为《大学》诚意之诚,乃诚之始。“诚意”为何意?依《大学》解之,则是“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6]28。恶恶臭、好好色是人自然的天性,不假任何刻意。唐君毅先生说:“大学言仁之诚意正心,皆言人能自诚其意,而自正其心。亦即意能自求诚,而好善恶不善,心能自求正,能自安于喜怒哀乐之得其正者,而不安于其不得其正者之谓。”[7]83诚就是要如实显现自心,即如实显现真心。如何显现?恭与乐。《解蔽》曰:“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4]269杨倞注曰:“恭,谓乾乾夕惕也;乐,谓性与天道无所不适。”郝懿行曰:“恭则虚壹而静,乐则何强何忍何危。”郝注可谓是杨注的注释。恭,肃也,敬也[5]503。敬与肃互为转注,也可以忠释敬[5]343。忠为中(读四声)心,即与心一致,而此一致便是虚壹而静。乐,即是本心自然显发,无任何窒碍,其因在于心与道之无二,所显无不是道,故乐。诚,是就本心之认识本心而言;恭,是就虚壹而静言;乐,是就心道不二言。各有侧重,然其主旨皆在说明本心与大道之相合无间,即心言道,即道言心,即心即道,道心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