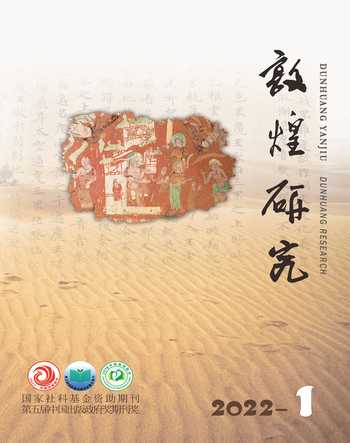从敦煌本《瑜伽论手记》《瑜伽论分门记》看法成对蕃、梵经论的解读及应用
内容摘要:《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是敦煌僧生听授法成讲经时所做笔记的汇辑。法成在对《瑜伽师地论》进行结构分析和内容解读的过程中,将汉、藏、梵本经论细致比对和交互使用,采用以经解论的方式对《瑜伽师地论》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大量蕃、梵经论的引用,可见法成佛学思想来源之广泛,同时也反映出汉藏两地佛教的交流以及吐蕃统治后期敦煌的佛教状况。
关键词:法成;《瑜伽师地论》;讲经笔记;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1-0120-09
敦煌本法成讲授《瑜伽师地论》的笔记可分为《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两个部分,“手记”是对《瑜伽师地论》内容的解释,“分门记”则是《瑜伽师地论》概要及主要结构,“手记”也包含对结构分析的一些内容。闻听法成授课的弟子有谈迅、福慧、恒安、明照、法镜、一真、洪真、福渐、智惠山等,于是就有了多个版本的随听笔记。现搜集整理的敦煌写本约有65个卷号,除上山大峻所列国外所藏的33卷外[1],还有国内藏32卷。这些笔记所涉及的是法成对《瑜伽师地论》前59卷内容的讲解,中间几乎没有间断,笔记中留存有听讲人姓名和时间的题记。《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内容丰富,既有《瑜伽师地论》原文经典的详解,又有很多蕃、梵经论中关于唯识学及佛学义理的解读,是我们全面认识法成佛学思想和《瑜伽师地论》及其他唯识经典内涵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一 对汉译本、藏译本经论的参考
法成佛学知识的构成,在北图BD14676(新876)《咸通六年正月三日奉处分吴和尚经论录》[2]中有着实体化的呈现[3],法成的佛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河西陷蕃初期昙旷的唯识宗思想,再加上法成本身的吐蕃佛教的修为和印度佛教知识,这就构成了法成佛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广博的佛教知识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使得法成的佛学素养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很好地运用在其所从事的佛典翻译和研究中。
正是基于这样超凡的佛学素养和知识构成,法成在讲授《瑜伽师地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与《瑜伽师地论》密切相关的汉、藏和梵本经论。对这些不同文本经论的解读和应用在讲经笔记中有多处体现,据粗略统计,仅在《瑜伽论手记》中引用的汉、藏和梵本经论多达四十多处。比如P.2061、P.2036、P.2344、P.3716、S.1154、S.1243、S.2613、
S.4011、S.6440、S.6670等中都有引用。其所引用的经论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乘经类,主要有《大宝积经》(三回)、《华严经》(二回)、《梵网经》(二回)、《般若经》(一回)、《维摩经》(一回)、《十地经》(二回)、《长者所问经》(一回)等;二是小乘经类,有《阿含经》(五回)、《增一阿含经》(一回);三是大乘论典,主要是唯识论典,包括《三十唯识论》(一回)、《二十唯识论》(一回)、《毗婆舍论》(一回)、《解深密经疏》(一回)、《最胜子释》(十回)、《弁中道论》(一回)、《大乘百法明门论释》(一回)。另外,还有《八啭声颂》(二回)、《论语》(一回)等其他经典。以上对这些经论的引用,足以说明法成已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和对佛教经典经论内容的习熟。除此之外,法成还在讲解的过程中着重参考了《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诀》《成唯识论》等唯识宗经论。以下试举几例详述。
如P.2061中对《解深密经疏》的参考,在论述至“八门中第四种子具不具相中之所熏门”时,这样讲道:“七明所熏门中文二:一者本有因,二者新熏因。《解深密疏》中多门解释或云本有或说新熏,令此论中有二义,双立论文自明。(法镜《瑜伽论手记》卷2)”[4],这里指出了《解深密经疏》中对“熏门”有更多分门别类的解释,于是产生了“本有”和“新熏”两个释义。圆测所作《解深密经疏》本就是一部唯识学经典,就是法成根据汉文经籍翻译、校阅并审定的[5]。所以,《瑜伽师地论》才会将《解深密经》全文收录在其第75—78卷中。二者皆依玄奘本而来,两者内容一脉相承。
对《阿含经》的引用是在讲解至《瑜伽师地论》第四卷时,曾两度参考此经。如“初中言如经中说者,如阿含经中说有诸天子及以天女将欲没时,五相先现,如论所明。”又如 “言经中者,阿含中说,若天摄者,何不名天?故论答云:實是天类等。(法镜《瑜伽论手记》卷4)”[4]49其中将《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中对“诸天受苦”内容进行比对,并作出解释。末句中“故论答云”和多次出现的“是以论云”中的“论”所指均为《瑜伽师地论》。
同样在P.2061写本中,也有对《百法释论》的参考,在论及“地狱苦”时文曰:“初中言文于四种者,谓八热等四地狱中唯有苦受,故百法释论云:那落迦中唯名为苦,恒受九重无分别故。是以论云,无有乐受。”[4]50同样的论述还见于日本增贺所作《瑜伽论问答》中:“那落迦苦重,无忧可现行。故唯识论云:那落迦中唯名为苦,纯受尤重无分别故。如极乐地意悦名为乐。无有喜根故。极苦处意迫名苦。无有忧根。故余三言定忧喜乐问,同唯识论云,瑜伽论说。”[6]这里所说的“唯识论”有两种:一是《唯识二十论》之略称,二是《成唯识论》。二种皆为玄奘所译。这里将不同经论中有关“地狱苦”进行比较研究,结论中的“同唯识论云,瑜伽论说”明确指出这些论述之间的异同,与之相较,亦与之相合。
除此之外,还有“初中言成就修者,此依《梵网经》说修四无量能成就者,故论文言:亦有四相。(法镜《瑜伽论手记》卷5)”[4]59“言广大五欲者,谓此福德之诸天生彼天时,所受色等五欲境界过于余天,故《维摩经》云: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法镜《瑜伽论手记》卷4)”[4]49等分别是对《梵网经》和《维摩经》的参考和引用。
法成在讲解《瑜伽师地论》时所引用和参考的这些经论中有唯识学的著作,亦有大、小乘其他宗派的论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不仅有汉文的经典,对于藏文、梵文译本的引用和参考也不在少数,对此将在下文详述。所以,仅凭讲经笔记丰富的内容,足以看出法成佛学知识之广博,为了更好地阐释《瑜伽师地论》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唯识经典之精妙,旁征博引,但又不局限唯识一派。
二 对“最胜子释”的理解和运用
在整理研究《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的过程中发现,法成对“最胜子释”引用和参考最为突出。仅在P.2061法镜本《瑜伽论手记》第1—5卷中,法成对“最胜子释”的引用竟有10次之多。“最胜子释”即唯识十大论师之一的最胜子(Jinamitra世友)等人所著的《瑜伽师地论释》(玄奘译)。但是,这个“释”,并不是由玄奘全部译出的。《瑜伽论释》原来的注释所有的内容约为六百卷,最胜子《瑜伽论释》梵本颇多,非玄奘全译,仅有“十七地总论”的部分内容,且只有一卷。或许是译者进行了删减,尽管如此,它却成为汉传《瑜伽论释》的标准样本[7]。因此,《大正藏》所收录的,仅仅是对《瑜伽师地论》卷一开头的“本地分·十七地”中“嗢柁南”部分进行了解释就结束了[8]。
法成在讲授《瑜伽师地论》的开始部分,就引用了最胜子“释”的部分内容。如P.2035《瑜伽论分门记》卷首曰:
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五识身相应地等前十二地同卷最胜子菩萨将释此论。先立三门之义,方释论正文。言三门义者,一归敬等门有六行颂分为五门,一归敬三等门。颂初一颂,二叹说门。谓次一行颂,三赞造论门。谓次两行颂,四赞论功门。谓次一行颂,五造论意门。谓次一行颂,第一所为门分十:一久住并益门,二隐不隐门,三破无见有见门,四成就大小门,五离倒生信门,六利略广门,七立正破邪门,八破增损门,九不相违有差别门,十位果差别门。第二所因门分:一明教初兴由,二明二宗起由分二:一明胜义皆空宗兴由,明唯识中观兴由分二:一明造论因,二叹论功,三明智所被分二:一天二小,释论正分二。一释论题目。二释论正分……[9-10]
卷首有小部分残损的法镜本《瑜伽论手记》(P.2061)中也有相类似的内容:
论所为中十门:一久住普益门,二隐不隐门有姓无姓,三破无见有见门,四成就大小门,五离倒生信门,六利略广门,七立正破邪门,八破增损显无倒门,九明不相违有差别门,十位果差别门。今说此论所为云何者,最胜子等意中,此论不同集论有□无用,及得著伽龙王如意宝珠,有用无方便取得耶,故此□谓有二缘,故说此论等也。有情界中者,五趣皆名有情界。世间善名增上生,决定胜者涅槃。世间道理者,有四种观侍法尔。证成□用如下说。二藏者,经藏、律藏。此随转理门,具说三藏,名真实理门,即本母□。所以云:瑜伽论者,即是本母,能出生三乘教法故。境界者,六尘教境界及三乘人所缘境界也。论所因中文分四:一初圣教兴由(游改为由),二中教兴由胜义是,三后教兴是,四唯识宗是,一一皆有病药二义,后结。无知者,于世法都不能知;处中实相者,即中道实相之义。[4]22
以上笔记中所记内容和玄奘所译出的《瑜伽师地论释》的内容基本一致。但是在P.2061这份笔记中,除了对《瑜伽师地论》结构的解析、分类的解释之外,还对其中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用藏文在字里行间加以注释。特别是在引用的“最胜子释”和“蕃本”时行间的所作的藏文批注尤多,这些注释并非是对字词、语句的简单的汉藏对应翻译,更多则是对相应的字词句所作的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玄奘翻译出的部分,刚好相当于法成所讲解的《瑜伽师地论》的序论部分,在法成所注疏的《大乘四法经释》和《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开头部分也引用与《瑜伽师地论》相类似的内容。同样的,法成把“最胜子释”也作为自己讲义的序论,但并非照搬套用玄奘译本,而是参考了梵文本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虽然“最胜子释”全译本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却可以在法成所讲的《瑜伽师地论》中看到其对“最胜子释”的引用和参考情况。如例:
(1)言八之德水者,此明功德:一冷,二轻,三软,四甘,五净,六不臭,七饮时不损喉,八饮不腹。故最胜子释论云:冷轻及以软,甘净而无臭,饮时不损喉,饮已不伤腹。(P.2061《瑜伽论手记》卷2)[4]32
(2)言目呼剌多者此云息。故最胜子释云:一弹指倾有六十刹那,一百廿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以腊缚,卅腊缚成一莫目呼剌多,卅目呼剌多成一日夜,卅日夜成一月,十二月为一年,一年之中有冬夏等,名之为时。(P.2061《瑜伽论手记》卷2)[4]33
(3)言由此道理等者,由上道理等也,故最勝子释云,第六名为王,此着彼亦着,不差彼非着,若着说名愚。
……
依最胜子释,此六善巧为破六见而建立之:一执一合见,二执能生之见,三执增过十二法见,四执补特伽罗二世移见,五执无住法见,六执我能于境受用身在见。但起一物之相,为破此见,故佛世尊说五蕴等诸法和合破一合见。
……
此九事相依最胜子释,五义建立:一蕴相续义,二六处义,三根本相应义,四佛及弟子诸义,五部分义。与一、一、四、一、二事,随次配释。(P.2061《瑜伽论手记》卷3)[4]43
(4)第八明二世乐静虑分三:一问,二略答并如论,三别释中虽有九文,依最胜子释义分为二:一唯依后世乐,立前三种分三:一依未入正法有情明神变静虑,二依下劣放逸有情明祀说神变,三依已入正法有情明教诚神变,并如论。(P.2036《瑜伽论手记》卷43)[9][10]213
(5)言如经广说者,最胜子释云:彼经言佛诸苾刍有受味喜,有离受味喜,有胜离受味喜,从五欲生者,名有受味喜。具足初静虑住名离受味喜。住第二静虑者名胜离受味喜,如喜有三种、乐有三种、舍有三种,亦如是知……
二释分九如论,故最胜子释云:言染者于诸缠相应故。(P.2061《瑜伽论手记》卷5)[4]58
(6)依最胜子释,此四种依二时所受:一乐时三种,二苦时所受。谓病缘 ……
此九种法,依最胜子义分二,前之四种依世法立,后之五种依情非情立。于后五种坏法尽法、通情非情为若财物及己眷属有其变坏及尽之时,皆主苦故。老等三法唯约有情立趣之中悉皆遍故。(P.2036法镜《瑜伽论手记》卷42)[10]209
(7)此一种精进于最胜子疏五门所摄:一先与欲愿所摄,二舍所损得所摄,三修习教法及证法所摄,四饶益有情所摄,五守护自学所摄。与前七门一、二、二、一一随次配释。
二明差别于最胜子义分为五:一依三摩地加行明六种清净精进分六;…… 第二依无畏无喜足加行明不舍轭清净精进,故论文言有诸菩萨闻说等也;第三依三摩地資粮加(行)明不舍轭清净精进,故论文言诸菩萨于密护根门等也;第四依平等加行明平等清净精进,故论文言为诸菩萨发勤等也;第五殊胜果加行明回向大菩提清净精进,故论文言谓诸菩萨精进等也。(P.2036法镜《瑜伽论手记》卷42)[10]212
(8)三别释分二:一明六种遍满静虑分二:一标可见,二释中虽有六种,依最胜子疏三门释之:一依行相立初二,故论文言:一者善静虑等也,谓为不以善心及无证十八变等修现法乐住等。三静虑者,不得名为遍满静虑也;二依品类明立中二静虑如论;三依作用立后二静虑。故论文言,五者等也。(P.2036法镜《瑜伽论手记》卷43)[10]213
(9)二别释虽十文,依最胜子义分为六:一依世间净立初一种,故论文言二者等也;……第二依出世间净立一种如论;第三依共有果净立三种分三……第四依自在清净立三种分三……第五明所依净,故论文言九者等也;第六明二障清净,故论文言,十者等也[10]213。
三别释中虽有八文,依最胜子释义分为四:一依利乐有情利初四利,二依护圣教有力立此二种,三依饶益宗属立此一种并如论,四依善解王正等立后立种。(P.2036法镜《瑜伽论手记》卷43)[10]214
(10)此中有问:最胜子释菩萨地同于声闻地有其四处,此中何故明其十耶?答:此中十义门四处摄故,谓种姓发心二瑜伽处摄,初持故相等八种修行处摄,建立一种得果一所摄,故不相违。(P.2036法镜《瑜伽论手记》卷35)[10]185
(11)此中有问:最胜子释等略释中,言独觉地中者种姓发心修行得果四瑜伽处,以声闻同,何故此中列五相耶?答:谓住及行并是得果瑜伽处,故与上无别。(P.2036法镜《瑜伽论手记》卷34)[10]184
以上所列数例可见,“最胜子释”在法成的讲经笔记中出现频繁,将《瑜伽师地论》中字词句义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比较说明,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另外,在P.2036、P.2344、P.3716、S.1154、S.1243、
S.2613、S.4011、S.6440、S.6670等《瑜伽论手记》中也大量参考了最胜子的《瑜伽师地论释》。上山大峻曾在《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の研究》[1]219-246一文中,指出日本僧人善珠(约723—797年)的《唯识义灯增明记》引用时曾说,最胜子的释论约有500卷左右,但玄奘并没有全部翻译出此部论释,这一点毫无疑问。而法成讲解的《瑜伽师地论》中所引用的最胜子的《瑜伽师地论释》却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完全超出了玄奘所译出的部分内容。所以,法成对《瑜伽师地论释》的引用,除了参考玄奘的汉译本以外,还应该重点参考了最胜子的梵文原本或藏文译本。
三 对蕃本经典的应用
在《瑜伽论手记》《瑜伽论分门记》中屡屡可以看到“蕃本中……”“故蕃本云……”“若依蕃本……”“若于(约)蕃本……”等这样的语句。目前所搜集整理的写本中至少40个以上的卷号中存在这样的情况。这里的“蕃本”或许就是依据了吐蕃已经翻译成藏文的《瑜伽师地论》。以下举例来说明参照的方法。
《瑜伽师地论》第33卷中“复次依止静虑发五通等”[11]814,对应在《瑜伽论手记》(P.2036)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广解中大门第六明神通分六。一总标如论。若依蕃本,无其‘等’字有‘神’字”[10]181,其所对应藏文转写为拉丁文: de la bsam gtan la brten nas mngon par shes pa Inga mngon par’grub par’gyur te。经此比对不难发现,在法成的授课笔记中,指出了汉译本与蕃本之间的差异,前者只有“五通等”,后者则加上了“五神通”的“神”字和不能缺少的“等”字。在确认是藏文时,和“通”对应词语为mngon par shes pa,应该是“神通”的意思。另外,正如法成指出的那样,“等”意味复数rnams,这个词语中在蕃本中却没有。
又如,同样在《瑜伽师地论》卷33中,“复次于有寻有伺三摩地相。心能弃舍。于无寻无伺三摩地相。系念安住。于诸忽务所行境界。能正远离。于不忽务所行境界安住。其心一味寂静。极寂静转。是故说言寻伺寂静故。”[11]824是有关“四静虑”的论述,与之相对应的是《显扬圣教论》中的:“寻伺寂静者:谓或缘离初静虑欲增上教法,或缘彼教授,为境界已;初静虑地寻伺寂静,不复现行。”[12]在谈迅·福慧本(S.4011)《瑜伽论手记》卷33中对于“四静虑”的解释是这样的:“若依蕃本,此四静虑一一皆先标其经句,后方解释。谓大小乘经皆说。言第二静虑者谓寻伺寂静故,内等静故,心一趣故,定生喜乐。于第二静虑具足安住。言成此彼于等者。经云:言第三静虑者,依此离欲,安住于舍,有正念、正知,有身乐受,诸圣宣说具足舍念及与正知,住身受乐依其无喜。第三静虑具足安住,释义如论。言喜者,是第二乱心也。言喜相违心者,谓舍受也。言色身者,前五色根也,言意者,意根也。言第三静虑已上等者。此二门显说诸因也,言下地者,第二静虑已下也;言上地者,是第四静虑已上也,言诸圣者。”[9][13]172显然,在法成的授课笔记中将“静虑”即“禅定”的涵义依据蕃本进行了延伸,而且解释得更加细致明了。同时听讲的僧生法镜笔记中“依据蕃本”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一立因,故论文言。复次,于有寻等也。若于蕃本,此四静虑,一一皆先标其经句,然后解释。汉本虽无,应如是说。经云:言第二静虑者,得寻伺寂静内故、等静故、心一趣故,定生喜乐。于第二静虑具足安住。”(法镜本P.2036《瑜伽论手记》卷33)[10]179。意思是说,汉译本中没有关于各种“静虑”说明解释,在此进行了补充说明。同样依据蕃本进行补充的,还有在讲解至《瑜伽师地论》第27卷时的“四种所缘”之“净惑所缘”时,文曰:“所缘广解第四净惑所缘境事分二:一总问可见,二广大分二…… 此义汉本虽无,依蕃本出说者应知。”(P.2134法镜《瑜伽论手记》卷27)[14]
关于是“六十四种有情众”还是“六十二种有情众”,梵文本和汉文本中记载也并不一致。在法镜本《瑜伽论手记》第2卷中有这样的说明:“第十明,六十四种有情之类分二:一问,二答,三轮王差异,问文可知。答中若依蕃本,有六十四类。汉本之中虽六十二,义具足故。最胜子释中亦六十四。虽四十三中取近住弟子,四十六中取贪利恭敬者,为六十四。”[4]33(P.2061)在这其中,至于到底是“六十四”还是“六十二”,法成先后对照了汉、藏、梵三种文本。“最胜子释”中是怎样的情况,由于此论已佚,无法得到证实。但现存汉文本的《瑜伽师地论》第2卷中确有“复有六十二种有情之类”“六十二种有情众生的类别”之说,在玄奘译出的《显扬圣教论》第8卷中却是“有情界无量者,谓六十四种有情众”[12]。其差异正如法成所说,在汉文本《瑜伽师地论》所列出的第四十三条中将“共住弟子及近住弟子”合并为一类,将第四十六条的“贪利恭敬者”合并为一类,这在《显扬圣教论》中却是分开列出的,于是多出两类。
从藏文《大藏经》和后世的一些佛教著作所编入的译经目录,以及敦煌遗书中汉藏两种文字的著述题记中可知,法成是精通藏、汉、梵三种文字的。正是利用了这样的语言条件,法成在讲授《瑜伽师地论》时,可以熟练地在梵文本、藏文本和汉文本之间交互使用。如论及“明日月宿起之因由”时,法镜本P.2061《瑜伽论手记》卷2中有这样的论述:“十八门中第十五明日月宿起之因由分二:一标,二释。就标中分二:一因,二果。言又彼依止者,依止即是劫初人身,谓劫初时身有星宿渐当而起。言渐者初日出,次月后星星有五谓太白星等,宿者谓廿八宿……七亏盈中言于上稍敌者,月初出时,轮回转近,人之分障,其远分令不见故,但见近分半月论中,彼余分障近分者,此谓梵汉句义前后有异。若于蕃本及详正义,近障于远与理相应。若依小众分别论宗,但言日月远近中间明暗有异。日近于月,其月即暗;日若远时,其月即明。若依最胜子释中,但谓众生共业熟故,敢明其暗,非由远近及以回转。”[4]32从引文的论述中可见,法成先是指出了梵、汉本中的前后是有差异的,又接着说蕃本中对此的定义较为详细准确,而后是其他的小众宗别中是如何理解的,最后指出“最胜子释”中是怎样的观点。这种多个经论版本和各宗派关于同一问题的观点皆被一一罗列出来,其讲解不可谓不详细且内容包罗众象。
另外,S.4011谈迅·福慧本《瑜伽论手记》卷33、34中有“若依蕃本云,如是六种作意”“若依蕃本先标经句,后方解释”“故蕃本云,其身相状而沉于地也”“蕃本云,其心如空……”[13]171-173等对于蕃本的应用比比皆是。
关于《瑜伽师地论》汉藏文本的对照问题,李方桂(Li Fanggui)1961年在《通报》杂志上所发表的(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敦煌的一本汉藏词汇集》[15],就是《瑜珈师地论·菩萨地》的语词摘编,可能就是当时吐蕃翻译家为了统一译语而留下的工作纪录,也是敦煌藏文卷子中很重要的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写本没有前后封面,标题和编者也不明确。李氏研究的内容是对《瑜伽师地论》中的术语、难懂词语进行了藏汉对照的汇编,可以作为藏汉双语对照《瑜伽师地论》的学习资料。根据李氏的研究,这个汉藏对照词汇编中的藏文词汇,与现存的藏文本《瑜伽师地论》中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瑜伽师地论》是否还存在其他译本?目前尚不明确。但上山大峻认为,此写本的笔迹和法成的笔迹有相似之处,属于法成亲笔书写本的可能性较大[1]238。
以上所依蕃本之内容,仅是法成讲经笔记中的典型范例,虽然只是不同文本中的有关词语或是数字之间的异同,法成都进行详细的比对。法成这种精细严谨的治学态度显而易见。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法成对于唯识经论,特别是蕃、梵本经论的熟识,对各种经典理论的结构和意义的把握与理解,并将其应用到注疏和授课之中。
四 法成对梵文音译与语法的解读与引用
上文就法成对“最胜子释”的参考作了叙述,而在《瑜伽论手记》《瑜伽论分门记》还有不少关于梵文音译词语的存在。如P.2061法镜本《瑜伽论手记》的卷3中有这样的记录:“二列数中,文六。谓蕴善巧等,如论。若约梵本,应言应知摄蕴善巧…… 为破此执,故佛世尊说十二缘起。故论文言:缘起善巧。若依梵本,摄字于先。五言处非处者,谓诸有情不了善因能生善果,执无住法见,谓言善因无其善果。”[4]43与之类似的“若于梵本……”“若依(约)梵本……”“梵语……”“梵云……”这样的表述,在法成的讲经笔记中有数回。
一般情况下,在遇到相关的梵文词语时,法成则会采用音译方式,用发音近似的汉字来进行表述。例如P.2061《瑜伽论手记》卷2中:“言正学者,梵云或又尼也。言勤宗者,梵云沙弥。言近事男者,梵云鸟彼索迦,谓五受戒故。女者,梵云斯迦。”[4]34又如P.2036《瑜伽论手记》卷34[10]184中所说的“伊师迦”是梵语isīka的音译,有二释:一近王舍城,有高大山,坚硬常住,我等亦尔。或复有草,名伊师迦,体性坚实,故喻我等[16]。以比喻永不衰坏之事物。又如:在P.2036《瑜伽论手记》卷44中有曰:“言局崛罗香者,梵语此云安悉香也;言遏迦花等者,梵语此云臭香也。”[10]217这里所说的“局崛罗”是梵语guggula的音译,意为安息香;“遏迦花”,又叫阿罗歌,梵语arka之音译,意译为白花。在印度,多以此花之葉在祭祀中使用,所以把它称为“臭香”。同样的,在S.2613中《瑜伽论手记》卷44[17]中也使用了“局崛罗”这一词汇。
但也有例外,比如P.2061中:“言四大河者,无热池有其四口:东方牛口、南方鸟口、西门师子口、北方马口。四河之名皆是梵语,无义可翻,但存本语,谓劫初时于此四河边有四人,于中修道因以为名,烧迦等四,皆是仙人之名。”[4]32又如“初言从铁设拉末梨者,此时梵语,前后无翻。灰水等义,如论所明。”[4]48,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梵语在汉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解释,所以只能照抄过来。
对于梵文音译和语法的解读,最值得关注的是P.3950、P.2061(P.tib783)、IoL Tib J625和周绍良藏《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中都有声明学论著《八啭声颂》{1}的相关内容。前三件文献已有语法和内容释读方面的研究[18-19],周绍良藏《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为北京伍伦2019年春拍首次公布,方广锠先生为其撰写跋[20]。这里面的《八啭声颂》属于加文,抄写于此写本的第八纸。和英藏IoL Tib J625(此写本有尾题:“大编审堪布、译师法成由天竺本译出审阅并确定。”[19]59)相类似的是,这纸《八啭声颂》的首题下署:“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法成讲授的《瑜伽师地论》笔记中有汉文、藏文两种文字版本的《八啭声颂》,为了更明确这一问题,兹转录汉文本内容如下:
八转声颂
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
盛华林有树,其树披风飖,以树推象到,为树故放水,从树华盛发,是树枝甚低,于树鸟作巢,咄咄树端严。
第一显本事,第二知是业,第三作作者,第四为何施,第五从何来,第六由曾上,第七示住处,第八是呼词。
八转声颂一卷[21]
从内容上看,其主要内容是以“树木”为例,对语法学中“八格”进行了说明,简单地说,就是以“树木”为例这个名词的八种变化形式。就语法规则而言,玄奘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3指出:“言八啭者:一诠诸法体,二诠所作业,三诠作具及能作者,四诠所为事,五诠所因事,六诠所属事,七诠所依事,八诠呼召事。”[22]玄奘在这里用“啭”字来指代梵语的一个曲折变化。P.3950《八啭声颂》的汉译本[23]中把“增”当作“曾”,P.2061则是“增”,是对的。“增上”为梵语,有统治者、王者、主的意思。法成则用lhag-pai dbang-du代替bdag,这或可算作是早期的对译词汇的一种表达形式。关于这种属格的变化及关系,印度著名语法学家帕尼尼(Pānini)的《语言结构规则》(Astādhyāyī)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种以树木为对象的特殊的举例方式在藏区曾流行过一段时间,吐蕃时期的译师们基本上都精通梵文,从该论著的语法、举例形式来看,可以肯定当时藏族学者的写作习惯受到天竺班智达的影响[19]57。《八啭声颂》是源自于印度的语法学,这一点毫无疑问。由此或可说明法成所译汉、藏本所依据的底本应源于梵文本。
那么为什么法成在讲解《瑜伽师地论》的过程中,会为听讲的僧生加入《八啭声颂》这一语法学的知识呢?查看原经卷不难发现,加入了《八啭声颂》这一内容是法成在讲解《瑜伽师地论》第2卷时。《瑜伽师地论》第2卷的内容为“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二”,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云何众多言说句?谓即此亦名释词句,亦名戏论句,亦名摄义句,如是等类、众多差别。又诸字母能摄诸义、当知亦名众多言说句。彼复云何?所谓地、根、境、法、补特伽罗、自性、差别、作用、自他、有无、问答、取与、正性、邪性句。又有听制、功德、过失、得、不得、毁、誉、苦、乐、称、讥、坚妙智退、沉量、助伴、示现、教导、赞励、庆慰句。又有七言论句,此即七例句,谓:补卢沙、补卢衫、补卢崽拏、补卢沙耶、补卢沙(多页)、补卢沙娑、补卢铩,如是等。”[11]43其中“七言论句”是关于语言句式论述时举出的例子,显然此“七例句”来源于梵语八种语法中的七种,第八种因为只是词尾的变形,所以未被罗列在内。而对于精通梵、藏文的法成来讲,在讲解到这一内容时,将原来的语法向学僧们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于是《八啭声颂》以汉藏文两种形式,被记录在僧生们的听讲笔记中。僧人法镜在《瑜伽论手记》(P.2061)全文摘录了藏文《八啭声颂》于写本的背面,并且对于“树木”和介词之间的意义用藏文作了注释。
结 语
从以上法成在讲授《瑜伽师地论》时所参考的汉文经论可以看出,法成的佛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吐蕃占领河西初期昙旷的思想,即佛教中的唯识宗。从法成对“最胜子释”、蕃本经论、梵文音译和有关语法的解读与引用,又可见法成对藏文、梵文等吐蕃佛教的相关经论的熟识。所以,在法成的身上体现出了唯识宗与汉、藏及印度佛教的结合这一独特的宗派特色。
《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中多次出现的“故蕃本云”“若于蕃本”“梵语”“梵云”等词句,更确切地证明法成在讲授《瑜伽师地论》时,充分利用了自身语言条件,运用汉、藏、梵三种文本的经论进行对比解读和应用,汉、藏、梵文经论与汉文佛典中的唯识学知识得以互证、互补,从而丰富了《瑜伽师地论》的内容。此外,此敦煌写本文献中汉文和藏文同时使用是藏汉交流的需要,亦是汉藏佛教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例证,其中首次使用汉藏文本所进行佛学的研究,对当今仍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上山大峻. 敦煌佛教の研究[M]. 京都:法藏馆株式会社,1990:219-246.
[2]杨富学,李吉和.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78.
[3]上山大峻. 关于北图效76号吴和尚藏书目录[J]. 刘永增,译. 敦煌研究,2003(1):100-103.
[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4)[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8.
[5]张延清. 翻譯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J]. 敦煌学辑刊,2008(3):78.
[6]大正藏:第65册[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07.
[7]宇井伯寿. 瑜伽论研究[M]. 慧观,周丽玫,等,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18.
[8]最胜子,等. 玄奘,译. 瑜伽师地论释一卷[M]//大正藏:第30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883-888.
[9]大正藏:第85册[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804.
[1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14.
[11]弥勒菩萨,说. 玄奘,译.瑜伽师地论[M]. 精校标点本.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814.
[12]玄奘,译. 显扬圣教论卷第一[M]//大正藏:第31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20.
[13]黄永武. 敦煌宝藏:33[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71-173.
[1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6)[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69.
[15]Li Fanggui.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J].T’oungPao,1962,49:233-256.
[16]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532.
[17]黄永武. 敦煌宝藏(21)[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455-486.
[18]扎西当知. 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吐蕃时期藏语语法解读[J]. 中国藏学:藏文版,2010(1):18-28.
[19]南拉才让.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释不同版本的声明学论著《八转声颂》[J]. 西藏研究,2016(2):57-62.
[20]方广锠. 周绍良藏《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跋[J]. 收藏家,2019(6):97-99.
[2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0)[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77.
[22]慧立,彦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3:76.
[23]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0)[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77.
收稿日期:2021-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藏敦煌汉文非佛经吐蕃文献整理与研究”(19BZS014);敦煌研究院院级重点课题“敦煌本《瑜伽论手记》整理与研究”(2021-SK-ZD-3)
作者简介:彭晓静(1980- ),女,江苏省徐州市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代宗教与敦煌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