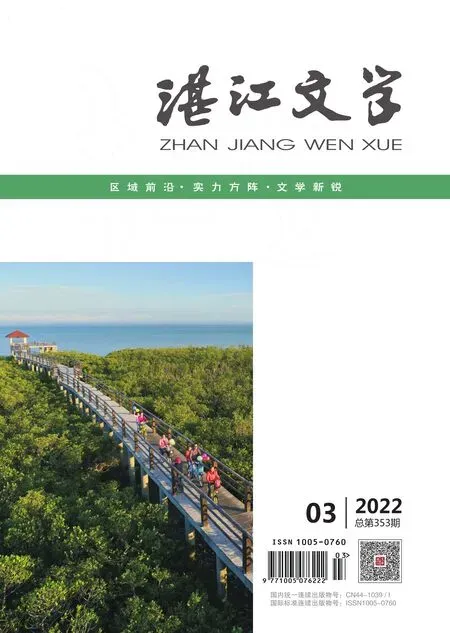故乡谣
◎ 王贤友
我在故乡的风中
我在故乡的风中,不是在写生,我要在大雪覆盖小路前,推开虚掩的门。
已是雪花飞舞,少见行人,偶遇一位满头白色的老人,像是对我说,下雪了,鱼比前几天贵了一些,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这条路,从茶棚老街向前而去,可抵达巢湖,但我走了一小半,就要转弯。在路的两边,一边是干枯的河,一边是抛荒的庄稼地,连接田地的是老旧的房子。不论是开裂了的砖墙,还是旧式的房子,或是随地势而起伏,或是孤立,那些紧闭的窗子,紧闭的大门,使我无法确认是谁家?
纵然是一级美术师,这时一定也会像我:失去动笔的欲望。
因为,画中的线条是作者的心情,心有柔情,则缠绵;心有怒气,则狂癫。而心境如水,只有待风撩拨。就在我疾步时,身边的柳树在风雪中,或仰,或府,或忧伤,或激奋,我不知缘何心中,竟然有泪欲落。
移动的云团,堆积着,似崇山峻岭,而眼前的路,白得刺眼。身后的天空,低矮。正在行走时,又遇见了一位老人,他似乎认识我,就笑了: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回来了?
有一股冷气瞬间袭击心腹,感到整个世界“好冷”。
细小的脚步声,在雨雪中像一面小鼓,发出一种天之韵。如果有人用心来听,会听到,会听懂,但不全是人间之声。
草草地吃了一顿饭,还没动身,就觉得肚胀,没敢说,就忍着。她们也没有深问,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
迎着风雪,我们在村囗告别。在我上了车子,走了一段路,见她还站在那里,不免有了些许悲伤。虽然,我知道,纵然再有飞雪缠雨,纵然我再回故乡,也不会“再见”了,却没有忘掉她。
一晃几年就过去,多种梦,常常涌来,有工作上的难心,有学术上的苦心,有人事上的痛心,但枕上的日子,还是故乡的鸡鸣狗吠,乡邻们的声音,多一些。
每到这个时候,就想回到老宅,写一写《归来兮》,这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愿望,可一个“拆”字,让梦醒。
就在飞雪扑鼻时,村里的干部打来电话:回迁房已动工了,我又是落下了泪。
这声音,我听到了,就听到了故乡的呼唤,便似听到了天之籁……
遥远的石头
那年,那天,见过一位漂泊的少年,他的眼睛很漂亮,像海边被浪花涮洗一千年的一块石头,用有神不如用暧昧,瞬间就可以打开重重的心门。
那一年,我回巢湖之畔的滨丰村签字拆迁,就遇见这样一块石头,像敦煌石壁上的那一块,不过有些破损,但很坚硬,在这上面,有断断续续的文字,深深地刻着滨丰村的历史,坚韧地表达了一个村庄里男女老幼对人生的困惑和对生命永恒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的渴求。
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永恒不过是学术郎中口里的八卦,不靠谱。但人们还是迷恋永恒,就像盖房子,用石头打墙基……我不敢对乡亲们说,如果不是文化的石头,就并非坚不可摧。眼前一栋栋房子,在推土机面前,如羔羊。在岁月的浪涛中,不是文化的石头,都已经是裂开了,或是只是残块和断片……
那天,这位小伙子,我的后辈,用手坚强地拉着他呆痴的父亲,另一只手紧紧地推着车子,弯曲着身体,却昂然向前,皮肤黑嫩,血管鼓胀。我仿佛以为他是小盛?小钱?小方?小马?……这是古老土地上的一片风景,也许,他面前的村庄,就是一座被拆毁的博物馆?或许是一件残缺的古物……
在我回望被岁月风暴席卷而去的村庄时,有一种感觉涌出来,残缺,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还有一种沧桑感,那就是时间的指针,被加速了。这时,那块蠕动的石头,就一点一点地被剥落,被斑驳,也就朦胧了起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岁月感?
这是壬寅春节快来了,那些古旧的事物,让我心烦。比如捆起来的旧报纸,成堆的书籍,被灰尘覆盖的摆设,被世俗的故友,还有自己手背上的沟一样皱纹,还有额头上那根飘动的银发,都不能复原了,都有了岁月和人间的陈色,似乎也少了美感,有了一种空谷无烟的意味。
时间,是没生命的一件古物,对谁都冷酷,不信,你打开看看,记录的是不再美丽的年轮,谁想把古物翻新,谁就更愚蠢!
在我们村庄的入口处,有一块石头,有时长一点青草,有时蹲着一只青蛙。多少年了,不知道。
在这块石头上,有一丝若现的车轮般的线条,我以为,这象征着大自然的生命,象征着生命的成长,象征着生命的孕育之力量,雪落其上,透明的,绝无任何杂质,也无杂音。
倾听,就使人随时感知大地的生命的韵律,内心也有了一撮火在燃烧。
所谓故乡,只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罢了。这是威廉·乔西所说,是不对的!
大年跟前了
大年跟前的近义词,是年关。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半是迫切的等待,多半是岁月的迷惑。
大年跟前,不是暴风雪,就是阴风撵走树上的鸟儿,还有别人家杀年猪,此情此景,有的已销声匿迹,有的还在,但,年味更淡,却是无可争议的。
这种无可争议,就是说人们多半默认了这更淡,内心也许有几份抗议,但终竟随波逐流了。
年关,与红色是一种绝配,门,窗子,还是要贴上传统的春联。这春联,也在变化,由印刷到手写,由分不清上下联到掌握平仄而区分了。
红,是一种喜色,所以在雪中飘舞的红灯笼,与那洁白的雪,形成极大的反差,这其中有无别样的寓意,那是民俗了。
年三十夜晚,就是眼皮打架,一听到鞭炮,就豁然开朗,所以,现在人,过年基本上都是晕晕欲睡,提不起劲,提不起神,给长辈拜年,给晚辈压岁钱,全然是走过场,少了味了。
三十的年饭也好,大年初一的午餐也罢,少不了一道菜,豆腐果炒白干,其象征“老带少”,代代传。但现在,这道极简单的菜,已不见了,民俗之意,也就断了……
那时过年,极讲究,一是接祖,二是祭神。一者不忘“我从哪里来”,二者是旧时中国人生活太苦,又缺少科学知识,想请神仙来“帮一帮”,这是安慰自己,也是宽慰!
年,是“中国结”,虽然我们不十分理解这种中国符号,大年跟前,还是说:新年,好。会不会好,那是另一回事了。
望着窗外雨雪乱飞,抬眼一见,高高的灯笼和红红的门对映红了天……我的眼角泛起别样的喜悦!
一言难尽
我独自沉吟了好几天,还是决定写一点文字纪念已逝的岁月。
所谓沉吟,就是不想写别人或是自己已写过的二三事,那就写一点零碎的,与我个人有关的,认为值得说说的。
这又有几份为难,纯粹是个人的,别人兴趣不大;千篇一律的,别人兴趣也不大,所以,还是不能板着面孔,因为人们喜欢听听闲话,而又不是闲扯的东西。
这几年,可说的事,很多,但不一是找到出处的,往往是经历苦难与挫折后,还可以保持旷达的心态,去实现自己没有忘却的理想。在这期中,无数次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明月却装饰了我窗子,使我想起童年的月色下的乡路,有了珍惜人间美好的情感,虽是一刹那的,但却知道,人可以背离故乡,却忘不了故土。
就在我几近陷入梦里不知身是谁时,有幸一脚踏进合肥之西南的庐州文化村,在姜夔旧影里,我仿佛见到诗人仰头远眺,滴下一粒硕大的泪珠,是重逢的惊喜?是别后的思念?也许是触景生情:泥土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纽扣,是愉快与兴奋的场所,那种泥土的滋味和泥土的气息消失殆尽的地方,怎么会有结满果实的植物把身体挺向太阳的信仰?怎么会有对大地感恩后的报答?因为,泥土是有生命的,是孕育生命的……
所以,我坐在澡雪轩的小窗前,仿佛看到雪花长着翅膀,和那年长着翅膀的蒲公英一样,给了我生命的翅膀。
但翅膀用来飞翔,不是用来背井离乡的。
现在我感到气味的寒冷,没有香气,有刺激心肺的油腻味,像蚂蚁钻心。
过往的日子,记得也好,最好忘掉,人间哪里有什么永恒?李清照说:“应是绿肥红瘦”了。
我们清醒的日子少,浑噩的岁时多,你问我,恰如苏格拉底的名言“你问我知道什么,我最知道的是我不知道。”
见到那些面容原本干净的人,非要挖空心思给自己涂抺上颜色,去做生活的小丑,似乎去挣什么身份,其实,这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抄袭”,没什么读者,观众。
在人生的路途上,我与魏先生一别已过十余载,一日在小巷子口遇见他的儿子,十分感慨,而事后,有人说到他:一看又是不懂人情世故。我则认为:在他的身上可见魏先生的流风余味,我十分高兴……
有感于此,我写下了《萨都剌诗情为谁涌动》和《子胥台前凭吊谁》,也许一言难其中味,算是辞旧迎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