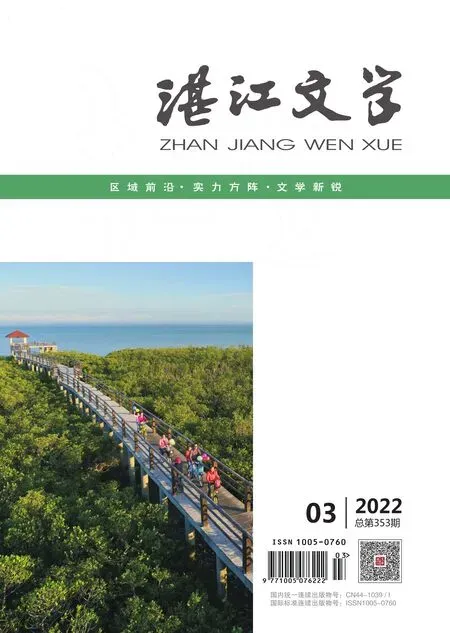生命的异化与心灵的焦灼
——评林登豪城市题材散文诗
◎ 崔国发

在林登豪的散文诗谱系中,城市题材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与其他写都市题材的散文诗人不同,林登豪以现代人的独特视角,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别具一格的、新的城市话语系统。他对于当下城市复杂的、多元的、斑驳的镜像有着自己的观照,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与事物的新变有着丰富的敏感,将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内心世界中的深层意识,凭藉富有表现力的意象和情境,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的城市题材散文诗,不仅介入到了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介入到了城市发展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介入到了书写城市的现代散文诗发展的内在的深层的要素,而且深入到了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本质进入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其对城市生活中高度的人性关注与精神沉迷,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从自然的传统诗意中走向城市的人们的现代经验和现代人的情绪与感觉,对城市的各种喧嚣与多种语言的哗变所造成的激烈的文化冲突和生命的异化物化,于灵魂的焦灼与审美的挤压中,进行了形而上的理性追问和诗意的重建,艺术地勾勒了一幅现代市井生活的心灵史与流变图。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登豪便开始了他的城市题材散文诗的创作。虽然那时的他曾经有过对于乡土的美好追忆,有过对于自然山水的体味吟唱,也有过对于花鸟虫鱼的热情讴歌,并且在这方面为我们奉献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但从他所出版的散文诗集《边缘空间浓似酒》便看得出来,登豪对城市题材日见深切的介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纯粹的城市题材在他的这本散文诗集中虽然篇幅有限,只有十几篇,但篇篇精彩而绚烂,成为他的散文诗创作新的“亮点”和最重要的“增长点”,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也是能够产生强烈共鸣与心理认同的“兴奋点”。王光明、孙绍振、王幅明、南帆、邹建军等名家纷纷评论,从林登豪致力现代经验的艺术整合、寻找都市叠影的复合感觉、感触心灵世界的矛盾反差、探究如谜的人生况味、索解隐喻的丰富歧义、捕捉声色的感觉意味、戏谑反讽的沉重深刻、孤独情致的自由抒放等方面,对他的城市题材散文诗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褒扬举荐。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在散文诗批评专著《审美定性与精神镜像》中,对林登豪城市题材散文诗也有过专节论述。在我看来,他能以多维度的广阔视野,观照城市与人生,在艺术的边缘空间,铭刻着让人心怦血沸的现代经验;他对于现代都市人的生存本相和心灵独语,坚卓扎实地建立在生活的本真之上,深层地呈现现代感、生命感与艺术意志,在先锋密码中隐喻自由的意蕴、新颖的语境和面对都市文明弊端的那一种影响的焦虑;他的城市题材散文诗艺术地再现了城市中某些生命的异化与心灵的物化,犹如神明的符咒和词语的魔术,于超常、超前和超我的诗美空间上显影灵魂,使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出世与入世、日神与酒神、城之底片与心之镜像等,在诗美创造的深层上融合为一。诗人感到城市节奏、声音、色彩、旋律的延伸、颤动与淋漓,每每站在高楼上鸟瞰或俯望,坐在酒吧与咖啡座上覃思或遐想,漂移自己的心路历程,表现迷幻的情感与人生,实现城市题材散文诗美学的革故鼎新,由欲望与情感的层面,向哲学与理性诘问的层面进入,探索从城市生活到文化精神心灵升华的诸多可能性。我以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红尘滚滚、市声喧嚣、心灵浮躁的当下都市,像林登豪这样能够超越功利写作散文诗,本身便具有高雅的、净化的、文化的、审美的意义。
让我非常钦佩的是,一直以来,林登豪在散文诗坛标举着城市题材散文诗创作大纛,他的此类散文诗不仅数量与日俱增,而且在质量上也突飞猛进。他告诉我,即将出版他的城市专集,并把他积年所写的精品力作示我,让我有幸先读而大快朵颐。曾几何时,我们的一些散文诗人,太过注重于山水游记与自然风光的描摹,太过注重乡土与田园牧歌的沉醉,太过注重季节应景与政治话语的演绎,太过注重浮生物语浅显哲理的阐发,太过注重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式的平铺直叙,当然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写这些,但是大家一窝蜂地上,同质化与相似感便油然而生,倒是那些着眼于城市化、个性化、生命化、心灵化的文字打造出了良好的艺术生态,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著名散文诗作家许淇说,散文诗从它一出生便打上现代都市的胎记,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就是写城市的,写城市的各种文化心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以写城市诗而闻名的诗人宋琳说,他从福建乡村考入上海的大学,进入都市生活的感受就像波特莱尔的那种经验,认为都市生活环境对于一个现代诗人的意味就是“震惊”,本雅明也特别总结了一种“震惊”的经验。诗人无疑是自然之子,对大自然的感受是一种天赋,尤其是乡村生活赋予诗人以生命中源头性的东西,大家对这类题材趋之若鹜,一直以来出现了不少经典性的作家,今后可能还会出。但是人一旦进入都市,他的诗歌或散文诗从自然或田园发展到进入城市这样一个空间,它在美学上和诗歌感性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宋琳所说的对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散乱无序的生活细节都充满了一种好奇。漫步街头,一旦与城市有了亲密接触之后,于独特的情感体验中往往就会产生创作的新的灵感,产生主体特有的意绪与审美的感觉,产生现代生活激撞内心的那种苦思焦虑与紧张迷惘,散文诗正好能适应这样的衍变与嬗递,从而更好地表现出现代生活中现代人的潜意识和深层意识。因此,都市不仅仅是空间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有别于乡村文化的异质性,对于我们来说,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新质,这些新的东西和新的隐喻,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体系,它是那么的耐人寻味。对此,林登豪有着他自己的深刻理解,我注意到了他的诗观是这样表述的:
“从自然中走来,却不断被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所异化,尤其是在科学理论高度张扬的近代社会,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使人类沦为失去灵性和个体的群体,人的感性倍受严重的肢解。为了对抗这种强大的异化力量,寻找自我的形象,生活在这个时代拥有存在意识的人就必须从贫乏的外部世界回到丰富的内心世界中,通过内心世界碎片般的回忆,重建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我。”
从诗人对于现代城市理解的深刻性上来看,林登豪正是以自身的都市遭遇为切入点感知到,远离了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在他的散文诗中呈现,他发现城市和城市中的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所异化,过去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和谐、宁静、纯真、朴素已不完全存在,传统的古典的诗意在字里行间渐次消解,人们擦肩而过的只是速度、节奏、力量与声色光电,是高度发达的交通和信息业,长期使用电脑还导致有的孩子连汉字都不会写了,更遑论人的想象力的丰富!非诗化、物质化等科技层面对人的想象力与灵性的解构,与诗人在新的城市化的变异空间殚精竭虑地对感性与诗化的东西的建构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诗人提出,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新的城市语境中开始自己的探索,从对城市文化的光怪陆离与城乡心态的严重失衡中找到对抗与重建的路径,它或许就是碎片般的回忆,或许就是戏谑与反讽式的接受,或许还是别的什么。要想寻找到一个自然、完整的自我,就必须想方设法去完成散文诗中的城市话语从感性向理性、从外在向内心、从静态向动态、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根据以上对他诗观的解读,我们不妨来看看林登豪的城市题材散文诗书写是怎样实践他的诗歌主张的。
城市是人类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某种角度上来考量,它既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和标志,又是我们面对时难以看透的迷宫式的空间。作为生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城市人,或者像美国诗人爱伦·坡所说的“人群中的人”——他们在林登豪的散文诗里,可能就是——走进城市的爸爸、阳台上浇花的老人、丈量着乡村与城市距离的打工妹、盯着屏幕行情的股民、睡在犹如伪劣产品的工棚中的农民工、把灵魂典当给都市生活在围城里写作的诗人、如一群又一群的工蜂涌动着的熙熙攘攘的上班族等等,无论他们是从乡村走进城市,所目击的东西由自然意象转变为城市意象,还是一直在城市土生土长,他们所感觉到城市发生改变的,由“过去时”的意象转变为“现在时”的意象,都好比是一尾尾游动在城市波涛中的“鱼”,出没于登豪散文诗所写到的那些丰富而又复杂的空间或场所--城边站台、地铁、喝茶的斗室、广场上的酒吧、街心茶楼、露天大舞台、阳台、电梯、高楼、天桥、工棚--貌似包容性很强而让人深入其间自由出入的这座城市,一度成为人们追求的现代性理想与现代文明的寄托,也许他们曾经喜欢的事物,那些标志着城市符号性的东西,在登豪散文诗的及物写作中显得司空见惯--残缺的线装书、PK时髦的狗类宠物、逆光中的古榕、灯海中的红帆船、都市的屏幕、脚手架、袒胸露乳的大楼、轻轻搅动的咖啡和葡萄酒、泼水节的水--在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地、事、物、情、景所折射出来的都市化色彩中,那些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发展后对自己面临的生存处境,无不使我们感到身体的疲惫、心理的困惑和灵魂的压抑,无不使我们在感触到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整个城市的关系的难以把握与处理,无不使我们在主动适应与介入城市的变化之所不堪其忧的那种杂乱的纷扰、主体的焦虑和被异化的感觉。像“一座座狂妄的夜总会,犹如一个个吝啬的国王,不肯分给我立锥之地。”(《都市叠影》)、“我正在语言的迷宫前发呆,高楼上的落体砸伤了我的影子。”(《父亲走进城市》)、“城市还在滋生长舌女人的流言蜚语;人行道上,贪婪的目光如子弹,扫射透明的神秘,丰富了一种诱惑。”(《城之底片》),无论是夜总会的“狂妄”、高楼上落体的“惊险”,还是市侩的流言、目光的贪婪,都给人以茫然所失、焦躁不安、迷离恍惝之感,城市既因为“丰富了一种诱惑”而使人感到理解、亲近与包容,又因为“吝啬”“迷宫”“神秘”,又使人心生抗拒、对立与繁复之感,这种对应与对抗的纠缠、对立与统一的交织,精彩与无奈的杂糅,正是现代城市人当下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林登豪散文诗中的人,常常以一种异乡人和流浪者的角色,与城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客居在城市的边缘,置身于社会底层,以他们的艰难困苦与对生活酸甜苦辣的多重体验,经由对生存真实与当下生活的反思,来进入人的现代境遇和内心世界的观照。《打工妹》一诗这样写道:
“走进租来的十几平方小房间,拿起桌上的镜子,认真地端详自己。/最担心自己不认识自己。/坐在流水线前,舞动无法缩回的双手,心流疲惫,金属反光她们无精打采的脸庞。/面对灯红酒绿,有不少人被都市言中羞处。/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
跨进陌生街区的打工妹,以城市暂居者的身份展开与这座城市的全部关系,她有着“青春的色彩”,在流水线前,她感到十分“疲惫”和“无精打采”,偏偏又遭遇到公司倒闭,“两手空空,钱包空空,心灵空空”,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反差和理想落空。不仅如此,她还可能在“灯红酒绿”面前,被七彩霓虹和漫天酒气所羞辱。面对都市新鲜的刺激和物质化生存的潜规则,她是非常的不适应,甚至于揽镜自照,最担心“自己不认识自己”,又“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乃是一种酒色人生对自己生命的侵扰,她游离于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一直以来为她所珍视的纯洁、安宁、尊严以及那个“自然的”“完整的”自我仿佛已经“丢失”,极度膨胀的自我喊叫,耽溺肉欲的颓废呻吟,凡俗化的市民狂欢与戏谑,使她变得无所适从,又难以抗拒。“意外的奖金催促打工妹走进‘服装世界’,时装令人眼花紊乱,走出商场大门,模特身上的服饰已在自己身上。”打工妹对城市的态度便是这样的复杂与暧昧,她似乎无法与城市决绝,也无法向现代工业文明妥协,虽然未来不可预测,但她无意挣脱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相互纠缠的关系,“爱拼才会赢”,也许她现在还想在城市继续打拼一番,那双“隐形之手”,虽然抹去她不少青春的倩影,但也仿佛在向她发出挽留式的召唤。
“爸爸终于走进了我居住的城市/穿着那双舍不得穿的解放鞋/而今,我爸爸用电动刮须刀,旋转着剩下的岁月,他经常在日光灯下凝视着自己粗糙的双手。”(《爸爸跨进家门》),走进城市的父亲,从小镇人到城里人的角色转换,从古典情结向现代意识的蜕变,诗人通过两个细节--穿着那双舍不得穿的解放鞋、用电动刮须刀旋转着剩下的岁月--便已完成了从“城市的异己”向“城市的同道”转变的表达。记得诗人树才说过,城市的经验需要有更多的肌质和肉感的细节来真正把一个诗人在城市的体验表达出来,一些城市生活的细节还需要像细节的发生那样被揭示出来。我在想,登豪是一位对城市生活有着非常独特体验的诗人,写都市散文诗正需要像他这样富有经验的沉淀,厚积才能薄发,有了现代经验,才能在散文诗中锲入富有表现力的话语深度。“没有耐性的灯光,闪烁出我爸爸的一圈圈年轮,我的记忆沿着父辈的足迹,沿着城市的皱纹,一级又一级地攀登着。”城市是通向现代的唯一通道,都市的各种质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习性与品格,那些小镇和乡土上的人和事,已由父辈带给自己的记忆中,也许对于那个乡镇的体味在多数时候也只能深深地留在回忆中了,现代的城市生活经由一定的调整与塑造,在“我”与“父亲”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生活印记。下面这首《这个人,这个人》,正是能够凸显诗人都市散文诗诗学主张的精粹之作:
你见过这个人,我也见过这个人。
你大概在乡下见过这个人,我大概在城里见过这个人。
你见过他一面,在深山老林中,再看他一眼,四处静悄悄;
我见过他一面,在都市的熙攘中再看他一眼,只千人一面。
你见过这个人,在梯田中挥动锄头,他不时停下来,擦一擦眼屎,近正午时,又掏出旱烟袋,一次又一次地吸着气。
你再寻他时,暮色已越来越浓,四周无一人,一股股炊烟,越升越高。
我见到这个人,在昏沉沉的舞厅,他用手臂勾住邻座,音乐响起,他贴着她,她搂紧他,前一步,后一步。
在子夜、在烟头明明灭灭里,在长城白葡萄酒味中,他不知道自己自何来,向何去……
我再寻他时,东方透出鱼肚白,突然,连自己都不见了。
连“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更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抑或是从乡下走进城里的人?“这个人”我们似乎都见过,但是,“你”见过的是“乡下人”,“我”见过的是“城里人”,最后“我”在茫茫人海之中再寻“这个人”的时候,不仅没有找到“他”,连“我”自己也丢失了。作为一位20世纪五十年代出生、曾有过插队知青的经历、后又回到城市的登豪先生,对乡村和城市的理解都可谓刻骨铭心。但凡人们在乡村的时候,都向往和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进入城市,一旦进入了城市,虽不再想回到乡村,但就像诗中的“这个人”,当他遭遇城市生活中那“熙熙攘攘”(过于喧闹)、“千人一面”(个性泯灭)、“昏沉沉的舞厅”和搂搂抱抱(戏谑狂欢)、“烟头明明灭灭”“长城葡萄酒味”(空虚寂寞)的时候,心中涌起的是浮躁、紧张、动荡、焦虑、空虚、寂寞、冷漠等情绪,此时此刻他会情不自禁地又怀恋起乡村的“深山老林”“四处静悄悄”“梯田”“炊烟”等这些自然朴素、安宁平静、和谐温暖的事物。在“非线性、大信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受到城市逼仄空间的挤压与各种斑斓色彩、斑驳意象的炫惑,很容易丧失“自我”,——因此,“我”在寻“他”时,“突然,连自己都不见了”,不是一种或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结局。生命的异化与心灵的焦灼于此可见一斑。
林登豪城市题材散文诗便是这样,都市里“人群中的人”成为他创作的全部背景和灵感,他总是带着现代经验进入诗的语境,在城市生活的密度、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创新、变异和拓展,深刻地揭橥了城市对于人的生命的异化与物化所产生的歧变。在一个以娱乐、快餐、时尚盛行而诗意与理性缺乏的消费时代,诗人的都市话语,却渗透着心灵的焦灼与忧郁,蕴含着新的精神内涵、丰富的情绪与多元厚重的特质,在道德自觉与文化自省上具有一种醒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