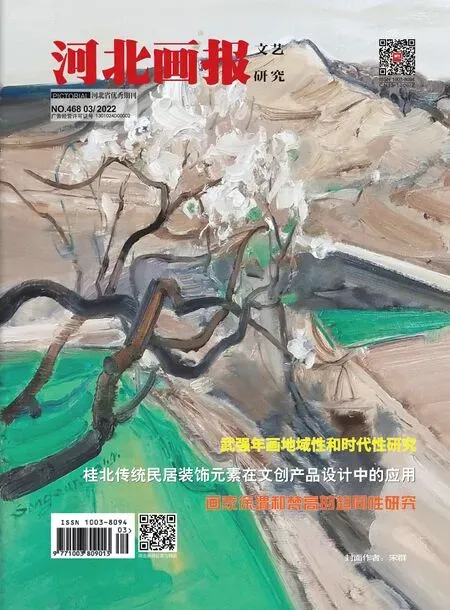新兴木刻在桂林的图像场域和意义生产
——以赖少其的木刻作品为例
黄静玲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
二十世纪初期至三十年代末,中国画坛中存在着各种流派混乱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既有深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又有没能创造新时代精神的中国画,这些绘画被当时的进步人士认为是一种脱离“现实”且“聊以自娱”的方式。新兴木刻运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由鲁迅倡导带领下的一批青年的艺术家们开始思考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找寻艺术的出路。所谓的“新兴木刻”,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木刻技法,在鲁迅出版的《艺苑朝华》中他明确指出“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另一方面新兴木刻运动也是要将广大劳动人民作为画面的主人公,反映表现他们的真实生活现状。
韩丛耀[2]提出因为图像同时具有技术性、构成性和社会性这三种形态,因此,在分析图像意义的产生时需要考虑三个“场域”①,分别是“图像制作的场域”“图像自身的场域”和“图像传播的场域”。新兴木刻作为一种特殊的图像,随着木刻家流动进入新的传播场域中,是否在形态和传播上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本研究对新兴木刻的制作场、图像场和传播场进行分析,同时,以木刻家赖少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木刻作品为例,探究文化场域视角下新兴木刻在桂林的意义生产。
一、制作场:用“刻刀”代替“画笔”
所有图像再现都是通过某种方式制造得来,新兴木刻也因为其制作材料和生产过程而具有特殊的本体语言。“木刻”最早指的是“木板雕印”[3],指的是一种木板雕刻的技术,后来概念慢慢转变为“通过在木刻刻版并经由印刷而得到的图案”。这种雕版艺术在其制作过程中包含了很多技巧,而创作者仅仅通过线的交错和点的聚散中就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形态[4]。现代木刻在创作中往往会追求木刻媒介自身特点,注重艺术家个人特性的表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便是将木刻作为一种大众的艺术,再加以学习西方现代木刻技巧,从而来表现当时劳苦大众生活、传递民族精神的。
木刻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适合中国劳苦大众的艺术,是因为它本来就诞生于中国。最早的木刻作品是清末时期敦煌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扉页画(见图1),绘制的是佛祖在抵园为须菩提长老说法的情形[5],上面刻着“唐咸通九年”几个字,证明了早在公元八百多年前我国木刻的技艺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而因为石印等西方印刷术的诞生的传入,中国古代木刻发展到清末民初时濒于灭亡。自十四世纪传往欧洲的木刻却成为西方人“文明的利器和印刷的祖师”[6]。后来英国艺术家毕维克发明了一种木口木刻,这种技法打破了把黑轮廓线作为主要表现方式,使木刻能够表现出从黑到白的不同灰色,从而雕刻出更为精美的画面(见图2),因此,在十九世纪基本替代了传统的木面木刻。新兴木刻运动便是希望青年木刻家能过吸收这种技法,创作出更具有力量的木刻作品,这也是为什么鲁迅会指出“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

图1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扉页画

图2 毕维克《鹿》
如果说现代木刻在创作中追求木刻媒介自身特点,注重艺术家个人特性的表达,那么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就是学习西方现代木刻技术的,用来表现劳苦大众生活、传递民族精神的。在创作时,雕刻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的,并且中西方的刻刀,有不一样的效果,据赖少其1934年的文章所记载:“西洋用的木刻雕刀,柄很短,可以拿在掌心,用拇指及食指执刀头,刀身几与板面平,用腕力压去,以刻曲直线。但在东洋用的斜口刀,拿时多与版面成直角,即把刀柄拿在掌心,竖直按在板面上刻。这两个操刀的方法都是正当的姿势,但后者,握东洋的法,刻出来的线是比较爽直而有力。西洋用腕力平刻是比较自由。”从他早期的作品(见图3、图4)中可以看出他创作时洋溢在刀锋中的艺术激情和力量感,因而可以判断他创作时更倾向于用东洋斜口刀,正如他认同的可以将外国作品作为提神木刻技巧的“借镜”,最终目的是创造符合民族特色的中国自己的艺术[7]。但是同样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构图还较为简单,技法也很生涩,在风格表现上有很浓厚的欧洲版画的影子,还没有创造出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

图3 《孩子死了》 1935年4月15日

图4 《浪子》 1935年6月15日
桂林的木刻活动,在赖少其负责的木协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得到蓬勃发展,办刊物,举行画展,发展木刻教育事业,还在1938年底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作品三百多幅,可惜开幕不久即遭敌机炸毁。在目睹这场敌袭后不久,赖少其创作了一幅木刻组图《母与子》(见图5)发表于《救亡木刻》创刊号上,配文中完整版记录了一个普通的农妇在孩子被敌机炸死后由不可置信的痛苦到绝望死心的转变:一开始母亲仅仅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然而敌机却炸毁了她的孩子,配文中出现的“警报”“敌机”和图像出现的“大火”都像是还原了赖少其当时经历的那场敌袭,母亲“就这样守着孩子的墓地过了一天”也与《火中的木刻》中赖少其自称为“守墓人”[8]相呼应,只是他将自己换成了更能够诉诸同情的母亲形象,被付诸一炬的木刻乃至桂林城被拟化为孩子的形象,深深地表达了作者的悲愤、痛苦与无奈。虽然同样画的是母亲和孩子的题材,但是对比他此前同类题材的创作可以发现在创作技法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在视觉修辞上融入了更多民族的元素,并且加入了更多的故事性。

图5 赖少其《母与子》
二、图像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创作
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就开始用图像进行表意。历史上有一派学者认为对图像的分析可以解读出“时代精神”,例如,波蒂切利笔下的维纳斯,代表着一种师徒突破中世纪宗教束缚的“奥林匹斯山式”的自由的象征。潘诺夫斯基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2011)中提出了著名的图像学研究“三段式理论”②,在分析图像自身场域时,更像是一种“图像志分析”,需要充分考虑画面内容构成了何种主题。赖少其在1932年考入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但在求学期间被新兴木刻艺术所吸引。在1934年,他参加了老师李桦组织的“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积极创作木刻版画,此时的他会创作一部分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见图6),但是同样会有一些装饰性较浓的藏书票或者小资产者自由主义风格的作品(见图7)。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赖少其会侧重处理画面中的人物、配景,注重画面的“统一”和“变化”等。

图6 《光明来临了》1936年

图7 《都市里的男人和女人》1934年
在桂林继续美术运动的赖少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改变,他总结了1934年以来漫画和木刻创作上的经验教训,认为以前“一部分的漫画是没有一定的目标和路向的,纯粹是小资产者自由主义的作风……”[9]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战士英勇的姿态,表达民众愤慨的情绪的漫画与木刻取而代之;在创作上也不应该过于强调形式,以至于内容的选择迁就了形式的表现,相反,应该是为了表现大众的艺术,而选择“现实主义的作风”“旧形式的利用”和“以及民族作风(即中国气派)的建立”[10]。
因为木刻是一种与实际应用关系最深切的艺术,所以赖少其在木刻创作上十分注重与社会、大众紧密结合,注重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例如,自古以来大众在庆祝新年时都有寄贺年片、在门前张贴年画的习惯,因此,利用大众这种心理与习惯,赖少其在1938年冬于桂林创作了一副以年画为题材的套色木刻,在其中融合了传统民间年画的题材、藏书票或图案设计中的精致图像特征和当时桂林人民的日常生活元素,精心安排整理从而传递出年画的趣味。这幅大家日后都耳熟能详的经典套色木刻年画由当时桂林行营政治部大量印发,五色套版,共印了十多万份,遍及城乡各地,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赖少其在桂林时期创作的木刻作品除了描绘大众的生活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罗兰·巴特[11]对当时法国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进行了符号学的分析,解构出了两层符号系统构成的“神话”。以《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见图8)为例,这些可见的线条和黑白分明的颜色是可以通过视觉系统直接识别的能指,勾勒出的所指正是一个个年轻“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坚毅的脸庞中都是爱国之心的自然流露,他们眺望着远方,向所有的观看者传递出坚定不移的信心,也就是那个时代需要的“神话”。

图8 《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1939年
三、传播场:依托于报纸的大众传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为桂林位于祖国大后方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上千文化名人、美术团体甚至出版机构都聚集在桂林。李桦、黄新波、陈烟桥、丰子恺和刘建庵等艺术家都在桂林进行了艺术创作和街头艺术展,给桂林本土艺术家带来了先进的艺术思想和观念,推动了桂林美术运动发展的高潮。著名版画家鄂中铁曾这样评价桂林文化城时期的美术界:“当时的桂林,由于政局的演变,已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美术’力量比重庆强得多。”[12]桂林也因此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中心。纵观整个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可以发现,有几个美术机构在桂林文化城的美术事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艺术机构都仅仅是在美术界内部展开活动。
要达到面向广大群众进行图像传播的目的,还是需要用到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刊物。因为舆论具有不可见的本质属性,因此,大众媒介一直被当作沟通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图像通过这种“移动宣传”的载体,能够实现快速的传播。报纸刊物的流动性很强,除了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受众,还面向国际社会。当时在桂林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二百种,赖少其作为全国木协在桂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桂林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漫画图像,并发表在当时流行的报纸刊物上,从而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图像不是静态地处于被生产出来的阶段,而是始终要走向观看者,因此,分析图像的传播场可以更好地理解图像意义的接受问题。从图像的社会性构成来分析,虽然有些图像中有相对固定的视觉元素和构成形态,但是因为一些隐藏在画面中的涉及历史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信息,可以使得不同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的观看者接收不同的信息。例如,赖少其在以母与子的视觉元素进行创作时,在画面细节、人物关系乃至用笔习惯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不同,这便是考虑到不同受众对于图像有着不一样的阐释图示,而这一点则是从以往观看者给出的反馈信息而来。在这种创作者与观看者的潜在交流,则慢慢建构出一种有机的“创作—接受—再创作”的图像意义生产逻辑。
注释
①这一概念最早由布尔迪厄提出,后由韩丛耀将“场域”概念引入图像研究中,可以此为单位探究图像的意义生产和背后的种种关系。
②第一层次的“前图像志描述”主要是一种风格形式的分析;第二层次的“图像志分析”是从图像的类型史(或母题)与主题进行分析;第三层次的“图像学阐释”开始分析图像的深层含义、隐含义及与时代精神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