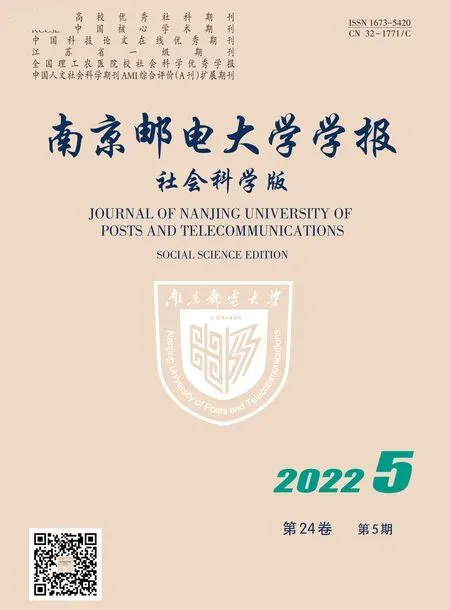近代中国邮政与国家符号生产
熊玉文,张 瑛
(1.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自从被迫打开国门以后,近代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由家族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近代中国邮政作为国家通信基础设施和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公共服务机构,不仅为国民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系网络和最便捷的交往通道,而且深深参与了国家符号的生产。它既通过国家权力裁撤传统的驿站、民信局和外来的客邮,实现邮权的独立和统一,又通过邮政网点和邮票等方式扩大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空间,将民众的邮政需求纳入国家认同的集体行动逻辑。近代中国邮政在生产国家符号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国家符号之一。
所谓国家符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国家是一种自在的符号,即国家存在的符号化。自从民族国家诞生后,国家是世界各民族存在的主要单位与形式,成为“永恒的民族的模仿者”[1]313,因此国家自身就是民族生存必须构建、强化和信仰的符号,对国家符号的生产即是对国家符号的构建、强化与信仰的活动。另一方面,国家是一种自为的符号,即国家形象的符号化。象征一国政治特色、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国旗、国歌、国徽,具有一国本土特色的建筑、服饰、自然风光,代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军队、警察、国营企业,等等,都属于自为的国家符号。近代中国邮政作为国营企业,其与国家符号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所重视,以致影响了人们对邮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作贡献的认识。
一、近代中国邮政代表国家走近代化道路的意志
近代中国开关之前,邮递系统有驿站和民信局。驿站是中国古老的邮递系统,自周秦开始,一直用于官方的信息传递,至清末时已积弊丛生,腐败不堪,效率低下。民信局是民间的通信组织,弥补了驿站不通民信的不足,开办时间可追溯到明朝,到了近代虽然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规模小、组织分散、竞争无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在轮船、铁路等近代交通工具出现后,这两大传统邮递系统还使用人力和畜力作为主要寄递力量,经营原始、生产落后、效益低下,成为邮递系统近代化的阻力。
近代中国邮政基本是按照英美邮政体系建立起来的新的邮递系统,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代表性元素。它既通官书,又通民信,兼备驿站与民信局的功能,还拥有驿站和民信局不具有的优势,即交通工具的发达和管理制度的先进。近代中国邮政尽管诞生时间晚,成立于1896年,然而由于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成长十分迅速,到驿站被决定关闭的1912年,短短16年时间,邮政网点发展到6 816处,邮路里程达39.9万华里[2]380,427,初步构成了遍及全国各省的邮政网络。到民信局被取缔的1934年,邮政网点扩展到46 567 处,邮政里程达100万华里左右[3]291-292。
近代中国邮政对驿站和民信局的取代,经历了一个反复较量的过程,代表了走近代化道路的国家意志的胜利。裁撤驿站的动议,自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许多有识之士,如冯桂芬、郑观应揭露其弊端,力陈裁驿置邮的必要性,然而清政府始终左顾右盼,不敢痛下决心。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就宣告将驿站裁撤,两年后在中国存在三千年的驿站制度寿终正寝,这反映了新生的民族国家与旧时代的家族王朝走近代化道路的意志的不同。民国政府对民信局的取缔虽然遭到多次激烈的反抗,但到1934年各地民信局被勒令一律停业,这更能反映出国家意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说近代中国邮政对驿站和民信局的取代是国家意志对邮递系统的刚性治理的话,那么近代中国邮政被中国民众接受则是新式邮递系统代表的国家意志在民间的柔性渗透。邮递系统传递的不仅仅是邮件,还有附着在邮件上的邮递方式及邮递方式所传递的思想与观念。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形式革命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认为只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人们就会“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接受技术的影响[4]46。和驿站与民信局陈旧的邮递方式相比,近代中国邮政利用轮船、火车、飞机等工业革命条件下的交通工具,通信风雨无阻,到达准时,向国人展示出技术的魅力与邮政的权力。国人也通过使用这些先进工具进而认识到其背后的世界,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关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科学技术等近代文明的意识形态,变成提倡和支持近代文明的力量。
1876年清政府官员李圭作为参加费城世博会唯一的中国代表,到华盛顿参观邮政局,在看到西方新式邮政的设施设备、业务运行和经营管理后,明确意识到“邮政为政治大端”,能够“裕国便民”,进而主张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国家邮政体系[5]50-51。李圭的事例典型地反映了近代邮政对国人的影响,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4]47。近代邮政建立后,很快得到国人的信赖。1901年,人们购买商品需要邮寄时,对新旧邮递系统的态度泾渭分明,“远方寄购请交邮政局,速而且妥,包无假冒之弊”,民信局“则不可靠”,“慎之切切”[6]。近代邮政代表了走近代化的国家意志,并在中国近代化征程中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因此,在驿站和民信局被裁撤后,国内民情波澜不惊。
二、近代中国邮政象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近代中国邮权既不统一,又不独立。鸦片战争后,经济往来频繁,来华外国人增多,催生了列强在华建立邮局的需求。英国率先于1842年在五口通商城市开办邮局,随后法、美、日、德、俄也相继在中国各地设立邮局,而这些邮局一般被称为“客邮”。
国与国之间互通邮件,属于正常行为,但一国在另一国开设邮局,“即与在他人之地建造炮台、派兵驻守,开征税项等蔑理之事无异”[7]100,客邮在本质上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的外来邮递组织。因有客邮存在,列强出于保护其利益的目的而要求中国在本土开设邮局需得到其同意,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如1917年3月中日《胶州湾租借地及胶州湾铁路间邮电事务之处理办法》规定,中国同意日本在济南和潍县胶济铁路车站区域内开设邮便局各一所,“日本国承认,中国在青岛继续开设邮务局、电报局各一所”[8]1258。客邮不仅侵犯中国主权,而且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母国的邮政章程、贴用母国的邮票、收揽中国人的国内信件和包裹业务,甚至还有走私贩毒等不法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此外,客邮使用母国的邮袋装运邮件,不受中国海关和邮政的检查,这也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
西方列强开办客邮的一个主要借口是中国没有近代邮政。对中国政府而言,欲收回邮权,创办国家邮政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邮政是作为客邮的替代物出现的。然而,近代中国邮政创办时,客邮只有25家,之后近10年时间却增至65家,至一战结束的1918年竟达344家[9]17。客邮在近代中国邮政创办后数量不降反升,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和中国收回邮权的艰难。
与驿站、民信局相比较,客邮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邮政体系,(1)客邮对中国近代邮政的影响,参见金燕、叶美兰:《英国与晚清中国邮政发展研究(1840—1911)》,《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且受特权保护。为了撤掉客邮,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晚清政府采取了铁路不准带运客邮邮件、降低境内资费等措施,但“大多不起作用”[9]33,后来北洋政府意识到“诚以裁撤一举属诸外交,即应归于外交政策之内”[10],于是通过外交手段,试图依靠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国际法准则来达到目的。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陈述裁撤外国邮局的理由为“援各独立国之通例,国内不应有他国邮政机关”[11]131。1921年6月7日中国外交部在致美英法日四国公使的照会中提出,邮政为“主权所在”,世界各国在其领土内“均不容他国代庖”,“此固各国之通例”,要求撤去在华邮局[12]。在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强调客邮“侵害中国主权”,美国代表也承认无论中国如何“姑容”,客邮“究系侵害主权”,同意撤去[11]369。
客邮撤销后,近代中国邮政得到快速发展。1923年,即中国收回邮政主权后的第一年,上海一地收寄邮件数量较上年增加2 400万件[13]49,此后中国邮政高速发展,10年后收寄件达到7.39亿件,比1922年多出3.13亿件[3]295。平均每年3千多万件的增长速度,得益于邮权独立对邮政事业发展的保护与促进作用。有研究认为客邮撤销对近代中国邮政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巨”[14]17。邮政主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完整收回的国家权益,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统一的伟大斗争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近代中国邮政对国家符号的生产
近代邮政的创办标志着中国通信事业近代化的开始。邮政不同于驿站和民信局:驿站不能通达到民间,邮政则服务全体人民;相对于民信局的唯利是图,只要民生需要,无论地理位置是否偏远,邮政都将其列入开拓计划。是以近代中国邮政的创办,对国家符号的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救国,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危机,国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险”[15]513,529。近代中国邮政创立于1896年,这与甲午战争失败不无关系。不论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将邮政视为“富国之法”的六种之一[16]126,还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创邮政以删驿递”奏折中把邮政当作省耗收盈的进项大宗[13]12,邮政自出现的那天起,就承担着生产国家符号的使命。
在生产国家符号方面,近代中国邮政具有行业的独特优势。利用其四通八达且深入穷乡僻壤的邮政路线和网点,它使不同地方的民众能够普遍感受到国家的存在。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邮政业务 “已相当普通”[17]11,在其取代客邮、驿站及民信局后,已经能够充分满足国内外的通信需求。在邮政网点遍及全国的情况下,邮局、代办所、邮站、邮亭等邮政设施与身着官衣的邮差作为一种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众的国家观念。不单在近代中国是这样,其在塑造新生的美利坚时也是这样。美国在建国初期孱弱松散,邮政作为连接各州的国家基础设施,是国家的化身,“它代表着中央政府”[18]62。邮政工作相应地承载着维护国家形象的责任。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在投递过程中有60多名中国邮差受伤,14人牺牲;1926年邮差殉职人数达到22人,即使在交战区和土匪出没之地,邮政职工也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投递;1924年仅云南省一地“邮差被土匪袭击者83起,因而毙命者7人,受重伤者26人”[19]1063,1129,1040。
近代中国邮政的另一个行业优势是利用邮票强化对国家符号的认同。邮票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通过图案和铭记来表达和传播国家的价值诉求、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晚清邮票使用龙作为图案,用龙来象征皇权、象征中国。清政府被推翻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此时的邮票图案设计为帆船、农夫刈禾、北京国子监的圜桥牌坊三种样式,预示着新政权对与民生相关的生产、生活及教育的重视。
通过对国家符号的重复使用,邮票激发出国民对国家的情感。邮政越发达,国民认知的空间就越大,国家认同感就越高。1831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看到美国发达的邮政事业时曾惊叹,邮政带来的信件与令人吃惊的报纸流通量,为“思想之间提供了巨大的联系”,并将思想“渗透”到“荒芜的心脏”[18]62。陈独秀直到1904年才知道“通些时事”的“巧妙的法子”是看报,也是在这一年他才明白中国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才知道国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20]15,39。巴黎和会召开时,湖南的一群师生每天想从报纸上得到外交消息,“报纸一到,大家抢着先看”,当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全省人民 “准备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21]189-190。过去人们在研究新闻史与新文化运动史时,往往突出报刊在中国人思想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其实邮政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被誉为“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写道,“要让平民团结起来,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复运动,而只能依赖重复理念”[22]23。一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邮政事业突飞猛进,国家符号经常地、大量地重复出现在报刊中,而报刊又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读者手上,可以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与当时发达的邮政不无关系。从1919年4月1日起,北京每天的信件递送增加到12次[23]。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曾高度赞扬托马斯·杰斐逊在任总统期间把高速公路通向乡村的伟大规划,认为“道路保证了国家的统一”[24]6。毋庸讳言,邮政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和国家认同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功能上看,邮政并非是维持生计的必需品,邮政事业与国家的经济状况、意识形态高度相关。近代中国邮政的创立和发展,反映了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水平与能力不断提高,走近代化道路的意识不断增强,并以救亡图存和国富民强为目标。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国家符号的作用,而邮政行业的优势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符号的生产,成为国家共同体构建的一部分,最终使其成为国家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