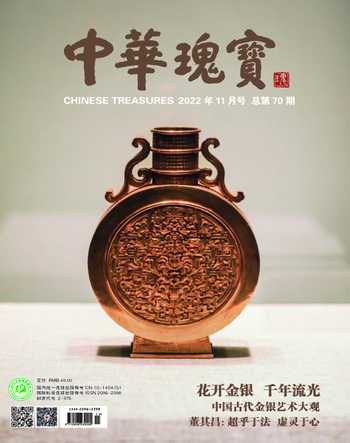接续宗教彩塑艺术正脉



中国宗教彩塑源远流长,辉煌迭现,代表了东方文化的审美特性。作为宗教彩塑技艺传承人,史延春潜心笃志,谨怀虔敬,致力于探究古代彩塑艺术,在技艺的流变与承袭中,接续了宗教彩塑艺术的正脉。
史延春,1970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西彩塑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山西长治彩塑艺术研究院院长。自幼受家学陶冶,倾心于传统绘塑技艺。从事寺观彩塑艺术工作30年来,主持完成了云冈石窟、大同华严寺、长治法兴寺、五台山殊像寺、芮城广仁王庙等世界文化遗产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彩塑修复、复原及创作项目。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被中国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
寺观彩塑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黏土加上植物纤维、细沙、水糅合成的胶泥为材料,在木制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后阴干填缝、打磨,再着色彩绘而成的宗教雕塑。寺观彩塑艺术在经过唐宋时期的高峰后,至明清时渐趋衰落,艺术质量再难企及前代高度。为重现寺观彩塑的辉煌,史延春艰辛求索,从历代宗教彩塑精品中苦心探寻接近古人的路径。
幼承家学 与古为徒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翠云山麓的法兴寺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繁盛于唐宋。其主殿圆觉殿建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殿内保存的十二尊圆觉菩萨造像沉静清雅、文质相兼,代表了两宋宗教艺术的高度,被誉为“宋塑菩萨之冠”。然而,常人不知道的是,其中有四尊菩萨造像在岁月侵蚀中早已残损,现存的造像是20世纪末重塑复原的作品。而担纲完成这一重要文物保护任务的史延春,当时尚未及而立之年。
史延春出身于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的一个民间艺术世家。其曾祖父史广和是清末辽西地区知名的民间艺人,专长于寺观宗教美术。其祖父史宝海深得家学。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史延春自然对传统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很早便跟随父祖学习彩塑与壁画技艺。
宗教彩塑技艺自明清以来逐渐式微,到了近现代,寺观彩塑的质量和艺术思想普遍偏低。据史延春回忆,在他学艺之初,祖父已年近古稀,而父辈在祖业传承方面,又曾一度中断。“可喜的是,随着国家对宗教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寺观美术创作也重现生机。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承袭了彩塑艺术的衣钵。”他说。
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缘,史延春第一次到访山西。山西素有“彩塑艺术博物馆”之誉,现存历代寺观彩塑造像遗存万余尊,涵盖了唐宋至明清千余年的经典之作。在山西,史延春与跨越千年的佛像产生共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1998年,应文物部门之邀,史延春开始在山西长治法兴寺探索性地复原宋代风格的菩萨造像。为了能够高标准地完成任务,他师法宋代古塑,开启了中国彩塑艺术的寻根之旅。“我的学习方式从家族技艺的小传承,开始转变为以历代经典艺术作品为师的大传承。”对此转变,史延春概括道。他不再仅依托师徒间的口传心授,而是通过钻研历代经典古塑,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物态传承和多元传承。史延春不断钻研古代彩塑的美学思想及技艺手法,汲取前人的艺术经验,并先后到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深造,博采众长,为彩塑艺术创作开辟了新路。他由此实现了由技入道,从民间艺人成长为职业艺术家。
三晋大地上丰饶的文物古迹带给史延春不竭的创作灵感,令他难以割舍。为了更好地在这片沃野上汲取养料,他决定定居长治。当时年轻的史延春或许不会想到,山西不仅是他开启未来艺术道路的起点,日后也成为寺观彩塑艺术的传承之地。
融创新境 不愧前人
在家族传承和艺术院校培育的双重滋养下,史延春一方面根植传统,传承千年本土彩塑技艺;另一方面融会贯通,广泛学习国内外优秀彩绘艺术经验,在创作中把握传统范式与时代诉求之间的平衡。他坦言:“我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古塑修复与复制工作。”多年来,史延春辗转于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进行宗教美术实践,主持修复、复原和创作的寺观造像千余尊。
“宗教造像有着一套严谨的制式仪轨,其题材、场景、人物、服饰等也皆有出处,不可主观编造,其创作过程犹如被‘捆绑着跳舞。”对于宗教彩塑艺术,史延春形象地比喻道。
为法兴寺复原重塑的四尊圆觉菩萨像是史延春艺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组作品,其中以圆觉殿西山墙北侧第二尊造像尤为精彩。此尊圆觉菩萨面如朗月,双眉修长,体态娴静优雅,目光低垂深沉。其服饰衣纹流畅洒脱,褶皱刻画准确自然。满含哲思的微笑静谧安然,超旷拔俗,呈现出一种无所挂碍的禅定状态,充满内省之美。此像温润典雅的两宋风神与圆融无碍的宗教情怀相得益彰,营造出菩萨洞悉万物真理,以无量的慈悲光照人间的圓觉境界。
扎根山西的20余年里,史延春还担纲完成了大同华严寺多座殿宇的彩塑重塑任务;修复云冈石窟第十窟中主尊佛像,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得以更为完整地延续;2012年,史延春带领团队历时3年完成了突破传统规制的晋城普陀别院七十二观音群像,其中主尊正观音通高达18米,为少见的“鸿篇巨制”;2015年,他又完成了唐代建筑芮城广仁王庙中的一组龙王造像,令千年古迹重现神光。史延春以学习传统彩塑技法为基础,通过临摹,把握了多种几近失传的技法,理解、吸收了唐宋时期彩塑艺术的特点和风格,在大量的寺观美术实践中接续了宗教彩塑艺术的正脉。
供奉于江苏常州花神宫的老子像是史延春近年来的一件力作。为了追慕唐代艺术风貌,他选取西安碑林藏老子像、山西古建筑博物馆藏老子像等盛唐造像作为参考资料。数易其稿后的老子形象丰须长髯,法相庄严,神情温厚肃穆而又气宇轩昂,沥粉贴金熠熠生辉,尽显崇高之美。
在主持完成寺观造像工作之余,史延春亦兼顾个人创作,《夜读春秋》便是其匠心独运的一件精品。孟子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延春塑造的关羽魁梧健硕,凤眼生威,形貌如生,手持《春秋》,静思夜读。造像的整体与细节把控均颇具功夫,人物形体结实饱满,表情细腻生动,衣纹收放有致,衣物图案多为两汉魏晋时期的纹样,表现出较强的整体叙事性。为了突出关羽的儒将气质,青龙偃月刀还被用红绸包裹以隐藏锋芒。造像采用的矿物质色彩和谐沉稳,沥粉贴金技艺尽善尽美。作品彰显出关羽匡扶正朔、万世人极的英雄气概,可谓“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
传承技艺 守望文明
后继乏人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同面临的时代难题,宗教彩塑亦不例外。在文人画占据中国美术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寺观美术的从业者长期处于工匠地位,社会认可度较低。其技艺传承方式也多为师徒父子间的口传心授,未能上升至理论研究层面,相关专著尚付阙如。而自20世纪以来,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大多以西方美术体系为主干,本土传统美术技艺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如何改善中国传统彩塑的传承生态,让这门传承千载的技艺重放异彩,史延春深感责任重大。多年来,他始终沿袭传统的带徒授艺方式,把技艺传承到了第六代。此外,他还不遗余力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南京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高校开设传统造像艺术课程,不断丰富技艺传承模式。一次讲课期间有学生对他讲:“校内关于西方雕塑的课程较多,很少涉及传统雕塑。”史延春回答说:“大家以往上课学的同样是传统雕塑,只不过是欧洲传统。”这句话令学生顿时明白了他们对于“传统”的误读。史延春将深埋民间的彩塑技艺融入高校教学之中,让众多学子通过彩塑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广博与精深。
在位于长治市潞州区的山西长治彩塑艺术研究院内,陈列着许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彩塑作品,史延春正為学生讲解古代彩塑艺术源流和彩塑技艺要点。2010年,为了更好地发掘、研究和传承彩塑技艺,史延春创建了山西长治彩塑艺术研究院。在他的带领下,团队相继完成了云冈石窟、大同华严寺、五台山殊像寺、太原龙泉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彩塑修复和创作任务。
有感于传统技艺“重术轻道”的缺陷,史延春在实践领域探索的同时积极着力于理论研究。近年来,由他主持或参与编撰的《长治彩塑艺术研究》《佛影》《小张碧云寺》等专业书籍先后出版。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中国古代雕塑课程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的普及与建构。由山西长治彩塑艺术研究院积极策划参与的“中国传统雕塑传承与复兴”学术论坛已在长治成功举办四届,论坛邀请专家学者现场探讨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的传承情况,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冯骥才曾赞誉史延春的作品“立土为神,规模最大”,并为其题字“宗千年古艺,诚当世神工”。传承和弘扬传统彩塑艺术是史延春的毕生追求,他的人生注定与泥土为伴。“传承传统艺术不易,但值得我们坚守。”他恳切地说。今天,史延春依然活跃于寺观彩塑实践的一线,当他在脚手架上攀高据险调整造像时,中国宗教彩塑艺术的旷世仪容正愈发清晰。
张超越,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