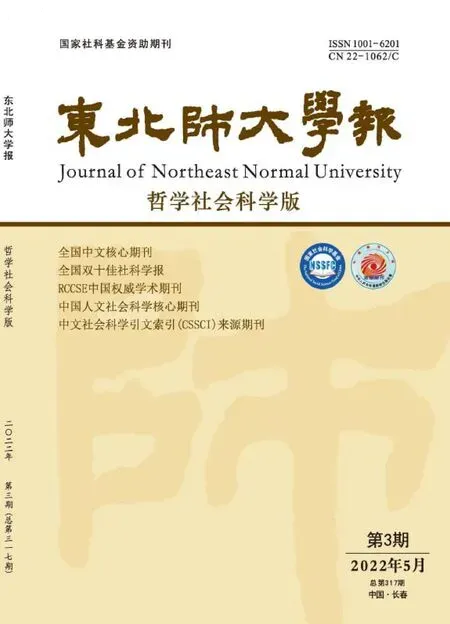社会认知视域下语言意义建构刍议
——以多义现象为例
许葵花,王 萍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引 言
语言意义的衍生,就像探究人类如何进化一样,一直是先哲们思考的问题。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语言意义的变化具有恒常性,否则现代人对于前人的语言作品的理解是不会有障碍的。从中世纪古英语文学作品《贝奥武夫》,到几百年前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经典之作《哈姆雷特》,再到近代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当代J.K.罗琳的畅销书《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都彰显了语言的历时演变,进行跨时空阅读存在着社会历史空间差。毋庸置疑,有些语言单位的意义随着时光的流转、社会的变迁,悄然发生着演化(1)根据Byrd等人1987年的统计,韦伯斯特大学词典(MWCD)第七版大约69 000个词条中有21 488个词条有2个或更多的意义,占到40%。而且这只是词典收纳的意义,实际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可能比这还要多得多。最常用的词往往也都是多义词(Ravin Y and Leacock C,“Polysemy:An overview”,Ravin Y and Leacock C,“Polysemy: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9)。。作为语言意义建构的一种现象,多义词词义衍生的机制(2)五十多年前(1951年)语言学家Ullmann曾认为多义现象这一有着多种且相互联系的涵义网络的语言事实,是语义分析的核心(Nerlich B and Clarke D,“Polysemy and flexibility: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Nerlich B,Todd Z and Herman V,et al.,“Polysemy: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Berlin &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3,pp.3-30)。,是语言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也一直是语言学界一个恒久不变的研究主题。本文首先简要梳理意义衍生研究的三个传统视域,基本上也是意义建构研究的历时发展线;在此研究背景下,以新兴的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为理论框架,从社会认知视域对多义衍生中的意义建构的环节——浮现和规约化进行阐释;继而探讨多义衍生的社会发展取向;最后强调意义建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的社会属性。
一、研究背景
从Bréal把多义现象这一概念引入语言学领域一百多年来(3)Bussman H,“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6/2000,pp.371.,意义衍生(或建构)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历时研究视域——社会文化观、语境观、认知观,各有其聚焦点。初期的词源学研究(4)Bréal M,“Semantics: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translated by Mrs.Henry Cust),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00/1964;Ullmann S,“Seman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Oxford:Basil Blackwell,1962.侧重把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多义衍生的参数,指出社会文明的不断繁盛,致使新概念不断涌现,人们或通过官方干预统一语言使用,或通过民间出于便利达成的共识,把既有的词汇用来表征新概念,出现词汇泛指或具指、借指或隐指等词义衍生的现象,而且也指出语言社团内的广泛使用对于多义涵义得以确立的社会驱动力,以及人们进行意义衍生活动所内隐的隐喻思维特质,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但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意义衍生的社会因素及心理现实性还只是观察性的表象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之后,也有学者转而从语境,如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5)Malinowski B,“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I)”,Ogden C and Richards I,“The Meaning of Meaning”,New York &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3,pp.296-336.,再具体一些,如语言社团规约的诸如场景、参与者、传递信息的形式及内容、语言风格、事件、言语行为等社会语境要素(6)Firth J,“Speech”,London:Ernest Bern Limited,1930;Firth J,“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Firth J,“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177-189;Hymes D,“Models of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setting”,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2,No.1,1967,pp.8-28.,以及语言语境化解掉词汇多义性的重要性(7)Cruse A,“Lexical seman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54-57.去阐释意义的建构,虽然反映了语言现实性的一面,但其或侧重强调情境因素、或聚焦在语言因素上,而大大忽略了人的心智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8)在此期间,结构主义的研究思潮更是摒弃了所谓“异质的”“偶然的”言语研究,也即摈弃杂乱的社会因子和人类心智,聚焦在“规范的”“纯粹的”共时语言研究的价值上,如从其内部进行原子式的语义成分分析,以及后来的生成语法掘弃语境、语言的使用,进行纯粹的语言形式的逻辑推理,也就与一形配多义的意义建构研究渐行渐远了。。而随后受认知科学的影响而盛极一时的语言意义建构的认知研究,如概念隐喻(9)Lakoff G and 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原型范畴(10)Lakoff 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Taylor J,“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意象图式(11)Johnson 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概念整合(12)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Cognitive Science,Vol.22,No.2,1998,pp.133-187.、语义框架(13)Fillmore C,“Frame semantics”,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Seoul:Hanshin Publishing Co.,1982,pp.111-139.、构式语法(14)Goldberg A,“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等理论,试图从人脑内部的认知构造机理,来探究人脑这个黑匣子在意义建构中的思维特质,如多义衍生中的跨域语义映射,多义涵义间意义拓展的层级辐射网络状分布,人类通过具身体验来进行跨域概念组织的意象图式力,意义经由两输入空间的某些特征有选择地映射到整合空间后的浮现,事件框架的多义潜势消解功能,构式对于词汇衍生义的压制作用。但认知研究大多是利用人工自造语例对人脑的语言处理机制进行内省的研究,这又不免过于夸大人类心智的作用,而忽略了语言意义生成的社会性和语境元素。因为语言意义的建构如果只取决于人类的心智,那么它不会有纵贯历史、跨社会、跨语言的异质性。如果不同时考虑语言、智力、意识、自我、社会及文化交互等综合因素,那么意义就不会产生(15)Jackendoff R,“Foundations of language:Brain,meaning,gramma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68.。多义衍生的社会文化观、语境观、认知观都有各自的研究侧重,反映了语言的一方面,但缺乏从社会和认知整体上关照语言意义建构的现实性及其全貌(16)陈晟:《方言词典释义应注重百科性和理据性》,《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62—168页。。近二十年来,认知语言学领域有众多学者转而从社会文化视域来研究语言认知,开启了该领域研究“再语境化”(17)此处语境指广义的语境。的社会转向。据此,本文以社会认知研究(18)语言的社会认知研究由于其尊重意义在社会交互及社会发展进程中生成的现实性,有着极强的容纳力、历时和共时的解释力。这与语言的社会语用转向研究(Mey J,“How to do good things with words:A social pragmatics for survival”,Pragmatics,Vol.4,No.2,1994,pp.239-263.)注重意义建构的话语小语境及社会大语境,即尊重语言的交际性、文化性、社会性,甚至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社会认知研究同时也关注语言使用的心智过程,即社会化下人脑的认知机制,本文认为这一认知机制归根结底是社会认知,两者相辅相成,前者又蕴含后者,此方面的研究作者将另文赘述。由此,本文也认为传统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二分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为理论框架,尝试探讨多义现象中意义衍生的社会认知处理机制。
二、多义衍生的社会认知机制
语言具有社会属性(19)Saussure F,“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ondon:Peter Owen Limited,1959.,语言是基于使用的(20)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lated.by Anscombe G.)”,Oxford:Blackwell,1958;Langacker R,“A dynamic usage-based model”,Barlow M and Kemmer S,“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Stanford:CSLI Publications,2000,pp.1-63;Bybee J,“Language,usage and cogn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多义词词义的衍生离不开语言使用者,是语言使用主体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进行具有交际目标的交互性社会认知活动。衍生义始于这样一个三链条构成的社会交互活动(21)Croft W,“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Beijing: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0/2011,pp.95.:链条一,一个社会个体,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下,进行了偏离语言社团规范的语言系统的用法创新,以达到交际的经济性和有效性;链条二,信息接收者,作为另一个社会个体,通过交际合作原则,会对创新用法进行再分析,把创新用法(如多义词的衍生义)从一个违反常规的“错误”,即在语言社团词库中缺少该社会值的形式,重新进行形义匹配,接受该用法,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链条三,接受者继而会在另一个语境中复制该创新用法,赋予其社会值,而被第二接收者接受进行复制使用,那么创新用法的传播就开始了。这种衍生义的传播及其惯常化(routinization/habituation),逐步会被语言社团认定为规范的语言,成为所谓“正确的、规则的”用法。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及人们的交际需要,衍生义进行裂变,再次冲破规约,成为所谓“错误用法”,由于其新奇、生动、强表达力等特点,往往受到大众的追捧与使用,逐渐成为规则的、正确的用法,如此周而复始,词汇形式相对来说是稳定的,而其涵义却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多义范畴网络不断向外拓展,语言系统也由此不断扩张且具有动态活力。简而言之,词义衍生包括浮现和规约化两个主要的社会处理进程,即社会认知环节。前者是一种社会交互下的个体行为,具有即时、即兴、灵活、强表达力等特点;后者是一种相对的社会行为,具有历时性、趋向稳定等特点。
(一)浮现的社会认知机制
浮现是语言使用者使意义偏离语言社团规约的意义,语言单位意义发生突变的意义衍生或创新现象。人们的社会文化交互活动是多义涵义衍生的触发器,主要体现在社会话语交际、书面语交际、跨语言社团的社会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的社会情境中。结合Blank(22)Blank A,“Why do new meaning occur?”,Blank A and Koch P,“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Berlin &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1999,pp.61-89.的语义变化原因,我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认为,多义衍生的社会驱动有社会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新概念的出现以及相近概念或事实关系的发生、语言使用者实现交际经济性和有效性的目标、对具有情感标记的概念或禁忌语的回避。新义浮现的社会认知效应要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一是语言使用者进行社会活动所内化的百科知识,二是即时交际语境中语言使用者(既可以是语言交互双方,包括说者和听者;也可以是书面语交际的参与者)进行交际协同的各种构成因素。
1.语言使用主体内化的社会百科知识
意义的实质是百科的(23)Haiman J,“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Lingua,Vol.50,No.4,1980,pp.329-357;Langacker 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I):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87/2004;Evans V and Green M,“Cognitive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Beijing: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6/2014.。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创造衍生义是依据其所掌握的原型义或原初义的百科知识体验,包括对该词在语言社团中具有中心度的规约知识的习得,既包括使用者对该语言形式的词典定义的学习,也包括其对该词的社会体验式的识解知识。它是语言使用者赋予语言形式的社会值,既具有语言社团共享性、语言社团使用的固有特征,又具有个体所体验的非规约知识,是一个社会个体所获得的语言知识经验包,是一种意义潜势。这种意义潜势来源于社会活动,在社会交际中词汇被卯定具体的语义使用值;它是一个随着语言使用者在不断的社会交互活动中不断丰富的庞大的社会知识认知框架,具有开放性、经验性,在稳定中呈现动态性,是意义在线识解必备的背景知识,是语义抑制、语义融合等认知机制的先决条件。如记者在亲历受台风袭击后灾民进行重建家园——rebuild his house的语言使用事件时,受当时情境的触发,并激活其储备的关于rebuild的百科知识,用了rebuild his life的隐喻表述进行报道(24)Kövecses Z,“A new look at metaphorical creativit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ognitive Linguistics,Vol.21,No.4,2010,pp.663-697.。真实世界的事例使记者对于rebuild的社会体验更加地丰富,其rebuild的社会百科知识进一步拓展,被赋予了更多的语义值——隐喻用法,这一用法源自生活情景,作者只是进行了视角复制,使报道表述更加经济、实效、生动、贴近生活。再有,这种建构在共享的社会百科知识下的创新,会很容易被交际另一方所识解接受,因为共享的社会活动经验会使交际另一方付出最小的社会认知努力来识解。如在许葵花(25)许葵花:《多义化识解的多维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2页。进行的多义词衍生义识解的有声思维实验中,一位被试对weed在“In this country,men plant the corn,women laterweedit.”中的名转动拓展义——除草的识解,即来源于其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亲历“父亲种地,母亲随后做一些除草这样的小活儿”。经验是一种意义的源泉,一种能用来理解、反映或影响现实世界的潜势(26)Halliday M and Matthiessen C,“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London:Continuum,1999,pp.1.。因此,社会百科知识是语言使用者进行多义衍生的认知储备库,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在社会交际中使多义衍生具有可及性。试想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百科知识的狼孩儿,虽进行了基本的会话交际的训练,虽具有同样的人脑生理构造,但由于缺乏这种日积月累的社会活动所带来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所组构的百科知识,是不会有衍生义的创新或识解的。当然,一个人所累积的巨大的百科知识库,不会在衍生义建构时,全部被激活,我们在社会情境中具有共享注意,可以过滤掉一切不相关的信息知识,调出与当前交际相关的百科知识,从而在交际的协同中屏蔽其他意义的浮现。
2.社会情境中交际的协同
语言使用者除了具备社会百科知识累积,尤其是交际双方共享的语言社团百科知识外,进行衍生义创新,还需要有在具体即时社会语境中的交际协同。如对于场景、参与者、事件类型、意图、交际目标等的感知,以及诸如共享注意、相互(语义)支持、相互(语义)认同、相互(语义)遵从等交际协同行为,来进行成功的社会交互,使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经济原则发挥作用。语言创新使用虽偏离语言社团规约的用法,却可在此情此景中通过双方合作,进行成功交际,促成衍生义的创造和识解。
语言交际是一个共同的合作行为,需要交际双方进行协同。因为我们不是心灵捕手,不能像电子扫描仪一样,不需要借助语言等其他语境因素,就能够完全读懂对方的意图,即时扫描出对方所要传递的意义。但协同不是僵化的,双方依据语言形式,从词库中提取相应的意义即可;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就像谢林游戏(一种协同游戏)(27)Croft W,“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Beijing: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0/2011,pp.95.,它需要有共享的社会感知或认知焦点,来达到交际目的,使说者构建的意义能够被听者所成功接收,实现社会交互活动。在多义衍生的情境中,交际协同就是一种适应行为,听者借助各种语境要素来顺应说者的语言系统,正确读取说者所传递的意义。比如文学作品中隐喻意义的创新使用,作者基于共享的百科知识,借助于上下文的烘托,虽然使用了语言系统中语言单位非规约的意义,但共情的“社会情感效力”(28)Schmid H,“A blueprint of the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Yearbook of the Germ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2015,pp.1-27.却会作用于读者,使其体会出多义衍生义,达到书面交际的目的。比如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中“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读者不会冒出“秋天怎么长了脚?”“光线是能数的吗?”的疑问;“London street fashionscene”(伦敦街头的时尚风景)的表达,也不会使介绍伦敦百姓穿衣时尚的视频材料的学习者,感到异常突兀费解。而跨语言文化(语言接触)的多义衍生的高接受度也源自不同国度、社会间的互通有无,如经典的计算机领域的“window”“menu”“mouse”“garbage bin”等例,出于对衍生义使用者科技威望的遵从和语言交际的经济性和有效性,汉语言社会在保留这些词隐喻义的同时,略加汉语表达习惯上的调整,进行交际意义协同,直接顺从其表达的语义,以“窗口”“菜单”“鼠标”“回收站”转译到汉语中,而且根据意义使用中对计算机这些功能的实际体验,这种非规约义的使用并不显得突兀而不可接受,从而沿用至今。再如汉语的“酷”字,在汉语中,“酷”一义为“残酷”,如酷刑、酷吏;二义为“程度深”或“极”,如酷热、酷寒、酷似、酷暑。但由于英语中的“cool”(义为very good,excellent,fashionable)的先锋、时尚文化理念的传入,国人用“酷”字来对应,因此汉语中的“酷”又多了意义,意为“形容人外表英俊潇洒,表情冷峻坚毅,有个性”,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
(二) 规约化的社会认知机制
语言单位的衍生义在社会交际中浮现之后,由语言社团的非规约义到规约义的固化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处理进程的。高频率的重复使用是关键因素。驱动高频率的重复使用的因素主要有语言使用的生动新奇性使其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对使用者的威望遵从、群体归属感带来的仿效等。这些因素使衍生义的使用惯常化,逐渐成为社团所约定俗成的语义值,成为公共词库中的用法,有的甚至为词典所收纳,成为规范的用法,如上文“酷”的衍生义出现后,《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还未收入此义,但在之后于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中已收入此义。
创新义(衍生义)浮现时,由于其新奇性和表达的效力(expressivity),在类似的使用事件中反复出现,被赋予了社会表达值,成为一时涌现的社会语言现象,那么其传播者就会加以复制使用,使其具有极大的传播力,成为一种语义的社会使用时尚。如汉语“被”由一个中性意义,不常用的被动义,增添了在诸如“被忽悠、被下岗、被自愿、被自杀、被就业、被小康”的讽刺、戏谑义,并在一段社会历史时期成为一种频繁出现的时尚语义。
衍生义的传播同语音变体的传播一样,需要使用者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力”(29)Labov W,“The social origins of sound change”,Labov W,“Locating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pp.251-266.,使仿效的社会行为得以发生,加速语义的“流通度”(30)张普:《关于语感与流通度的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使其惯常化,成为规范用法。如“给力”的衍生义(31)《“给力”衍生义》,http://baike.so.com/doc/5109073-5337807.html,2021年7月21日。源自闽南方言“很棒、很精彩”,由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力,该义被传播到普通话中,形容人或事物等“够劲儿、使人振奋、感到有力量”,其流通度开始并不高,但2010年11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中使用了这一普通话中非规约的用法,就此该义从口头用语成为书面正式用语,甚至被牛津新词词典所收入,英语语言中有了“gelivable,ungelivable”的语义表达法。网络媒体如今成为新词语等语言新现象最重要的孳生地和集散地(32)李宇明:《语言竞争试说》,《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群体归属感所施加的社会压制(33)Schmid H,“A blueprint of the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Yearbook of the Germ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2015,pp.1-27.,作为一种语言规范化的社会效力,也会促就衍生义在语言社团内同伴间相互仿效,作为个体的群体身份的认同和凝聚力的表象,不断地重复使用和传播。这一点在时尚用语中显得尤为突出。如现今流行语中的“醉了”一词原指饮酒过度,神智不清,现在已具有另一种语义表征。如在街头等待红绿灯过马路时,一年轻人看到街道上密密麻麻众多的车辆造成交通堵塞,对同伴冒出了“我也是醉了”的感叹。这种用“醉了”来形容某事件超乎想象,难以接受或理解的语义在年轻人中使用很广泛,已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当然,除了词义惯常化的社会驱动力,如新媒体的“推波助澜”、群体归属感之外,衍生义的规约化也部分受衍生义与基本义(原型义)之间内在联系的影响。如“窝心”词义的衍生,“窝”的原型义和典型义是“蜷缩或待在某处不动”和“郁积不得发作或停滞不能发挥作用”,如“窝在家里”“窝火”,后来衍生出“窝心”义——“形容因受到委屈或侮辱后不能表白或发泄而心中苦闷”,此义与基本义有着极高的相似性特征,而“窝心”的另一义“暖心、贴心、心里很舒服的”义,由于其与基本义的相似性太少,流通度稍不高,只在南方有使用,因此也没有像其贬义那样正式收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由此,规约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词汇语义可接受度的影响。
总之,多义衍生的社会认知处理进程为(34)许葵花、葛晓华:《语言意义建构研究的历史嬗变——以多义现象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在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基于衍生义创新者和接收者内隐的百科知识和共享焦点,以及外显的语境及言语交互者双方相互的协同,衍生义浮现,并由接收者进行传播,经过惯常化后,逐渐成为语言社团规约的用法。
三、多义衍生的社会发展取向
语言使用既是个体行为又是社会行为(35)Clark H,“Using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多义衍生经历浮现和规约化的社会认知进程,从历时来看,呈现出主要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
有的成为语言社团长期的规范用法。如英语be going to从表实体移动义演变为表将来的认识情态义;keep在“keep the house”中的“保留、保有”的实义动词含义,增加了与另一个实义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组合,强调“保持或一直做某事”(如keep complaining),只起辅助意义的语义功能。汉语中“看”(36)用例选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在“看医生”中的转喻用法,“我冷眼看他这几年”中的观察义,“样子倒中看”中的喜爱义,“上外头看看,咱这些人快比不上叫花子啦”中的比较义,“看,非让我跑腿”中表嗔怪、责备的语用功能义。在时间维度上,词汇语义在历时使用中,是语言使用者综合了生理、感知、情境等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敏于变通的结果。如英语形容词hot,其词义衍生的粗略历程(选自《牛津英语词典(OED)》),如下表所示:

表1 “hot”的词义演变
“hot”语义从1 000前年对于物质物理特质的原型描写义,400年后延伸到对于人或动物的热感觉拓展描写义,随即于500年后衍生出描写体热感所伴随的拓展特性义,600多年后再延伸到对于事物热度的拓展描写义,近900年后发展到对于人出色行为表现的拓展描写义,1 000多年后到今天形容炙手可热的流行人物的拓展描写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社会体验的不断丰富,繁复的概念化进程使hot的社会使用功能也呈现扩大之趋势,从原型义到各类次典型衍生义,上下跨越了几百年至千年不等的历史,仍然在并行使用。“一个民族文化越发达,就会有更多的词随着语言使用的不断变化增添新义”(37)Bréal M,“The beginning of semantics:Essays,lectures and review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olf 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56.。
社会容忍度影响语义变化(38)Bartsch R,“Norms of language: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London:Longman,1987,pp.209-214.。由于社会容忍度的不同而发生衍生义的此消彼长的现象。如英语中的“gay”一词,根据OED,该词在19世纪原型义为“快乐的,欢快的;轻松的,愉快的”,如1843年的例句,Edward was the handsomest,thegayest,and the bravest prince in Christendom.到了20世纪,在1935年却滋生了“同性恋的”的非典型义,但此种现象受当时宗教教义的影响,在社会上讳莫如深,受到严厉的压制和禁止,也不是其主流义。
而 “gay”的“同性恋的”义随着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容忍度的逐步提高(虽然当今也是比较有争议的社会现象),已成为社会公认的主流义。涵义之间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认识的变化,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即主流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更替,见矢量图1:

图1
在图1中,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社会发展,两轴作为观察gay词义发展轨迹的参照,可看出该词的语义品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S2成为主流义后,S1的使用因为受S2的影响,成为情感标记概念,需要规避,其使用在现代已落败。该词因为其隐晦性,在汉语中被人们依据语义创造性类推,用 “同志”来指代,使汉语词汇“同志”有了新的社会义衍生。
有些语义经历一定历史时期的兴盛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所承载的社会值已不具有当代意义,社会嵌套义已显得陈旧过时,带有了历史特异性,最终退出社会使用的舞台,如六零后、七零后曾经耳熟能详的“革命的螺丝钉、倒爷、大锅饭”等的隐喻义。有的只是一种社会便利下促生的一时用法,如中国北方某一小城,出租车起价5元,便宜而且多如牛毛,逐渐“招手”有了“出租车”的转喻用法,但随着现而今网约车平台的出现,这一用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再有社交媒体上风靡一时的新奇创新,由于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嵌套,只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中流通,如“内卷”“凡尔赛”。前者喻指“激烈竞争”,是一种小众的用法,后来由于其直指现今社会教育现象,很快成为全社会谈论教育时趋之若鹜的时尚语义表达;后者喻指“忍不住偷偷炫耀自己的优越”,则还只在一定文化群体圈中使用,流通范围较小。还有随着手机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爆”出现在“爆屏”中衍生义的使用,以及“刷”在“刷存在感”的衍生义以及新近的“断片”(思维短路)衍生义等用法有着发展的不确定性。因为受社会发展的影响,意义的演变也不是像算法或大脑的生理机制一样,有恒定不变的稳定性。
结 语
纵观多义研究的历史,最初从词源学的角度,单一地把多义衍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观察和描写,到以内省的研究方法来从语言内部探讨其所依附的人类心智,再回归到语言演变的终极目的——社会交互,多义衍生研究终归要考量语言所具有的社会和认知双重属性。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跨学科研究的日益成熟,“语言的社会性和功能性”(39)Harder P,“Meaning in mind and society:A func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tur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2017;Geeraerts D,“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2-103.越来越得到学者的共识。语言社会化的进程预设语言意义衍生的恒常性。语言作为人类进行社会交互活动的中介,必然是社会文化的折射镜;同时,语言使用者通过社会言语行为(口头及书面的),也构建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世界(40)Goodwin C and Duranti A,“Rethinking context:An introduction”,Duranti A and Goodwin C,“Rethinking Context: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4.。社会文化活动是多义衍生的孵化器(41)许葵花、葛晓华:《语言意义建构研究的历史嬗变——以多义现象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人类诸如注意、焦点、突显、记忆表征、意象图式抽象化、联想语义跳跃、隐喻思维、类比、范畴化、融合等认知能力,只有在社会语境这个孵化器中才能实现,因此认知功能带有社会属性,否则没有语义的非常规突变,也没有由高频率重复使用形成的惯常化,更不用说语言社团所约定俗成的规范用法了。多义衍生是社会变化的指数(42)Goddard C and Wierzbicka A,“Language and society:cultural concern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Elsevier,2001,pp.8315-8319.。社会认知视域下的语言意义建构研究,给我们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索绪尔早就指出语言的社会属性以及外在因素,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语言的影响(43)Saussure F,“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ondon:Peter Owen Limited,1959,pp.13-14,20-21.。随着各学科的长足进步和发展,人类对于语言研究不断深入,我们并不否认从语言系统内部进行认知研究的一些普世性的机制,如概念隐喻等,但不能否认的是,独立于语言使用个体和社会交互及其社会文化环境,这些语言认知机制就像散落在沙漠中的机器零配件一样,无法进行自洽工作,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社会文化百科知识、语言使用主体、社会交互活动,对于探索语言的奥秘都是至关重要的,更能展现语言意义建构的全貌,让我们更接近语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