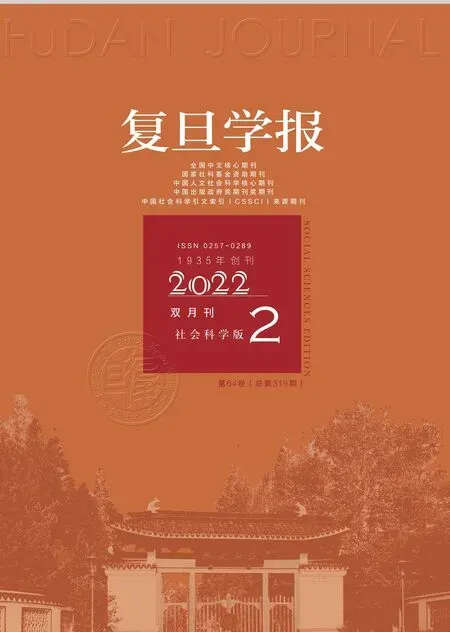杜甫晚年的家国情怀与诗歌艺术创新
——以寓居夔州之初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李芳民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杜甫自大历元年春晚携家自云安移居夔州,至大历三年正月白帝城放船出峡东下,其寓居夔府,计约一年零九个月。虽然这段时间不算长,但却是他诗歌创作最高产的时期。据统计,杜甫这段时间共作有诗歌四百三十余首,占其现存诗歌30%左右。夔州时期不仅创作量高,题材内容丰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宋人黄庭坚曾称道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九,四部丛刊景宋乾道刻本。清人彭端淑亦云:“工部至夔州后诗,年愈老,识愈精,阅历弥深,而笔力弥健。不独《秋兴》《诸将》等篇为前此未有,即将前后纪行诗较之,意见笔力,自判然各别。故吾以山谷之言为定。”(2)彭端淑:《雪夜诗谈》卷上,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而若从诗歌所表现的情怀及其艺术探索看,则夔州诗亦别具价值与意义。本文拟以这一时期杜诗往事回忆与故国之思主题表现为中心,对其暮年心理、情怀以及诗歌艺术探索作一论析。
一、 “忆往事”“思故国”的创作心理基础
杜甫夔州四百三十余首诗歌,其题材内容非常丰富。清人黄生在评杜甫《返照》诗时,曾因此诗而及杜晚年诗作之特点云:“年老、多病、感时、思归,集中不出此四意。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无不曲尽其情。”(3)《杜诗说》卷八,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341页。这个概括,就杜甫晚年创作的大致情形而言是不错的,但若就夔州诗来说,却也不尽全面。一是就感时而言,由于夔州地僻,消息迟缓,故杜甫这一时期反映时事之作就相对较少;二是杜甫晚年诗歌有关往事回忆这一内容,黄生即未提及。而就这方面来看,杜甫夔州诗歌中有影响的作品,大多与此有关,如《八哀诗》《往在》《壮游》《昔游》《遣怀》《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解闷十二首》《秋兴八首》《返照》等作。其中《八哀诗》与《秋兴八首》皆为组诗,《壮游》《昔游》《往在》《秋日夔府咏怀》诸诗,亦皆为五古或五排长篇,这些作品不仅对后世影响大,且皆为作者当时用心经营之作,因此在讨论杜甫晚年诗歌创作时,显然是不可遗漏的。
杜甫诗歌中这类主题与内容,何以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初居夔府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实值得注意。事实上它确也曾引起了学人的关注与讨论。冯至先生以为,杜甫此类诗的写作,与其此时创作时间的充裕有关。他说: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这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的面前活动起来。他写了不少长篇的诗叙述他过去的生活。(4)冯至:《杜甫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页。冯文炳先生也有类似的意见,以为“杜甫在夔州两年,因为生活单调,又比较地安闲”,所以一组一组地写往事回忆诗。见氏著:《杜诗讲稿》,《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
陈贻焮先生则以为与杜甫对自身的健康之忧有关。他在分析杜甫大历元年秋所作《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及《存殁口号二首》诗后,联系此前所作《贻华阳柳少府》一诗中的情绪,指出:
老杜意识到自己在世不会太久,已在考虑身后事了。这种身世之忧,可说是他当时感伤情绪所由产生的主要根源。《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存殁口号二首》本身的价值并不大,但从中可以窥见诗人思想感情中的新变化,有助于理解他近来何以写作了那么多忆旧怀人、悼友自伤的诗篇来。(5)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莫砺锋先生的看法则稍有不同,他认为杜甫此时之喜欢追忆过去,既与其人生走到尽头的心理有关,也与杜甫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失望情绪有关(6)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1页。莫的这一看法与程千帆、张宏生论文《晚年:回忆与反省》大致相近,见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著:《被开拓的诗世界》,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第158~159页。而沙先一《试论杜甫的夔州回忆诗》文中,曾概括诸家之说,终则赞同程、张文之观点。沙文见《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如果从杜甫夔州生活整体情况看,上述诸家对杜甫心态的把握,可以说都有其道理,但如果仔细考察杜甫夔州诗歌中这类往事回忆与思念故国主题的时间点,则对搞清这类诗歌创作心理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或不无帮助。现据《杜甫全集校注》,对这一时期此两类主题诗歌的系年,列表如下:

杜甫夔州忆往事与思故国(乡)主题诗歌表

(续表)
据表中统计可知,杜甫夔州寓居期间涉及追忆往事内容的诗歌共计16题24首,涉及思故国(乡)内容者共计19题26首,两者合计35题50首。而依年度分析,大历元年忆往事与思故国(乡)两者合计20题34首,大历二年为16题16首,则杜甫在大历元年所作的追忆往事与思念故国诗篇的数量,是大历二年的两倍。而以上数量统计,还有几点因素需要考虑。一是从创作时间看,杜甫是永泰二年(本年十一月改元大历)春晚由云安至夔州的,因此,其大历元年的夔州生活,总计约只有九个月,而大历二年的夔州生活则为一整年。二是从诗歌本身的特点看,大历元年有关往事追忆以及思念故国之作,主题与内容比较集中,且多为组诗与长篇之作,如《八哀诗》《秋兴八首》皆组诗,《壮游》《昔游》《往在》等皆五古长篇,而大历二年所作,除《洞房》《宿昔》几篇外,诗中忆往事或思故乡往往仅是作品在叙事抒情中的情绪流露或个别诗句的表现,而非整个作品主题表现的核心。三是从作品的成就看,其中影响较大者,大抵皆大历元年之作。由此看来,杜甫夔州寓居时,大历元年是其往事追忆与思念故国作品表现较为集中的时期,而其中的组诗写作,显然更是刻意为之的创作行为。
那么,杜甫何以在大历元年比较集中且刻意写作以往事追忆与故国之思为主题的作品呢?这显然和此时特殊的心理状态有关。而这种心理状态,又与其身体健康状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杜甫离开成都,原本拟出三峡而北归,但至云安后却不得不因病滞留。从杜诗所述看,他这次病得实在不轻。其在云安时所作《别常征君》诗云:
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白发少新洗,寒衣宽总长。故人忧见及,此别泪相忘。各逐萍流转,来书细作行。(7)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440页。
诗前两句,可见当时之病情病状。因病体虚弱,致使行走困难,即便有子相搀扶,仍不能脱离拐杖,且病情拖延了整个秋天,犹未见好转。次联“白发少新洗,寒衣宽总长”,写病后之衰容体态,极为生动传神。三联“故人忧见及,此别泪相望”,其中信息十分重要。于前句,清人黄生《杜诗说》引汪几希语曰:“‘故人忧见及。’言恐大命之见及。见常厚于己,深以其病为忧也。”(8)黄生:《杜诗说》卷十二,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464页。于后句,杨伦谓是故人见其病况,“言不觉而下泪也”。(9)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72页。可见故人已担忧杜甫病之不治,虑大命之将及,不免伤心落泪。总之,从此诗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杜甫的病状病情是十分严重的。
杜甫此次所患何病,竟至如此境地?从杜甫此间所写涉及他身体健康情况的诗歌来看,当是糖尿病以及由此引发的并发症。杜甫《别蔡十四著作》有句云:“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复据诗中“主人薨城府,扶榇归咸秦。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忆念凤翔都,聚散俄十春”句可知,诗应是郭英乂被崔旰所杀后,蔡著作扶护郭灵柩归秦,杜与之在三峡相逢时作,而郭之被杀在永泰元年闰十月,则此诗作年应在永泰元年末至大历元年初之间,此时杜甫恰因病滞留云安。而永泰元年末所作《十二月一日三首》,又分别有“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与“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句,移居夔州初所作《客堂》诗亦称“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以上诸诗,三次提及“消渴(中)”,一次提及“肺病”,可知其病乃以消渴为主,又兼肺病。而古人所谓“消渴”,即今之糖尿病。从现代医学观点看,糖尿病是一种由胰岛素分泌或利用障碍所导致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疾病,主要症状为多饮、多尿、多食和消瘦以及疲乏无力等,其危害在于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导致全身重要器官发生病变,而下肢无力、麻木乃至引起坏疽,则是诸多症状之一。糖尿病一般为慢性病,但若急性并发症不及时处理,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杜甫《客堂》诗曾说“旧疾廿载来”,则他可能早就患此病,而这次之所以在东下半途而滞留不前,应是旧病复发且极为严重。正缘于此,他此时不仅形神消瘦、虚弱疲乏,甚至连行走都极为困难了。《客居》诗写及他的病状与心理云:“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徐步视小园……览物想故国,十年别荒村。”其中说到因担心腿脚功能遭病被废故强力徐步小园情形,亦可见病情之严重,而“览物想故国”二句,则是因病而思念故国故乡之情的自然流露。至移居夔州后,忧虑病情与思乡之心理,无疑就更加强烈了,《客堂》诗云:
忆昨离少城,而今异楚蜀。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别家长儿女,欲起惭筋力。客堂叙节改,具物对羁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芦笋绿。巴莺纷未稀,徼麦早向熟。悠悠日动江,漠漠春辞木。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主忧岂济时?身远弥旷职。循文庙筭正,献可天衢直。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形骸今若是,进退委行色。(10)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8页。
此诗内容,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二语,已言及生死问题。二句看似达观,细味乃极悲哀语。其二是“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所流露出的思念故国故乡之情。其三是“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的恋阙报国之意与“形骸今若是,进退委形色”的无奈。而将后二者与前者作对比,则更可体会杜甫此时心境的悲凉。对故乡的思念与对朝廷的依恋,使他岂能甘愿为殊方之鬼?但死亡的阴影却已无情地逼来。特别是自去年春晚移居夔州后,夔州极为难捱的炎热之夏,令其特别感到不适应(11)至云安后,杜甫对当地气候之干旱炎热感觉很不好,《寄常征君》中曾云:“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大历元年移居夔州后,于夔之风土印象也不佳,谓其是“形胜有余风土恶”(《览物》),而整个夏季,夔州之炎热尤令杜甫感到不适,在《雷》《热三首》《火》《毒热寄崔简评事十六弟》等诗中,他反复言及当地之炎热及瘴气。毫无疑问,对于身体本就不佳的杜甫来说,这种气候无疑会加重其对己性命之忧的负面心理。,而虚弱的病体,遭逢炎热的气候,导致“多病纷倚薄”(《赠李十五丈别》),都使他每每产生死亡将至之虞。其《贻华阳柳少府》中即云:“南方六七月,出入异中原。老少多暍死,汗愈水浆翻……余生如过鸟,故里今空村。”南方夏日炎热,乃至无论老少,皆有因热而死者,对他这样身体虚弱的病人,死亡当然就更属寻常之事了,“余生如过鸟”正是对生命无多的悲叹。但是对社稷苍生与故国故乡的眷恋,使他深感在死亡到来之前,对自己的一生不能不有所交待。他感到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个人的身世经历与对社稷兴衰的认识及故乡故国的深情,做一次梳理,因此,杜甫在度过了夔州难捱的炎热之夏后,便有了追忆往事与思念故国的系列诗作。由此而言,他这一时期诗中的追忆往事与思念故国主题,实应是他感受到生命危机即将来临的产物。
二、 往事追忆与故国之思的抒写
杜甫夔州追忆往事与思念故国故乡之作,虽约有五十首,但主题表现集中且影响较大者,则为《壮游》《昔游》《往在》《遣怀》《八哀诗》《秋兴八首》诸篇。而无论是往事回忆还是思念故国故乡,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将个人遭际与命运,放在国家盛衰变化的大背景下展开,因而两者的主题,就显得特别深厚而具有深刻的意义。而就艺术表现而言,杜甫于两种主题又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前者以叙事为主,形成了其独特的传记性书写,而后者则以抒情为主,将诗歌的抒情艺术推向了极致。
杜甫追忆往事的诗歌,细分又有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为主的回忆与围绕国家盛衰变迁为主的公共回忆之别。个人生活经历为主的回忆以《壮游》《昔游》《遣怀》等为代表,国家盛衰变迁为主的回忆则集中于《往在》与《八哀诗》诸作。这些诗歌固然可以单独成篇,但如果综合考量,其相互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壮游》《昔游》与《遣怀》,作为个人经历回忆的集中代表,每一篇当然都有各自的意义与价值,但是三者合观,则可看出杜甫以诗歌叙事的形式追忆个人生活经历时极为巧妙的叙事策略。三首诗可说是《壮游》属经,《昔游》《遣怀》为纬,各自特色分明,合观则又相互补充,共同织就了杜甫平生经历的往事图景。
《壮游》一诗甚长,其价值主要在于叙述杜甫一生经历的完整性。诗从杜甫十四五岁出入翰墨场叙起,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写了早年的吴越与齐赵漫游,中年的长安经历,以及安史乱后长安沦陷、二帝蒙尘与入朝仕宦,最后写到晚年漂泊夔州与中朝隔绝的遭际与心理,可说是一篇较为完整的杜甫诗歌传记。对于此诗的传记意义,后世论者也多有论及。宋人赵次公即云:“公之生平出处,莫详于此篇,而史官为传,当时人为墓志,后人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书之,甚可惜也。”(12)见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98~1199页。明人王嗣奭则谓“此诗乃公自为传”(13)王嗣奭:《杜臆》卷八,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第257页。,浦起龙也将之与《八哀诗》相提并论,称“此诗可续《八哀》,是自为列传也”(14)⑤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2、163页。。
《壮游》作为杜甫的自我传记对杜甫一生的叙述是比较完整的,但是从叙事角度看,它主要还是以杜甫生平中几个主要时段的经历、际遇为核心,故其纵向的叙述较为丰满,而横向的延展则略显不足。比如,杜甫一生中个人交游层面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内容,诗中虽有涉及,却显得较为模糊,这样作为个人传记的丰富性就不免受到影响。而《昔游》与《遣怀》则是对于《壮游》的线性叙事为主而纵向延展不足的补充。盛唐士人多个性豪迈,颇尚交游,友朋往来是其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杜甫一生交往甚广,但自其晚年看,最值得记忆的则是天宝三载与李白、高适的梁宋、齐鲁之游。《昔游》一诗,即是对三人早年交往的追忆: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共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商山议得失,蜀主脱嫌猜。吕向封国邑,傅说已盐梅。景晏楚山深,水鹤去低回。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15)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111页。
《壮游》一诗,写及与友朋的齐赵之游曾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昔游》与之相较,不仅有叙写繁简之别,而且在诗的蕴涵上,也有深浅之异。《昔游》将三人梁宋之游,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不仅补充了《壮游》中未及的内容,同时通过今昔盛衰变迁的感慨,使个人传记性叙事增添了丰厚的历史蕴涵。诚如清人浦起龙所说,此诗乃“专忆东游宋、齐时事,以致今昔之感。在昔朋游寄兴,正值国运丰盈之时;今观乱后登庸,独成羁孤远引之迹,能无慨然”(16)⑤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2、163页。。而《遣怀》一诗,则专写其与高适、李白三人在宋中之游,这既是对《壮游》诗中交游一节的又一次补充,也是对《昔游》诗高李杜三人交游的再次补叙。浦起龙尝谓此诗,“大意与《昔游》同旨。但《昔游》专慨本身,兹篇系怀故友,由前诗递及之也。首段从宋中形胜风俗说起,雄姿侠气,足以助发豪情。次段入高、李同游事,文酒相从,平台吊古,诚为不负名区。三段带述明皇黩武,指出盛衰聚散关头。末段遣怀本旨。‘拓境’四句,总括乱端离绪。十余年事,一笔凌驾。以下客怀交谊,一往情深,此老平生肝膈,于斯见焉”。(17)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5页。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此诗的意旨与内容。而与《昔游》相较,此诗开端叙述宋中风俗习尚、都市情景,尤见出色,可谓是唐代盛时宋中都市面貌之写真影像。
如果说杜甫此类诗歌是以个人生活经历的追忆为主而兼及历史的盛衰变化与诗人身世之感的话,那么在公共性往事追忆诗歌中,时代变迁与历史盛衰则成为其叙写的焦点。他在诗中不只是简单地追忆往昔历史,而是力图通过诗歌叙事,追溯国家盛衰之变的原因。如其《又上后园山脚》:
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逝水自朝宗,镇石各其方。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朝廷任猛将,远夺戎虏场。到今事反覆,故老泪万行。龟蒙不复见,况乃怀旧乡。肺萎属久战,骨出热中肠。忧来杖匣剑,更上林北冈。瘴毒猿鸟落,峡干南日黄。秋风亦已起,江汉始如汤。登高欲有往,荡析川无梁。哀彼远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父祖茔,累累塚相当。(18)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660页。
诗从早年东岳泰山之游写起,但除了开头数句写游观外,自“平原独憔悴”以下,即转入对时代之盛衰变化原因的追溯,指出当国家富盛之时,玄宗不能节用自守,反任用猛将,轻启边衅,极意武功,致使国事反覆,贻害至今,而追惟往昔,故老伤心,真乃噬脐无及也。此诗虽从追忆个人往昔经历起,但核心却在于对国事反覆的慨叹,因此,它实则是将个人经历的追忆与宏大的历史记忆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公共性往事追忆以审视历史兴衰为核心的诗歌主题。诚如清人汤启祚所云,此诗乃是“因上山脚,感念昔游,匪志见闻,有悲时事”(19)汤启祚:《杜诗笺》卷三,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665页。也。
杜甫这种往事追忆的主题,于《八哀诗》表现得尤为突出。《八哀诗》不惟题目别有新创,用意也与前人有所不同(20)关于《八哀诗》题目的特点,宋葛立方曾有论及,见《韵语阳秋》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0页。。杜甫没有袭前人《七哀》之旧题,沿用《七哀》之故意,而是改《七哀》为《八哀》,变 “抒七情”为“哀八人”。对于《八哀》之命意,杜甫在《八哀诗》的“序”中曾有说明,云:“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殁,遂不复诠次焉。”则于所哀之八人,各有侧重,后人围绕此“序”,于《八哀》之意旨多有诠释。明人王嗣奭云:“王、李名将,因盗贼未息,故兴起二公,此为国家哀之者。继以严武、汝阳、李、苏、郑皆素交,则叹旧。九龄名相,则怀贤。序简而该,亦非今人所及。”(21)王嗣奭:《杜臆》卷七,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第235页。明末清初的卢元昌所解更周详,云:“《序》曰:‘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是于王、李二公,当从‘伤时盗贼未息’六字洗发。乾元初,邺城师溃,九节度惟李光弼、王思礼军独完。寻破史思明。后思礼为河东节度,治太原,持法严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礼未殁,幽蓟荡平,河北诸蕃,谁敢负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伤之,吐蕃之寇,代宗诏入援,迁延不行,遂疾笃而薨。假使谗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无恙,为万里长城,不惟抗幽燕,即怀恩亦何至反侧!此公伤时之意。……《序》曰:‘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是于严武以下六人,当就‘叹旧怀贤’四字洗发。公于苏源明、郑虔、李邕、汝阳、严武,皆有旧谊,苏、郑为生死交;李邕为忘年交;汝阳门下,自居申白;严公幕中,本为旧僚。‘叹旧’二字,划在苏源明等五人。‘怀贤’二字,则专属张相国。公于相国,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诗》独以张相国殿者,盖伤代宗时朝廷无贤宰相,以李岘、颜真卿之直而不用,所宠任者惟元载,如明皇用李林甫、疏张九龄。此‘怀贤’二字宜专属之。”(22)卢元昌:《杜诗阐》卷二十一,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从诠解看,卢氏于杜甫“伤时盗贼未息”与“叹旧怀贤”之意,体贴更细致,发掘也更深入。但是,其诠解也只就《八哀》“序”以及所涉八人而论,对于杜甫何以选此八人而致哀,仍未有所解说。即以杜甫旧交论,房琯与杜之交谊,不下严武,舍房琯而取严武,宜乎人有所疑(23)《八哀诗》不取房琯,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卷十三曾有解说,今人曹慕樊则驳辩之,刘明华复有《〈八哀诗〉无房琯辨》文,提出新解。曹之辩驳见氏著:《杜诗杂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15~216页;刘之新解,见《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诸将之可哀者,亦非仅王思礼、李光弼二人,若高仙芝、封常清于安史之乱中守潼关,因中人边令诚之谮含冤而死,无论于国家于个人,岂不可哀?而汝阳王李琎,杜甫固然自居为申白,然其一生安享富贵,卒后亦蒙玄宗褒崇(24)《旧唐书》本传载:“琎封汝阳郡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天宝初,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赠太子太师。”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14页。《新唐书》本传云:“琎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帝爱之。封汝阳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梁涉等善。薨,赠太子太师。”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99页。,又何以置于八哀之列?苏、郑与杜交谊不浅,而杜于李白亦终生不忘,频致云树之思,且白暮年长流,老无所依,沦落而殁,亦甚可哀,而诗则未及之。由此可知,“八哀”所选,杜甫必经仔细斟酌与考量,而“序”之“八公前后存殁,遂不复诠次焉”,自也不能无深意存焉(25)此意王嗣奭、卢元昌皆未及,今人曹慕樊谓:“‘不依存殁先后,’就是说次序别有用意。”“八人中三方镇居先(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意在‘天下危,注意将’。张九龄贤相,排在最后,重‘功人’之意。”见氏著:《杜诗杂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
其实,从《八哀诗》之所哀人物看,杜甫是兼顾了唐之盛衰也即自玄宗之盛世至肃、代之动荡两个阶段的代表性人物的。八人中,李邕、苏源明、郑虔、李琎、张九龄主要活动于玄宗时代,而王思礼、李光弼、严武,则主要活动于肃、代二帝时期,各时代人物的特点也有所不同,故借此八人,实含有总结唐之由盛而衰历史教训之意。李邕一代文宗而终遭杖杀,乃有慨于权奸之害贤;苏源明、郑虔才艺之士,皆沦落而殁,乃为盛世之才士遭际鸣不平;李琎为让皇帝李宪长子,不惟以“谨洁”著称,且礼敬贤才,是杜甫眼中宗室人物之楷范,哀李琎者,哀宗室之礼贤者之不复见也。九龄则治世贤相,忠耿立身,政治与文学俱佳,而终被疏远,致使延颈恋阙,归老故林。此五人之哀者,正哀玄宗治世之失也。肃、代处战乱不宁之时,正当用将之时,而王思礼禁暴御乱,勇略过人,严武瑚琏之器,镇守西南,治蜀有方,却于国家用才之时,不幸而殁,是为国而致慨也;李光弼一代名将,却因受谤忧谗,赍志以殁,是为肃、代之不能善待名将而致哀。至若八哀所及之人排列顺序,于“不复诠次”中,当然也含有其深意。其意殆将人物分为三组,分别述之。因伤时乱未靖,故以武将(王、李)能臣(严武)为首;贤才系乎世之盛衰,故汝阳次之,并接以李邕、苏源明及郑虔等贤能才士。而治乱根本,贤相至为关键,故以曲江殿之。总之,《八哀诗》诚为杜甫用心结撰之作,其借追忆八位已逝之名将、才士与贤相,于人物之遭际,见历史兴衰之迹,用心之良苦,实不可忽。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返归故乡,原本就是杜甫旅居异乡一直未能忘怀的夙愿,愈到暮年,其思乡之情愈加浓烈。特别是他自滞留云安起,病体缠绵,深恐大命之将及,思乡之念更为迫切。在诗歌创作中,这种情感几成为作品之主调。“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三),“览物想故国,十年别荒村”(《客居》),“有猿挥泪尽,无犬附书频。故国愁眉外,长歌欲损神”(《雨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夜》),“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中夜》),“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吹笛》),等等,皆可见其于唱叹之际,眷念故国故乡之浓情愁思。而集中体现这种情怀的,则当推《秋兴八首》。
《秋兴八首》是杜甫一生七律组诗之绝唱。其气势雄浑,韵律严整,虽各自成章,却浑然一体,固然内容丰富,但却主题集中。对于组诗的主题、意脉与艺术表现特点,前人多有概括总结。其中清人范廷谋的解说更见细致周详:
此诗八章,公身寓夔州,心忆长安,因秋遣兴而作,故以秋兴名篇。八章中,总以首章“故园心”为枢纽,四章“故国平居有所思”为脉络,方得是诗主脑。若浑沦看去终无端绪可寻。首章以“凋伤”二字作骨,凡峡中天地、山川、草木、人事,无不萧森,已说尽深秋景象,提出“故园心”三字,点明遣兴之由。“暮砧”句,结上生下。“孤城落日”承上咏暮景,“山郭”、“朝晖”,又承上咏朝景。虽俱就夔府而言,细玩次章曰“望京华”,三章曰“五陵衣马”,仍是不忘长安,正所谓“一系故园心”也。四章则直接长安,煞出“故国平居有所思”,将“故园心”三字显然道破。下四章即承此句分叙,抚今追昔,盛衰之感,和盘托出,却首首不脱秋意。“蓬莱”一章,指盛时言。“瞿唐”、“昆明”二章,指陷后言。“昆吾”一章,追忆昔游而言,皆故国平居之所思者。末则以“白头吟望”结出作诗之意,总收全局。统观篇法次第,一首有一首之照应,八首有八首之联贯。气体浑厚,法脉周密,词意雄壮。其间抑扬顿挫,慷慨淋漓,全是浩然之气相为终始。公之心细如发,笔大于椽,已可概见。至于忧国嫉时,怀才不偶,满腔愤懑,却出以温厚和平之语,全然不露圭角。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三百篇》之遗响犹存,真所谓大家数也。(26)《杜工部七言诗选直解》,清雍正范氏稼石堂刻本。
就八首之主旨而论,诚如范氏所说“故园心”为其枢纽,即对故国故乡的思念是八首之核心。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范氏所谓“忧国疾时,怀才不偶,满腔愤懑”之意,这实际也就是八诗中所蕴含的忧国伤时之情怀。这一内容,八诗中的表现隐显不同,而其四则较为显豁: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27)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807~3808页。
此首所慨叹者,乃自安史之乱以后至作者寓居夔府时之历史迁变。首联点明长安,盖长安为唐政治之中心,观长安自可觇当代政治之晴雨,而今睹世事之变幻有若弈棋,则悲慨油然而生。颔联集中表现肃、代二帝两朝之人事更迭,蕴涵极为丰富,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大抵杜甫所慨非止一端,缙绅之非故,冠裳之倒置,官爵之滥赏,时俗之易旧,皆在其中。”(28)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而颈联写战乱不宁的时事,据史书所记,亦皆有据。《通鉴》二百二十三载,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寇,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未久即东向攻长安,代宗于仓惶之际,命郭子仪出咸阳以御敌,而郭则因长期闲废,部曲离散,仅募得二十余骑而行,逮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已渡渭桥,代宗狼狈幸陕,长安失陷。其时六军叛散,吐蕃大肆劫掠,京城一片狼藉,幸赖郭子仪苦心召募,竭力苦战,吐蕃方退,代宗也才得以返驾回銮。又两《唐书》之《李光弼传》载,当吐蕃犯京师时,代宗曾诏天下兵,李光弼因与宦官程元振有隙,虑遭其陷害,因迁延不至(29)《旧唐书》载:“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李光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10页。《新唐书》亦载:“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见《新唐书》一百三十六《李光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0页。杜甫所谓“征西车马羽书迟”,当谓此也。。杜甫此时虽远在殊方,但当耳闻时事,遥想故国政局,反思自身如鱼龙之寂寞,自不能不生深切之感怀,此即末联“有所思”之深衷所在。“公诗叙离乱多至百韵,或五十韵,或三四十韵,惟此篇最简而切也。”(3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13页。宋人刘克庄的评论,颇为中肯。
杜甫寓居夔府孤城,深感生命无多,故回顾生平,眷恋故乡,成为其诗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初居夔州的大历元年,他通过往事回忆,为自己也为时代写真存照,又以对重要人物的传记书写以及对故国往事的追忆,表达对历史兴衰与世事沧桑的认识与感受,凡此都可见出其一生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三、 “千秋之绝调”与“自我一家则”
追忆往事与思念故国,是杜甫寓居夔府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与内容,而这两者虽有多篇作品涉及,但以表现之集中论,则不能不推《八哀诗》和《秋兴八首》。《八哀诗》与《秋兴八首》皆为组诗,前者为五古,后者为七律,各由八篇构成,无论就作品内容之分量还是艺术形式之严整,都可谓是杜甫用心结撰与苦心经营之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杜甫晚年在诗歌艺术上追求创新与突破的代表作。但是,就后世的影响看,《八哀诗》却远不及《秋兴八首》。
后世对《八哀诗》虽不乏褒赞,但批评之声亦不少。刘克庄曾说到宋人对此诗的不同意见,云:“杜《八哀诗》,崔德符谓可以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韩子苍谓其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惟叶石林谓长篇最难,晋魏以前无过十韵,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不敢议其病。盖伤于多,如李邕、苏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尽善。余谓崔、韩比此诗于太史公《纪》《传》,固不易之语,至于石林之评累句之病,为长篇者不可不知。”(3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77页。明人卢世(德水)也说:“《八哀诗》,未免伤烦伤泛,中有数十光洁语,堪与日月并垂者,自不为浮云所掩,大概诗家之元气在焉,杜诗之体统存焉,不可遗,亦不容选也。”(32)《杜诗胥钞余论·论五言诗》,明崇祯七年卢氏尊水园刻本。这些评论所涉及的批评,虽有所指擿,但还算客气,至清人王士禛所论,出语就严苛得多:“杜《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啽呓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又云:“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剪裁。而前辈多推之,崔鷃至谓‘可表里《雅》《颂》’,过矣。试摘其累句,如《汝阳王》云:‘爱其谨洁极,上又回翠麐;天笑不为新,手自与金银;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盼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众归赒济美,摆落多藏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苏源明》云:‘秘书茂松意,溟涨本末浅。’(《文苑英华》本异,亦不可晓。)《郑虔》云:‘地崇士大夫,况乃精气爽;方朔谐太枉,寡鹤误一响。’《张公九龄》云:‘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讽咏在务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末缺只字警。’云云率不可晓。披沙拣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为群瞽语白黑也。”(33)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3~54页。除了指摘诗中之句外,亦有人批评其叙事选材之失者,如明人杨慎颇不满意杜甫《八哀诗》之张九龄一篇,乃别作一首,并作跋语谓:“刘须溪云:九龄大节,在奏请斩禄山以绝后患。杜公《八哀诗》,既不明白,末亦不及另祭事,殆失‘诗史’,未免拾其细而遗其大也。慎辄为补一篇,岂敢以庞凉斗华袞,铅刃齿步光哉,亦续须溪之余蕴,发曲江之幽光,观者勿哂之。”(34)《补杜子美哀张九龄诗》,杨慎:《升庵集》卷二十二“五言排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围绕《八哀诗》之批评,确存在褒贬毁誉之异,对此,《御选唐宋诗醇》作调停云:“子美《八哀》,自是钜篇。然以韵语作叙述,情绪既繁,笔墨不无利钝。大家之文,正如黄河之水,滔滔莽莽,鱼龙砂石与流俱下,非如沼沚之观,清泠可喜而已。论此诗者,誉之或过其实,毁之或损其真。惟卢世曰:《八哀诗》未免伤烦、伤泛,然诗家之元气在焉,杜诗之体统存焉,不可遗,亦不容选。斯言得之。”(35)《御选唐宋诗醇》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相较而言,对《秋兴八首》的褒赞则要远多于对它的批评(36)今所见持批评意见者,仅明人卢世、清人袁枚与今人冯文炳。卢世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八首中的其三与其五,见《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明崇祯七年卢氏尊水园刻本。袁枚的批评则出于个人的趣味,见《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45页。冯文炳则认为杜甫夔州诗因多用典故、注重形式而缺少了生活气息,见《杜诗讲稿》,《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但总体看,这些批评属于少数派,而对《秋兴八首》的褒赞要远多于这类批评。。在后人心目中,《秋兴八首》不惟被当作杜甫七律的代表,甚至还被认为是唐人七律之作中难以企及的典范。清人徐增谓:“《秋兴八首》规模弘远,气骨苍丽,脉络贯通,精神凝聚。痛是真痛,痒是真痒,笑是真笑,哭是真哭,无一假借,不可动摇。论才情,真正是才情。论手笔,真正是手笔。七字之内,八句之中,现出如是奇观、大观,真使唐代人空,千秋罢唱。寄语后世才人,勿再和《秋兴》诗也。”(37)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十七,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九六》,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沈德潜亦称其“怀乡恋阙,吊古伤今,老杜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38)沈德潜:《杜诗偶评》卷四,清乾隆十二年赋闲草堂刻本。而清佚名则从七律角度推尊其无上之地位,谓:“盖唐人七律,以老杜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郁结,与其遭际,暨其伤感,一时荟萃,形为慷慨悲歌,遂为千古之绝调。余尝总而计之:唐人七律,莫盛于早朝应制诸篇,而未免言之太庄,工丽有余而生动不足。中晚以后,鲜新旖旎,而气格寖微,若高华典赡,而望之又如出水芙蕖,妍秀轻灵,而按之又龙文百斛,则惟此《秋兴》之为独步也。”(39)〔清〕佚名:《杜诗言志》卷十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又云:“八首先后次第,彼此映照。如游蓬山,处处溪壑迥别。如登阆苑,层层户牖相通。以言格律,则极其崇闳,议论则极其博大,性情则极其温厚,罕譬则极其精当。然皆其兴会所至,一笔写来,自然妙丽天成,不待安排思索。此天地间至文也!读者详之。”(40)〔清〕佚名:《杜诗言志》卷十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9~230页。
后世围绕《秋兴八首》与《八哀诗》的褒赞与批评,实际上也反映了杜甫在五古组诗与七律组诗创作上进行创新探索的成败与得失,因此,对之作出分析与总结,对于整体认识杜诗在各体诗歌创作史上的贡献,应是颇有意义的。
杜甫的诗歌淹有众家之长,因而有“集大成”之誉。但杜诗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继承前人,而且还在于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守正而又能变,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言:“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有众调,故绝不可及。”(41)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3页。《秋兴八首》与《八哀诗》也可以说是他在七律组诗与五古组诗两种体式上创新探索的具体实践。
七律是唐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定型于初唐,此后历盛、中、晚而又有所变化与发展。在初盛唐时期,七律的题材尚较狭窄,内容较单薄,主要为宫廷场合的应酬与唱和。而杜甫对于唐代七律的发展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五:篇制多,一也;一题数首不尽,二也;好作拗体,三也;诗料无所不入,四也;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42)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0页。概括言之,在七律创作上,杜甫除了晚年所作拗体外,正格七律的新变与贡献,则主要以题材内容的开拓、体制的变化、结构的讲究最为显著,而这几点,《秋兴八首》也可以说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典型。
杜甫七律题材内容的开拓,主要在于突破了初盛唐诗人仅限于奉和唱酬、登临游览的狭窄范围,而把唐诗所能表现的几乎所有题材内容,都引入到了七律这一体式之中。“他在奉酬赠别之外,把题材扩大到忧时伤乱、咏物怀古、羁旅述怀、日常遣兴等多方面。”(43)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页。而就《秋兴八首》而言,杜甫对七律表现内容所做出的开拓创新,也基本上都有所体现。以内容与格调而言,《秋兴八首》所表现的家国之思与沉郁之情,无疑是杜甫诗歌同时也是其七律创作特征的最集中体现。杜甫把诗歌最崇高的主题与最沉挚的情怀融入《秋兴八首》的创造之中,当然也就具有开拓唐人七律题材内容方面的典范意义。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他运用组诗形式对七律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上。杜甫晚年曾先后创作有《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等几组大型的七律组诗,这是杜甫在七律创作方面对前人的重要突破。而从创作时间看,杜甫的这些七律组诗,比较集中地出现于寓居夔州的大历元年(44)《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作于广德二年,是杜甫最早的七律组诗,也可说是杜甫的初次尝试。但夔州寓居以前,大型七律联章组诗仅此而已。。很显然,这是杜甫有意识进行大型组诗创作的新实践。前人曾将早前创作的《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一组与后来所作的几组作过比较。清人仇兆鳌即云:“杜律如《秋兴》八首,《诸将》《古迹》诸首,虽叠章联络,而语无重复,故其气骨风神,俊迈不群。若《寄严公》五首,意思颇嫌重出,盖赴草堂只是一事,寄严公只是一人,缕缕情绪,终觉言之繁絮耳。”(45)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10页。他认为《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一组诗,从整体结构来看,不免有所欠缺。这说明,杜甫最初所作之七律组诗,尚未臻于尽善尽美,而后来再作《诸将》《秋兴》与《咏怀古迹》就不同了,无论结构还是整体艺术,都臻于极高的境地。清人吴农祥即云:“公诗藏议论于抑扬之间,陈世事于音律之外,自辟堂奥,独树旌旗,《秋兴》《诸将》《咏怀古迹》而已。”(46)刘濬:《杜诗集评》卷十一引,清嘉庆九年藜照堂刻本。但是,从组诗结构的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各自成章而又有机统一来看,《秋兴八首》似又更为出色。清人陈廷敬曾称道说:“杜此八首,命意炼句之妙,不必论,以章法论,章各有法,合则首尾一章,兵家常山阵庶几似之。人皆云李如《史记》,杜如《汉书》,予独谓不然。杜合子长、孟坚为一手者也。或谓八章摘取一二者,非。又杜此诗古今独绝,妄儗者尤非。”(47)陈廷敬:《杜律诗话》卷下,见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五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人吴瞻泰则有更细致的分析,谓:“其惨淡经营,安章顿句,血脉相承,蛛丝马迹,则又八篇如一首,其次序不可紊焉。”(48)吴瞻泰:《杜诗提要》卷十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294页。可见《秋兴八首》在组诗的结构艺术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由此也可以说,《秋兴八首》是杜甫在唐人七律创新上运用组诗形式成就最突出之作。
与《秋兴八首》不同,《八哀诗》则为五古组诗。五古是源远流长的诗体之一,不过后世的诗论家论及五古,大多以汉魏为典范,而于唐人五古则褒贬不一(49)如明人李攀龙、陆时雍即从汉魏典范出发,对唐人五言多有贬抑,分别见李攀龙《选唐诗序》(《沧溟集》卷一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陆时雍《诗境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3页)。。杜甫的五古,对前代多所继承,但同时也做出了很多创新,而在五古艺术及体式上的革新尤为显著。清人沈德潜即谓:“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又云:“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50)沈德潜:《说诗晬语》,见《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534页。这主要是针对杜甫五古叙事与议论的运用技巧而言的。管世铭则从体式的创新上,指出杜甫的开创性贡献,云:“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砯》,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51)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46页。
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吸收彼此的手段与技巧,通过“破体”而寻求艺术上的突破,是中国古代各体文学获得新发展且被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所采用的艺术创新方式。杜甫五古组诗的创作,也是如此。但是,以“破体”创新,既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与失误的风险。《八哀诗》的创作以及由此引致的后世相关之批评,大致即反映了这一点。
管世铭以《八哀诗》为碑状体,大致是说其兼有古代碑、状两种文体的特征。但在古代文体学家划分的文体类型中,“碑”与“状”实为两种不同属类。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古文体式划分为十三大类,其中传状与碑志即在不同属类中。“传状”类中,“传”本之于史传之人物传记,而“状”即“行状”,其以记述人物事迹为主,目的是备史传与碑碣作者之采择。二者侧重虽略有不同,而皆以记述人物生平事迹为主,所以姚鼐将其归为一类。而“碑”之用,则在刻石。姚鼐谓:“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52)⑦ 《古文辞类纂·序目》,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页。因传状与碑志两者用途不同,故行文风格也因此有所不同。传状写人,多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叙述人物事迹,往往选择典型之言行以传其神,而碑志则重在忠实记录志主之生平大略,语以典雅为则,多质朴凝重,故姚鼐称“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53)⑦ 《古文辞类纂·序目》,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说杜甫《八哀诗》为碑传体,也即是说杜甫吸收了“碑”与“传”的一些表现手法,将二者兼而用之。对于《八哀诗》与史传之间的关联,前人多有论及。明人郝敬称:“《八哀》诗雄富,是传纪文字之用韵者。文史为诗,自子美始。”(5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六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20页。清人李因笃也说:“《八哀诗》叙述八公生平,称而不夸,老笔深情,得司马子长之神矣。”(55)刘濬:《杜诗集评》卷三,清嘉庆九年藜照堂刻本。应该说,《八哀诗》确有一些因吸收史传写人技巧而显得生动传神处,如《故司徒李光弼》之“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写李光弼遭谗不敢入朝及其临死之悲愤;《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之“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刻画李琎容貌特征与气质等。但以诗融碑志手法,整体上看,毕竟还是显得板滞有余而韵致不足。诚如王夫之所云:“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檃括生色,而从实着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56)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而碑志体又讲究用语凝重典奥,这也增加了《八哀诗》语言风格的整体上偏于古奥典雅而清新自然不足。如《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之“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分宅脱骖间,感激怀未济……荣枯走不暇,星驾无安税。几分汉庭竹,夙拥文侯篲。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用事典赡,而终欠灵动。刘克庄亦曾谓:“《八哀》诗中,如郑、苏二首,非无可说,但每篇多芜辞累句,或为韵所拘,殊欠条鬯,不如《饮中八仙》之警策。盖《八仙歌》,每人只三四句,《八哀》诗,或累押二三十韵,以此知繁不如简,虽大手笔亦然。”(5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4页。其实,这里还不仅是繁简的问题,关键在于以碑志语为诗,不免造成诗语典重板滞之弊。
无论是传状还是碑志,一般皆以叙事为特色,作者的主观情感应尽量藏而不露。但是,《八哀诗》叙八公事迹,乃以诗作志,而诗歌体式的特点,又使作者不能不在其中表现对八公之情感。“八哀”以“哀”名题,本身就体现了作者主伤悼的情感基调。不仅如此,作者写《八哀诗》,也还隐然有融入自身身世之感在内,故其对所传人物之事迹,多有从自己感受认知出发的特殊剪裁。浦起龙在分析《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不写张九龄早识禄山一节时曾说:“此篇为《八哀》之殿,须融汇老杜一生心迹看。识更卓,意更微,自来罕有窥测者……直借曲江作我前身。因而序中特许为‘贤’,诗中特略其彰彰事迹。专以忧谗寄兴,为一篇宗旨。此又寓怀之微意也。太史公作《史记》,杜公作诗,都是借题抒写。彼曰‘成一家之言’,此曰‘自我一家则’,意在斯乎。论者徒观曲江本传,以为能识禄山反相,乃一生大节,讥此诗不免挂漏。不知‘伤时盗贼’之意,已发露于王、李两篇。此篇本旨,不属乎此。”(58)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58~159页。其实不惟写张九龄一篇如此,写严武也是这样。严武镇蜀,破吐蕃,收盐川,为当时第一功,而诗中未叙,却于严武承命赴灵武谒肃宗事特别著笔,自是别有意味在。清人杨伦即指出:“镇蜀为严公一生事业,且知己之感存焉。至扈从赞议事,本可简笔带过,以公于是时亦自陷贼谒上凤翔,触着当时情景,故不觉言之详耳。”(59)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80页。
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夔州时期是杜甫晚年于诗歌艺术臻于极诣的阶段,其创新意识也更为自觉。《秋兴八首》与《八哀诗》既分别是七律组诗与五古组诗的精心结撰之作,当然也应该是其创新诗歌体式与艺术表现的重要成果。前者将七律的艺术表现功能发展到了极致,显然是七律艺术创新的巨大成功,故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与推崇;而《八哀诗》则是他融合碑、传二体来拓展五古艺术表现的一种新尝试,只是由于未能使不同体式间的融合达致尽美尽善之境,不免使人稍有缺憾之感。《秋兴八首》或可以受“千秋之绝调”“天地之至文”之美誉,而《八哀诗》之“自我一家则”,则因这种缺憾,也就未能成为后世诗家普遍所许之“诗家之通则”。尽管如此,杜甫于诗歌艺术追求上所显示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毫无疑问是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