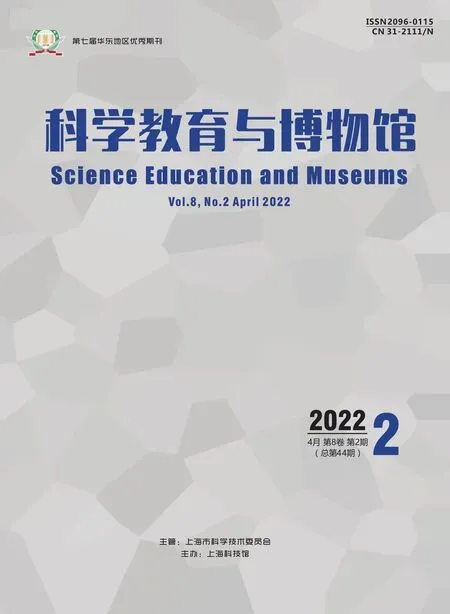微信实现馆校合作教育新模式
胡 盈
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
0 引言
疫情时代对场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传播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对场馆教育来说,新媒体的利用比拼正成为博物馆的新战场[1];对学校教育来说,在线教学环境的设计和利用成为一种“新常态”[2]。依托互联网,场馆教育通过“数字博物馆”“云游博物馆”等多种形态呈现;而学校教育打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间束缚,实现了教育空间的拓展。
2021 年,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要为大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提供有力支撑”[3]。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存在空间上的天然隔阂,分属于两个独立活动系统[4]。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学校空间的馆校课程常常失去了博物馆学习的情境性和自主性;而在博物馆空间的课程又往往牺牲了学校教育严格的课程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的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教育的课程设计成为当前讨论热点。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知识传递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改革了传统教育体系[5]。《人民日报》专文指出,“教育现代化应与社会现代化同频共振。”[6]在互联网社会蓬勃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到来为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的教育空间建设提供了可能[7]。然而,尽管互联网已经走入生活,但对于馆校结合教育来说,如果需要依赖外部设备和外部软件的投入则会使得课程建设投入成本高而无法在学校普及,同时,高技术壁垒也会阻碍教师利用互联网开展教学[8]。因此,利用日常生活熟悉的互联网平台打破空间隔阂,连接场馆与学校教育成为馆校合作教育拓展的必须途径。而微信正是这样一个广泛融入日常生活,也被场馆广泛利用作为物理空间延伸的平台。在疫情期间,微信上的沟通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工具,通过微信发布的各类线上博物馆云游资源也成为场馆教育的延伸。尽管日常生活的信息获取与微信平台结合紧密,但如何有效利用微信平台结合场馆学习实现学校教育空间拓展需要经过探索和设计。本文即致力于对此课题的探索。
1 微信结合场馆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
研究述评
首先,从资源基础的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场馆教育的辐射。微信公众号在博物馆社会教育中担任起宣传员、讲解员、社会教育教师、联络员四大职能[9]。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起到对博物馆展览内容的阐释、公众参与、信息发布、娱乐互动的多重作用[10]。而除了博物馆自身开发的公众号以外,第三方平台对于博物馆的宣传和阐释对场馆学习融入生活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强了公众的微信场馆教育“黏性”。
其次,从学习效率的视角来说,微信上的即时学习以“碎片化学习”和隐形知识建构的样貌出现,是对正式教育系统学习的有效补充。王竹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学习及应对之策——从零存整取到‘互联网+’课堂》一文中将广义的碎片化学习定义为用零散时间和空间、碎片化资源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学习[11]。碎片化学习具有跨学科、易接受、高度灵活性以及对碎片化时间的有效利用、易维持学习者兴趣等特点。碎片化学习和系统学习成为当代人必不可少的两种学习方式。个人的知识体系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同构成,而碎片化学习对隐性知识的架构起到重要作用。微信平台正是人们日常有意识或无意识碎片化学习的重要手段,将其与课堂学习相结合。利用微信平台实现“零存整取”的学习,并与学校教育的系统化学习结合,完整知识的获取、加工、整合、应用、迁移、传播、再创造,是互联网时代学习方式的改革。
第三,从学习模式的角度来说,作为新媒体平台之一的微信实现了基于社会教育的新的学习互动模式。胡钦太、林晓凡总结了“新媒体社会教育的互动循环模式”“新媒体社会教育的裂变传播监督模式”和“新媒体社会教育的分级传播模式”三大模式[12]。而微信的信息传播、信息发布和即时通讯功能都符合这三种教育互动模式,因而能达到对知识系统的构建、互动诠释和加强深化的学习效果。
通过搜索知网发现,关于微信辅助教育教学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理论研究有诸如“基于微信平台的移动教学设计研究”[13]、我国教育领域微信应用可视化研究[14]等。应用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在具体学科或课程中的应用(如大学英语等)[15]、在某一学习领域(如思政领域)的研究应用[16]、对于教学支撑平台或管理平台的应用[17]。当我们更聚焦对于“微信”辅助“场馆教育”或“博物馆教育”的研究时,发现大部分文章都仍然将“微信”结合“场馆教育”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讨论,如“微信公众平台对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影响”[18]、“新媒体在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应用与意义”[19];而微信辅助场馆教育在学校场域中的论述却寥寥无几。而事实上,微信可以为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教育带来新的维度,通过增加学习的渠道、改变学习的方式来促进教学方式的改革。2010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NMC Horizon Report)首次推出博物馆教育版,标志着新技术与博物馆的融合研究正式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20]。这些新技术的推行拓展了教学的“场域”,也有助于学校教育者通过场馆提供的“技术空间”来实现教学手段的创新。
博物馆教育创造了共情和尊重自己的空间[21]。情境化是场馆教育学习的一大特色。美国学者福尔克(John H.FaIk)和迪尔金(Lynn D.Dierking)将影响博物馆学习效果的三种情境确定为个人情境、社会情境和物理情境,认为这三大情境的互动作用对参观者在场馆学习过程中的知识获得产生了积极影响[22]。如何将“场馆情境”搬入“课堂”常常是学习的难题。而“数字博物馆”作为“场馆空间”的延伸,无法直接和课堂教育衔接,因此需要第三方平台来搭建馆校结合的空间桥梁。作为融合信息发布、传播和交流的新媒体平台,微信承担着丰富的社会教育功能:从场馆教育的角度,微信平台体现了“融入生活”的学习样态;从技术实现角度,微信的功能包括信息的主动发布、信息链接与共享以及信息实时交互。具体功能,如:公众号的发布、小程序的应用、二维码场馆导览的实现、第三方平台教育产品(如展览APP等)通过微信的链接传播等。然而,尽管微信平台的出现连接了学校教育和场馆教育,实现了教育空间的互通延伸,但信息技术推进的“表征的空间”须在信息技术背景下形成不同于传统教学秩序的内外空间组构,否则个性化的学习将依然被压制[23]。因此,如何利用微信,结合场馆服务于学校教育的目的,实现教学秩序的“空间重构”,且探索有效学习模式的建设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2 微信结合场馆的学校教育课程建设分析
2.1 微信的场馆教育应用
微信在场馆中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场馆教育的“翻转课堂”,公众从被动地观看博物馆的展览走向主动、积极地选择从场馆资源中获取知识信息,并实现场馆教育在生活中的延伸。这其中的技术有场馆本身开发的公众号、二维码导览等,也有第三方开发的小程序、APP 等,可以被教学有效地利用(见表1)。

表1 微信的场馆应用
第三方小程序,如“博物官”,能通过拍照识别艺术品,并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知亦行博物馆”则根据地域提供展览介绍,能培养学生在课外自发去博物馆拓展知识,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而一些展览APP,如“爱去博物馆”,则提供主要场馆的参观路线和展品介绍。这些小程序、APP 等,不仅是教师的得力助手,而且更方便学生通过场馆自主学习、小组学习。
2.2 微信平台在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微信功能的不断升级开发,其与教学的融合也越来越深入、广泛。作为一款多功能的即时通讯工具,微信及其电脑客户端对于多媒体资料的接收和发布、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锻炼,以及师生间的互动、教学评价都能提供便捷的平台辅助(见表2)。

表2 微信的教学功能
2.2.1微信上的教学辅助平台
微信中也有一些公众平台以教学辅助为定位。比如“微助教”公众平台,本身相当于一个简易的在线教学平台,包含课堂签到、课件发布、在线讨论、小测验、课程存档等功能,使用便捷,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设备。该平台为教师、学生分别提供独立的功能通道,在关注“微助教”公众号后,教师经过认证,学生选择“加入课堂”即可建设课程。
2.2.2个性化课程应用:课程公众号的建立
对于课程公众号,教师则可以根据课程的实际需求,自定义菜单项。比如“博物馆课堂”公众号是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里的中国”课程的教学辅助公众号,目前设置的菜单分为“课程相关”和“学生作业展示”两类。在“课程相关”里,主要包括课程信息、教学资源发布、讨论区、和教师的联系等。课程公众号的设立有助于打造课程特色,并提供教师与学生专享的教学成果发布空间。
2.2.3在线讨论:“微社区”
“微社区”是微信的一个重要功能,内嵌在微信公众号里。微社区需要单独申请(http://wsq.qq.com/),绑定微信公众号。其实质类似论坛,具有发帖、回复功能,是在线多人沟通共享观点的社区。“微社区”的使用,能帮助师生实现线上讨论、共享的效果。相比“群聊”,“微社区”能提供针对某个话题更正式、严谨的学术讨论。
2.2.4课程效果评估:“问卷星”等工具的微信链接
微信功能的强大还在于它能方便地与其他程序结合,在微信中开展实施。对于课程效果的评估,“问卷星”和“微信”的结合,能有效地实现课程效果评估、学生能力评估和课程应用反馈的效果。“问卷星”提供的“在线考试”功能,可以将题库与考试内容一键导入“问卷星”创建考卷,将考试链接生成二维码通过微信发放给学生。“问卷星”开发的“360 度评估”功能,也可以用在课堂上实现自评、互评与教师评价结合的多元化评价。
2.2.5协作学习:微信上的合作编辑平台
另外,微信上也有一些有助于合作完成任务的公众平台,如:“Tower”“金山文档”等,方便团队开展讨论,查看项目进展,有助于促进协作学习,辅助小组合作项目的完成。这些平台的应用为项目化学习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2.3 微信辅助馆校结合课程应用分析
工具的使用可以帮助学习目标的实现。微信作为平台辅助工具,可以在课程的前、中、后三个阶段结合场馆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和理念(见表3)。
2.3.1课前学习阶段:问题导向的自主学习
课前学习的目标不仅在于知识的准备,更在于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服务,自主建构知识的开始。这一点正是场馆教育和通识教育共同的目标,而微信可以帮助这一目标更好的实现。
在课程开始前阶段,利用“翻转课堂”的理念,学生在课前完成知识储备以及场馆学习的准备工作。此时,学生通过学习课程公众平台发布的学习资源、视频信息等,可以完成自主探究的知识储备,还可以利用“微信搜索”进行学习资源探究。微信的“搜索”与百度等浏览器“搜索”不同在于,微信上搜索的范围是所有公众号、朋友圈等的内容匹配,相比于百度等搜索网站,搜索到的内容过滤了大部分广告等无效信息,包含更多官方发布、精心制作的推送、新闻等内容。尤其在场馆资源的利用方面,微信搜索有很强的信息功能。
对于场馆学习而言,另一重要准备在于课程开始前学习单的制作。学习单的制作可以帮助学生带着目的、带着问题的探索,而这正是学校教育借助场馆所希望实现的学习方式。以学生为导向的学习单制作,强调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个性化确立学习目标。这一过程中,同伴和教师的帮助可以使学生达到学习的“最近发展区”,更好地完成学习目标的确认。“最近发展区”的概念由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他将人在教学中的发展分为两个水平:现在发展区和最近发展区,在指导和帮助下,通过努力可以达到最近发展区,从而实现智力水平的提升[24]。此时,微信的“微社区”功能便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学习单制作环节,微信的即时通讯功能和大信息量都能为学生展开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提供便捷。
2.3.2课程中阶段:情境学习的互动探索
根据情境学习理论,知识与活动是不可分离的,活动不是学习与认知的辅助手段,是学习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5]。学习本身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实践[26]。因此,对于通识教育而言,在课程中的学习是建立在情境学习基础上的文化科学素养的养成。
通过微信链接的在线场馆资源(线上博物馆、虚拟展馆、云游博物馆等)可以营造情境化学习环境。然而,如果情境化的学习环境中没有教学引导,则失去了课堂教学的严谨目标;如果在场馆教育的环境中教师不能很好地把控教学节奏的推进,则教学的效果将大受影响。
有时,由于场地的限制和其他观众的干扰,学生们很难在场馆学习的环境中继续跟紧课堂教学的节奏。而微信的好处在于,通过电脑客户端和移动端的同时登陆,学生可以在云游博物馆的同时通过微信客户端链接课程学习资源,与教师和同学互动探讨,完成任务单填写等诸多教学活动。这一过程从技术上并不需要安装或运行额外的APP 以增加移动客户端的负载负担,同时,又人人可及能用,创造了无障碍的沟通。
2.3.3课后学习阶段:合作分享的学习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发展,致力于在真实情境中问题的解决。因此,将知识学习服务于自身能力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在课后学习阶段,微信将有助于实现知识的内化和迁移。根据认知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生的认知从“记忆、理解”走向“应用、分析”走向“评价、创造”。[27]对于教学而言,前两者都容易实现,而第三步则需要外部的平台和资源支撑。所幸,在微信上可以方便地帮助学生实现“模拟展示”而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和空间。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博物馆里的中国》通过课程公众号给学生提供了策划“虚拟展览”的平台。学生们通过合作学习(Team-based Learning,TBL)设计微信展览实现了认知的“创造”,完成了知识的内化和迁移。同时,通过分组在微信上展示各自的虚拟展览成果,帮助学生实现相互评价,在评价与分享中不断提高。(见表3 和图1~图3)

表3 课程前、中、后三个阶段场馆结合通识教育的学习模式

图1 课前阶段通过课程公众号提供学习资料

图2 课中阶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结合场馆学习实现实时沟通

图3 课后阶段通过课程微信公众号完成虚拟展览和教育设计
在这一案例中,微信结合场馆资源运用于大学通识教育阶段。亚里士多德提出以“理性的发展、心灵的培养”为目标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被认为是现代“通识教育”的起源[28]。瑞切特(Richter)认为,场馆教育终极性的意义就是它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帮助[29],这一点正与通识教育的理念契合。通识教育和场馆教育的契合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特点等方面。而微信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为促进两者的结合起到了深化教育效果、实现教育目标的作用。从教育效果来看,学生对微信融合场馆教育的教学方式非常喜欢,而兴趣激发了他们在课余时间更多地前往博物馆实现自我提升。通过课程调查了解到,61.3%的学生在课程期间去过博物馆,90.6%的学生认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有助于了解博物馆和欣赏文物[30]。可见,微信平台的作用并不在于“替代”场馆教育,反而更促进了场馆教育在学生学习生活中的融入。
3 讨论与反思
上述分析呈现了微信结合场馆服务学校教育课程设计各个阶段的学习呈现。而本文的论述也带来了进一步问题的思考。
3.1 “真实”的“在场”与“缺失”
尽管技术实现了“足不出户”开展场馆学习的可能,但同时,技术所营造的虚拟情境是让我们更接近真实还是远离真实?技术是否有带动学生们更多访问博物馆的兴趣还是只是作为空间隔离的一种“补偿”[31]?今天社会是“读图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图像而非“真实”来理解世界,技术营造的“幻境”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是帮助还是阻碍?对教育者来说,当我们在“营造”真实情境的时候,“真实”的缺失是一种代偿还是一种被替代的实境?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探索。
3.2 技术的“支架”与“依赖”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构成了学习的支架[32],促进了教育手段的革新。而同时,技术是否也会成为一种学习“依赖”?当学生们更多选择在线上“留言”“互动”时,面对真实的课堂,他们是否变得更加“沉默”?当技术给予学生自主寻找答案的便利时,是否也抑制了自主思考的过程?对于场馆学习而言,当学生过于依赖通过微信获得关于展品的介绍和学习经验的分享时,是否削弱了对展品主观观察、思考推断的动力?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跟踪调查来解决。
3.3 教学手段的革新与内容创新
尽管微信与场馆都是教学的好工具,对于这些教学工具的使用必须创造相适应的学习内容,否则,微信的使用和场馆的利用都仅仅流于形式。从学习资料的角度来说,教师能否发布适合微信阅读或收看的,图文并茂、高信息量的学习资料;从场馆学习的角度来说,教师是否能有效利用场馆提供的微信资源设计好针对课程内容的教学方案;从课程评价来说,如果作业报告通过微信提交,教师是否能设计适合微信发布的接地气的作业?同时,对于碎片化学习与系统学习之间的融合、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也是值得教师反复思考和推敲的。
4 结语
疫情时代对教学改革的呼吁催生了新的教学手段,微信成为连接馆校结合的桥梁。本文展示了如何运用微信这一线上平台实现馆校结合的学校课程设计,并讨论了技术革新带来的教育困惑。本文从课程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展示了微信结合场馆融入学校教育的课程实施并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其中的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