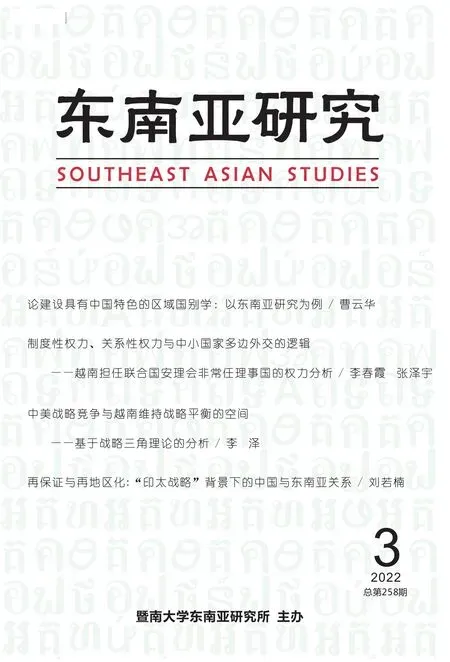缅甸宪法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缅甸)伍庆祥
引 言
16-19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民族主义逐渐萌发和崛起,掀起了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二战后,东南亚各国先后取得独立,但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挑战。其中,缅甸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迄今为止,这个国家仍未基本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8年独立后不久,缅甸即开始陷入大规模内战和民族冲突。至今70多年来,缅甸内战仍未能平息。期间,缅甸发生了四次军事政变,导致国家体制数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军人废除了两部宪法,制定了两部宪法。截至目前,缅甸共出台过三部宪法,分别是1947年出台的《缅甸联邦宪法》、1974年出台的《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以及2008年出台的现行《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这三部宪法的废立过程实际上正是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其中存在的问题、冲突与困境是我们理解这一议题的重要视角。
目前,学界对缅甸宪法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在理论视角上都遵循了政治宪法学将宪法的政治性作为“中心概念”(1)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于嬗变》,《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或“根本属性”(2)参见泮伟江:《宪法的社会学启蒙——论作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的宪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的出发点,但在研究方法上则分为两种范式。一是将宪法作为分析缅甸政治材料的宪法解释学范式,如1947年宪法所体现的国家发展战略(3)祝湘辉:《制度设计与现代化的挫折——试论1947年《缅甸联邦宪法》与缅甸发展战略的选择》,《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5期。、2008年宪法作为继续保持军人干政的策略(4)范宏伟、肖君拥:《缅甸新宪法(2008)与缅甸民主宪政前景》,《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8期。和“装饰性掩盖”(5)Susanne Prager Nyein, “Expanding Military, Shrinking Citizenry and the New Constitution in Bur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39, No.4, 2009,pp.638-648.所提供的法律保护(6)Stewart Manley, “Exploring the Paradox of Limitation Clauses: How Restrictions on Basic Freedoms in the 2008 Myanmar Constitution May Strengthe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16, No.1, 2010, pp.155-192.,以及民族国家构建设想(7)刘务:《缅甸2008年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兼论缅甸的边防军改编计划》,《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4期。等。二是将研究的重心从宪法文本转移到形成宪法的政治规则研究的宪法社会学范式(8)参见喻中:《宪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如英日殖民遗产对1947年宪法的影响(9)Maung Maung, Burma’s Constitution, Netherlands: Springer Netherlands, 1961.、1974年宪法与选举的准备过程(10)Albert D. Moscotti, Burma’s Constitution and Elections of 1974,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1977.、民族问题对1974年宪法的影响(11)Robert H. Taylor, “Burma’s National Unity Problem and the 1974 Constitu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 No.3, 1979,pp.232-248.、军人集团的专业化程度对权力分享的影响(12)Aurel Croissant and Jil Kamerling, “Why Do Military Regimes Institutionalize? Constitution-Making and Elections as Political Survival Strategy in Myanmar”,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2, 2013,pp.105-125.、缅甸制宪过程产生的“社会整合”效果(13)David C. Williams, “Constitutionalism Before Constitutions: Burma’s Struggle to Build a New Order”, Texas Law Review, Vol.87, 2009,pp.1957-1993.、2008年宪法制宪作为军政府建设“军国体制”的“先发制人的过程”(14)Melissa Crouch, The Constitution of Myanmar A Contextual Analysi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9; Melissa Crouch, “Pre-emptive Constitution-Making: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Military in Myanmar”, Law & Society Review, Vol.54, No.2, 2020,pp.487-515.等。
以上成果为理解缅甸宪法的内容及其背后的政治结构和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首先,两种范式都将宪法解读为制宪者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策略和手段,这种简单的工具性分析忽略了宪法背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观政治过程。其次,以上研究都专注于对某一特定宪法的文本或制宪过程进行分析,这样的截面研究无法窥见缅甸三部宪法变迁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最后,两种范式对文本和过程的选择性偏向,难以显现三部宪法的制宪过程、宪法文本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简而言之,现有研究成果未能剖析出三部宪法背后所蕴含的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过程与思想变迁。
宪法研究应该是对“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15)喻中:《宪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页。的研究,但仅仅指出什么是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还远远不够,这些真实规则是如何产生以及运作的,为此需要结合宪法解释学与宪法社会学的方法解读宪法产生的文化结构、情境与标记(earmarking)过程。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指出,宪法作为“法律之法”,不只是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更是社会团结的符号表征,这种文化结构体现在动机、社会关系和制度三个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递进式层面(16)Jeffrey C. Alexander, The Civil Sp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64, 56-57; Jeffrey C. Alexander,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1.。而为了对这套文化结构的作用进行细致的探讨,需要把互动的“情境作为出发点”,“个体是以往互动情境的积淀,又是每一新情境的组成成分”(17)〈美〉 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2-33页。。标记是本文对缅甸宪法进行分析的主要工具。择利泽(Viviana A. Zelizer)在其名著《金钱的社会意义》中创造了这一概念来解释人们通过对金钱赋予不同的意义和用途,创造出主观上不同价值的金钱并以此来定义社会关系和情境;标记的过程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赋予货币不同的意义,二是制定或分配货币的使用,三是创造或转换出崭新的货币(18)〈美〉维维安娜·择利泽著,姚泽林等译《金钱的社会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9-50页。。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在形塑货币,但当人们需要面对微妙或复杂的社会互动时,才会给其中的货币贴上不同的标记。而且,人们不仅标记金钱,对所有类型的事物都会进行标记,以此来定义社会关系。择利泽的标记概念属于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范畴,通过借鉴社会学的概念,有助于揭示宪法的社会意义及其映射的社会情景和社会关系:制宪者是如何赋予宪法意义,如何为宪法指定用途,如何创造出新的宪法的。
具体到缅甸宪法的案例,正如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规范或根本法”(19)〈德〉卡尔·施米特著,刘锋译《宪法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二战后脱离殖民统治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大多都将起草宪法与实施宪政视作建国的当务之急。无论制宪者信奉何种意识形态,属于哪个政治利益集团,当其开展制宪过程——即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制定一个总体框架时,就必须回应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各种挑战,无论这个回应是否只顾及到某个利益集团或者只是权宜之举。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可以将制宪过程理解为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缩影,制宪者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愿景则反映在成文宪法之中。因此,制宪过程以及成文宪法的内容对于研究宪法及民族国家建构都是不可或缺的。
缅甸三部宪法诞生的政治背景、政治目的、过程与面临的挑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试图对缅甸民族国家建构问题进行回应和解答。这些问题反映在动机、社会关系与制度层面,它们的长期存在和变迁以及政治行动者各自试图解决的努力,使得情境产生连续的变化,宪法的成文就是不同政治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对同样问题的不同标记。三部宪法的标记,在动机层面,试图确认民族国家建构最本质的政治追求目标;在社会关系层面,试图去回答各民族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与平等对待;在制度层面,试图为国家做出最正确的发展道路选择。
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路,本文将以宪法社会学与宪法解释学为视角,结合过程分析与文本解释路径,运用缅甸宪法文本、官方文献等材料,通过考察缅甸三部宪法诞生的“情境”变化下,制宪者们如何在动机、社会关系和制度三个层面进行政治“标记”,来理解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政治过程和思想变迁脉络,从而把握缅甸宪法隐含的缅甸政治的本质。
一 对动机的标记
(一)1947年宪法的“独立自由”标记
1885年,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缅甸民族主义者谋求民族独立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昂山(Aung San)领导的独立运动影响最大。二战时期,昂山先与日本人合作,暂时驱离了英国殖民者,后又与同盟国合作赶走日本。战后,昂山带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与英国进行了多次谈判,要求获得国家独立。
此时昂山需要回答的是独立后的缅甸将要建成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这个问题。昂山领导的同盟是当时缅甸力量最大的政治团体,但是同盟之外依然还有许多与其竞争的政治势力,如巴莫(Ba Maw)、吴素 (U Saw)领导的势力,缅共以及少数民族势力等。这些政治势力与同盟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争取缅甸独立。因此,昂山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实现“独立自由”为纽带团结所有政治势力。
1947年1月27日,昂山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签署了“昂山—艾德礼条约”,同意缅族将争取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建国,并承诺尽快举行建国议会选举,制定宪法(20)【缅】觉年、丹伦、丁温:《1945—1948 缅甸政治》,缅甸文化部历史研究司,2013年,第277页。本文使用的缅文资料,均为笔者自译。。但是,昂山的这个成果不仅受到政敌吴素等人的质疑,也受到缅甸民众和各政治势力的质疑。为此,昂山回到缅甸后,于1947年2月4日通过广播向民众承诺:“有人说我们未能获得一年内独立的承诺。一年内能否获得独立是我们自己的事……只要我们能在5月或6月举行建国议会。我们越快做好决定,我们就能越快获得独立。”(21)【缅】昂山:《昂山将军的讲话》,文学库出版社,2017年,第127-129页。这个“一年内获得独立”的目标催促着昂山和同盟尽快与少数民族领袖达成协议,举行建国议会选举,并出台宪法。
为此,昂山于1947年2月12日与掸族、克钦族和钦族领袖签署了《彬龙协议》,获得了少数民族与缅族共同争取独立的条件。4月9日,建国议会选举举行,同盟赢得了90%以上的席位,成为主导建国议会的第一大政治组织。7月19日,在建国议会召开期间,昂山被暗杀身亡,但在建国议会召开之前,他已主导制定了14项宪法起草原则,完成了宪法草案。9月24日,建国议会完成使命,出台了1947年宪法,吴努(U Nu)被选为临时总理,并赴英国与艾德礼签署了“努—艾德礼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缅甸于1948年1月4日正式独立。
然而,1947年宪法反映的对“独立自由”价值的保障,在实践中反而不仅对同盟内部的团结造成影响,也导致了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撕裂。同盟内部团结破裂的极端表现就是昂山被刺杀。在这之前,缅甸共产党已经脱离同盟。建国后,同盟内部的各个政治组织继续发生分裂,导致军方于1958年发动不流血政变,接管了权力。国防总司令奈温(Ne Win)上将组建的看守政府一直执政到1960年,才将权力移交给大选中获胜的吴努。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撕裂也在建国之初就已发生,为了获得自治与自主权(民族邦地位),克伦族、克伦尼族、孟族、若开族等都在建国后不久与以缅族为主的中央政府发生冲突。1962年,体制内的掸族政治势力也提出“联邦诉求”,军方以国家面临颠覆危险为由,于3月2日发动政变,推翻同盟政府,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政府。缅甸政治行动者们在追求政治独立和自由时的政治内耗与民族对立,引发了政治危机,为军人政权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缅甸独立以来的民族矛盾常常被简单地解释为英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结果,然而这样的论断忽略了1947年宪法下缅甸民族问题的动态发展。独立前,若开族与孟族原本就与缅族联手争取独立;掸族、钦族、克钦族等则是在“彬龙会议”后与缅族达成了统一建国的共识;仅有克伦族对加入缅甸有所抵触,但也未与缅族发生直接的冲突。而缅共虽然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依然是合法政党。缅甸以1947年宪法建国后,缅共和克伦族才与中央政府发生武装冲突,原本已与缅族达成共识的孟族、若开族、克钦族与掸族等也都与中央政府发生了武装斗争。可见,英殖民时期遗留的“结构性因素”并不会自动产生民族冲突的结果,两者之间还需要一个“文化过程”,即1947年宪法的标记过程。当然,为了更深入地解释缅甸民族冲突的问题,除了宪法在动机层面的标记外,还要关注社会关系与制度层面的标记,这是本文后续章节将要继续讨论的话题。
(二)1974年宪法的“社会主义”标记
1962年奈温第二次发动政变后向全国发布公告,表示“为控制已经陷入极其危险境地的缅甸联邦,缅甸国防军接管了政权并进行保护。”(23)【缅】缅甸历史真相写作组:《缅甸政治转型期(1962—1974)》,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奈温所说的“危险境地”,一方面是指同盟及后来的联邦党政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以及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对缅甸民族国家建构造成的重大威胁。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团结且强大的政治组织,以社会主义来统一各民族。但他认为军人干政并非良好的政治现象,“革命委员会不该一直只由军人来参与工作。军人也不能一辈子都统治国家。”(24)【缅】缅甸历史真相写作组:《缅甸政治转型期(1962—1974)》,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62页。他希望成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指南的政党,出台社会主义宪法,实施一党专政。
随后,在奈温的指示下,革命委员会起草了日后成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以下简称“纲领党”)意识形态基础的《缅甸特色社会主义》。该文表示,缅甸发动独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然而无论是同盟还是缅甸共产党都未能有效地实践这一制度,提议缅甸应该实施符合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5)【缅】缅甸历史真相写作组:《缅甸政治转型期(1962—1974)》,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这篇文章最后以《革命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宣言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之名于1962年4月30日向全国进行广播。随后,奈温根据这份纲领于7月4日成立了纲领党。
纲领党成立之初人数非常有限,是由13名军方高层组成的“干部党”和“核心党”,而到了1972年时已发展到73,369名党员,其中军人党员有42,359名(26)【缅】吴哥哥勒:《缅甸军治与进退维谷的政治》,丁萨北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随着纲领党完成初步的党建后,将军人统治制度化为纲领党统治的时机也来临了。1971年6月28日,纲领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奈温在开幕演讲中宣布纲领党今后的三大任务:(1)建立严密巩固的党;(2)实现各民族团结;(3)制定宪法(27)【缅】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组织部:《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政治转型期历史性演讲3》,印刷与出版公司,1975年,第153页。。关于制定宪法,奈温表示:“我们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已经从核心党发展为人民党。因此,起草宪法也应该由党来主导。”(28)【缅】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组织部:《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政治转型期历史性演讲3》,印刷与出版公司,1975年,第169-170页。1971年9月25日,纲领党开始了制宪工作, 1974年1月3日颁布了新的宪法。
1974年宪法明确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基于吴努政府未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对此宪法前言特别强调:由于“独立后的旧宪法的缺陷以及资本家议会制的弊端,封建主、地主、资本家等的影响日益扩大,导致社会主义几近消失。为从该局势下获得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因应历史责任而诞生,并制定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1974年宪法前言部分还批评独立后上台的吴努政府和执政党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他们的统治下缅甸不断偏离社会主义目标。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践行者纲领党才“因应历史责任而诞生”,全体人民要“忠诚地接受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领导”。而在制宪期间,奈温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已经提前卸下军职,并在后来根据宪法举行的1974年选举中当选为纲领党政府的总统。在奈温亲身经历了同盟政府的不断分裂以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力后指示起草的1974年宪法,不再将政治行动者的动机标记为“独立自由”,而是标记为“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目标只能由纲领党来实现。
(三)2008年宪法的“国家利益”标记
然而,纲领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未获得成功,由于多次失败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不断下滑,民怨累积,最后于1988年8月8日爆发了全国性抗议运动(又称“8888运动”),纲领党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在奈温的指示下,9月18日国防总司令苏貌(Saw Maung)上将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成立国家恢复秩序委员会,并承诺将在社会稳定后再次举行大选,还政于民。于是,自“8888运动”中兴起的民主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与其政治伙伴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党。而纲领党也经过重组,改名为“民族团结党”。军方的本意是希望在大选后以民族团结党的名义继续执政。然而在1990年5月12日举行的全国多党制大选中,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取得了绝对性胜利,在485个席位中赢得了396席。计划失败的军方拒绝将权力移交给获胜的民盟,改口要求胜选“代表”在军政府的领导下召开制宪大会,起草新宪法,国家恢复秩序委员会(后改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只会将权力移交给根据新宪法成立的政府(29)【缅】蒙育瓦昂欣:《全国民主联盟记录(1988—2010)》,五边形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1992年,军方在国民制宪大会协调会上定下基调,要求“在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要以国家利益为主”(30)【缅】蒙育瓦昂欣:《全国民主联盟记录(1988—2010)》,五边形出版社,2016年,第81页。。这种对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分成为此后指导军人参政的思想基础。国民制宪大会发布了六大目标:(1)维护联邦团结;(2)维护民族团结;(3)巩固主权;(4)促进真实的多党民主制度;(5)推动公正、自由与公平等三个社会真理;(6)实现军队在未来缅甸国家政治中的领导(31)【缅】蒙育瓦昂欣:《全国民主联盟记录(1988—2010)》,五边形出版社,2016年,第86页。。这六大目标即缅甸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军人领导被联系起来。由于民盟的抵制,国民制宪大会被迫中断。随后,军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上,将国家利益进一步具体化为“我们的三大责任”:“保护联邦不被分裂;保护民族团结不受破坏;保护主权巩固”(32)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军方要求所有的报纸、杂志、期刊、电视台、影视作品等媒体刊登和播放这个内容,直到2010大选结束后才停止。,成为日后再次启动制宪工作时的意识形态基础。
2003年5月30日,昂山素季的车队在德拜因市遭到大规模暴力袭击,造成多人死伤,甚至一度危及昂山素季本人的生命安全。德拜因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美国为此出台了第一部专门制裁缅甸的独立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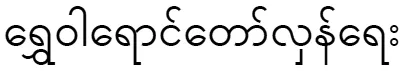
由于此前同盟政府的“无能”导致民族团结崩溃,而军人退出政治后国家再次面临严重动荡,改名后的民族团结党又在大选中失利,再加上20年来与民盟的艰难互动及制宪过程的周折,军人认为国家建构工作不能完全寄托于政党,且“党争”是动荡之源。因此,有必要强化超越党派利益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并由军人来保护“国家利益”。在这个思路下,2008年宪法为政治行动者标记了新的动机,宪法的第一章“国家的基本原则”第六条规定的国家六项原则,就是国民制宪大会提出的六大目标的再现。
在2008年宪法中,政治行动者经历了从“独立自由”到“社会主义”再到“国家利益”的动机转变。将“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区分是丹瑞(Than Shwe)新军人政府对民族国家建构工作的一个核心标记,通过赋予军队参与和领导“国家政治”(即面向全国福祉的政治)的权力,使其政治行动有别于“政党政治”的党派斗争,不仅赋予军队参政合法性,更给予了军队在缅甸政治中超然的地位。
二 对社会关系的标记
(一)1947年宪法的“自由抉择”标记
1885年,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殖民者对缅甸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将缅族聚居的内陆平原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区分开来。而且,即便在山区中,也对钦族、克钦族、掸族、克伦尼族、克伦族等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殖民政策导致缅族与山区少数民族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产生了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缅甸民族主义者战后寻求国家独立时充分暴露出来,并深刻影响着此后缅甸国内的和平稳定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当1947年宪法标记了实现“独立自由”的动机后,就需要将这个标记扩展到民族关系之上,即要让各民族拥有“自由抉择”的权利。
二战结束后,英国希望保留山区的殖民统治,仅让缅族地区独立;缅族希望缅族地区与山区获得一体的独立;而少数民族则意见不一,与缅族同是平原民族的孟族和若开族等基本同意与缅族共同建国,但山区民族却相对犹豫。这是因为,一方面,历史上缅族政权就未曾对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过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的殖民政策使得山区少数民族和缅族关系更为疏远,山区少数民族担心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只是换来缅族的“殖民”统治。为了打消各民族的顾虑,使他们愿意与缅族共同建立一个统一自主的国家,昂山需要保证各民族关系是平等和自由的。为此,昂山在与掸族、克钦族与钦族等三族土司与山官谈判时表示:“缅族不是英国之奴,山区人民也不是英国之奴,另外山区人民也不是缅族之奴。”(35)【缅】昂山:《昂山将军的讲话》,文学库出版社,2017年,第136-137页。最终各方达成了同意共同建国的《彬龙协议》,保证少数民族代表拥有参政权。而且,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会议上,为了获得少数民族领袖的信任,昂山还承诺,将会把少数民族要求可自决去留的问题提交到建国议会上讨论(36)【缅】色莱连穆:《彬龙承诺》,缅甸民族与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第ix页。。
但是,刚在英国殖民和封建制度遗产下独立建设民族国家的缅甸,其民族身份及领土问题尚未定型,这尤其体现在1947年宪法对国家领土与行政划分的模糊不清的表述上。克伦尼地区在殖民时期被定性为一个单独国家,因此1947年宪法第二条在描述国家领土时特地强调缅甸领土包括:“(1)此前不列颠国王通过缅甸总督进行统治的所有领土及(2)包括克伦尼领地在内的缅甸全国组成的缅甸联邦”(37)在1961年第一修宪法案中,关于缅甸领土的表述增加了两点内容:1960年10月1日签署的《缅中两国边境划定条约》中包含的土地;未来若获得新土地,也须涵盖在内。,并在第五、六、七条中对掸邦领地、克钦邦领地及克伦尼领地进行了界定。但是,在第九章第三节“克伦邦”第180条关于克伦邦的内容中,宪法又规定克伦尼邦、萨尔温区及总统特别工作组所确认的周边地区,如当地居民及全国克伦人愿意,则可合并成立克伦邦。第181条规定,在克伦邦确定之前,该地区暂定为郭都嘞特区。掸邦的勐别地区,经过当地人民同意,也可并入克伦尼邦。第196条则将钦族山区和若开山区定为“钦特区”(38)在缅语里,该“特区”与之后强调特殊的政治形态的各种“特区”不同,是强调具有“民族特征”的区。在缅甸当代法律史上,仅对钦使用过这个名称。(不是钦邦)。
这种充满了交叉和不确定性的自由抉择条款,不仅造成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领土矛盾,也造成少数民族对缅族的不信任与不满。虽然1947年宪法为克伦族设立邦提供了可能性,但在独立前后,克伦族提出为克伦族设立邦的领地要求,中央政府又未给予回应。同时,孟族与若开族的设邦诉求,也未获得政府的回应。随着缅族和克伦族之间的矛盾激化,缅甸独立后第二年即1949年就发生了克伦族的武装叛乱,克伦族甚至一度攻至当时的首都仰光市郊。随后,克伦尼族、若开族、孟族等地区也都发生了武装反叛。吴努政府这才通过1951年的修宪法案第四条设立了未包括克伦尼邦地区的克伦邦,第八条则将克伦尼邦改名为克耶邦。但是否将掸邦的勐别地并入克耶邦,则又悬而未决。孟族和若开族要求成立邦的诉求依然未被采纳。少数民族之所以希望获得民族邦的地位,是因为根据“彬龙精神”,民族邦将获得自治和自主的权力。根据1947年宪法,缅甸立法机构分为人民院与民族院(39)1947年宪法中的民族院与2008年宪法中的民族院的缅语原词并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多民族”之意,后者强调的是国家层面的“国族”之意。,拥有邦地位的民族会在民族院获得相应的席位数量。
此外,1947年宪法第201、202条根据“彬龙精神”给予了民族邦在10年后可决定脱离联邦的权力,这使得缅甸联邦在独立10年后可能面临被“解体”的风险。标记为“独立自由”动机的1947年宪法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表现出极大的自由。根据“彬龙精神”,1947年宪法对被认定为民族邦的少数民族给予特殊的政治待遇和特权。但是,当缅族掌握政权之后,以缅族为主体的联邦政府并不乐见国内有“太多”民族邦出现,除了根据彬龙会议对克钦与掸成立民族邦做出承诺外,对其他少数民族成立民族邦的诉求都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同时,由于处于自殖民时代转入建立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对少数民族的身份、地位与领地的认定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为了回应日益严重的民族团结问题,缅甸中央政府在1961年的第三修宪法案中,将缅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试图以宗教途径实现民族团结,但此举反而加深了信仰基督教的克钦、克伦和克耶族与缅族的隔阂和猜疑,民族关系进一步撕裂。
(二)1974年宪法的“淡化民族”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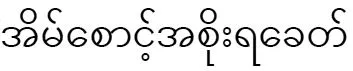
吴努于1960年再次上台后,基于竞选诺言进行修宪。其间,掸族提出为了实现真实的联邦制度,要求将缅族地区也划为缅邦,与克钦、克伦尼、克伦、钦、孟、若开、掸等七大民族组成八个平等的邦,这一诉求得到了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程度的响应(41)【缅】色莱连穆:《彬龙承诺》,缅甸民族与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第87页。。吴努政府对各民族提出的“联邦诉求”持开放态度,召开人民议会、国民制宪大会商讨“联邦诉求”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联邦诉求”的声音,并有“掸族谋求独立”“联邦即将崩溃”等谣言出现。1960年3月2日凌晨,军方以防止联邦分裂为由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是国家建构的两面,要实现这两点,关键在于公民与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联系(42)(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奈温认为各民族过于强调民族间的差异,是导致缅甸民族国家建构困难的根源(43)【缅】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组织部:《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政治转型期历史性演讲3》,印刷与出版公司,1975年,第107页。,因此需要将社会主义的标记扩大到社会关系层面上,以此来淡化民族之间的差异。
奈温主导制定的1974年宪法在国名上虽然保留了“联邦”一词,但却不愿强调民族联邦的概念,在回应各民族的建邦诉求的同时,也建立了民族平衡的格局。1974年宪法新设立了克伦邦、钦邦、孟邦和若开邦,保留既有的克钦邦、掸邦和克耶邦,形成了七个民族邦。至于少数民族提出的将缅族聚居的内陆地区也划分为缅邦的意见,缅甸中央政府通过将缅族地区划分为七个省来回应,这样既满足了少数民族建邦的要求,又以同数量的七个省来平衡民族邦的地位。为了防止任何单一民族对领土划分等问题提出诉求,宪法第39条规定必须由相关的省邦各方的人民来共同决定,以此杜绝了1947年时少数民族可各自决定其领土划分的问题,创造了缅族与所有少数民族在领土划分上的平衡对等,淡化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政治特权。
此外,1974年宪法在赋予权力方面也刻意淡化民族概念。如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由“以农民、工人为基础,包含各族人民的公民所掌握”。在立法方面,仅设立一个人民议会,不再设人民院与民族院。关于议员的首要条件,宪法第173条a款规定为“真实代表劳动人民的人民代表”,也不再以民族身份来设立议员。而候选人是在纲领党及其领导的各阶层组织和人民协商后,由纲领党提出。各阶层组织是指纲领党领导的农民、工人、作家、音乐家、戏曲家、电影工作者、画家与雕塑家等行业和职业组织和团体,没有任何民族团体和机构。
可见1974年宪法试图通过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以此来解决1947年以来的民族分化问题,其强调的是农民与工人的阶层身份以及公民的政治身份,而不再是民族身份。1947年宪法中允许少数民族在缅甸独立10年后脱离联邦的权利也被取消。所以,虽然缅甸国名上依然保留“联邦”之名,但比1947年宪法,具有更加明显的“单一制”(unitary)特征,虽然设立了七个民族邦,但民族身份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则被淡化了。
(三)2008年宪法的“央地分层”标记
1974年宪法下的缅甸民族问题,依然未获得解决。1988年,新军人政府上台后,也将解决民族问题作为主要工作之一。1989年,从缅共分离出来的佤邦联合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果敢)和民族民主同盟军—掸东军(勐拉)与军方签署了和平协议。1994年,克钦独立军与军方签署停火协议。签署了和平停火协议的民地武获得了特区身份,实施自治,缅甸民族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多数时间处于和平停火的状态。在这一时期,民地武不再谋求“反攻”或扩大领土,而是满足于在各自地区的“自治”。但是,由停火割据团体、武装对峙团体与新兴团体等形成的势力格局使得缅甸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更加复杂化。
因此,2008年宪法在民族权力划分和行政区域划分问题上又进行了更复杂的标记。基于在政治动机上区分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的标记思路,在社会关系上进行了“央地分层”的标记,在扩大民族地方权力的同时,也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制衡,并保证中央对民族地方的绝对领导。
2008年宪法第九条a款规定,在保持既有的七个民族邦不变的情况下,将七个“省”(District)改名为“大省”(Region)(44)虽然2008年宪法在英、缅两种语言版本上都做了这样的改动,但在中文语境中一般依然沿用原来的译称“省”。。宪法第56条规定,在实皆省内设立那加族自治区,掸邦内设立德怒族自治区、勃欧族自治区、崩龙族自治区、果敢族自治区与佤族自治省。自治省和自治区以领土面积而定,自治省大于自治区,但在实际的自治和自主权上并无区别。而与果敢和佤一样由缅甸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勐拉由于不具有特定的民族身份,未被给予自治身份。
不同于1974年宪法虽然对各民族邦的领区进行划分,但没有给予实际的自治和自主权,2008年宪法给予了民族邦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2008年宪法中,议会被区分为联邦议会与省邦议会两级,联邦议会由人民院和民族院组成,省邦议会则只有单一议会。人民院议席由军方代表(25%)以及以城市为单位的代表组成,民族院则由军人代表(25%)和每个省邦各12席组成,其中,省邦内的自治地方均各占一席。这一点与1947年宪法中基于人口对不同民族邦设定席位数量不同,也和1947年宪法中仅由少数民族代表组成民族院不同,而是对14个省邦都一视同仁,为每个省邦划定了相同的席位。民族院议席的设定,看似提高了七个民族邦的自主权,但实际上用同样数目的七个缅族省的议席来制衡和抵消了民族邦的自主权。此外,缅甸总统的产生办法是,由民族院、人民院选举产生的议员及两院的军人议员,三方各提名一名副总统候选人,再通过联邦议会全体表决,从中选出总统及两名副总统。由于民族院的议席中,七个民族邦与七个缅族省数量相同,而以城市为单位产生的人民院议席中,除掸邦由于领区广大席位最多外,其他六个民族邦的席位都远远低于七个缅族省。因此,在这样的设计下,即便七个民族邦的少数民族政党赢取了各自邦的所有席位并形成同盟,也无法获得独立组阁的权力。省邦议会则以军人代表(25%)以及省邦内每个城市两个议席和少数民族议席组成。省邦议会中的少数民族议席是指,在任何一个省邦中,为非该省邦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未拥有自治地方,且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0.1%的民族所设定的席位,该少数民族议席同时也是该省邦的相关民族事务部长。不过,所有省邦的首席部长都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而非省邦议会任命。
1988年新军人政府上台后,继承了吴努政府以佛教民族主义进行社会整合的路径。但基于1960年将佛教定为国教引发少数民族反弹的经验,2008年宪法第361条将佛教标记为“具有全国国民信仰人数最多的崇高特征的宗教”,以相对委婉的方式行佛教作为“国教”之实。
2008年宪法对民族关系的标记,与前两部宪法相比,显得更加细化和严密。它对民族权力进行了精细的划分,除了1974年设立的七个传统民族邦外,另外设立了自治地方,设立自治地方时也并不仅仅考虑民族武装的实际控制,也考虑该民族武装的民族身份特征。当其民族身份不突出时,即便在实际上实施自治,也不给予民族自治身份。在给予了七个民族邦同等的代表权时,也给予了七个省同样的代表权,使得少数民族的代表权扩大的同时,缅族的代表权也扩大了,最终使少数民族的代表权被“稀释”。而且,省邦两级立法机构都无权自行选出各自的省邦首长。这种标记的背后,反映出2008年宪法在认同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依然保留着缅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力。
三 对制度的标记
(一)1947年宪法的“单一制”标记
昂山曾在建国议会前召开的先行筹备大会上表示,缅甸必须采取“联邦制”(45)【缅】昂山:《昂山将军的讲话》,文学库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昂山的判断来自当时缅甸各民族实力强大且尚未信任缅族的现实格局。虽然建国议会依据昂山的指导原则起草了宪法,但缅族主义者并不完全赞同昂山的“联邦制构想”,因此,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完成宪法起草后表示:“虽然我们都坚信单一制政府的好处,但现实是我们要实行联邦制”;而且,由于缅族地区在“人口、领土、财政能力、政治觉醒度”等方面都高于边境地区,因此“不将缅族地区设为邦,而是与中央联邦政府结合为一体”,并希望未来能从联邦制改变为单一制(46)【缅】缅甸历史真相写作组:《缅甸政治(1958—1962)》,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基于这样的构想,1947年宪法虽然以联邦的形式联合了各民族地区,但在许多细节上存在明显的单一制标记。
根据1947年宪法,国会由总统、人民院与民族院组成。人民院议席基于人口比例与选区选举产生,且议席必须高于民族院议员人数的两倍。民族院代表的则是少数民族的权力,由掸邦25席、克钦邦12席、钦特区8席、克伦尼邦3席、克伦族24席、其他地区53席组成,共125席。因此,不同民族邦在民族院中的权力地位并不相等。总统是国家的象征,由人民院与民族院联合召开的议会选举产生,但是作为联邦政府首长的总理一职则由人民院单独提名,民族院无权参与,政府也向人民院负责。
在立法权上,民族院的地位也低于人民院。1947年宪法规定,无论人民院还是民族院通过的法案,都必须获得对方的同意才能正式通过。当两院在有关法案上产生分歧时,由总统召开两院联合议会进行商讨和表决。由于人民院议席数量多于民族院,因此当两院为分歧进行表决时,人民院占有数量优势。在立法范围上,涉及财务的法案也只能由人民院提出,民族院只能提交建议,而不是修改和否决,且人民院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民族院的建议。当民族院质疑人民院提交的法案不属于涉及财务的法案时,则由总统来裁决。
民族院的权力更多地体现在民族邦的立法权上。根据宪法规定,由民族院的相关民族邦议席组成各邦的理事会(47)即邦议会。,实行邦内的立法。邦理事会通过一部邦级法律草案,必须由总统签署后才能正式出台。而在邦政府的任命上,由总理与邦理事会商议后,从邦理事会成员中任命一人为邦政府主席,该职务同时也是联邦政府的相关邦事务部长。虽然邦政府主席从邦理事会中产生,但任命权在总理而不在邦议会手上。此外,总统可不通过与邦政府或邦理事会商议,宣布该邦进入紧急状态。在财政税收上,邦内的部分税金属于联邦政府所有,但邦政府无权分享联邦政府的税金。
总体而言,1947年宪法披着联邦的外衣,但核心依然是单一制特征:有少数民族邦,却没有缅族邦,缅族政治地位等同于中央;人民院与民族院两级议会权力不平等;各民族邦在民族院中的议席数量不相等;民族邦的自治权极为有限;联邦财政分配不公正等。正因为如此,1962年掸族政治集团要求实现“真正的联邦制”,其中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将缅族地区设立为与其他少数民族邦地位相等的缅族邦。然而,这个要求触碰了大缅族主义者中的最强硬派国防军的敏感神经,从而促使其发动政变,并建立了更加单一制的体制。
(二)1974年宪法的“一党制”标记
1974年宪法在国家制度上实际上是将1947年宪法未能完全实现的“单一制”推进为“一党制”。1974年宪法第一章“国家”第一条说明:“缅甸国是劳动人民的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名称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章“原则”第五、六、七条将国家的目标、经济制度与组成原则明确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组成”。可以说,1974年宪法处处都强调其社会主义立场和特征。由于不满1947年宪法多党制的“弊端”,1974年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采用一党制。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是国家唯一的政党,并领导国家。”
197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依据社会主义实行一党专制。因此,与1947年宪法和2008年宪法不同,其政治结构较为简单。在进行政治权力分配时,其指导原则是“中央领导下的地方自治制”。1974年宪法只设置了一个人民议会,并将其定性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而国家委员会负责根据人民议会所颁布的法律、法律细则与决定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指导、监督与协调。国家委员会及中央权力部门向人民议会负责。国家委员会由人民议会代表推选而来,并在其中产生国家委员会主席(总统)、副主席(副总统)及秘书长。中央政府由部长团队、人民法官团队、人民检察官团队和人民工作纠察团队组成,均由国家委员会自人民议会代表中选出。国家委员会之下,设有省邦、市、区、村等各级人民委员会。人民议会代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其候选人均由纲领党提名。
由于强调纲领党对政治的领导,因此1974年宪法在权力分配上是以“党领导一切”进行的。虽然在权力结构的设立上,立法(人民议会)、行政(国家委员会、部长团队、人民工作纠察团队、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法官团队、人民检察官)各自独立,但除了各级人民委员会之外,所有行政和司法人员同时也必须是人民议会的代表,而人民议会代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成员也皆由纲领党提名,因此表现出立法、行政、司法不分家的“一体化”特征。
(三)2008年宪法的“混合制”标记
1947年宪法的单一制通过1974年宪法的一党制得到强化,但依然在民族国家建构上表现不佳,军政府在2008宪法中将国家制度标记为“混合制”,采取了相对温和、中庸,既照顾到少数民族和民主派的政治诉求,又保证军人领导的路线,将联邦、民主和纪律三者混合,形成缅甸特色的“纪律严明的民主联邦制”。2008年宪法在政治结构的设计上更为复杂和完善,特别体现在政府、议会、民族、政党及军队之间的结构设定上,并且为了确保军人对国家政治的领导,军人参与了到政治结构的每个领域。
如上文所述,2008年宪法规定无论是联邦议会的人民院、民族院还是省邦议会,都设定了无需选举、由国防总司令直接任命25%的军人代表席位,保证了军人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立法工作的参与。军人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还体现在总统的推选程序上,总统是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政府领导人,总统自联邦议会中产生。具体而言,由人民院中选举产生的议员、民族院选举产生的议员及军人议员各推选一名副总统候选人,并由联邦议会对三名副总统候选人投票,根据得票高低分别产生总统、第一副总统及第二副总统,这保证了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军方参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法途径。
而对于总统的一个特殊规定是,当选为总统及副总统之人,自当选之日起不得从事政党工作。这个规定切断了总统与自身政党之间的联系,防止任何政党代表在获取国家最高权力地位后“权力膨胀”至“无法控制”的局面。同时,内阁中属于武装暴力机构的国防部、内政部及边境事务部也由国防总司令提名,使得国家暴力机构依然全权掌握在军队手中。这就使得军方即便没有掌握最高行政权力,依然可维持自己对国家政治的领导地位。
2008年宪法第一章“国家基本原则”对军队的地位、组成、权力与责任进行了清晰且丰富的规定。如军方事务军方自主,国防总司令是所有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而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并且明确了军方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守护宪法。此外,还设定了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两名副总统、人民院议长、民族院议长、国防总司令、国防副总司令、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与边境事务部部长组成。由于军方代表占六席,因此国家最高的国防与安全机构也是由军方掌握话语权,这使得在民主联邦制下,军队依然拥有极高的自主权。
与前两部宪法相比,2008年宪法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对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及军方在紧急状态下接管政权的行为进行了制度化。宪法第10章“紧急状态相关规定”写明:总统在与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商议后可对全国或任何一个省、邦、联邦直辖区、自治地方等宣布紧急状态,并将行政、立法、司法权移交国防总司令。紧急状态为期一年,但国防总司令可依据情况申请延期两次,每次6个月。紧急状态结束后,权力应交还总统并在六个月内举行大选。而在紧急状态下,行使权力的机构及个人的所有行为,均免于日后追责。军人在1958年、1962年及1988年的政变都因为缺乏合法性而饱受诟病,2008年宪法则通过“紧急状态”的规定,为军人提供了合法“政变”的途径。
关于宪法修改的条件,2008年宪法也制定了详尽且严格的条件。在第12章“修改宪法”中规定,首先,修宪法案必须获得联邦议会20%议员的同意,方能提交至联邦议会进行讨论。对于宪法中的重要条款,必须获得联邦议会超过75%的议员同意,并在全民公投上获得一半以上选民的同意方能进行修改。而对于次要条款,则在获得联邦议会超过75%的议员同意后就能修改。这种设计使得任何违反军人利益的修宪行为在没有军人的同意下都不会得到通过。
2008年宪法抛弃了1947年宪法和1974年宪法相对简单的设计,做了极为复杂的标记。通过设定多党制大选,部分回应了民主派的诉求;通过设定省邦议会和由人民院、民族院组成的联邦议会,部分回应了少数民族的联邦诉求;而军队的自主权、各级议会中的军人议席、军人对行政权力的参与等则又保证了军人领导国家政治的诉求。这种混合制体现了对1947年宪法的单一制和1974年宪法的一党制纠偏的努力。
结 论
通过对缅甸三部宪法产生的政治背景、制宪过程、内容、影响及相互之间联系的研究,可发现缅甸宪法虽然充满了权力、利益的分配,但同时也是关键政治行动者或集团在不同阶段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的回应。1947年宪法反映的是缅甸在谋求独立建国之时,面对复杂的党派政治、民族关系和社会思潮的竞争,试图争取最大的社会团结的努力。1974年宪法见证了1947年宪法带来的社会分裂,是试图以一体化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巩固社会团结的尝试。2008年宪法则是总结了前两部宪法的不足后,面对更为复杂的民族、民主政治格局,以更加精细的方式在民族、政党和军人之间寻找权力平衡与制衡,从而维系社会团结的实验。
三部宪法内含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体现在对动机、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标记上,而一套成熟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应在这三个层面体现出一以贯之的递进关系。1947年宪法的“独立自由”动机,体现到社会关系中就是“自由抉择”,然而拓展到制度层面时却出现了外“联邦制”而内“单一制”的冲突,可见当时缅甸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尚未定型。1974年宪法的“社会主义”动机和制度层面的“一党制”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但在社会关系层面淡化民族标记的做法,未体现社会主义对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而是大缅族主义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2008年宪法是缅甸迄今最为完善的一套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基于“国家利益”的动机发展出央地分层的平衡关系并扩大建立纪律、民主和联邦的“混合制”。
三部宪法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也存在内在的传承和纠偏的逻辑关系,后者通过审视前者的经验、去芜存菁、革故鼎新来完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如在动机层面,1947年宪法以“独立自由”的动机标记来争取各民族的团结,却迎来了独立后的内战和政治混乱,因此1974年宪法改以“社会主义”为动机标记,但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缅甸对社会主义也失去了信念,最终2008宪法将动机从主义之争中抽离,修改为更具操作性的“国家利益”,试图在民族国家利益的号召下实现不同主义、不同势力的团结。在社会关系层面,1947年宪法强调各民族自由抉择的权利,导致民族矛盾在独立后不久即激化,因此1974年宪法试图通过淡化民族的标记来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但也没有成功,最终2008宪法以央地分层的方式使各少数民族势力和主体民族缅族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而在制度层面,1947年宪法是在联邦制的外衣下实行的单一制,这种内外不一的制度失败后,1974年宪法制定了内外一致的、强化版单一制——一党制,而后来一党制也失败后,2008宪法选择了更具包容性的“混合制”。
缅甸三部宪法的诞生是缅甸政治行动者建构民族国家的三次努力。这些努力既吸取了前人的经验,也受限于政治行动者自己对民族国家建构和当时政治格局的理解。1947年宪法和1974年宪法都未能通过历史的考验而维护缅甸社会的团结,2008年宪法在实施了10多年后,2021年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2008年宪法是否能够继续维持缅甸社会的团结,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何时才能找到适合的方案,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