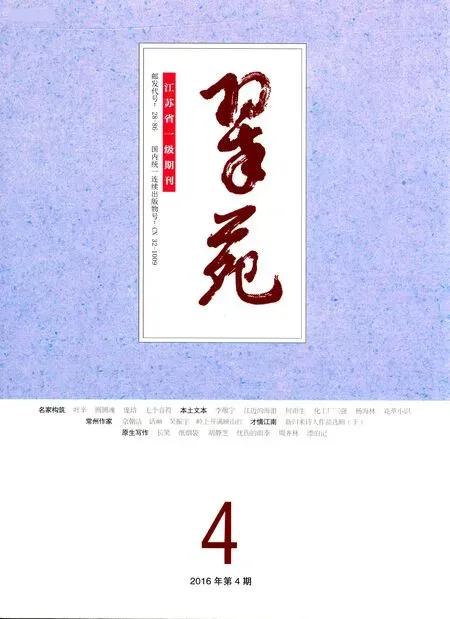“救亡未压倒启蒙”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再解读
○ 张 蕾
贞贞是丁玲诸多小说中个性鲜明的一位女性,尽管她的身份曾在某个时期备受争议,但无论是作为作者的丁玲,还是叙述者“我”,对贞贞都是饱含同情和佩服的。据丁玲描述,贞贞的故事来自前方同志的述说,她听后深受触动,尤为遭遇悲惨境遇的那位女性难过。“于是,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从丁玲的写作动机可以看出,可能有出于对那位女性过去和现在经历的怜惜,遭受磨难为革命工作牺牲自我的折服,更有对这位女性不公待遇的维护。小说自发表以来,冯雪峰对贞贞是赞赏的,其文也成为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经典评论,1954年后伴随着对丁玲的批判和双百方针的结束,丁玲连同她的作品遭到了严厉批判,贞贞被认为是丧失了节操的“寡廉鲜耻”的女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女性主义、革命主题是三种主要解读方式。小说表面书写失贞女性牺牲自我服务革命的故事,实则暗含着启蒙与革命的主题。如丁玲所言“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丁玲:《谈自己的创作》)。显然,丁玲不只在写女性,更有时代的、社会的问题容纳在小说中。女性、革命、启蒙的主题在小说中各有突显,但三种主题并非独立成章,呈现出交互、层层深入的关系,并非“未完成的启蒙”“救亡压倒启蒙”“忠贞观的变奏”,或某两种关系“女性与革命”“启蒙与革命”的不完整阐释。短篇小说的篇幅,蕴含的话题和可供讨论的空间却是深厚无限的,需要结合女性、革命、启蒙三种方式来回应丁玲对时代的思考。
叙述贞贞故事的新旧两类人
小说中贞贞的出场用了较大篇幅的铺垫,贞贞无疑是小说的主人公,她的经历和遭遇牵动着我的神经。原本我是去霞村休养身体的,离政治部只有三十里路的霞村,乘车不过18分钟就能到达的安静之地,但在霞村的两个星期中,我体会到了寂静—热闹—冷清—嘈杂—死寂—热闹—寂静的环境变化,我的休养计划一再被扰乱。每一次的动静起伏都与贞贞有关。初到达霞村前往刘二妈家,妇女们聚在一起热心的谈话,同行女伴阿桂的变化,黑夜中院子里嘈杂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此时的我刚到霞村只是觉得奇怪,还无心理会其中详略,直到霞村负责人马同志的到来,我随便询问得到答案的惊讶,马同志的一句“明天他一定叫贞贞来找我”,打破了我与贞贞的外围关系。我的休养计划被重新规划,贞贞的故事呈现出他人言说与自我讲述两条线上。
贞贞的故事是什么?为何有如此多的他人言说?他人与自我在言说方式上有何不同?我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述说?我、贞贞、他人的叙述共同构成了贞贞故事的完整性。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回顾性叙述我在霞村的经历,其中有两种视角在交替作用,分别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被追忆的“我”正在体验事件的眼光。通过“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可以更自然更直接接触贞贞的内心,读者往往容易随体验事件的“我”一同感受观察和感受,较大程度受“我”的眼光的影响。那么,我如何观察、如何看待贞贞是关键所在。最初我听到的贞贞的故事来自他人的言说,有村人的窃窃私语、神秘交谈,马同志佩服的描述,阿桂无言的叹气,杂货铺老板的讥讽责难,妇人间的嘲笑议论,后两种声音我是在散步时听到的,也是极不愉快的,所以匆匆回到了家。杂货铺老板和妇人的言语如利剑般上升为伦理道德审判,和马同志提起贞贞的“了不起”截然不同,可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在失贞与革命的角度上显示出对贞贞态度的差异。失贞、革命只是贞贞故事的一部分,贞贞为何会失贞,失贞后如何走向革命之路?刘二妈的述说解答了贞贞失贞的原因,因逃婚去教堂做姑姑,被日本兵侵犯,不仅失贞还患病。作为贞贞的亲人刘二妈虽然解释了贞贞失贞的因由,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贞贞失贞感到惋惜与担忧。刘二妈对贞贞的言说没有杂货老板、妇人的言语刻薄讽刺,却也和他们一样始终关心着贞贞失贞的问题。
贞贞故事中贞贞如何走向革命这一部分,由贞贞自我言说,如她自己所言,她对那边熟悉,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被派去继续待在那里。关于这些,贞贞述说时非常平静,没有丝毫抬高自己为革命工作所做的牺牲。作为亲历者在谈及自己的悲惨遭遇时,却是如此的冷静,仍然保有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对革命的坚定信心。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有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丁玲:《延安作品集 我在霞村的时候》)。我对贞贞是欣赏和佩服的。贞贞的故事被不同的人述说着,形成了故事的完整性。在这些叙述者中,小说中的我把他们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杂货店老板那一类人,“总是铁青着脸孔,冷冷地望着我们”;一类是村里的年轻人,那些活动分子。他们之所以对待贞贞有不同的方式,源自关注角度的不同,第一类人以封建伦理道德的贞洁观看待贞贞,第二类人从革命信仰来看贞贞的付出与牺牲。从我对贞贞故事的叙述观念、情感态度上看,我对第一类人持批判厌恶之情,对第二类人饱含同志之情。贞贞故事的背后,展现的是霞村新旧两类人的思想状态。
最难的工作为“文化娱乐”
失贞问题是旧中国封建思想下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约,霞村杂货铺老板、贞贞的父母、妇人们无疑都是旧思想的捍卫者,无情地对贞贞施加枷锁。这个离政治部不到20分钟车乘的村子,一年半前也遭受过鬼子的扫荡,村里因此成立农救会和自卫队,革命本应有的如火如荼在霞村却格外清静,只有谈论到贞贞时村人看热闹般地聚在一起显示出嘈杂的场景。丁玲对霞村环境动静气氛的描写,暗含了霞村人革命意识并不强烈,封建旧思想大于对革命的认知。杂货铺老板一类的旧人用旧思想对贞贞在日本人那儿做慰安妇进行严格的伦理道德审判,用冷漠、异样的眼神、难堪的言语继续中伤贞贞,完全抹杀贞贞的个人痛苦,以及为革命作出的牺牲,使贞贞遭受的精神创伤远远大于身体上的伤害。丁玲对杂货铺老板一类的旧人持批判的态度,听到他们的谈话每感不愉快,“就独自坐在窑里读一本小册子”,书籍成为我排解烦闷情绪的方式。读书的细节描写不仅表现出我的知识分子身份,还象征书籍的启蒙作用。我在读书学习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摆脱现实的孤寂和不快,读书于我而言是重要的,我关心着村里的读书学习情况。
与负责人马同志谈及村里学习情形时,他坚定邀请我“做一个报告;群众的也好,训练班的也好,总之,您一定得帮助我们,我们这里最难的工作便是‘文化娱乐’。”(丁玲:《延安作品集 我在霞村的时候》)马同志是村里的负责人,也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对村里的精神文化生活表示担忧,恳切希望我能帮助群众。可以看出霞村的文化启蒙显得尤为迫切,是无法深入展开其他工作的症结,对于工作人员来说颇有些无能为力的困境。马同志介绍贞贞于我,并提醒我“贞贞”那里有很多材料可写,而我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即政治部来的休养干部,有文化有知识,应现实的需要和自身对思想文化的认识,充当着文化启蒙的导师角色。
我的文化启蒙作用在与贞贞见面后的交谈显得更为突出。我与贞贞初次见面,因顾及不碰着她的伤口,不知如何开始谈话,贞贞率先开了口。贞贞向往像我一样的南方女人能读书,渴望向我学习,说明霞村及北方农村女人教育普及率低。随后谈到在日本兵那看到日本女人写的信,对日本女人读了很多书表示羡慕。贞贞没有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而是以坚韧的毅力面对生活,对自己走上革命之路拥有精神寄托表现出坚定。如果说革命让贞贞重获新生,找到了自我生命的新方向,那么革命带给贞贞最大的改变是对学习、对新事物的兴趣愈加强烈。她拒绝夏大宝的求婚和家人的挽留,决定前往延安学习,在她看来“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还可以重新做一个人……”(丁玲:《延安作品集 我在霞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她的话的确值得我们研究,我当时只能说出我赞成她的打算的话”(丁玲:《延安作品集 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去延安展开新的生活,我的内心是佩服和开心的。在霞村短短两周的生活,我与贞贞是朋友,也是同志,对我来说同贞贞的每次聊天于我的学习和工作都是有极大益处的。我满足贞贞对霞村之外的新事物及革命的好奇,贞贞的自我成长与蜕变,也使我收获了启蒙的成果。因此,我的惊诧不仅仅是为贞贞开启新生活的打算,也包含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革命实践。贞贞的经历虽然悲苦,但她代表着农村女性的觉醒,对霞村乃至整个中国农村女性都是一种鼓舞。遭遇如此坎坷的女性都能自觉加入革命,有浓厚的学习意识期望改变落后守旧的现状,最难的文化娱乐工作对革命者来说是有希望的。在这个时代,“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丁玲:《延安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
革命救亡未压倒思想启蒙
霞村新旧两类人的革命、学习态度相差甚远,根源在于村民旧思想的根深蒂固,最难的工作是文化娱乐,意味着思想启蒙任务的艰巨性。丁玲拿起笔来正视并揭露这些现实,她坚信暴露这些社会问题才是消灭其弊病的唯一有效方式,“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应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懦”(贺桂梅:《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丁玲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追求个性解放,“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我、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贺桂梅:《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婚恋自由是五四以来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贞贞的故事源于逃婚终于逃婚,因为不自由的婚恋引发的悲剧,以及霞村村民看客般对封建家庭制度的维护、对贞贞的残酷审判,这些是丁玲和五四知识分子要着力剔除的。
五四的第一代先生们将妇女解放视为社会斗争的任务,青年一代则更关注个人,转而到了自己解放自己,俞平伯等发表文章论及“自我解放”的重要性,这些是五四青年论著的重要特征。丁玲个人的经历就是一部自我解放、自我放逐的个性人生,小说在揭露、批判霞村看客的麻木、冷漠、愚昧的同时,借助贞贞顽强反抗困境,从革命中获取学习的动力,重获新生,塑造出青年觉醒解放案例。这是丁玲也是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对启蒙认识的深入,是更为中国本土化的启蒙现代性实践。对自我的不断追求,导致被解读为“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丁玲“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贺桂梅:《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
丁玲对杂货铺老板一类旧人的封建落后的婚恋观念持批判立场,映射出霞村文化启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任务仍然在路上。霞村只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对贞贞好,这些年轻人包括贞贞代表了活力、新生,向往学习和革命,他们都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人与旧人、恋爱加革命的叙事模式是常见的革命叙事方式,新思想与旧思想、婚恋与革命以政治隐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年轻人的思想启蒙与革命事业是相伴相生的。实际上“知识分子与革命有共生的关系,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如果把知识分子与革命视为两个彼此分离的事物,那就失去了进入复杂纠缠的历史深处的契机,实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金蝉脱壳之术”(贺桂梅:《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民族救亡之际,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延安,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即使有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革命之路如何展开的思考从未减退。丁玲更是从文小姐变成了武将军,晚年的丁玲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贺桂梅:《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这些不仅需要革命实践,还要在革命之路中不断学习和内化,与旧的思想、旧的自我斗争,以新的尊重个性和人性发展的精神面貌改造自我、改造社会。
李泽厚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认为五四后因为民族危亡局势,打破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衡关系,即“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李泽厚是落脚于“新时期”张扬文化启蒙的必要性,而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中践行的是“普遍的启蒙”,即针对“五四启蒙运动(甚至西欧市民阶级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特殊的、局部的、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进入毛泽东延安《讲话》的政治逻辑,推行全民启蒙、全民教育的可能”(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鲁迅曾在1927年黄埔军校演讲中谈到,“没有革命人,就没有革命文学;旧世界不被推翻,不但新人描绘和讴歌新世界的文学无从谈起,即便旧世界的挽歌文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还没有灭亡”。丁玲作为知识分子与革命者,非写贞贞不可的动机与此一致,可谓是经过思虑的超越苦难的自我认知与革命信念,是属于丁玲的“革命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