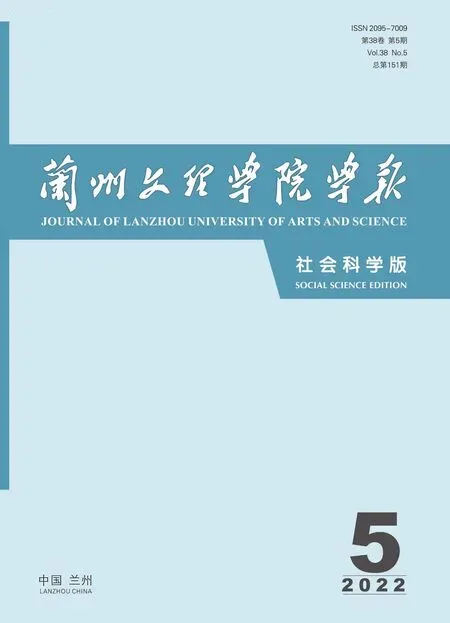从“力效平衡”到“力效思维”
——敦煌舞教学体系的审美构建刍议
夏 莹 莹
(兰州文理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引言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讲到:“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1]。敦煌艺术作为各类多元文明长期交融的智慧结晶,是敦煌舞蹈艺术发展的重要前提。
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的诞生标志着敦煌舞教学体系的创建,迄今已有四十余年。在这期间,由高金荣先生创建的敦煌舞教学体系,一步步从敦煌壁画乐舞走向系统教学,为敦煌舞蹈表演人才的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继高金荣之后,敦煌舞教材方面作出相应贡献的学者、前辈们还有贺燕云的《敦煌舞蹈训练与表演教程》(2009年)、史敏的《敦煌舞蹈教程——伎乐天舞蹈形象呈现》(2012年)以及孙汉民的《敦煌舞男班教程》(2014年)等。2007年,贺燕云通过教材的实践与研究,将敦煌舞首次引进北京舞蹈学院[2]。同年,西北民族大学将敦煌舞正式纳入本科高校专业课程,并于2019年成立敦煌舞研究中心。2021年,兰州文理学院将敦煌舞纳入舞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成立敦煌舞表演专业方向,开设敦煌舞基本训练、敦煌舞剧目、敦煌舞教学法、敦煌舞编导等课程,进一步推进敦煌舞在高校的全面发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秉承着和平合作、开发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融、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3]。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策略的大力推动下,关于敦煌题材的舞蹈作品层出不穷,如星海音乐学院《伎乐天》(赵文婷/2014)、香港舞蹈团的《缘起敦煌》(陈磊/2015)、郑州歌舞剧院的《乐天舞》(佟睿睿/2015)、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度》(耿子博/2017)、“一带一路”文艺晚会的《千年之约》(陈维亚/2017)、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敦煌》(费波/2017)、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团《敦煌飞天》(张浩/2018)以及东方歌舞团的《心应胡旋》(刘翠、刘迪/2020)等,不同舞蹈家们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敦煌艺术语汇进行多层级的“解”与“读”。敦煌壁画乐舞似乎已不再局限于某种特定类型,而是作为丝绸之路文化符号,被当代艺术创作者不断提炼、选择、融合与创新,对敦煌舞蹈文化发展而言,无疑是探索性的成功尝试。
伴随敦煌舞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敦煌舞蹈创作与发展呈日新月异之势,并与不同艺术形式融汇与借鉴。本文基于敦煌舞当代的发展现状,以身体元素为构成基础,讨论敦煌舞如何规训外部形态发展,表达内部动态韵律与舞蹈风格,并以此来界定自身的“保护元素”①,即“自律性”与“排他性”。在时代创新性的挑战中,如何在壁画舞姿之“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中,进行“思”而有“觉”的理性表达。本文拟结合自身舞蹈教学与实践经验,借鉴舞蹈“力效”理论,试从“力效平衡”“力效思维”“力效和谐”三个方面来探讨敦煌舞“力”与“美”的艺术化表达,旨在对敦煌舞形态性、风格性、文化性、审美性进行再次确认。
一、从“力效平衡”看“S”形曲线的逻辑起点
敦煌石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至十四世纪已形成包含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在内的庞大石窟群,在壁画、彩塑、绢画上均有琳琅满目的舞姿造型,在这些壁画舞姿、彩塑、雕像和绢画中,舞姿造型依稀可见西域乐舞文化影响的印记,即“三道弯”或“多道弯”的审美形态。这种“S”形的体态特征,最早可追溯于印度古代早期的石雕当中。现存桑奇大塔东门的砂石圆雕托架像《桑奇药叉女》(Sanchi Yakshi),约作于公元前1世纪末叶或公元1世纪初,这尊雕像动态灵活,头部向右倾侧,胸部向左扭转,臀部向右耸出,全身构成富有律动感的“S”形曲线(见图1)。

图1 桑奇药叉女 公元前1世纪末叶桑奇大塔东门托架像[4]
这种身体弯曲成“S”形的姿势被称作“三屈式”或“三折姿”(tribhanga),自《桑奇药叉女》雕像初创这一程式以来,逐渐发展成塑造印度标准女性人体美的艺术规范[4]。受到印度塑像的影响,敦煌壁画舞姿以此形成了既定的审美范式,并在舞蹈动态发展中进行实践性转化,继而构成敦煌文化语境中的“动作思维”,即一种“对称力学”的身体结构关系。
敦煌舞蹈身体语言以敦煌石窟壁画舞姿为主要依据,是一种“非言语”性的动作样态,无论壁画、彩塑、绢画均具有动作信息的本质内涵,即发送、接受与交流的过程。敦煌石窟壁画舞姿作为动作语言最直接的信息符号,是透过身体动作表达其特有的文化意涵,“三屈式”或“三折姿”(tribhanga)就是敦煌舞蹈语言形成的基本起点。敦煌早期壁画舞姿受到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从北凉天宫伎乐到唐代经变伎乐,身体曲线的动力特征就以“Z”逐步向“S”转变,从而形成身体躯干上、中、下,同时向对侧或相反方向(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或上或下)的移动、推动,形成敦煌舞身体符号的“力效思维”,在敦煌石窟壁画舞姿静止与平衡的空间秩序中,进而外化出肢体语言的动态张力。
在敦煌舞的训练中,若要形成特定的曲线造型,训练者需要从头、肋、胯、膝、脚不同运动轨迹中,学习如何借助身体“反作用力”,掌握身体关节对向的发力方式,以此突出身体曲线的线性美感,以及掌握舞姿重心的基本稳定。格赛尔动力学系统规律对动作发展动态性的三大原则理论认为:“影响动作发展过程的相同和相反的力量总是交织在一起,经过再组织后才能得到平衡”[5],敦煌舞身体曲线的元素对称就是这样一种“再组织后的平衡”。
莫高窟初唐第331窟北壁的东方药师经变中,有一幅立于圆毯上起舞的舞伎造型,高金荣先生在《敦煌舞训练教程》中将其命名为“大曲线”舞姿。以该舞姿为例,若左腿为主力腿,右腿向上勾脚抵“大靠腿”的位置,胯部向左侧推出,身体侧肋向右平移,头转向左侧微低,双手成“侧托按掌”,眼睛保持与左手高度一致,身体重心最大限度下沉,形成头在两条手臂中间,单腿立于地面的舞姿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造型中,头的位置向左,肋的移动向右,推胯方向朝左,右腿的膝盖向外打开,身体重心的“力”由上至下来看,是在人体额状轴(左右关系)中形成左(头)、右(肋)、左(胯)、右(膝)的“力效平衡”(见图2)。
此外,从人体垂直轴(上下关系)来看,该舞姿身体重心整体向下,右手侧托,左手下按,低头、抬右膝,形成上(右手)、下(低头)、上(右膝)、下(屈膝)的“力效平衡”(见图3)。再看莫高窟最具代表性中唐第11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反弹琵琶”舞姿,该舞姿左腿直立于地面,双胯向后推,身体前倾,双手手臂于头后侧做反弹式,头探于手臂前端,眼神落于斜下方,右腿勾脚屈膝向上,大腿前侧贴合腹部,从人体失状轴(前后关系)上来看,形成后(手)、前(身)、后(胯)、前(腿)的“力效平衡”(见图4)。
由此可见,通过人体运动三种不同维度与空间轴来看,敦煌舞身体“力效”遵循着人体在物理空间的运动法则与运动规律,从前后、左右、上下不同维度中发展出对称和谐的运动轨迹,其中包含着“力”的对抗、“力”的和谐、“力”的关联以及“力”的相互制约,并以此彰显出敦煌身体语言的质地与美感。

图2 左右关系

图3 上下关系
敦煌舞身体曲线的和谐建构是“力效”规律的重复组织与再现,也是身体感知觉在文化语境中重要的审美体验。通过对身体内部动力的不断训练,从而达成身体“动力定型”的整体记忆。从审美角度来看,身体“力”的规训与呈现,也来自于不同“创造者”的“同一”结果。在敦煌舞教学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历程中,舞蹈表演是受训者与舞蹈编导内心情感与自身艺术体验之间相互融合的外在显化,这种显化的背后主要包含着四个部分。第一,壁画本体的物质材料(由画匠所创造的壁画舞姿);第二,编导家们对壁画舞姿所进行的重新构建(舞蹈的具体表演形式);第三,表演者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度创作(表演的重新再造);第四,审美主体(即观众)对审美结果所进行自我的情感追随。因此,敦煌舞身体“力效平衡”是这几个部分共同参与、感知与创造的,在不同审美主体下,敦煌舞身体语言的重复组织是在统一文化背景与审美经验中的再现,是敦煌舞形成“力效思维”的审美归属。
二、从“力效思维”看呼吸动律的情感表达
呼吸是表达生命节奏的重要手段,呼吸的外化是理解舞蹈本体的起点与开端。呼吸动律主要是指身体动作与舞蹈情感、舞蹈态度之间的相互对应。敦煌石窟壁画舞姿是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养礼佛均是舞蹈情思的直接表达。呼吸的长短、快慢、轻重、急缓,是动作表现的内在推动力,在敦煌舞蹈表演中是一种关于“心力”的外化训练。在著名舞蹈理论家鲁道夫·拉班③看来:“力效是动作起始的内在脉冲,并坚持力发于心而形于外,内外一致,是身心合一的动作统一论”[7]。
敦煌舞蹈的风格成因是以呼吸为基础构建的独特动态,将佛国仙乐的端庄、肃穆,融于身体内在的起落之间,形成“顿挫中又有连贯”(高金荣语)的软舞风貌。笔者将其归纳整理为“吸、提、吐、沉”四种可视、可感、可知的呼吸动态。呼吸节奏是时间的映照,它的节奏发生于动作之中,并持续在动作的留白之外。刘青弋老师认为,呼吸“是动作发生过程的秩序和持续时值,它使动作获得节奏质感方面的基础”[8]。根据拉班所提出“力效”的四种基本元素所构成的八种不同力效方式(轻与重、快与慢、延伸与直接、流畅与阻碍)为理论基点,将“吸、提、吐、沉”这四种不同呼吸节奏对敦煌舞风格内在质地进行提炼,便会对舞蹈的精神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即“吸气”为轻与快,形成顿悟的警觉,“提气”为重与慢,意味思考的延展,“吐气”为直接与阻碍,则为内观的平静,“沉气”为延伸与流畅,形成从容的沉寂,通过“力效”不同的时间因素、空间因素、重力因素由此构成敦煌舞佛教色彩的生命意涵与审美质感。
呼吸是人体生发的自然节奏,是身、心和谐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舞身体力效的基本成因,是内在力效与外在力效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身体的“力”与呼吸的“力”相互推动而构成。呼吸的训练作用于身体,身体的表达让心与灵相互浸染,呈现出“反者道之动”[10],即在反向的迂回中得到“力”的传递与呼应。在敦煌舞肢体语言的互动中,使得内在精神与外在表达彼此消融与整合,以此形成“以佛传舞”“佛在舞中”的艺术情思。
三、从“力效和谐”看审美心理的净化与提纯
敦煌舞力效意识的建立对敦煌舞表演、敦煌舞传播以及敦煌舞普及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力效平衡与力效思维的理论分析对敦煌舞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动作和谐、心理和谐,更主要的还意味着关于“美的和谐”(毕达哥拉斯语)。拉班认为:“‘力效’代表着某种心理的能量,它与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情绪、审美等心理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10]。敦煌舞蹈的发展,是透过肢体语言去触碰神性的内在情感,用呼吸去连接“心”与“灵”的真实,通过体认舞蹈的表演,去追溯历史,回望民族文化交流,感知丝路文明的灿烂交汇,从而对艺术的全部含义进行深刻的感悟与觉察。
敦煌舞审美的客观基础来自于“实在”与“美感”之间的关系,它的物质实体是敦煌石窟壁画舞姿,艺术创造则是不同艺术家对美感经验的具体表达,它是华夏民族广采博取、兼收并蓄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圆融精神的智慧结晶。通过壁画舞姿与灿烂历史文明的对话,在不同维度的历史空间中感受到舞姿定格背后那“一瞬间”的时间质地,在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身体动律的“力”向中,破碎掉传统的运动轨迹与肢体记忆,从而重新建立新的身体思维方式,理解身体运动与空间、时间、力量内在的逻辑关系,“通过有目的的身体全面训练,获得力效经验,获得生命的纪律性和表现性,以崇高、完善的人格显现出和谐的生命状态”[7],通过身体“力”的表达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曲则全”[8]186的大“和”精神。
敦煌舞蹈的力效思维与力效意识是对敦煌舞姿当代建构的重新理解与认知,是身体语言对自然规律审美表达的渗透与传递,是人体力效与审美意象的全面整合与统一,以体现敦煌舞身体语言中“力”与“美”的和谐共生。
四、结语
在敦煌舞不断深入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力效平衡”是帮助舞蹈者重新认识敦煌舞“S”形曲线重要的逻辑起点,是立足于敦煌舞文化语境中形成“动作思维”的基本立场,通过规律的重复组织与再现,达成身体“动力定型”的整体记忆,并在“力效思维”中,借由不同的时间因素、空间因素、重力因素,构成敦煌舞的生命意涵与审美质感,在“力效和谐”的审美心理中,继承丝路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里。
敦煌舞教学体系的发展对敦煌舞表演与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性作用。敦煌舞蹈的教育者、研究者、表演者以及创作者,在敦煌舞当代构建的发展历程中,需要在实践创作中基于敦煌石窟壁画舞姿中的造型,来试图还原敦煌舞蹈的“全貌”,即舞蹈创作的艺术性、舞蹈内涵的宗教性、舞蹈表演的文化性。在敦煌文化语境的中,以身体语言为基础,通过从实践到理论、理论作用于实践的有效路径,把握舞蹈内在的文化基因,在“力”与“美”的共生关系中,构建敦煌舞审美体系的哲学内涵。
【注释】
① “保护元素”是指建立自己的保护层,包括自己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并在体系中拒绝与体系特色相违的动作与动作韵律。参阅吕艺生.舞蹈美学[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240及72至73页。
② 图中标识由笔者添加。图2-3经变舞伎(线描图)莫高窟初唐第331窟北壁药师经变;图4反弹琵琶舞伎(线描图)莫高窟中唐第11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
③ 鲁道夫·冯·拉班(Laban,Rudolf von,1879~1958),捷克裔舞蹈理论家,是“拉班舞谱”提出者和创建者。该舞谱以数学、力学、人体解剖学为基础,运用各种形象的符号,精确地分析并记录舞蹈及各种人体动作的姿态、空间运行路线、动作节奏和所用力量,其中“力效”就是其中重要的理论内容之一,可分为有重力、时间、空间和流畅度四个基本要素,四要素又各分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