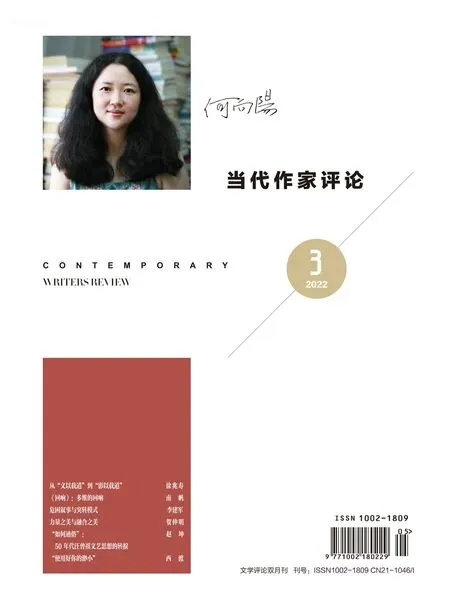以未来为经验:论王威廉的“纯文学科幻”写作
唐诗人
一
然而,理解和书写“现在的经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代作家该如何把握作为偶然、瞬间、短暂的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地记录现实、反映现实的复制和投影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作家从破碎中把握整体,在特殊中理解普遍,于现象中透视本质的创作技艺和思想能力问题。毫无逻辑的零散式拼贴往往只能承载最表象的日常事件,若想获得现代性的另一面——永恒之美,“现在”就必须进入作家关于这个时代的总体性判断。所谓总体性判断,是作家关于时代、关于真实等根本问题的精神认知和思想洞见,它们将当下意义上的瞬间性感受定格为能反映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真实的永恒性经验。
直面当代现实,书写当下经验,这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一直是悬在心头的文学使命,也是文学研究界习惯使用的批评话语。尤其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而言,文学叙事的个人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几乎每个作家都会强调自己的现实观和当代性,都相信自己的写作揭示了当代生活的某种本质、真相。这种现象于近10年的文学界更是如此,“现实”“现实感”“现实主义”等概念随处可见。强调呈现现实和书写当下,意味着当前中国的纯文学依然处于本雅明讨论的现代小说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代作家笔下的文学经验,要抵达的不只是作家反映了何种生活现实,更是这些当下的、日常的文学经验能蕴藏着怎样的永恒之美,即日常生活的本质性存在、当下经验的普遍性内涵。
二
以上是“80后”青年作家王威廉对于“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他把“现实”拆成两层:一层是现在、此刻的即时性;一层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规律。这与波德莱尔从瞬间性和永恒性两个维度来理解现代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与我们谈及的书写现在经验颇有难度也相似。王威廉也指出了“现实”并非不言自明的道理:写作要抵达真正的现实,作家必须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努力去把握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王威廉这一现实观值得重视,这不仅意味着王威廉的小说创作带有深度现实主义特征,更可能是一个帮助我们深入阐释当代作家如何表现当代经验的重要入口。王威廉相信现实主义创作应该具备一种“现象学味道”,即如何通过书写此时此刻的世俗生活抵近现实世界的精神根源,从偶然现象的表达到必然规律的发现,以及从现时经验的呈现到永恒价值的确认,这是极具深度的写作哲学。
哲思性是王威廉小说最主要的美学特征,他的作品始终在探寻着人存在于世的本真性意义。在科幻性质明显的《野未来》系列小说出现之前,王威廉的小说主要呈现两种风格:一是写实性比较强的如《生活课》系列;另一类是如《倒立生活》等荒诞性比较突出的作品。对《生活课》这一类,是从拷问日常世俗生活一类琐碎的非本真存在来进入本真存在。夫妻到底谁该负责洗碗?这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借海德格尔存在论思维来分析,这洗碗问题就是一种不“上手”的工具,是一种“在手”状态的天天都需要为之操劳的实际事物。对于洗碗,如果其中一方很愿意、毫无怨言地把它完成,它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一旦它成为问题,它就是“在手”状态了。操劳于洗碗、操持于夫妻关系,这些事情占据了整个生活之后,个人也就必然会进入一种自我反思状态,难道这就是生活本身?开始了这种询问、质问,也就开始了对本真性存在的探寻。这种本真存在到底是什么,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因为有这个根本性问题悬在文本之上,整部小说所叙述的现实生活就变得不再真实,或者说,不再被认可是人之为人的本真性存在状态。所谓“生活课”,作家不是要教给我们什么具体的生活经验,而是让一系列非本真的现实生活以一种刺目的、极端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活不应该这样子,这不是人存在于世的根本价值。作者要我们相信,人的存在应该有一个超越维度,超越琐碎的、日常的、世俗的生存状态。
精神的超越性也体现在《倒立生活》《辞职》这类风格荒诞的小说中。《倒立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因流产而想摆脱重力的束缚。对重力的恐惧,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作家将这一不正常的心理状况放大,以极端的方式呈现这种非本真的生活。这种极致化的书写,写出了作为此在的个体去感受本真存在状态时的可能性境遇。这种可能性生活是荒诞的。透过这种荒诞,可以了解哲学上所谓的本真存在并不可靠。小说最后,男主人公梦见自己身上长满了可以产生分子力以抵抗重力、战胜重力的绒毛,也就是摆脱了“畏”,不再害怕大地的吞噬时,才感受到存在可以是一种幸福。但梦醒之后,这可能也就回归到不可能,存在依然被重力、被大地紧紧缠绕。
对非本真存在状态的超越性追求和对本真存在状态荒诞性的超越性质询,让王威廉的小说显得极富辩证性。这种超越性不是人物的超脱于世,而是让人物去体验多个层面的存在性超越。在感受了超越性意义上的存在感之后,人再次回到生活世界的非本真存在状态,即便继续操心,继续畏惧,也必然是摆脱了盲目,越过了重重迷障之后的操心和畏惧。这样一种回归于世,也表现了王威廉对现实、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度关怀。
三
《生活课》和《倒立生活》两大风格类型小说表现的当代现实,其深刻性极为难得。但这些深刻依然是通过哲学思考来揭示,我们的分析将借鉴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用存在主义、现象学哲学来理解王威廉小说中世俗生活的本真性,或许可以解释王威廉的深度现实主义写作观,也能够确认王威廉笔下那些“现在进行中的经验”所揭示的当代人的生存真相。但是,看到了生存真相之后呢?发现了生活真谛之后呢?作家能够通过个体性的文学表达,引导读者看到更广大的真实和更普遍的真相,这自然是一种可贵的叙事品质,意味着作家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可无论如何,这类哲思意味浓厚的小说,包括我们带有哲学性质的阐释,仍旧是围绕着现代性这个理论圆心展开的。小说叙事和文学阐释似乎也无法摆脱瞬间与永恒、偶然与普遍、现象与本质、在场与存在、幻象与本真等类似性质的二元性思维结构。这类二元性思维曾经是后现代理论着力批判和拆解的对象,然而对于现实主义风格主导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后现代性难有生长空间。即便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很多作家、批评家喜欢借用后现代理论话语张扬一种先锋风格,但也多流于表层的技巧实验,技术游戏过后基本上也返归传统的现代叙事。正如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视作现代性的一副面孔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特征,宽泛而言依然属于现代性范畴。
真正对现代性思维构成冲击的,并不是由现代性理论衍生的后现代理论,而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当下生活经验的变化。这里所谓的科技发展,与近代哥白尼日心说等一系列颠覆性的科学革命不同,后者推进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并与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力量一起促成了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生成。21世纪以来的科技发展,多数时候不是颠覆世界观,而是不断地重塑我们的日常经验,改变我们对生活本身的理解。近代的科学革命是世界观性质的,改变的是人心秩序,是一种宏大理念的变革。而当代的科技发展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更新的是人的生存环境,是一种微观感觉层面的持续性变化。比如网络赛博技术的更新换代,愈来愈灵敏的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对人类生老病死的重造,以及被无数大大小小的科技产品所填充的现代城市生活空间。如今的世界,技术力量已无处不在,微观层面的生活感觉变化有一种升级为宏大理念革新的趋势。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什么是情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自由等一系列支撑现代人生活信念的知识,都面临着新的历史性变革,现代性知识也不例外。
科技支配了当代人的生活,如今还能满足于在现代性范畴来思考我们的时代现实吗?现代性思维处理的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感问题,如今的现实却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可能性关联问题。“传统—现代”等对比性概念亟须转换为“现在—未来”。过去早已不能决定现在,未来才是支配当下的力量。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新变,不仅过去的、传统的经验贬值了,当下的、现在的经验也在加速贬值。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在当下已成了保守和逃避社会现实的代名词,唯有看到未来才意味着直面现实。如此,本雅明意义上的传递经验性质的“讲故事的人”,是不是可以调整为“讲未来的人”?怀旧的本雅明,对未来是拒斥的,他游荡于现代大都市,真正想看到的却是历史。那么今天呢?我们游荡于大都市,还要装模作样地去那些由新技术复原出来的旧街古巷中寻找历史感吗?这恐怕只是少数怀旧派的专利,不会是多数现代人的心理现实。当前的城市,最醒目的存在毫无疑问是科技化的物和事。注重表现现实、强调书写当下的当代文学,如何能对此类现实视而不见?
四
审美的、精神的光辉是当代中国小说具备超越性维度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但它们也是导致文学变得越来越“纯”的重要原因。多少年来,很多作家习惯性地以一种精致的审美追求作为拒绝介入现实的理由,把自己禁锢在一片唯作者能自足的精神世界里,这导致作品越来越“纯”。精致化、纯粹化的文学不等于“纯文学”,它只是脱离现实的“纯”,这类写作极大地限制了当代文学的社会接受度,导致很多有现实感的传统写作也难有出路。陷入狭义“纯文学”困局的当代文学该如何破局?对此,王威廉用《野未来》系列小说投石问路,寻找新的“纯文学”创作出路——科技现实主义,或曰“纯文学科幻”。
五
未来作为经验,针对今天的人类生活而言,具有人性价值和教诲意义,并不需要等到未来才生效。如此,作为经验的未来故事就是介入当下生活的一种精神力量。未来经验作为精神力量介入现实生活,这话看似简单,实则可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我们通过科幻作品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于是今天会做出更理性更理想的选择;二是科幻作品既然能讲述未来故事,也意味着我们还是相信人类是有未来的,且是比现在更发达更科技化的未来。这两重含义说明,王威廉的“纯文学科幻”既是反乌托邦文学,也是乌托邦文学。传统的反乌托邦文学,如《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等经典作品所呈现的未来,是绝对灰暗的、不值得期待的未来。而传统的乌托邦文学,如《乌托邦》《新大西岛》等,又对未来、对科学的发展前景过于乐观。如何在悲观中存有对未来的希望,在乐观中抱持对被科技异化的警惕,这是“纯文学科幻”写作最特别、最难得的价值所在。
《野未来》系列小说的叙事者,延续了王威廉小说人物的哲思气质,始终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和反思性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日益被技术统治的时代,但此系列小说与《生活课》《倒立生活》一类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在于作者在叙事中流露了相对清晰的对未来的希望。比如《野未来》中的赵栋,他最后消失在时空隧道,这诗意化的结局,也意味着作者让这个沉浸于科幻世界的青年真正去到了他理想的未来世界。《不见你目光》里被小樱的故事所震惊的摄影师,开始对自己镜头里的美产生感觉,陷入欲望与道德的困境,他镜头里的女孩子也开始害羞起来。这意味深长的结局,内含一种人性的觉醒。《退化日》的叙事者本身即是一个逃离技术、拒绝进化的人,他的存在即是对自由的希望和对梦想的肯定。
“纯文学科幻”的乌托邦性与反乌托邦性的并存,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是小说的诗性空间和思想张力所在。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肯定对未来有所期待,同时又充满犹豫。作为作用于当下的未来经验,“纯文学科幻”当然要回应我们今天的生存疑惑,我们将何去何从?对于理想的未来一面,我们可以满心期待,而对于那可怖的一面,我们当然要心存警惕、要小心规避,这即是以未来为经验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