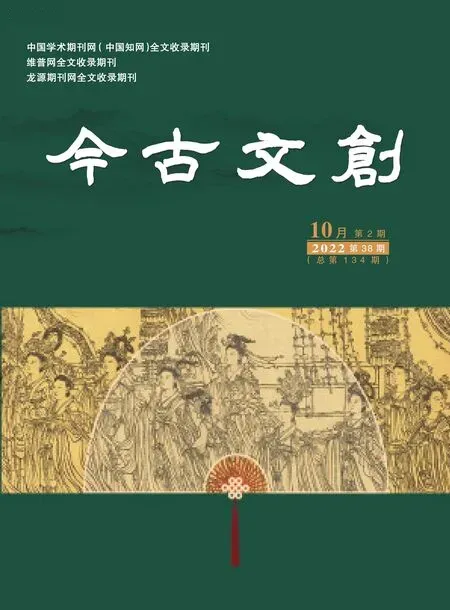浅析顾赛芬《论语》法译本中的文化翻译策略
◎朱 烨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论语》在法语世界的译介历史较为悠久,自16世纪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译本。其中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译本,语言晓畅,阐释丰富,是产生较大影响的译本之一。该译本作为其翻译《四书》的一部分,出版于1895年。顾赛芬神父是法国耶稣会士,1870年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北方居住。他在翻译中国典籍时采取的态度是较为客观的:“顾赛芬通常用双语对汉文译释:法语和拉丁语……没有做任何独出心裁的解释或个人评论的意图。”他的“译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世殊时异,19世纪时主要由西方的汉学家或传教士进行中国典籍翻译的潮流早已过去,当今由我国主导的典籍外译工作更多的是出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考量。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古代典籍是中国文化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外译问题,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站在文化翻译视角,考察顾赛芬神父的法语译本,对我国典籍翻译工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本文尝试就译本中一些涉及中国文化的翻译处理进行分析。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分析《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第二,分析《论语》中比喻修辞的翻译处理;第三,分析其针对文化信息的翻译补偿策略,旨在总结出有借鉴意义的文化翻译策略以及该译本给我国典籍外译工作带来的启示。
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翻译《论语》,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翻译,比如“君子”“仁”“孝”“义”“忠”“道”等。由于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在法语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这些概念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这为翻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总体上,译本并没有针对某个词语统一采取一种译法。下面仅以“君子”的翻译为例,分析顾译本针对文化负载词采取的翻译策略。
针对“君子”一词,顾赛芬采取的译法主要有以下两种:l'homme honorable和le prince。“君子”在《论语》中一般可以理解为“有德行的人”,对应l'homme honorable;而如《论语·泰伯》中“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一句中的“君子”,则应该理解为“统治阶层的人”,对应le prince。问题在于,“君子”的两方面含义是不是完全割裂的?法语中一词多义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是与此不同的是,“君子”的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的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顺承和发展的关系,最初的没有感情色彩的字面意思,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被附加上了道德含义。“君子”一词,最早指居于统治地位的人,随后其含义发生了转变,被附加了道德标准,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论语》中:“君子”作“居于统治地位的人”讲的章节只有九处。由于《论语》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君子”最初的意涵反而不为人所知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君子”一词的使用中,包含了“治理者同时应当是一个道德的典范”的儒家政治理想。“君子”作为这两方面含义的统一体,被分开来翻译成两个完全不同的词,不利于儒家思想内在逻辑性的传达。另外,除上述两种主要的译法外,有时译本又采用le sage等的译法,以“君子”内涵的某一方面作为翻译的出发点,也使得这些基本概念的翻译缺乏前后连贯性。
从译者角度来说,解决办法之一是对这些词全部使用一种译法,即更多地采取异化的翻译。对于“君子”这样的文化负载词,或许可以考虑采用音译的方法。如果说在顾赛芬的时代,汉字的发音拼写尚且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时至今日,汉语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拼音系统,使得采取统一的拉丁字母拼写方法音译这类文化负载词成为可能。音译法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观念的传播,也可以对西方语言中出现的纷繁不一的译法起到统一的作用。
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读者也不可置身事外。因为“翻译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包含了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当今世界,信息获取的便利程度前所未有,读者对待译作的态度或许也应该有所转变,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索。正如在谈及异化翻译的可达性时,孙艺风提出“欲使异化翻译发挥功能,首先要异化的是目标语读者,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他们。”异化目标语读者,应该落实在全方位的文化传播与输出上,仅靠译者的某种翻译策略难以完成。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才能使世界愿意来主动了解中国文化。
二、比喻修辞的翻译
比喻作为最常见的修辞手段,往往借助于人们熟知的事物,达到使语言生动形象的目的,因而往往承载着许多文化内涵。中国先秦诸子中,有很多都善于用譬喻的形式来阐发精妙的道理,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子与孟子。而《论语》中,孔子以譬喻的方式言理的篇目也有许多。将比喻视作文化信息的载体,讨论其翻译策略同样是不无意义的。东西方的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比喻时,或是涉及一些本文化中特有的事物,或是目标语读者不熟悉本体和喻体在源语社会背景下的联系,这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以下将分析顾赛芬译本的《论语》中针对比喻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以探讨文化典籍翻译中比喻手法翻译的可能性。
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差异往往较大,然而不同群体之间也经常存在相似的文化体验。例如《论语·雍也》中的第四章:“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本章中,孔子将自己的弟子仲弓比作一只红色毛皮、双角周正的小牛,认为他尽管出身不好(“犁牛之子”),但是品行出众,最终还是会受人赏识,不至于被埋没。在此顾赛芬采取直译法,并且没有对文化背景做其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西方神话中也有用挑选毛色美丽的牛犊向神明献祭的描述,在类似的文化背景下,法语读者可以很好地理解孔子这一比喻中包含对弟子仲弓的赞赏与激励。
译本针对上述章节的翻译处理方法是简单直接的,文化同质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更多时候,译者需要对两种文化的差异给出自己的翻译解决方案。例如《论语·八佾》中的著名段落:“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是“仪”这个城市的一名官吏拜会孔子后,对孔子做出的评价。他告诉孔子的弟子们不要因为老师失去官职、离开鲁国而担忧,孔子正像一只木铎(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上天要借他向世人宣扬委顿已久的“道”。木铎就其形状和材质而言,可以直译为clochette à battant de bois,即“木质铃舌的铃铛”。古时官吏需要手持木铎,到各处去,边摇铃,边宣布政令。而当时孔子周游列国宣讲儒学,因此仪城的官员用“木铎”这一暗含动态含义的意象来比喻孔子。译本没有采用clochette à battant de bois的译法,而是选择将其意译为héraut,即“传令官”或者“使者”之意,用词简明,同时也较好地传达了源文本所暗含的动态含义。这样的处理从易于理解层面来讲是比较成功的。
在《论语·雍也》第二十三章中,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一种有棱的盛酒礼器,因为春秋时期社会动荡,诸侯不重视礼乐制度,觚的形制渐渐发生了改变,作为最大特征的棱消失了。孔子借此感叹当时的“名不副实”的社会现象和对礼乐制度遭到毁坏的忧虑。在翻译时,译本运用了直译,将“觚”这种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的器物音译为kou,并在其后的括号中对这种器物的形状进行了说明。而对于本句的借喻,则采用加注释的方式进行了较为充分地阐释。直译、音译与加注释相结合的策略是比较成功的,较为原汁原味地传达了文化内涵。正如韦努狄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所主张的,文学翻译不应以消除异族特征为目标,而应在目标文本中设法把文化差异表现出来。可以认为译文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对暗喻、借代等比喻手法,译本尽量采取直译的策略。在直译不能很好地传达文本意图时,则采用改变喻体的策略,以求优先保证原文内涵的传达。或在原文中直接补充叙述,或在译文后加注释,保证了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其灵活的翻译处理手法,对人们翻译典籍中的修辞手法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三、文化翻译的补偿策略
只要两种文化存在差异,翻译时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等。如傅雷先生所言:“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面对文化信息的缺省,需要采取一定的补偿策略。顾译本的《论语》长于阐释,主要的补偿策略有以下几种。
(一)添加注释
在翻译过程中,对于难以翻译的文化负载词添加注释是常用的翻译策略。译本中的注释非常丰富密集,且非脚注也非尾注,而是紧接在译文后,这可称作是顾译本的一大特色。例如《论语·雍也》的第一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译者先将本章的内涵进行了翻译,并将“南面”的字面意思列在译文中。译者为此章添加了两条注释:第一条是对“雍”这一人名的注释,补充了“雍”和“仲弓”实为一人的信息;第二条对“南面”的字面意思进行了解释,讲明“南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掌管政务”的含义,以达到补偿目的。
(二)直译加补述
在直译的基础上,直接在译文中增加补语来完善异语文化的意象也是顾赛芬译本经常使用的手法之一。如《论语·学而》第十一章中,孔子讲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如果仅直译,译文读者不免产生“三年”之期从何而来的问题。译文将其巧妙地处理为les trois ans de deuil(服丧三年),向法语读者传递了“父母去世后应当守孝三年”的文化信息,消除了读者可能产生的疑惑。
(三)音译加阐释
音译后,加同位语以解释说明音译词的含义,也是译本经常使用的翻译补偿方法。与前文已经提到过“觚”字的翻译方法类似。类似的例子还有《论语·公冶长》的第十四章:“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这里涉及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谥号。即对某个去世的人,按其生平事迹给予或褒或贬评价,往往只有一个或两个字。源文本在表面句意之外,还暗含了“卫国大夫孔圉去世后得到了‘文’字作为谥号”这样的文化信息。译本首先补充了“死后得到名号”这样在原文中没有直接说明的文化信息;又将他得到的名号音译为Wenn,与前面翻译“孔文子”这个名字时一致;在后面紧接着对“文”做出解释,表明他得到的名号“文”意为le Cultivé(有学问的),清晰地表达了源文本句意的同时,也完整地传达了暗含的文化信息,能使法语读者在阅读中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综合前述,顾赛芬译本《论语》中采取了灵活的补偿方法,如注释、直译加补述、音译加阐释等,使得译语读者可以详细了解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19世纪时,中国典籍的大量外译,主要源于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强烈好奇心。这一时期诸多古代典籍的外语译本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因而受到空前的关注。顾译本选择不厌其烦地频繁注释甚至阐释,或许与此不无关联。
四、结语
顾赛芬译本的《论语》作为19世纪中国典籍外译热潮中的一部译作,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译介。站在文化翻译的角度,对于原作中的文化信息,译文在较大程度上做了介绍,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兼而有之,对中国文化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具体策略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翻译古代典籍时,采取的具体策略需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调整,以求尽量完整地传达文化信息,对于无法完整翻译的文化内涵,可以采取加注、直译加补述、音译加阐释等多种补偿方式。顾译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典籍翻译经验,值得译者体会与借鉴。
另外,对典籍翻译来讲,目标语读者群的中国文化素养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外国读者因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而进行积极主动地学习探索,这当然是最为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通过多种媒介,官方宣传与民众交流相结合,向世界展示优秀的中华文化,翻译事业可以为此提供沟通的渠道,也可以因此而得到发展与繁荣。
注释:
①②保罗·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中)》,《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3期,第135页,第135页。
③张细进:《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05-111页。
④刘云虹:《翻译批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⑤孙艺风:《文化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页。
⑦此译法引用顾赛芬在原译文中加入的注解。
⑧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44-245页。
⑨傅雷:《翻译似临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