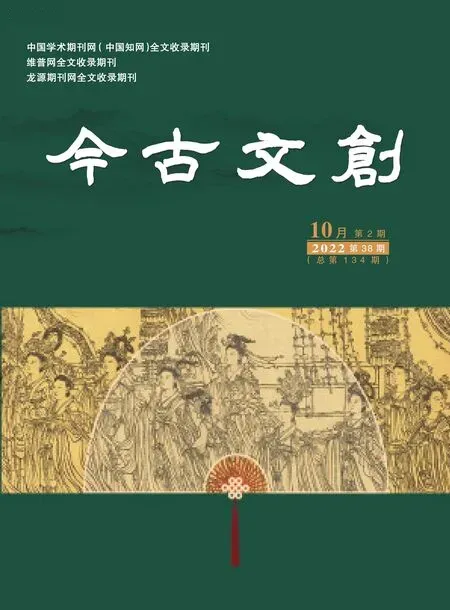伊丽莎白 · 毕肖普诗歌的生态意蕴
◎刘露溪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之一,曾获普利策等众多权威诗歌奖项,她的作品赢得希尼等诺奖诗人的高度赞誉。毕肖普的诗歌深刻影响了美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旅行,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也是其生命重要的存在状态之一。在毕肖普的一生中,她的旅行足迹遍布美国、欧洲和巴西,还在巴西旅居十多年。这些丰富的旅行经历书写了她非同一般的生活,也为其诗歌艺术创作提供了鲜活宝贵的资源。毕肖普的旅行人生印证了她对地理的热忱。她在旅行途中经历的形态各异的动植物群落及自然景观在其诗歌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毕肖普善于观察,其精准深邃的观察力和描写力在美国诗坛甚至世界诗坛都享有盛誉。毕肖普的诗歌密切关注自然世界,然而,诗人对自然的注视却摒弃了人以造物主自居、支配自然和控制生态世界的霸权思维。在毕肖普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细细感受到诗人以友好开放的姿态接近自然、认识自然、感受自然,因此在她的笔下,那些花草鸟鱼等自然景观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审视下单一、被动的客体。相反,这些自然景物形式多样、生命力旺盛并具有感受力。因此,在毕肖普的诗篇中,人类与动植物的关系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双向有所交流的主体—主体关系。维克多·哈里森(Victor Harrison)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亲密性诗学》(,)中以毕肖普的巴西诗歌为例阐述了毕氏诗歌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所以,在毕肖普的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受制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霸权机制,二者是相互平等、和谐共生的。可见,毕肖普的诗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及其运作,其诗歌艺术体现出生态进步性、生态整体性和多样统一的生态批评理论原则和美学意蕴,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一、《地图》:自然的权利
“从《北与南》《旅行的问题》到《地理学之三》,毕肖普的诗集大多具有鲜明的方位感与空间感,这也许照应了诗人蜿蜒曲折的旅行轨迹与漂泊不定的生命之路”。(刘露溪:2016,49)“她的三部诗集都拥有蕴含地理特征的名字——《北与南》《旅行的问题》和《地理学之三》——并且她感受到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冲动,这恰是因为她是一个客居者,而不是本地人”。(Vendler,1987:828)毕肖普五彩缤纷的旅行生活印证了其对地理持续一生的热忱,其诗歌创作也呼应了这份追求。
《地图》是毕肖普首部诗集《北与南》的第一首诗。通常,地图可以帮助人们制定旅行计划,因此是旅行者出门的必备工具之一。鉴于毕肖普不断在旅行人生的过程中探索和感悟人生的真谛,并在诗歌创作中将这种追寻和发现加以呈现,我们会感受到将《地图》安排为第一首诗意味深长,即毕肖普的一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地图》一诗则是其踏上行程的号角。面对一张地图,毕肖普出于本能似的仔细观察。地图,作为地形学对高原盆地、山脉海洋、湖泊冰川等地球表面各种重要实体进行观测之后绘制的图示,它的存在象征着科学理性与技术权威。然而,诗人对于地图上大海与陆地的边界交合关系提出质疑。
其实这是不同观察视角导致的结果,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却彰显一种洞见。通常,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注视体现出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一种把控。在人类看来,动物植物、自然山川都是静待观测的被动客体,人类通过知识技术的运用探测自然万物的实质与奥秘,进而把握和控制自然并为己所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主导与被主导、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因此,作为人类对于地理世界的观测与描绘结果,地图展现在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控制下的人类透过科学技术的客观、冷静视角打量自然、勾勒自然、确定万物关系、把握并驯服自然世界。对于地图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人类极少产生怀疑。但是,人类仰仗知识技术获得的自信甚至傲慢其实暗含了人类/自然、文化/自然、人类文明/自然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霸权机制,即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和疏离关系: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类掌握、占有自然,自然被动地服务于人类的利益。但毕肖普对海洋和陆地关系的质疑戳破了人类的自负,其相对主义视角令自然万物及其间关系得以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决定的固定位置关系中解脱出来,呈现多元、流动与差异。诗人观察自然的多元视角摆脱了自然受制于人类的命运,展现了自然的本来状态,伸张了自然的权利,体现了万物多样统一、和谐共生向的生态理念。
二、《巴西,1502年1月1日》:自然的讨伐
在毕肖普的旅行生涯中,邂逅巴西是其生命需要铭刻的节点。1950年代,毕肖普偶然的选择使她来到了巴西,此后她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旅居生活。充满异域风情的巴西为毕肖普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巴西,1502年1月1日》这首诗中,毕肖普将自己的游历与历史上葡萄牙人殖民巴西的过程并置。在这特意制造的共时化时空里,毕肖普以自己精湛的观察力向读者展现了巴西美丽富饶的自然世界:
每一平方英寸中都填满了叶子——
大叶子,小叶子,还有巨型叶子,
蓝色,青色,和橄榄色,
连同随意点亮的叶脉和边缘,
或是翻转过来的缎子叶背;
奇大的蕨类
形成银灰色的对照,
还有花朵,好像巨大的水百合
在空中伸高——在叶子里,伸高——
紫色,黄色,混黄的,粉红,
锈红和绿莹莹的白色;
(丁丽英译,2002:144-145)
各式各样茂盛、美丽的植物向刚刚抵达的访问者(诗人、葡萄牙人)热情地展示了大自然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壮观瑰丽。然而,美丽富饶的大自然没能调动起人类欣赏自然、赞美自然的积极性,相反,富饶的自然资源让人类变得不安分,其剥削自然、占有自然资源的贪婪之心又一次被唤醒。于是,疯狂追赶和企图占有象征巴西自然世界的当地女人将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又一次展露出来:
撕开衣服穿上悬挂的布片,
每人出去为自己抓一个印第安人回来——
那些疯了的小个子女人一直哭喊着
彼此呼叫(或者把鸟叫醒了?)
并且退缩,她们总是退缩在后面。
(丁丽英译,2002:146)
葡萄牙殖民者代表贪婪自大的人类,巴西新大陆代表自然世界,殖民者掠夺巴西资源,奴役当地民众是对人类以大地的主人自居,剥削自然世界、破坏生态环境的映射。二者互为镜像地反映出人类与自然不和谐、相互冲突的关系。但是,这首诗表明殖民者征服自然的野心遭遇了滑铁卢。面对蕴藏无穷力量的大自然,殖民者的武器失去了作用。虽然每个殖民者都想为自己抓捕一个印第安女人回来,然而,“凭借她们的秘密呼叫和无限退缩,她们是难以捕捉的。通过她们与自然的联系,这些‘小个子女人们’变得高大起来,不再弱势:依靠她们的‘呼叫,呼叫’,这些女人就好像‘象征性的大鸟’;在她们通过重复与退缩实现存活的过程中,她们就如同顽强的荒野一般”。(Keller& Miller,1984:541)象征着自然力量的巴西女人最终以顽强的力量战胜了殖民者邪恶的征服欲望,以此毕肖普向世人告诫:人类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如果人类始终维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疯狂剥削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话,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作为生态圈的一部分,如果枉顾生态整体性原则、无视人与自然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一事实的话,人类最终会为自己的自大、贪婪、自私和短视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人类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以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和价值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掠夺自然资源、奴役生态环境,为实现人类眼前、局部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破坏生态环境。为此,人类已经尝到了自然资源衰竭、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灾害爆发、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重重的恶果。所以,现在人类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努力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圈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考虑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毕肖普通过诗歌艺术创作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传达二者应该和谐相处的观念,这显现出生态整体性原则的智慧。
三、《鱼》和《麋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毕肖普的诗歌描绘了丰富多样的动物形象。对于这些大自然的精灵,诗人流露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因此,除了强烈感受到毕肖普对大自然生物的观察与刻画体现出精确、细致的特点之外,读者还能感受到这种描写彰显了动物自身蕴含的原始、纯净的动物性与自然性。毕肖普对这种珍贵的自然性持有一种敬畏、真诚的态度,能够与动物实现某种交流令她十分欢欣。所以,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下科学理性、技术和工具对自然的奴役、占有。在早期诗歌《鱼》中,毕肖普向读者讲述了一条大鱼的故事。某日,诗人捕获一条体型硕大的鱼,但并没有将其收入渔网,进而享用一顿鲜美的鱼宴。相反,观察的本能使她静静地查看眼前的大鱼。诗人专注的目光慢慢抚摸着大鱼的身体,其目光移动如此缓慢,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刹那都静止了,仿佛此时世界上除了诗人与这条大鱼外,再无其他:
他棕色的皮肤
四处挂成条状
像古代的墙纸,
而它深棕色的图案
正是墙纸的图案:
开足的玫瑰的形状
随着岁月而玷污败坏。
他身上洒满藤壶的斑点,
精致的石灰玫瑰饰物,
又染上
细小的白海虱,
他身下垂挂
两三根碎绿草。
当他的腮
吸入可怕的氧气
——那惊人的腮,
新鲜而脆,带着血,
极易削切——
(丁丽英,2002:72-73)
或许对于常人而言,这只是一条普通的鱼,很少有人多看它两眼。但是,诗人对这条鱼充满尊重,所以她才会用“皮肤”来称谓大鱼的鳞片,并且在其丰沛的想象力作用下,她描绘大鱼的鳞片像印有玫瑰图案且腐旧的墙纸。当看到大鱼带血的腮鼓起收缩的样子,毕肖普又与大鱼实现共情,她联想到这也许是大鱼呼吸困难所致。这条大鱼在遇到诗人之前有多次被捕捞的经历,因此它的嘴上挂有五根鱼线。这反映出大鱼勇敢求生的艰辛历程,这应该深深打动了诗人的内心。出于对这位大自然勇士的尊敬,毕肖普犹豫是否能将大鱼的嘴称为鱼的“嘴唇”,这拟人化的手法鲜明体现了诗人对大鱼存有的人文关怀。
对于大鱼,诗人感受着它的迥异性,欣赏着它的他异性,其对鱼鳃的鼓动做出的联想表明诗人积极回应着大鱼的生命活动。在用心欣赏完这个大自然造物的杰作之后,毕肖普选择将鱼放生。这展现出诗人对大鱼及其代表的动物群体和自然世界的尊重和爱护,她希望人类与大自然中的动物能够和谐共生。在毕肖普看来,动物、植物和人类都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其林林总总的生命存在形式体现出生态圈充满生命活力的丰富的生命形态。身处同一个生态圈,人类应该从生态圈的整体利益出发,与动物、植物及各种非人类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存在和谐共生,而不是将它们当作人类可以理所当然征服的战利品来任意宰制和浪费挥霍。毕肖普的诗歌向读者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只有对自然世界秉持尊重,人与自然才有可能共生共荣,这彰显出生态整体性原则和生态进步性原则的内涵。
在毕肖普旅人生活的后期,她依然十分关注动物。《麋鹿》是其后期诗集《地理学之三》中的代表作,该诗基于诗人真实的回乡返城之旅。旅途中,一只雌性麋鹿突然出现在行进中的客车前,挡住了人们的行程,但人们都不禁为这只麋鹿而赞叹。
她捱着时间,
察看着巴士,
显得高贵,脱世超俗。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确实
感到了这种快乐的
甜蜜的冲动?
(丁丽英,2002:247)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只麋鹿呢?关于这一点,诗人没有向读者交代,或许这只是一个偶然。如同毕肖普笔下其他的动物,这头麋鹿是大自然的化身,象征着自然的奇妙、神秘与伟力。毕肖普喜爱它们、欣赏它们、赞美它们,她的作品几乎赋予了这些动物某种神奇的力量,甚至是某种神秘的潜能。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中,麋鹿如同所有自然景物一样都是人类观察和把握的对象。在这些动物面前,人类高高在上,具备绝对的主导权。但在这首诗里,旅客们在注视麋鹿的同时,麋鹿也回馈了人类的注视。这种目光的交流展现了人与自然双向的注视与感受,而非人类对麋鹿所象征的大自然居高临下般的打量与定位,麋鹿也不是那个被动等待观察、剖析的刻板对象。人类无法得知麋鹿此时的所思所想,但却分明感受到她对异于自己的人类世界充满好奇的注视和富有生命力的呼吸。麋鹿的目光、呼吸以及自身的存在洋溢出令人惊喜的生命力的鲜活、纯净与美好,这好似一圈光晕将她萦绕。令人欢欣的是,这光晕也照亮了人们的内心。在这一瞬间,人类和麋鹿所象征的自然世界实现了某种愉悦、神秘的交融。毕肖普记录下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贵瞬间。在这个瞬间,人与自然不再是暗含主客体压迫机制的对立二元,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与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存、多样统一。
四、结语
毕肖普的诗歌紧密关注丰富多样、充满生机的自然世界,其作品对自然世界的注视与呈现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以及传统的以“人—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批判了人类霸占自然、贪婪占有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倡导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共存、友好沟通的价值观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展。毕肖普的诗歌艺术彰显了生态进步性、生态整体性和多样统一的生态批评理论原则与美学意蕴,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