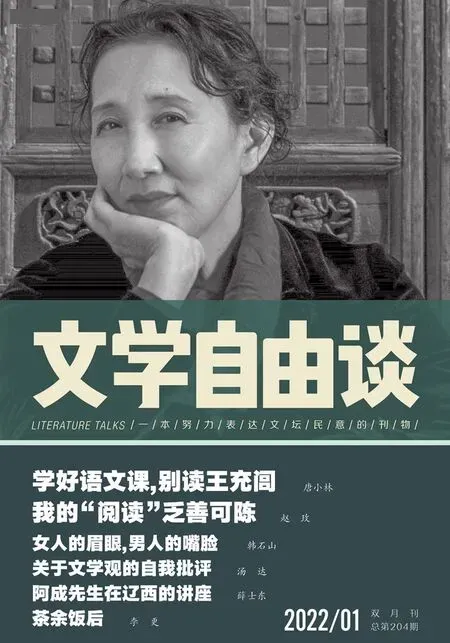疯狂写书的理由
□古远清
“老夫聊发少年狂”,人到八十岁,我觉得自已变“狂”了,居然不满足于出版《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半夜从梦中爬出被窝,赶紧将构思好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的提纲写出来,这正好与排版中的《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构成“三部曲”。
我觉得自己不仅变“狂”了,而且这“狂”已近乎“疯狂”。原计划今年八十岁出八本书,这八本书已成功出版——尤其是在对岸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后,又赶快写续篇“古远清台湾文学新五书”,其中《微型台湾文学史》已付印,《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已排版,《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亦杀青,马上要动手写《台湾百年文学论争史》《余光中论争史》。写史得“十年磨一剑”,可我已没有十年了。我这不是“以创作丰收自乐”,而是利用原已发表和出版的成果整理加工、再新写三分之一而成,这完全是“厚积”的结果。
我为什么到了人生的寒冬,还要乐此不疲地写书,“疯狂”地出书?其理由如下:
一、打发疫情期间的无聊时光。2020年武汉封城数月,无法再外出开会、讲学,便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整理胡秋原、余光中等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两千多封信,后又觉得时间充裕,还可再写一本《世界华文文学概论》,这本书花了半年工夫已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用心血浇灌的花朵,写书已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与两岸出版社相遇、投契、出简体字和繁体字书籍,是如此动人和奇妙,这令我愉悦,更令我难忘。
二、治愈精神创伤。近四年,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家暴”,被剥夺了看电视的权利,一被她发现便将遥控器收缴。退休老人看电视很正常,可她说“碍眼”。这坏事变成好事,我从此戒掉看电视的习惯,全心全意地写作。紧接着书房“沦陷”被占领,连进去取书都得小心翼翼。当她以让我休息为名,将计算机强行拔线后,只好买了一台手提电脑在卫生间旁边的一个小角落里偷偷地写。一想到台湾一位作家在日据时期躲在防空洞里写,我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写作,可以忘却痛苦,忘却烦恼,这是疗伤的最佳方法。我在接受学生采访时,信口说了这么三句话: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何以疗伤,唯有写书。
何以快乐,唯有出书。
三、享受人生快乐。有人认为旅游、打牌、抽烟是享受人生的好办法,可我腿脚没有年轻人灵活,走久了不行。即使我腿脚灵活的时候,我对旅游的兴趣也完全放在到不同城市逛书店上。2019年我趁到台北开会之机,把台湾的大小书店“洗劫”了一番,在新书店、旧书店拎着一包包书回宾馆。有人说快八十岁的人都不再买书而是将书处理掉,可我怎么舍得丢弃这些从海内外购回来的书?尤其是闯过层层关卡到我手上的书。购书、读书、写书,这才是我的挚爱,我的人生享受。
《中华读书报》有个专栏“我的枕边书”。我的枕边书不是别人写的书,而是把自己在对岸出版的繁体竖排书放在枕边陪我入睡,入睡前摸摸封面,嗅嗅墨香,这样可以忘却痛苦,忘却焦虑,忘却恐惧,忘却难堪,忘却艰辛,而忘却的最佳途径是对岸作家琦君说的“三更有梦书当枕”,尤其是用自已的书当枕,由此完成灵魂的救赎。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苦难只能盛载在著书立说的容器里,而写单篇论文这个容器毕竟小了些,必须在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体系,形成专著。
四、治疗健忘症。“文革”前邓拓曾说老年人常犯健忘症,当年体会不到,我到了耄耋之年,才真正感受到此言不虚。我写书之前,常常为找眼镜犯愁,有时眼镜已戴上,可还在四处寻找,可笑!更可笑的是我最近到汕头讲学,坐飞机前见前面有许多人排队,我没有仔细看自已的登机口,竟把邻口41当成我应去的40。当我到41登机口检票时,工作人员说你错了!这错,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错。错上飞机,那就回不来了,好险!我衷心感谢那位检票员认真核对,把我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生活中常犯错的我,写起书来是不可能犯这类错的。我有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友,新出的书竟把吴浊流编的《台湾文艺》错成外省作家夏济安主办的,这和一位香港学者把文学史家司马长风错为武侠小说家一样。像这类差错,我尽可能避免。我对一些作家的年龄和著作的书名,不用查字典均记得一清二楚,而误上飞机这不过是选择性的“失忆”罢了,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是不允许出现的。
读书、写书,可防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我从不抽烟、喝酒、打牌。开会、讲学、购书、写书、出书、搬书、寄书才是我最好的人生享受。这不是以学术的名义,在疯狂地消费读者和忽悠出版社,而是用按回车键的方式找回我的青春,找回我的快乐,找回我的欣喜,找回我的满足,找回我的人生。
五、答谢陕西师范大学给我的学术第二春。2019年我七十八岁时,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薪聘我做驻院研究员,使我受宠若惊。在签合同时,该院竟不实行考核制度,不“强迫”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要求我每年在重点刊物上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此宽松的学术环境,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不考核使我更感到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高等研究院”对我的期望。这也是我疯狂写书的一个理由。
老年散漫,老年懒惰,老年放弃,老年保命,老年只吃喝玩乐,这不是我的人生。一辈子快过完了,自己要看的书还未看完,要写的书还未写完,我隐隐感到有一盏著书立说的灯在照亮我奔向远方。贤茂老兄点赞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去年九月底医院给你下的‘病危通知’,应该属于愚人节的寓言。”
我绝不能让我的精力全耗在医疗保健上,我要保持旺盛的学术生产力,我要保持每天看书写作六小时的速度,我要保持对读书的热爱,对学术的忠诚。我要尽可能发挥余热,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对学术有建树的人。
以上均是我个人拼命写书的理由,说点严肃的理由吧,那就是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台湾文学两岸学者研究了这么多年,可就没有《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我便不自量力做这种填补空白的工作。此外,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已经行走了半个世纪,也该有人出来总结写“学科史”了。
北京一家权威杂志的主编收到我寄赠的一箱“台湾文学五书”后,他连忙问我是否疯了,这把年纪还写这么多书,叫我赶紧打住,要我收起“台湾文学新五书”的计划,可我怎么收得住,要是收住了,我的灵魂如何找到依托?现今把这本《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交稿后,我正发愁是先写“新五书”之四的《台湾百年文学论争史》,还是先写学术界十分期望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呢?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