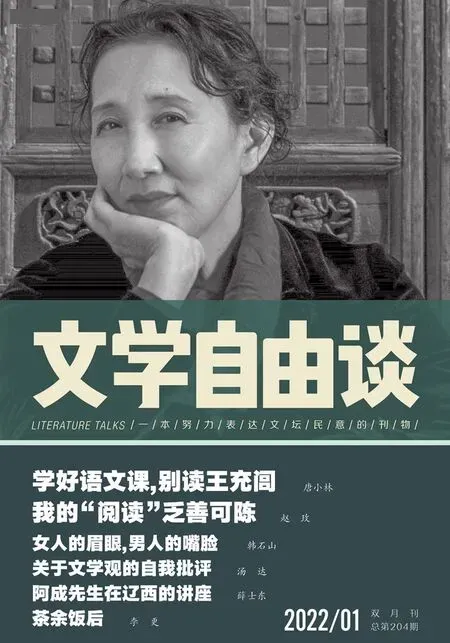我的处女作
□黄惟群
小说《黄土》和《雨天》,写于1983年,完成于一星期中。其中《黄土》算是我的处女作。
说起《黄土》,有点意思。那天上班,我带去一本《海明威短篇小说集》,看完其中一篇《白象似的群山》,一时觉得,浓浓的闷闷的情绪,把我整个人都包裹住了。然而,思绪并没停留在这篇小说的情景中,而是由这一浓烈沉闷情绪在自身经历中扩散,在扩散中寻遇落点——脑中出现的,尽是插队生活,尽是那些一辈子难忘的日日夜夜压迫人的环境、画面。最终,情绪落到了最具强烈反差感的“起点”,即插队到达凤阳的第一天。
那天的生命,经历的是一次“淬火”。恐慌、绝望、无助,沉闷致死都说不出话、发不出声的那种。熟悉的环境,亲人的关爱,看惯的城市、楼房,全没了,陌生的天地,陌生的人,扑面而来的一望无际的黄土,带着所有荒凉、原始、贫瘠,沉甸甸地压在胸口……在这样的情绪缭绕中,泉思如涌,还在上班,休息时间用铅笔和报告纸,趴在桌上,我写起了题为《黄土》的处女作,写那一片第一眼看见后再没离开过我的黄土。写的是感觉、情绪,由感觉造成的情绪,写的是一夜火车的裂变后,走着去生产队的二十一里地,写的是被所见所感震撼后的反应。小说不长,三四千字。停都没停,一气呵成。
写《黄土》时,返沪已四五年。四五年中,插队生活,一刻都没离开过。哪怕身处幸福无比的恋爱日子,白天的欢笑,照样挡不住夜里的噩梦。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几乎所有插过队的人的感受。
情绪被激发了。不几天后,我又写了《雨天》,写的也是插队生活。一篇纯粹的情绪氛围性的小说,只是,我将这种情绪氛围化作了“神用象通”的人物、景色。
小说写一个雨天,傍晚时分,茅草泥屋里,主人公和每天一样拉起了二胡。以往,他拉二胡,前面社房喂牛的孤老头老仁爷都会来,蹲在角落里,不出声,提支烟杆吧嗒吧嗒地抽。开始,老仁爷来,他不喜欢,但渐渐习惯了。这天,老仁爷却没来,他有些心神不宁,曲不成调,一次次放下二胡,走到屋前往外张望。可是,不见老仁爷,只见老仁爷喂的几头牛,一动不动,淋在雨里。这时,随着踩着稀泥的脚步响,来了个女知青,没进屋,身靠门框,面对灰天灰地灰雨,没头没脑说了些小时候对雨的记忆,说得他心乱。他再次走到门前往外张望时,女知青告诉说:老仁爷不会来了,死了。老仁爷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难受,想着想着,伤感郁闷的情绪中,不自觉地,他再次拉起了二胡。这次,琴声成调了,浸透情感,飘了出去,和屋外飘飘忽忽的雨丝、淅淅沥沥的雨声融成了一片。
这篇小说,或者说,这样的雨天,可谓是我整个插队生涯浓缩情绪的写照。小说既抽象又具体,既空灵又落地,写出了知青生活特有的厚厚沉沉的压抑心情,并将这一心情与二胡的声音、雨的声音以及湿漉漉的天气,揉合在了一起。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已说尽,所谓“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心雕龙·神思》),似乎散淡,但却实际,重得难以化解。我觉得是一篇有特色、有韵味的小说。知青小说有很多,但如此不重故事,纯写知青生活所共有的压抑、沉闷心绪的小说,至少在1983年,绝无仅有。那时我其实并不真懂写作,只是质朴地直觉地捕捉自己丰富细腻的感觉,并对自己的感觉,进行了容不得半点不适的反复体味、精准辨认,没半句虚言,没半句游离真实感觉的渲染与描绘。一部进入了精神领域的具有文学浓度的小说。
小说中很多雨的描写,至今还喜欢:
天上没有云,一丝都没有。蒙蒙细雨像层沙,飘飘忽忽。柳树光秃秃,孤零零二三棵,插河沿,枝上挂满雨珠。风,阵阵袭来,吹得雨丝贴着河面打旋,皱了水中阴沉的天……远处的山,被雨蒙住,近处的村庄都已湿透……
雨,还在下,但已看不清雨丝。屋檐上,雨珠沿着稻草杆滑下,掉在门前水槽里,滴滴答答,声响不住。门前原先没水槽,是雨点滴出来的。
雨小些了,风却刮得更紧,一阵阵,一阵阵。天渐渐暗下,屋外已看不清闪亮的水坑,看不清灰白的天,屋里一切都已消失在黑暗中。
《黄土》和《雨天》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它们是呼吸,是脉动,是心里流出来的,是生活的重压下挤出的一道浓液。
《黄土》一文,我寄给了《人民文学》。当然,不会有回音,哪怕我自觉再好也不会有回音。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作者处女作,想要转到最红杂志的主编手里,可能性为零。《雨天》,一朋友帮我转给当时正在为《春风》杂志编一期稿的编辑那里。朋友说,编辑看了非常喜欢,把它排在所组那期稿的头篇。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很激动。然而,稿件送到杂志社后,整整一期稿子中,唯一被删的,就是这篇《雨天》。后来,我又将之寄给《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看过后,找我去谈了次话。那时,能被杂志社找去谈话,已是很大的事,尽管小说最终还是没被刊出。
这样的小说,那时不可能被接受。没故事,没情节,不注明时间、地点,只有情绪和氛围,以及情绪氛围中暗隐的心情。那时的文坛,时兴的是改革题材小说。在编辑的劝说下,我也努力过,尝试过。但是,一败涂地。我的文学不在改革中;改革小说须有的要点,与我心中的文学元素不接轨,擦不出火花。
两篇作品,不断投稿,不断被退稿,从最好的杂志到一般的杂志,投了三年,小说才刊出;且是因为进了上海作协第一届“青年作家创作班”,认识了一些人之后,在他们的帮助推荐下才成功的。《雨天》发在《建设者之歌》,即之前的《工人创作》;《黄土》发在《奔流》杂志。
《黄土》发表后,《奔流》的编辑给我来信,称对小说的感觉非常之好,他很喜欢。那时“感觉”一词,刚在文坛出现,刚被注重。
《雨天》刊出早半年,但刊出的小说,看得我懊恼,其中莫名其妙被加一句“沉闷。乏味。忧郁。插队的生活哟。”原因是,编辑认为这篇小说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必须加这一句解决问题。可这一句加得太像从《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抄来的,什么都加个“哟”。因这一句,小说发表后,我甚至不想示人。这话能加吗?小说写的是哪年哪月,透没透出痛苦,是不是插队生活,主人公叫什么名,重要吗?一篇本不明说的小说,非要它明说,那是画蛇添足,是层次、格调的错乱,对小说造成的是根本性伤害。这篇小说,写出的是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心绪,是一种到达一定程度的抽象心绪。
很长一段时间,很迷茫。我为自己设立的文学标准中,最为看重的一项,是文学的艺术性。我一向认为,文学的最高层次是艺术,高级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以艺术取胜。一切看重故事性、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的小说,如果真好,那一定是艺术性好。只有艺术性好了,才能让故事性、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展现风采,感动人,打动人。所谓艺术,就是精确的、巧妙的、智慧的、制造出触动心灵的表现力、感染力。
我的文学起步,是在艺术之路上朝着理想目标努力的。然而,此路不通,我很失败,尽管内心深处从没承认过那些所谓的成功者,也没承认过自己的“失败”。
不甘失败,想学习,想向成功作家学习。我开始大量阅读当代小说,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然而,越读越迷茫。
一位发表过不少作品的作家,又在一本不错的杂志上发了个中篇。非常羡慕,也为他高兴。我向他借来那部中篇,几乎是以崇敬、虔诚的态度阅读,努力从中发现可被借鉴的写作优点。但是最终,读完小说后,我无奈地发现,我实在找不到这部小说的优点,不论语言、文字、细节、故事、内涵,都太一般,实在是太一般,太平庸了。
尽管如此,那个时期,我努力想做的和别人一样。写作时总想,别人会这么想、这么写吗?似乎别人也这样想这些写,自己所写才踏实、安全、可取。
多年以后,我一直告诫年轻作者:凡别人想过、写过的,就别再想再写,想了写了,也不值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只有真正在你心中属于你自己的,别人没想过没写过的,而你自己想了写了都会吓一跳的,才是真正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才能真正支撑你写出优秀作品!
至于1983 年完成、投稿三年难以发表的《黄土》和《雨天》,2019年,连同另一早期短篇《一个燥热潮湿的下午》,组成一组,我再次投稿《作家》杂志,一个月后,小说就刊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