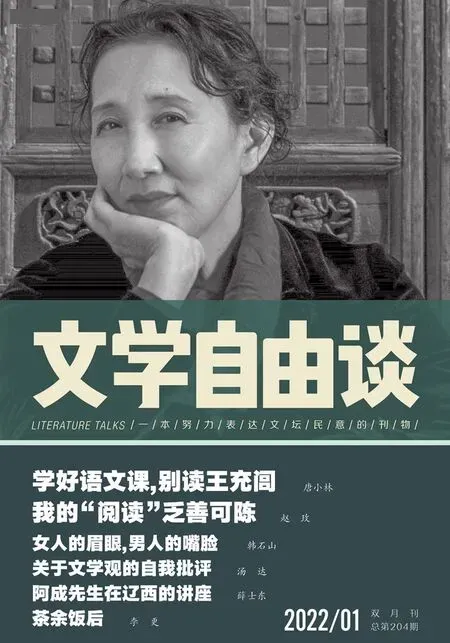点读几位作家
□林伟光
聂鑫森的小说境界
都说小说家厉害,也很让人钦羡。因为他能够用艺术的手段,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生动的文学世界。
聂鑫森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盛名已久;而难得的是,他的创作力还一直持久健旺。不久前,他的短篇小说集《贤人图》问世,所收的作品固然有新作旧篇,可是绝对不是炒冷饭。其中近几年的新作,颇引人瞩目。不但令人欣赏到他宝刀不老的功力,更让人看到他在短篇小说方面崭新的意境。
对于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而言,要超越自己谈何容易?如果没有一种奋进的精神,那就只能停笔了。年届七旬的聂鑫森,一直维持着创作力,当然缘于他在创作中的不知足。这种不满足,催动着他艺术上的不断探索。他说,我的小说立足于所在城市的文化背景,这种地域性的特征,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足是容易狭窄,陷入一种小格局的情调,并对某些小情趣的东西津津乐道。
短篇小说,即使篇幅小,也要能够容纳无限的空间,即所谓的“纳须弥于芥子”者。在创作时,聂鑫森总是力求“表现出深厚的中国小说传统的艺术功力,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芬芳……从中开掘出小说人物身上卓尔不群的文化特质和磊落胸怀。”
在他的笔下,学者、书画家、名医、企业家、贩夫走卒,都是常见的人物,这就是他的小说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地方。可是,这些人物却都是在某个具体的环境里,在独特的文化气氛影响下的生活者。这就出现了不同的异样,即小说中的“这一个”,让人在共性中看到了他们独特的个性。
他曾说,“我喜欢汪曾祺先生的说法: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小说而不像小说?这看来很像一种悖理,却并非如此。绘画里有曰:太似媚世,不似欺世,妙在似与非似间耳。精于国画创作的聂鑫森,可谓深明其中之旨;或者可以说,他正是把这种绘画的理念运用到了小说的创作。故事当然要有,可是他的故事,不是游离于人物与环境,而是通过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来展开。尤其强调人物的文化品格,着力挖掘他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多侧面地去展示他们的逼人才气、磊落胸怀、高贵操守和审美趋向。
这种守望式的关注与叙写,正是聂鑫森笔下的风华,是他有别于他人的艺术风格。
在《从〈贤人图〉说开去》中,这位有着五十多年艺术生涯的老作家,探讨性地提出了有关短篇小说创作的各种可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活跃,不拘泥一切的清规戒律,求变求新。当然,有时候规则是应该有的,否则岂不乱套了。可是规则不是死的,是可以有着种种的变化。世界变动不居,变是常态,不变则是暂时的。所以,不断尝试的变化,是聂鑫森小说吸引人的动人魅力所在。
他说,对于短篇小说的文字,要力图做到既讲究它的张力,同时又注重对它的“控制”,尽力使其古典、隽雅、简洁,不艰涩,不匆促,亦潇洒亦从容,具备诗意的韵趣。——这可以视为他近年来对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追求。
有人说小说是世俗的,是的,它必须描写世俗的生活;可是,精神却必须富含诗意。因为,没有诗意的小说,是缺乏境界的。
王祥夫的关心民瘼
有人说,“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麻木不仁”。王祥夫,在当下文坛究竟处于一种什么位置?有人称赞他是中国的“契科夫”。不管其中是否有玩笑的成分,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就是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出色。近期,他就推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劳动妇女王桂花》,受到读者的欢迎。
当下读小说的人渐渐少了,可是,王祥夫不但致力于孜孜以求,而且写作的出奇致胜,总能让我们获得阅读的快感和满足。
好的短篇小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其一是材料难找。有时候,适合长中篇小说的材料不一定适合于短篇小说;其二是短篇小说要留得住读者,作者必须煞费苦心。借王祥夫的话是:“一颗小小的琥珀珠子,你把它迎着亮光看,会看到那么意想不到的东西,人生活在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世界里,即如一颗珠子,在不期而遇的瞬间,我相信,许多许多的喜怒哀乐和其它更多的不可知的东西已经进入其间,并且凝固其间。”
《劳动妇女王桂花》中是一些怎样的小说?其中有大愤怒,通过一个个“难以启齿”的荒诞故事讽喻现实,表现一种历史反思的立场。现实总是残酷的,因此小说要如何表现,才深刻动人?是如刀锋似的锋利,还是让汹涌的暗涛潜藏于不动声色之间?
王祥夫,当然有自己的创作选择。他似乎把眼光更多地倾注于底层的叙事,内心总是充满温情,这使他在对底层人物的表现上,多了一份平和、宁静和狡黠,其间有快乐,却也不乏智慧的灵光。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真善美,透射着生命的真挚情感。这是以一种对生命的关怀,与饱含温情的关注来创作的。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或许正是小说家应有的态度。记得王祥夫说过,小说是世俗的。这种世俗性,正是他文学的美学追求。因此,他很注重对日常生活本身价值的叙写,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理解——即“新鲜感”,以抵达人性伦理的最深处,写出日常生活里真实的苦乐与悲欢。当然,他的小说也有深刻的批判意义,有对社会的评判,对人性的挖掘,其中内在的生命和外在世界的表里描写,使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社会价值。
与更多的小说家刻意追寻西方艺术的先锋性不同,王祥夫从中国古典小说、话本小说、笔记小说中去寻找自己创作的立足点。这种民族性的追求,给他的小说加上了一层“中国风”的特色。可是他的小说并不土,并没有把民族性同世界性对立起来,在对现代散文意韵的借鉴和现实小说人性挖掘的融合中,他为小说创作注入了现代意义的蓬勃生机。
对于创作,王祥夫有一种清醒的警觉。他说,一个作家要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对生活对创作,当然也包括对语言的运用。小说一如新鲜的肉体,每一回都是新鲜的;而优秀的作家有时候就像是某种锋利的刀具。我们知道想让一把刀保持锋利的话就要不停地去打磨,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才能让你得到鲜活的滋养,其实任何作家都无法与社会背景分离。
要讲好自己的故事,我想,就是能够从司空见惯的日常里去发现,而这种发现必然是带着当下的特征,有着当下的温度与情绪,是可以直击我们心灵的。作为生活主体的底层人们,他们并不悲观,那么活色生香的生活,充满浓郁的健旺气息。他们的痛苦和欢乐,都是扎实而有力的。于是,在王祥夫娓娓的笔触下,人物和生活,故事与精神,就都具有了一种质感的力量。
我尤其要致敬于王祥夫的,就是他的这种关心民瘼的精神!
熊育群笔下的精彩
熊育群,这些年几乎都在创作长篇小说,先是《连尔居》,又是《己卯年雨雪》,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他原是写诗和散文的,第一本作品是诗集《三只眼睛》,最新一部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散文写作则必须提到他带着个人独特体验烙印的行走散文了,如曾深入藏地,走过无人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写出的《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等。而今却倾力于小说,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作家而言,写什么和如何写,都是纠缠在创作过程中的问题,总要在不断的解决问题中推进。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我相信在熊育群的心里,是没有断然区分的;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他觉得所掌握的材料,或者说所要表达的东西,散文已经不能包容了,就开始写小说。所谓散文与小说,或者还有别的文体,不过是体裁上的不同。没有什么高下之别,都要立足于生活,是对真相的探究。
当然,表现的方式还是不同的。散文可以直抒胸臆,而小说更重曲笔,特别强调虚构。可是,虚构不是乌托邦,而是生活中的再创造。只有生活中必有,小说才有现实的意义,其艺术的力量才能无限地彰显。熊育群的小说,于此有特别感动人的表现。
就以《己卯年雨雪》来说,其感人的力量,恰恰不在于虚构,而在于真实。其人物的感情,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乃至场景、环境等等,都那么的逼真,宛如对当年的再现。熊育群说,这是他的一种积极尝试,是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小说充满了真实的气息,故“它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己卯年雨雪》来于真实的历史,那场让人震惊、难忘,同时充满着血腥味的战争,就发生在他的家乡。他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他觉得面对这么残酷的历史事实,任何的虚构都是没有力量的,任何的虚构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写小说,强调真实与虚构并不矛盾。把真实跟虚构截然对立,乃是一种误解,或者很肤浅的理解。因此,熊育群强调说,小说的力量就是真相的力量,还有真相激发的思想与艺术创造的力量。是啊,真实就是文学的力量,没有真实,就没有文学。
当然,小说的主角是人,而不是别的。当下,有所谓没有人物的小说,其实都是不能成立的,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小说的成功与否,就看它的人物是否刻划得饱满、真实,这虽是老生常谈,却是至理之言。
《己卯年雨雪》为何让我们感动?就是人物真实感人。与以往同类题材不同,它的描写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从敌我双方入手,超越了传统的视角,给人们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同时,所写的这些战争环境里的人们,都有某些非正常的因素。可能是疯狂的,残忍的;可能是怯弱的,恐惧的;也可能是被仇恨所激发的英勇者。正是这种非正常的特异性,使他们的感情和行动,体现了一种非正常的人性。如何写好他们?很不容易。常见一边倒的带着某些神奇色彩的描写,我们司空见惯。但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或者,只是有限制的真实而已。所以,我们渴望对历史的反映有突破性的描写,《己卯年雨雪》于此让我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战争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不但被强行改变,性格也被强行改变,可能由人变成了兽,由温和变成杀人魔鬼。这种由人而鬼的过程,触目惊心,而这种描写,也更具深刻、撼人的意义。这是对战争更深刻的反思。
战争让万万千千的人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更多无辜的人而言,这是极不公平的残酷面对。因此,要从更高的层面,反思和否定战争,或者正是我们写战争的目的。而《己卯年雨雪》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高洪波的文学情怀
高洪波是位诗人。我常常想,诗人最主要的情怀是什么?应该是一种童心。这位诗心与童心兼具的诗人,即使不一定写诗、散文、儿童文学作品,甚或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但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精神内蕴的诗意荡漾。
说到底,高洪波本质上是很纯真的人。不管外边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如一,坚持以一种童真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相信美,儿童就是美的化身,美的生动表现。因为儿童代表着未来,所以,他对明天也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作品中自然也充溢着信心和欢乐。这是一种诗的情怀,也是他整个文学世界里的一种温暖的色调。
你接触高洪波时,就会觉得他永远是快乐的。是的,这份满满快乐的情绪,会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让我们感动。
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很受小读者们喜欢的。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教训的口吻来说教,而是以亲切、恳挚的态度,跟小读者平等的态度,进入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认识美,欣赏美,获得飞扬的快乐。不错,真善美永远是文学歌颂的对象,而让更多幼小心灵健康茁壮成长,则是儿童文学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只有跟孩子们成为朋友,让专注的爱心去呵护他们,才是一种温馨幸福的润物细无声的美丽。
我注意到高洪波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写下的这些文字:耳畔响起的是蝈蝈的鸣叫,我与金波先生同好,都爱饲养这种山野的翠绿色的歌者。……他写蟋蟀、蝈蝈,写知了、豆娘,写草蛉、金铃子,甚至还写米虫、蝲蝲蛄、书虫,直到跟斗虫、蚁狮和屎壳郎,他在描写这些细小卑微的生命时,我能看到他专注而童稚的目光,欣喜又尊敬的姿态,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诗人用美妙的文字传递出对大自然的热爱,用快乐的诗心吟唱给小读者的生命之歌。——写的虽然是金波,但我觉得却也包含了他自己,这也是高洪波内心情怀的表现。这种快乐的诗心吟唱出的生命之歌,是每一位童心犹存的作家的最高境界,也是他们儿童文学创作中美学思想的体现。
当然,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追求和写作的自由。然而,纯真、自然、简单的境界,却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意境。让我们的心灵永远保持纯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保持纯真心地的高洪波,就彰显出了他文学的难能可贵的品质;而这或许也是他文学之外的人格魅力。
以一种纯洁的目光观照社会和自然,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情趣,当然也充满着无限的幸福,他的作品,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愉悦。这就是我们阅读高洪波那些情趣盎然的儿童文学作品后的收获。
高洪波是对生活充满着爱的写作者。不能说,这一生,他走过来时,就没有丁点的挫折;可是,他不把这些挫折夸大,而是乐观地面对,更以一种坦然的健康的心态迎对,让诗意化解忧烦,把欢乐留在作品中。与其说这是他独特的生活观,不如说是他有意追求的一种美学的理想。人生苦短,不如意者常八九;但是,这何尝不是一份难得的人生经验?在痛苦的不如意中活出灿烂的丰采,是一种睿智的人生。这当然也是他的豁达和智慧。
可喜的是,他把这种人生智慧带进了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审美思想。他的散文,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却不给人一份道德上的压力。文学评论家雷达就说过,他似乎不愿承担思辨的重负,所以,他的散文读起来轻松,幽默,富于情趣。
如此而言,他的散文,有的人就要嫌其不够深刻了。如果说不沉重,就是不深刻,似乎可以这么评价,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沉重与轻松,不过是风格的不同呈现,与是否深刻,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看似信手拈来的种种,包括不少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他笔下往往能够焕发出新鲜的色彩。他把思想融汇于妙趣横生的文字之中。于是,生活里的种种,经过他的吸纳、感悟、升华,就有了一种醇酽之美,醉人之美。
这自然是他童真的意趣所营造出来的文学之美。或者,其中有本真,有纯粹,有情趣和理趣,更有诗情的盎然与生动。